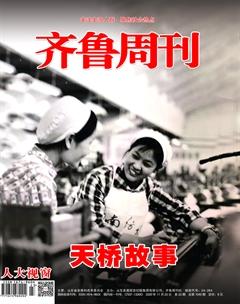電影《氣球》:落入日常的一個隱秘角落
宗禾
“萬瑪才旦電影的迷人之處,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淺看。淺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脫。”
現實與信仰
為了自由,人可以做出哪些事?
安迪可以數十年如一日,用藏在《圣經》里的鶴嘴錐一點點鑿開海報后的墻壁;麥克·墨菲可以冒著被摘除腦葉前的風險帶領全院病人一起出海狂歡;威廉·華萊士可以在屠刀已抵在脖子上的時候,仍然面不改色地怒吼出“Freedom”。
這些經典影片要表達的是同一個主旨,那種為了自由而傾其所有的勇氣也常使人熱淚盈眶。但很多時候,現實遠比電影殘酷。
這種殘酷,并非來自驚心動魄的某個瞬間,而是每個人都要生活在自己的困境中并為之掙扎,窮極一生,無法越獄。
“現實”的復雜在于“現實”本身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且,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往往包含著各種矛盾。
對于很多人來說,西藏是他們幻想中的“精神桃花源”,那里信仰純粹,民風質樸。
電影《氣球》主海報上寫的卻是這樣一句話:信仰和現實如何抉擇?
故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已有三個孩子的卓嘎意外懷孕,想要打掉孩子;丈夫達杰卻堅信孩子是去世父親靈魂輪回的轉世。“當輪回轉世的信仰和現實造成了難以抉擇、調和的矛盾,人們該何去何從?”
導演萬瑪才旦曾被認為開啟了“藏地電影新浪潮”,《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作品橫掃國內外各大電影節,被稱為“行走在藏地的文化符碼”。
藏語、高原、游牧、活佛,他的作品有鮮明的地域符號,同時試圖回應藏區在現代轉型中的迷惘與危機。
《氣球》里輪回轉世的信念,曾是藏人精神世界的根基。萬瑪才旦的爺爺就相信熱愛寫作的孫子是自己舅舅——一個有大量經書的僧人的轉世,對他特別偏愛,給他買來一箱子連環畫,還有一個收音機,40塊錢,在當時是筆巨款。
“突然有一天,一個官員或一個派出所長被活佛尋訪小組的人找上門,要求跟他們走。有人會放下一切,決然地走了;有人不愿改變現有的生活,選擇留在世俗人間。”
萬瑪才旦的創作,信仰與現實的抉擇,這一電影主旨,其最終的落腳點重點體現在女性生育權這一全球性話題上,而出家的妹妹卓瑪與情人,在信仰與情感欲望間求而不得的困境,也是卓嘎命運的對比參照。
卓嘎對自己生育權中“不生育權”的主張,是萬瑪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中比較少見的,是相當女性主義的議題。盡管這種主張更多地被統合在現實原因的考量下,但仍能看到卓嘎本人的某種覺醒。
然而,卓嘎對待妹妹及其情人的方式,又是另一種壓抑性的力量。她把那本小說丟進火中,并用謊言阻止了他們的見面,不論是為了消除誤會還是為了再續前緣都因此不再可能。這讓她在某種意義上又扮演了一個內化了男權邏輯的壓迫者角色。
這樣的人物寫得相當之高級。
2019年10月,由《氣球》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此后,導演萬瑪才旦帶著團隊,輾轉于多倫多、釜山、東京、上海、平遙、海南島,在各大權威電影節上獲得多項提名與獎項。影評人木衛二說:“這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萬瑪才旦作品。”
而王家衛導演曾說過:“萬瑪才旦電影的迷人之處,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淺看。淺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脫。”
搭建一個“馬孔多”
西北偏北的土地總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挖掘。那里肅殺、蒼茫,文明與尚未開發的荒蕪交糅,使得這里的藝術總是有種天然的使命感。那里的導演也一樣,萬瑪才旦也是如此。
2005年,萬瑪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一個藏族導演將藏區真實的當下生活鋪展于銀幕之上,在新中國電影史上是第一次。這一年,《靜靜的嘛呢石》擊敗顧長衛的《孔雀》,獲得金雞獎最佳處女作獎。
萬瑪才旦曾說:
“經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講述我的故鄉,賦予藏區神秘、蠻荒、與世隔絕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質。這些人常常標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實的,但這種真實使人們更加看不清我故鄉的面貌。我不喜歡這樣的‘真實,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述發生在故鄉的故事,故鄉人真實的生存狀況。”
萬瑪才旦的家鄉在青海貴德,屬于安多藏區,到拉薩2000多公里。沒火車、汽車的時代,人們就走著去、騎馬去、磕長頭去那座“圣城”。
幫家里放羊,是那個年代藏區小孩的必修課,也是萬瑪才旦關于孤獨的最早體驗。山上空無一人,收音機里播放的《夜幕下的哈爾濱》,制造出另一個時空,那是來自“外面世界”的聲音。
他的村莊在黃河上游。那時候,水利部門修水電站,勘探隊來到這里,每逢周末放電影,除了國產片,還放一些外國片,比如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還有《老槍》《佐羅》《狐貍的故事》等等。
遠方到來的人們,也打開另一個世俗的現代空間。
他回憶小時候第一次看到供電所的人來到村子的場景,“在此之前沒有外人涉足村子,那就像外來的東西突然打破了一種承襲的傳統,原有的生活與思維方式都變了。”
對于“傳統”的留戀一直存在于萬瑪才旦的內心,無論是之后辭去老師的工作考去蘭州上大學,讀研究生,還是前往北京進修,他在遠離藏區的將近二十年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環境變化,一次次前往更文明的世界,被現實沖擊。
這反映在萬瑪才旦的作品中即反映他的一種矛盾心理:既渴望逃離嚴酷的現實環境,又對那被現代文化慢慢侵蝕的藏地文化抱著極大的同情,希望保持純凈的人文風貌。
萬瑪才旦喜歡在作品中塑造形色各異的邊緣角色,譬如,明顯與世俗格格不入的人,在古老的復仇幻想中被施舍的人,以及處于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沖突變革期的女人等。
通過展現上述角色在現代文明下所受的沖擊,讓他們在現實與理想中徘徊、煎熬。從這點看,萬瑪才旦更像一位作家,在搭建一個位于中國西部的“馬孔多”。
十幾年前,萬瑪才旦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在中關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紅氣球在風中飄。
“那個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電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爾伯特·拉摩里斯的《紅氣球》、侯孝賢的《紅氣球之旅》,也聯想到一些發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雛形。”萬瑪才旦說。
2017年,他寫下小說《氣球》,發表在《花城》雜志。那一年,西藏是影視圈的“熱詞”,張楊導演的《岡仁波齊》將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銀幕上,憑借對現代都市人靈魂的想象性救贖,斬獲1億票房。
《氣球》顯得更為寫實。空中飄揚的紅氣球,在萬瑪才旦筆下,轉換為藏區孩子玩耍時用避孕套吹起的白氣球。
在這部電影中,萬瑪才旦的個人風格和探索文化矛盾的話題得以延續,并更加直白。爺爺對于電視上試管嬰兒的恐懼,宗教中占有著至高地位的生育信仰被極大的挑戰。從開始的人面對矛盾,到文化面對矛盾,萬瑪才旦的探索越來越深。
經年來,他始終在兩種語言中游走,寫小說,拍電影,聚焦真實的藏區日常。2019年帶著《氣球》走遍各大電影節后,萬瑪才旦回到青海住了大半年,往返于西寧和貴德。家鄉,用他的話說,也“只有山坡頂上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