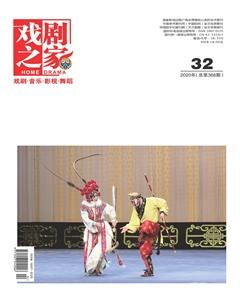生命維度下婚戀觀的美學呈現
謝昱辰
【摘 要】以藝術表現手法來闡釋婚姻與家庭是影視作品展現的熱門主題。觀眾們在觀看時會不自覺加入個人人生體驗和價值觀來進行審美活動,并對影視作品進行評價與選擇。經濟全球化影響下的新觀念與新思維沖擊著傳統價值觀與主流婚戀觀的地位。在開放多元的大環境中,文藝工作者對于價值觀的選擇性呈現和引導尤為重要。本文將討論馮小剛導演電影創作的轉變以及他最新作品《只有蕓知道》在生命維度下的“歸屬”意義。
【關鍵詞】馮小剛;價值觀歸屬;主流婚戀觀
中圖分類號:J905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32-0126-02
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作品開啟了華語電影賀歲檔新紀元,帶動了中國內地電影市場自覺化的創作,推動了電影產業化的發展。近年來,馮小剛導演從商業化創作逐漸向藝術化創作轉變,這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和思考。他的電影創作從傳統主流婚戀觀念與現代開放婚戀觀念的矛盾反思到渴望回歸主流婚戀價值觀的情感變遷也代表著當代中國社會大眾的情感遷徙。本文將分析電影《只有蕓知道》的“歸屬”意義,以此來探討馮小剛導演在生命維度下婚戀觀的美學呈現。
一、馮小剛導演的創作梳理和轉變
馮小剛導演的創作大致分為三大類:黑色幽默商業片、宏大敘事歷史片、純愛藝術實驗片。首先對于商業片,1997年馮小剛導演以電影《甲方乙方》開創賀歲喜劇先河,黑色幽默商業喜劇成為馮導標簽。馮小剛導演通過平民化審美視角反映尖銳社會問題,以嬉笑怒罵的喜劇方式來諷刺人生現實的荒誕,反映中國人的“真”與“誠”,表現在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的社會環境下的人性弱點與面具下的利己主義。[1]例如2001年《大腕》中精神病患者“不求最好,但求最貴”的引人深思的扭曲價值觀;2003年《手機》揭露技術發達與人體自由的沖突矛盾;[2]2010年《非誠勿擾2》展現現代人的愛情理想在現實性婚姻目的面前的慘敗;2013年《私人訂制》將升級版“好夢一日游”與《甲方乙方》對比,反映不同時代下中國人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現代都市個體的精神困境。其次對于歷史片,馮小剛導演將家國敘事貫穿在小人物身上,以平凡家庭的宿命變遷深挖整個時代的巨大變動。如2007年《集結號》以家國利益與個體生命的對立統一來體現英雄復位和人性光輝;2011年《一九四二》用超越血緣的家庭觀體現以天下為家、以群眾為親的中國式道德的大愛;2017年《芳華》展現動蕩的時代和復雜多樣的人性,歌頌亂世之下的美好品德,引發觀眾共鳴以及對青春、歷史的反思。[3]這些作品體現出平凡個體是渺小的,因為他們淹沒在廣大群體和時代洪流中;同時平凡個體也是偉大的,因為他們是時代精神的文化表征。第三對于純愛片,馮導最新作品《只有蕓知道》一改他往日黑色幽默片的戲謔調侃化和歷史題材電影的沉重寫實性,用舒緩音樂和新西蘭如畫風景帶給觀眾浸入式觀影體驗。《只有蕓知道》打破了他前期電影中城市空間與精英身份認同的對應設定,帶領觀眾領略異國田園式優美風光,窺視漂泊的風云人生。[4]馮導想通過新作品《只有蕓知道》來傳達他心中神圣莊嚴的婚姻在生活中原本的模樣以及對主流婚戀價值觀的認同。電影從生命的維度來對待婚戀觀與家庭觀,是馮小剛又一次自覺化的創作,體現著他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人文情懷的思考。下面我將結合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分析影片《只有蕓知道》中三個典型的“歸屬”意義。
二、國的歸屬
列斐伏爾認為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品,它是產品和物品總集所占有的一般性場所,是具有功能性的。[5]資本主義迅速膨脹加速了對自然界和工人階級的剝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男女主人公對于二十世紀末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自豪感和國外漂泊的離散感交織,產生歸屬焦慮。當苦守多年的自家小店在火中化為灰燼時,美好理想也在殘酷現實中消散了,身體空間從漂泊轉向安穩,渴望歸國的歸屬感更加強烈。下面分析影片中國的“歸屬”意義。
“國”代表土地。從電影男主人公的名字來看,隋東風諧音隨東風。他和妻子羅蕓的“風云際會”仿佛在訴說海外游子離開故鄉就像離開腳下堅實的土地,如同飄浮在天空的風云一樣無依無靠。兩個北京人在新西蘭小鎮克萊德開了一家中餐館,異國生活的疲憊辛酸在時間的不斷擠壓下膨脹飽和直至爆炸,歸國心切卻為時已晚。當隋東風捧著羅蕓一部分骨灰回到遠在北京的羅蕓父母家時,漂泊在外無處落腳的云才真正回歸故里、落葉歸根,躺在曾經成長過且堅實溫暖的家里,永遠安息。
“國”代表鄉愁。當初撮合兩個人在一起的林太雖然出場時間不長,但馮小剛導演也將林太的中國傳統女人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林太晚年客居異鄉,思念去世的丈夫,思念生長、奮斗過的故土。在隋東風與羅蕓結婚當晚,林太提到“按照我們的習俗,應當叫你一聲隋太”。“隋太”的稱呼正是印證了“嫁乞隨乞,嫁叟隨叟”“男主外女主內”的中國傳統婚戀觀。馮小剛導演通過這樣的人物設定、情節設定表達出身為炎黃子孫,無論漂泊到哪里,祖國都是心中最高的榮譽感與歸屬感所在,有國才有家。
三、家的歸屬
社會空間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娛樂場所和新的居住區雖然不再是勞動的束縛,但卻是生產“恢復”的場所。[6]房子和家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是十分重要的,這一點我們在1997年《甲方乙方》最后一個關于“家”的圓夢故事中也可以看到。電影《只有蕓知道》中,男女主人公對克萊德老房子的留戀證明他們對于家庭和房子的歸屬感。下面具體分析影片中家的“歸屬”意義。
“家”代表安定。林太有一句臺詞:“有了房子,有了生意,就是你給她最大的安全感。”隋東風和羅蕓在克萊德盤下了老房子和餐館生意,兩個人在一個屬于彼此的家里經營,雖然漂泊卻生活安心。兩個電影主人公安定平凡的生活方式和餐館幫手梅琳達自由隨心的生活方式形成鮮明對比。西方女孩梅琳達豐富的社會實踐和生活閱歷是中國姑娘羅蕓所不具備的。因為中國傳統家的含義就是團聚與相守。家是彼此間相互陪伴,是情感融合交融的靈魂棲息地,也是身心得到充分休息的舒適空間。羅蕓雖然羨慕自由的生活方式,但她無法拋下和隋東風共同經營的溫馨小家。
“家”代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究人丁興旺、兒孫滿堂以及含飴弄孫的天年之樂。《孟子·離婁上》中也提到:“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羅蕓因身體問題很難生育,殘酷現實導致兩個主人公的小家面臨無法傳承的難題。埋葬寵物狗布魯的時候,羅蕓有一句臺詞“看見上面的房子了嗎?那是咱們家,要記得回家的路。”這是有歸屬感的家庭觀念在潛意識中的表達。羅蕓去世后,隋東風帶著她回到北京的家里。羅蕓的父親老淚縱橫“回來就好”,羅蕓的父母還沒盼到頤養天年就已經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們只能通過“孩子回家”來撫慰這份傷痛。這就是中國人關于“家”的歸屬感。
四、心靈歸屬
每一種社會形態都生產自己的社會空間,社會空間里面有物質性生產關系和生物性生產關系,夫妻關系就屬于生物性生產關系。[7]心靈歸屬對于電影男女主人公來說是相對于現實的純理想化空間。他們在彼此忠誠熾熱的愛情中找到了原本在紛擾喧囂的現實中消失的歸屬感。下面具體分析影片中心靈的“歸屬”意義。
男主人公的心靈歸屬。在隋東風心里,妻子羅蕓并沒有真正離開他,他帶上妻子的骨灰踏上為心中的羅蕓尋找最終歸屬地的回家旅程。羅蕓的紅裙子在電影中作為重要意象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回憶羅蕓歸來,代表隋東風對羅蕓的想念;第二次是隋東風初到林太家看到羅蕓掛起來的紅裙子,代表隋東風對羅蕓的第一印象:明艷美麗;第三次是隋東風第一次見到羅蕓時,代表兩人的故事即將展開。紅裙子不僅代表羅蕓,也代表隋東風對妻子濃烈真摯的愛情。隋東風的歸屬來源于心中的羅蕓,而心中的羅蕓最終的歸屬還是在隋東風的心里,所以在影片最后羅蕓留給隋東風的信中提到:“我沒活夠的年數,你替我好好活”。隋東風帶著心中對妻子的愛與思念走在人生旅途中。隋東風的心靈歸屬經歷了一個艱難殘酷的遷徙過程,從真實深愛的羅蕓到心中懷念的羅蕓,隋東風選擇繼續帶著對亡妻的愛勇敢前行。這趟護送羅蕓的回家之旅也是隋東風心靈的回家之旅。
女主人公的心靈歸屬。羅蕓在愛情中找到心靈歸屬,從電影臺詞中我們看出羅蕓早已認定丈夫是她最溫暖的心靈歸宿。影片中新西蘭空中云霧連綿,如同羅蕓對無法延續的生命以及所愛之人的無盡留戀。隋東風與羅蕓搬離克萊德老房子時,羅蕓對著布魯的墓說:“媽媽去哪都帶著你,你永遠都有家的。”羅蕓這一句話表達的不僅是對十五年克萊德鄉村生活的不舍,更是對曾經的心靈歸屬地——老房子的告別。笛子作為電影中的重要意象,共出現四次:第一次是兩人第一次相見,隋東風正在吹奏笛子,代表羅蕓對隋東風的第一印象:自由灑脫;第二次是兩人約定再過幾年結束漂泊生活時提起;第三次是羅蕓病重手術前提起,第二和第三次笛子都沒有真正出現,代表隋東風還沒有做回自由瀟灑的自己;第四次是影片結束時隋東風又吹響笛子,笛聲傳遞思念與眷戀也代表希望與未來。電影女主人公羅蕓從漂泊無依到找到心靈歸屬,經歷了人生的重要階段——結婚。
漂泊海外的中國傳統女性形象的心靈歸屬。林太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代表著她在自己的心靈歸屬中找到了平衡。她開始了屬于自己的新旅程,去尋找等待她已久的丈夫。中國傳統女人的一生,在心靈歸屬的指引下圓滿了。
五、結語
淳樸真摯的愛情在當下快節奏、急速膨脹的消費時代中顯得格格不入,但這份彌足珍貴的情感正是當下社會欠缺的“真”與“誠”。馮小剛導演開創了黑色幽默式中國賀歲檔喜劇先河,又從偏重后現代游戲化、娛樂化風格的商業電影向藝術電影創作轉變,這也說明現在需要安靜的藝術平復凈化當下浮躁復雜的社會環境。[8]馮導在敘述中國式家庭觀、婚戀觀中提出對人生理想的終極拷問,平民化敘事和世俗化價值觀使觀影者的親切感油然而生,那么我們何不像馮導說的“溫一壺酒,聊聊往事”呢?[9]雖然黑色幽默的1997年過去了,我們很懷念它,但我們在馮小剛導演的新作品《只有蕓知道》中找到了新的心靈歸屬——家國情懷與真摯感情。
參考文獻:
[1]鄒鵑薇.精英意識平民化——馮小剛影視作品的改編原則[J].當代電影,2019,(11):170-172.
[2]季惠杰.馮小剛電影的悖論敘事景觀[J].電影文學,2010,(12):17-18.
[3]周星.從<芳華>的人物與行為細節透視馮小剛電影作品的價值觀[J].藝術百家,2018,(01):150-156.
[4]高培.馮小剛電影中的城市空間與身份認同[J].電影文學,2016,(16):75.
[5][6]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3+27.
[7]潘可禮.亨利·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J].南京師大學報,2015,(01):14.
[8]張燕,譚政.影視概論教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145.
[9]趙星,劉曉麗.馮小剛電影創作十二年印象[J].電影文學,2010,(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