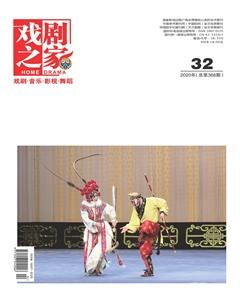中國山水畫戶外對景寫生的意象性表達初探
林志鋼
對景寫生一直以來是中國山水畫家探討的問題,中國古代畫家注重游覽總結,目識心記,而非直接用對景寫生的方式進行創作,而當下又有很多畫家主張對景直接創作,各家有各自的言論,在對景寫生的過程中,實景千變萬化,對景表現時,也有些各種不同的方法。在這過程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中國畫筆墨語言的局限性給寫生帶來一定的難度,引發我關于中國畫對景寫生的一些思考,什么是中國畫中的意象性表達?意象性表達的意義是什么?直接對景寫生如何用中國畫中的意象性表達?
一、寫生的價值
“寫生”一詞,顧名思義,是以實景為對象所進行的現場描繪,是訓練造型技巧和積累創作素材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也是一種創作方法。在當下,中國山水畫寫生越來越受到重視,直接對景寫生不僅可以使我們在自然中獲得最直觀的創作素材,將前人的畫面處理經驗和筆墨技巧在實景寫生中進行學習吸收,而且其也是最直接的一種創作手法,對于形成自身的筆墨語言和繪畫風格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法國畫家布丹說:“當場畫下的任何東西,總是有一種以后在畫室里所不可能取得的力量、真實感和筆法的生動性。”①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印象派繪畫和它之前的西方古典主義繪畫相比較,有著明顯的區別,無論是造型、色彩還是筆觸方面,都是如此。印象派畫家走出畫室以直觀的方式對景寫生,用色彩和形狀去概括大自然的瞬間變化,這一切都與待在畫室里根據草圖閉門作畫的畫家們不同,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價值。
在中國山水畫發展的過程中,前人給我們留下了對待自然、處理畫面的豐富的寶貴經驗,例如各種筆法、皴法、構圖樣式等,使我們在繪畫過程中得以借鑒,但假如只是滿足于前人的經驗,而不是靠自己觀察體驗,容易使作品變得“概念化”。時代在變化,情感在變化,對自然的理解也因畫家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及其感知力、文化背景等的不同發生著變化,當畫家直接面對自然時,就無法回避客觀自然給我們帶來的生動性,用程式化的方式處理畫面,會弱化自然帶給我們的感染力而使作品缺乏鮮活感,“以為作品不是觀察所得,過分地開發大腦、開發觀念而不相信手、不相信直覺,這必然會陷入一種狹隘。”②面對景物寫生有助于畫家準確地表達自己對對象的情感。
無論是西方繪畫還是中國畫,在實景寫生的體驗中,畫者都擁有360度的廣闊視角,又能移步換景地尋找自己感覺最佳的取景范圍。實體空間的縱深感使得畫面層次關系自然拉開,雜亂無序的植物和多余的物體顯得較難處理,但同時也豐富了畫面,常常會給畫面帶來意外的生動性。客觀物象更有著自身的生命意識,往往能給畫者帶來心靈的觸動。
二、中國古代畫家對自然的態度
南朝謝赫的著作《古畫品錄》中提出“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③其中“應物象形”對造型提出了具體要求,畫家應該根據自然物象造型,繪畫表現時應該對自然有著深入的觀察和理解。唐代畫家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從哲學層面上闡釋了繪畫和現實之間的關系,繪畫來自現實,以現實世界為源泉,客觀現實物象經過畫家主觀情感的提煉和表現后轉換為繪畫藝術。在繪畫中,客觀現實的形神與畫家主觀的情思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其中“師”字闡明了古代畫家對大自然是一種學習的態度,游覽、觀察、實地寫生是古代畫家對自然的學習方法。五代荊浩在《筆法記》中,總結了“六要”法則,其中的“景”進一步發展了《六法論》的“應物象形”,《筆法記》中所述,荊浩的松樹寫生達到數萬本,雖然有些夸大,但是可以看出他對實景的重視和對寫生的態度。荊浩還在《筆法記》中總結了“二病”,“夫病有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于山,橋不登于岸,可度形之類也。是如此之病,尚可改圖。無形病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④指出他認為繪畫中常見的兩個問題,其中一是繪畫外在形象的問題,如物象與時間不搭,物象遠近、大小比例不當等;二是畫面關系的問題,如畫面格調和畫面虛實關系處理不好會導致畫面失去生動性。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提出“三遠法”,高度概括他在山水畫中對自然觀察的結果,同時他的“云頭皴”、“蟹爪樹”也是取之于對自然的高度概括。
中國古代畫家由“師造化”而“得心源”,對自然是一種觀察體驗的、概括總結的學習態度,創造各種筆法來表達內心里想表達的畫面。
三、中國畫語言的意象性表達
中國畫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有著自身的民族性和獨立性,是中國幾千年以來悠久歷史滋養而成。由于文化、材料、工具等的不同,中國畫形成“以線造型,意象表達”的特色,筆墨成為中國畫造型語言的基礎。從南北朝謝赫《古畫品錄》的“骨法用筆”和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提到的“無線者非畫也”⑤,可以看出線條在中國畫中的重要性。
線條是造型藝術的基本元素之一,是點的運動的延續,用來分割制造面,形成有形式意味的空間,是人類觀察世界、表現世界的“想象性的抽取”,客觀事物本身是由不同的面組成。線條本身在造型藝術中具有很強的豐富的表現力。
中國畫里的線有著自身的特點,中國的毛筆雖然構造簡單,看似單一,但通過畫家的運用使其變得極其豐富。在中國畫悠久的發展過程中,畫家們總結出毛筆的不同用法,例如中鋒、側鋒、逆鋒、提按、頓挫、輕重、徐急、轉折等有節奏的用筆方法,既給畫者自身在繪畫的過程當中帶來愉悅感,同時在平面上創造出枯、濕、濃、淡、粗、細、長、短、方、圓等富有節奏變化的線條及其組合形式,形成中國畫獨特的審美價值。中鋒的線,堅挺渾圓;側鋒的線,生動靈活;藏鋒的線,柔中帶剛,因用筆差異產生不同線型,各具特色。中國畫的線,同時也能看出中國畫家內在的追求和修養,線,或纖細,或力透紙背,有劍拔弩張,有內斂含蓄,也有穩健流暢。美學家宗白華曾說“中國人這支筆,開始于一畫,界破了虛空,留下了筆跡,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了萬象之美”。⑥
正是因為中國畫是在平面上使用不是書法而又帶有書法節奏的線,經過組織后對客觀物象進行塑造來表達情感,所以這種書法化的造型語言對筆墨的使用提出了極大的挑戰,使得中國畫因其筆墨特點想如實地描繪客觀物象存在一定的難度,如實地描繪客觀物象極有可能讓中國畫本身具有獨特審美意義的筆墨消失。筆墨對如實表現自然客觀物象有一定的局限性。恰恰是這樣的局限性,使得中國古代畫家采取了意象性表達的方式,既保留了筆墨本身的審美意義,又能表現自身理想中的畫面,成為中國畫最顯著的特點。
“意象”一詞在中國文化語境中使用頻率極高,在我國文化發展史上流傳久遠,被藝術實踐和藝術理論廣泛運用,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說:“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⑦這句話指的是:有著與眾人不同眼光的工匠,能夠按照心中預先構思設計好的形象直接揮動斧頭。這與中國繪畫發展的特性相符合,隨著實踐探索不斷深入,意象表達的內涵也在不斷完善。“意象”中的“意”是指畫家主觀上對事物的認識,是自身內在的精神、意念、感情,“象”是指外在的客觀存在的物體。“意象性表達”,即將畫家自身所要表達的情緒通過具體的事物表達出來。意與象的聯系,標志著主客觀的交融,它與古代畫論中的“傳神”、“氣韻”理論互相聯系、彼此滲透。東晉顧愷之提出的“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的觀點,強調畫以神為中心,傳神通過寫形來表現,表現人的精神狀態可以從眼睛刻畫入手,因為從眼神中可以觀察出不同人的精神狀態和內在涵養,這真實又具體地體現出古代畫家的意象追求。顧愷之又提出“遷想妙得”,指出可以通過觀察、思考、聯想以達到傳神的目的。南朝的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到:“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⑧就是說畫家不應該被事物的各種表面現象所蒙蔽,而應該以把握事物的內在實質規律為根本,表達畫家的情感。謝赫的《古畫品錄》中提出的“六法”論,即“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首先就指出“氣韻,生動是也”。通過形體來表達物象的神韻和內涵的審美法則,一直是中國畫批評、鑒賞、創作遵循的總原則。
從我國山水畫的歷史發展來看,歷代畫者在追求表現大自然的形象的同時,也希望客觀物象在畫者頭腦中形成的情緒、情感能進行融合并把觀者帶入到這種氣氛之中。“氣韻生動”就要求作畫須重視“我”的感受,即畫者主觀的存在和畫者對氣韻的理解。五代荊浩的《筆法記》中言:“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⑨說到底,這是要求山水畫也通用人物畫的創作原則即注重外部自然、形象的真實,力求真實的描繪。他又說:“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接著又闡明了“氣”與“韻”二者的關系:“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遺不俗。”⑩畫家要具備觀察體會物象的“真”的能力,再加上得心應手地利用筆墨,心手相應,便可得其“氣”。畫家如果具備了“氣”,對物體的觀察體會又不停留在表面,就能達到“真”,便能“傳神”,如此便能“氣韻生動”。畫家觀察體會客觀物象是一個交融的過程,因此,“氣韻”可以說是畫家內在精神、情緒與外在事物的完美融合,這與前面說到的主客觀交融的意象造型觀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畫家在對待具體的事物時,注重個人內心感受,把這種感受通過真實的事物體現出來,并且融入自己的人格特性。既要體會、觀察自然中的形象,又要重視個人的主觀感受,主體的思想情感作用于外在的物體形象,使其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創作應該融入情感,而得到本質的東西。意象性表達的核心是畫家不要被表面的物象所蒙蔽、困惑、束縛,應該把握客觀物象的節奏規律,表達出自身的理解和情趣才是最重要的。意象性表達強調畫者本身,象與意之間看起來是矛盾的,卻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關系。
四、對景寫生中如何運用意象性表達
既然中國畫有著自身語言的特點和意象性的表達手法,那么我們在對景寫生中要如何運用呢?
首先是取景,中國畫的意象性表達是主客觀的交融統一,借景抒情。石濤的“搜盡奇峰打草稿”,強調尋景取意。在取景時,我們也應該有感而發,在大千世界里尋找與自己情感相符合的畫面。在面對實景時,我們應該尋找出隱藏在表象世界里打動我們情感的內在本質因素,由“景”生“意”,緣“景”生“情”,再用具有中國畫特色的語言進行表“意”的表達。
寫生既然是對自然的有感而發,那么就要求尊重自然,對景寫生并非是對對象機械復制的絕對真實再現,而是畫家在面對自然對象時,把握住所要表達的對象給我們帶來的感受,使之與自己的思想感情相融合,然后用自己理想化的審美進行表現使其成為藝術作品。這就要求我們在寫生的過程中必須得充分地觀察、感受和理解對象,并把自然對象給我們帶來的獨特感受和空間氛圍整理出來,把握自然對象的形式美感,用自己理解的具有中國畫審美特點的筆墨語言進行意象性的表達,使得觀賞者既能看出我們由景而產生的“意”,同時又能欣賞到有中國畫特點的筆墨語言。很多人在寫生的過程中過于強調主觀的存在,而幾乎放棄了對象,他們以“寫生重要的是創造”、“寫生要表達個人的思想”為由,對著實景畫著和景完全沒有關系、沒有融入由實景帶來的真實感受的畫面,我認為這樣的表現方式便讓對景寫生的意義消失了。
中國畫筆墨語言的自身特點給如實表達物象帶來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可以以客觀物象為依據,用意象性表達的方式,將心靈融入筆墨來進行戶外對景寫生,融情于景,主觀地把握自身對物象的理解,去追求內在的情感性元素。這就要求畫者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要準確地傳達對所要表達的自然物象的理解和畫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對構圖進行位置經營、留白,色調上隨“意”賦彩,對表現對象進行取舍、夸張、概括等意象性表達。
“經營位置”,要求畫家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主觀“經營”畫面,在景不如意的狀態下,對構圖進行主觀的處理,注重把握畫面結構中的主次、上下、前后、遠近、縱橫、聚散等關系,利用一切藝術手段加以意象化的提煉、夸張、取舍和概括,體現形式美的規律,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意”表達出來。
留白,中國畫意象化表達的一種手法。從自然中觀察不難發現,景色四時不同,早中晚各不相同,早晨云霧給畫面帶來了白,晨光給畫面帶來了層次明顯的空間虛實關系和空間氛圍,而中午的光線則是比較平均的,空間層次也比較平均,整體處在一種實的狀態。在對景寫生中,我們可以將早晨由于光線、云霧所產生的“意”,在中午的寫生當中進行主觀處理和留白,處理畫面虛實關系和營造特定的空間氛圍。畫者根據自身追求的意境來處理畫面中的黑白和虛實關系,使畫面虛實相生,實景厚重豐實、精當簡潔,虛景內涵豐富留有想象空間。“知白守黑”可營造出空靈、玄妙的意境,使沒有畫的白富有豐富的內容,給觀者豐富的想象空間,同時又能與畫面實的部分形成對比,突出實的內容。如若畫面只求實不求虛,容易顯得層次單一,不夠厚重。以虛寫實、虛實結合才能使畫面意味深遠。留白表“意”,是中國畫意象性表達中虛實處理的一種重要手法,在對景寫生中只有將黑白、虛實關系處理得當,才能將自然客觀對象在畫者心中產生的“意”更加藝術化地表達出來。
色彩在中國畫意象性表達中,與西方繪畫形態中的光源色、環境色等科學的色彩表現不同。從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國畫意象性表達的色彩是畫者根據自身內心追求的“意”對色彩的主觀運用,畫家的追求不是色彩的似與不似。南朝謝赫“六法”中的“隨類賦彩”告訴我們,我們賦色要以自然客觀為依據,根據物象的不同類別而隨之賦彩是尊重自然客觀的表現。在繪畫過程中,畫者不是將自然色進行再現,而是將對色彩的自我感受和主觀情感進行總結。“類”體現出中國畫的色彩,是意象化后的色彩,目的是畫家借造型語言中的色彩來抒情達意。色彩的意象性表達,體現出畫家對自然的觀察和體悟,成為畫家傳遞情感的語言,中國畫色彩運用的獨特性使中國畫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審美。意象性表達中的“賦彩”要求畫家宏觀把握畫面的色彩,要充分體現自然對象的神韻。畫家必須控制好畫面的整體色調,在山水對景寫生中,不應該被自然客觀物象中瑣碎的顏色所影響,對色彩的表現應該根據自己所要表達的“意”對畫面進行敷色,畫面中的所有局部色彩都應該統一于整體色調,讓色彩富有變化而又統一和諧,更理想化地表達實景。
在對景寫生中,用意象性表達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畫筆墨語言如何為造型和情感服務。古代畫家和我們在同樣的自然面前,卻畫出不同情感的畫面,在寫生當中,通過對客觀物象的觀察,我們可以驗證古代畫家為表達“意”而創造的筆法,借助前人的經驗進行寫生,也可以通過觀察嘗試新的筆法。例如在寫生當中,通常古人畫近處的樹用“雙勾”的方法,而遠處的樹則用單線勾勒,在實景觀察中,逆光下的柳樹呈現出粗的單線,在寫生當中,我們可以進行嘗試,用符合自己感受的筆法進行表達。在直接對景寫生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古人用“個字點”的筆法概括地表達對竹林的感受,近處遠處則用濃淡表達。而在寫生中,我們不難發現遠處成片的竹林通常給我們呈現的是規則的幾何狀,層次分明,在寫生中我們也可以用具有中國畫特點的線,用概括外輪廓的方式,皴擦出層次,同樣能表達出物象給我們帶來的感受。通過寫生我們不僅可以驗證古代畫家給我們留下的豐富的筆法和意象表達的思維,讓我們更加容易在前人的筆墨語言中找到與自己情感合拍的手法,同時,通過自己對自然的觀察體會,嘗試新的造型方法,舉一反三,可以將戶外寫生的發現和嘗試用于日后的室內創作。這樣的寫生方式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將會更有意義。
由此可見,用具有中國畫語言的筆墨在對景寫生時進行意象性表達,不僅能讓我們更好地借鑒前人的寶貴經驗,還可以找到興趣所在的景和符合內心情感的情,讓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實和理想化處理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自由表達的狀態,是心靈的嬗變與升華。
五、小結
自然對藝術家來說是取之不盡的靈感來源,歷史悠久的中國畫在長期的文化脈絡中形成自己的特點,中國古代畫家由“師造化”而“得心源”,對自然是一種觀察體驗的、概括總結的學習態度,創造各種筆法來表達內心里想表達的畫面。而實景寫生常常會給畫面帶來意外的生動性。客觀物象更有著自身的生命意識,往往能給畫者帶來心靈的觸動。將中國山水畫意象性的表現手法用于對景寫生,不僅有助于我們對自然物象的理解和感悟,同時有助于我們確立自己的審美理想,表達自身的情感,形成自身獨特的繪畫語言。由于畫者的思想感情不同、審美理想不同、天賦不同、表現技法不同,因而用意象性表達的方式對景寫生能為畫者提供更為寬廣的創作思路和更多的創作技法,表達的情感也將更為豐富。
注釋:
①里奧那洛·文圖里,《歐洲近代繪畫大師》,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版,第19頁。
②趙奇,《關于繪畫藝術的思考》,2010年4月第一版,第29頁。
③倪志云,《中國畫論名篇通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第202頁。
④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235頁。
⑤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版。
⑥畢建勛,《萬象之根》,河北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頁。
⑦劉勰,《文心雕龍·神思》。
⑧倪志云,《中國畫論名篇通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第53頁。
⑨俞劍華編著,《中國畫論類編》,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版。
⑩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2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