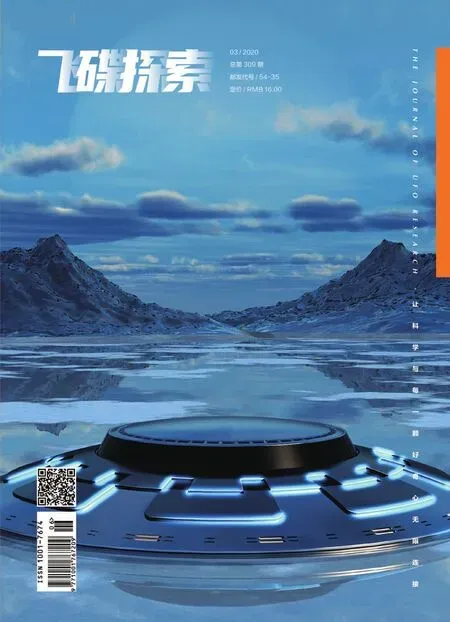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人類基因組正在衰敗
文|把科學帶回家
過去的致命疾病在現代社會不再致死,人類因此擺脫了自然選擇,但也可能會為此付出代價。早在70年前,科學家就注意到,人類基因組正在不斷累積有害基因突變,以人類的低生育率要如何破解這個難題?許多科學家為人類的未來感到憂慮。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現在患有近視眼、過敏、糖尿病、肥胖癥等疾病的人似乎越來越多。這些病,很可能是人類逃離了自然選擇后,患上的現代病。而許多人并不知道的是,這些疾病是人類基因組正在緩慢衰敗、累積有害突變的征兆。
隨著大量科學證據的出現,這個現象被命名為“突變載量遞增”。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后DNA發生的變化說起。
DNA是我們的合成藍圖,它們一半復制自我們母親的基因,另一半來自我們的父親。但在基因復制的過程中,DNA會出錯,這就是基因突變。
我們出生時,平均每個人會擁有100個父母所沒有的新突變。雖然不是所有的基因突變都有害,但要是在史前,攜帶多種有害突變的孩子恐怕無法活到生育的年紀,甚至都無法養活自己,他們的基因由此被自然選擇淘汰,無法進入人類基因池。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祖先都是非常優秀的,他們經歷了殘酷的自然選擇,給我們留下的遺產——DNA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
但是,隨著農業和工業革命的到來,現代人的生存環境相比人類祖先,已經變得越來越友好,許多致死疾病不再致命,自然選擇的作用開始減弱。比如,20世紀初的時候,攜帶I型糖尿病(一種高度可遺傳的糖尿病)風險基因的人一般會很早死去,服從自然的選擇。但是現在,患病者可以終身使用胰島素,過上正常的生活,生兒育女,把這一有害突變遺傳下去。
不少突變導致的疾病在現代社會里能得到更好的治療,過去的致命疾病現在成了慢性病,可以靠藥物控制,因此,相關的突變基因也不會從基因池中被剔除。
實際上,科學家們通過對小鼠、蠕蟲和其他許多動物的實驗發現,在沒有自然選擇的情況下,實驗室動物的基因突變發生率會不斷增長,整個種群會因此變弱,適合度(生物個體或群體適應環境的程度)降低。
換言之,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基因池逐漸成為有害突變的避難所。
自然選擇下線
最開始發現人類基因組在不斷累積突變現象的是美國遺傳學家,因為發現X射線誘導突變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的赫爾曼·約瑟夫·穆勒。
70年前,穆勒在研究中發現,有害突變會不斷產生:平均每個新生兒會帶著50~100個新的突變出生;而在這之前,我們已經從父母和祖先那里繼承了很多累積的有害突變;再縱觀人的一生,每次細胞分裂,我們都會收獲3個突變。穆勒擔心,不再受到自然選擇的諸多限制,甚至開始操縱自然的人類將為此買單,承受由于缺乏自然選擇而導致的惡果。
即使是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穆勒的擔心也并不多余。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大量測試核武器,輻射塵埃在大氣中四處散播。發現X射線誘導突變的穆勒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他擔心核武器試驗會把人類逼上滅絕的道路。
雪上加霜的是,穆勒還發現人類基因組里有很多基因連鎖群,相當于捆綁銷售(遺傳),這是一群無法拆開遺傳的基因。有害基因如果影響了這些基因連鎖群,會產生連鎖遺傳。這就是著名的“穆勒的棘輪”——基因連鎖群只會累積越來越多的有害突變,而無法得到修正,就像無法反轉的齒輪一樣。
意識到這一點以后,在1950年的《我們的突變負荷》一文中,穆勒指出,如果突變率太高,人類基因組會不可避免地惡化,最終導致人類滅亡。
“很難解釋人類是如何幸存的”
那么,人類的突變率究竟有多大呢?在穆勒看來,突變率高于0.5就危險了。也就是說,每代人中每個個體的突變不超過0.5個,才能保證人類不滅絕。
學遺傳學的人都知道,人類基因組累積了越來越多的有害突變,突變載量太大。現在科學家們的共識是,人類突變的速率是每代人的每個個體平均貢獻了100個突變。
——約翰·桑福德 康奈爾大學遺傳學教授
很難解釋人類是怎么幸存下來的,因為人類的突變率如此之高,而繁殖率又如此之低,這對一個物種來說是很矛盾的。人類,以及人類近親的有害突變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這些物種的存活很成問題。
——埃爾·沃克 薩塞克斯大學生物學家凱特利 愛丁堡大學生物學家
來自康奈爾大學的遺傳學教授約翰·桑福德研究突變載量已經18年了,在他的演講中我們看到,人類的個體突變量已經超出目前認為的安全值太多。關于這一點,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研究。
1997年,生物學的另一位專家,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遺傳學家詹姆斯·克勞指出,在過去的幾百年里,有害突變一直在不斷累積。克勞估計,有害突變在每代人中導致的繁殖能力下降率大概是1%~2%。
無獨有偶,1996年,一些得克薩斯大學醫學分校的研究者在對人類線粒體基因組(線粒體中也有DNA,和細胞核中的DNA不同)測序后,也發現大量累積的突變。在這篇被引用了260多次的論文中,他們發問:“我們要密切關注這個問題,那就是帶有這么高突變載量的系統要如何演化下去。”更糟糕的是,對于人類來說,幾乎所有的非中性突變都是有害突變。
作為證據,1999年,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和愛丁堡大學的兩位生物學家在發表于《自然》雜志上的一篇論文中提到:他們發現人類的基因突變率非常高,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是有益突變,大部分是有害的。這項研究目前被引用了超過400次。具體來說,這兩位生物學家對41 471個編碼蛋白質的基因堿基進行了研究,發現從600萬年前,也就是人類和黑猩猩分化后,人類累積了143個突變,其中88個是有害突變。
在美國,自閉癥、男性不育、哮喘、免疫系統紊亂、糖尿病等疾病的增長率遠遠超過了預期。
現在有大量的醫療技術可以減輕有害基因引起的病痛,導致自然選擇對有害突變松綁。每代人的生理和心智機能衰退1%,這些效應下可以預見的長期結果就是,人類的基因組衰退。
——邁克爾·林奇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生物學家
人類基因組衰落的癥狀
人類基因組的衰變已經有了具體的癥狀。
2017年,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在過去的80年里,愛學習的基因衰落了。
研究者對近13萬名出生在1910~1990年間的冰島人進行了基因測序,并計算了62萬個和受教育時長有關的多基因風險評分。他們發現,那些攜帶和更長受教育時間相關基因的人,生的孩子更少。也就是說,高學歷基因在整個冰島基因池中的百分比正變得越來越低。而即使是那些攜帶了“愛學習”基因,但事實上沒有接受很長時間教育的人,生的孩子也更少。
這項研究的主要作者表示:“人類是因為大腦才和其他物種不一樣,而教育是訓練大腦的重要途徑。但是和受教育年限有關的基因卻在基因池里變得越來越少。”
這不僅僅是冰島一個國家的問題。早在2016年,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喬納森發表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研究也指出,美國人的“愛學習”基因也在人群基因池中緩慢地消失。
其實早在2010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生物學家邁克爾·林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論文里就整理了人類基因組衰退的顯性證據。他估計,如果沒有自然選擇,人類的適合度將每一代下降1%~3%,人類會經歷生理、神經和外觀上的顯著失調,高度工業化的社會里,民眾的生理、形態、神經活動水平每過200~300年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為什么大自然要針對人類?
有些人看到這里可能會很吃驚,大自然為什么要這樣為難智人?其實,這不是大自然故意針對智人,而是針對所有無法快速繁殖的生物。
所有無法快速繁殖的物種在演化時都會面臨一大難題——霍爾丹的兩難處境(Haldane,s dilemma,亦即“自然選擇的成本”)。早在DNA測序技術發明前,生物學家們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1957年,英國演化生物學家霍爾丹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物種要花多少代價,才能消除基因池中的不良突變?
以人工選育動物為例,如果一個養殖場經過少量的幾代培育,消滅帶有不良基因的個體,篩選繁殖出一批最優秀的動物,養殖場的收益就能因此最大化。那么養殖場到底要繁育多少,淘汰多少,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呢?
一撥兒計算后,霍爾丹發現了一個令他十分困惑的矛盾:如果養的是牛,一半母牛都不能淘汰,因為牛的個體繁殖率不夠高,若淘汰太多母牛,會導致種群數量不夠延續后代,就更加沒法人工培育優良品種了。
霍爾丹還發現,這個矛盾在自然界也適用。簡單來說,如果環境發生突變,生物會通過讓不適應環境的個體死亡的方式淘汰不利基因以適應環境,結果它們反而會因此滅絕。換言之,無法快速繁殖的生物(如人類和牛)會因為無法快速演化而滅絕。這就是霍爾丹的兩難處境吊詭的地方。霍爾丹認為,這個兩難處境是生物學的本質,應當成為生物學研究的重心。
霍爾丹的兩難處境后來引起了另一位著名的生物學家木村資生的興趣。
1968年,他通過自己的計算,得到了更驚人的結論:如果要在保持種群數量的同時把有害突變替代,每個人都要生327萬個孩子才行。因為覺得這個數字過于離奇,他提出了著名的中性演化理論(在分子水平上,自然選擇是中性的,大部分突變并不會被自然選擇淘汰掉)。
樂觀派
當然,雖然大部分科學家承認人類基因組突變量累積的事實,但是一些人對這個現象的后果卻比較樂觀。他們的主要觀點大概是三類:
第一類觀點是,人類基因組里的大部分是垃圾DNA,它們不編碼蛋白,即使突變了,也不影響整體的功能。
但是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駁斥。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的公共聯合研究項目“DNA元件百科全書計劃”指出,人類基因組的80%都具有功能。2003年,上文提到的兩位生物學家指出,大多數突變都是有害突變,這是演化遺傳學上受到廣泛承認的原理,擁有分子遺傳學數據的證據基礎。
第二類是“突變計數”理論,它認為累積太多有害突變的個體會遭受懲罰。也就是說,大自然會給個體一個突變指標,如果超過這個指標,就會被自然選擇淘汰,要么活不到性成熟,要么無法找到配偶或者無法繁育后代,總之無須擔心。
第三類“協同上位”理論則認為,有害突變會互相放大,導致有很多有害突變的個體被早早淘汰掉,所以最終能留下來的人應該沒有很多有害突變。
上面兩類觀點比較近似,都認為總有一天有害基因會被淘汰掉。如果這類假說是真的,那么人類是否總有一天會看到,許多人在病痛中早死,而另一些人則孤獨地活著的怪現象。
總之,老師每年都說“你們是我帶過的最差的一屆”,原來,這可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