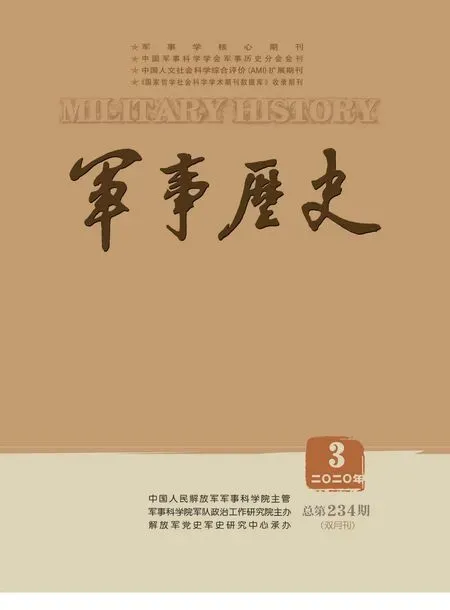傳統兵學在近代的回響與沉寂*
近代中國所面對的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對傳統兵學而言同樣如此。兵學昌明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然而有兵法護身的晚清軍隊在與列強的作戰中,卻鮮有勝績,原本被認為行之有效的兵學原則也在戰爭中屢屢失效,原因何在?這些不能不引發近代思想界對于傳統兵學的質疑,所以兵學在近代的發展,主要是對其自身價值的重新估定,對其觀念和原則的重新認識,以及對其體系重新建構的過程。
一、近代兵學發展的基本脈絡
(一)鴉片戰爭后對傳統兵學的警醒與反思
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它繪制了近代中國歷史長卷的底色。戰后,起初人們將戰敗原因主要歸咎于將領的怯戰和指揮的笨拙,之后認識則逐漸趨于冷靜,一些較有遠見的官員和學者開始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對戰敗原因進行剖析,逐漸將探察的視野聚焦于武器裝備和海防建設上。
一些具有開拓精神的近代科學家,如丁拱辰、龔振麟、丁守存等人在戰爭期間即著手研究西方造炮之法,試圖從制造原理上搞清楚清軍火器與西洋火器的差距,由此產生了《演炮圖說》《鑄炮鐵模圖說》《西洋自來火銃制法》等著作。比較具有國際視野并在鴉片戰爭中親自指揮過初期作戰的林則徐,對于中西方火器的差距體會更深,他在戰后總結道:“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①《致姚椿王柏心》,《林則徐全集》第7 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06 頁。在此判斷基礎上,林則徐提出了制敵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膽壯、心齊”,將提升武器裝備水平擺在了突出位置。對于戰爭期間制定的“以守為戰”策略,即不與敵水戰,而專于陸守,林則徐在戰后也進行了深刻反省,認為“彼以無定攻有定,便無一炮虛發。我以有定攻無定,舟一躲閃,則炮子落水矣”②《致姚椿王柏心》,《林則徐全集》第7 冊,第306 頁。,“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①《致姚椿王柏心》,《林則徐全集》第7 冊,第304 頁。,因此提出,將建造船炮、發展海軍視作衛固海疆久遠之謀。而魏源,作為林則徐思想的繼承者,對于海防的認識并未超出林則徐的水平。他所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②《海國圖志》上,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第1 頁。,實際上與林則徐提出的“以守為戰”并無本質差別。魏源的最大貢獻,在于從觀念和思想層面上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成為后來晚清開啟軍事改革,推進軍事近代化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
盡管鴉片戰爭后的這些探索在理路上仍然是嘗試性的,系統性和深度都不夠,但方向是明確的,即中國要擺脫軍事上的困局,武器裝備和海防建設必須要有突破,而要突破,必須放下虛妄的自尊,塌下心來向西方學習。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有價值的思想火花在顢頇的政治環境和頹廢的社會氣氛下沒能被導向深入,也就很快地在不斷消損中歸于沉寂,沒有對決策層產生影響,在啟發社會進步上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二)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前后對傳統兵學價值的再認識
真正對近代兵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是持續14年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其主要影響即如左宗棠所言:“始以勇丁助兵,繼且以勇丁代兵;始以將弁領兵,繼且以文臣代將。”③《閩浙兵制急宜變通謹擬減兵加餉就餉練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第110 頁。在太平軍的沖擊下,清朝經制兵八旗和綠營趨于沒落,動搖了清廷的統治基礎。為保住王權,清廷不得不賦予督撫更大的自主性,由督撫主導下建立的勇營制部隊——湘軍由此登上歷史舞臺。在湘軍建立過程中,督撫在制度安排、人員選擇、武器配備上具有較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因此勇營的招募制度和編制設置,與八旗、綠營有明顯差別。湘軍不僅統系更為嚴密,同時在充分吸收傳統兵學成就,特別是戚繼光練兵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特點和武器裝備水平,探索出了一套簡單有效的訓練方法和作戰方法。
文人統兵的出現對近代兵學發展產生了更大影響。文人往往善于總結和思辨,但易脫離實際,如左宗棠對言兵者的評價:“近時言練兵者,多系套話。”④《答浙撫楊石泉中丞》,《左宗棠全集·書信》(二),第212 頁。然而文人統兵,避免了文人談兵的種種弊端。在經歷了戰場上生與死的磨練后,這些統兵的文臣或士子對于戰爭的認識遠比無戰場經歷的文人深刻切實。如左宗棠所說:“理可憑虛而悟,事必親歷而知,非練習之深,不敢深信也。”⑤《答王璞山》,《左宗棠全集·書信》(一),第130 頁。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文武之間的互動關系,扭轉了長久以來文武兩途的截然對立,實現了理論與實踐在戰場上的碰撞,使文人得以在戰爭實踐中重新認識兵學的原則與規律,并對傳統兵學的范疇進行剖解,對兵學中的基本原則進行驗證,推動了兵學在近代的發展。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均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
曾國藩說:“推之齊家、治身、讀書之道,何一不然。”⑥《復吳廷棟》,《曾國藩全集·書信》(二),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第1179 頁。此言雖未提及兵事,但認真考察曾國藩的兵學思想來源,很容易就能看出兵學與儒學之間的關聯性。湘軍的很多將領都受過長期的儒學訓練,“修身”“窮理”已經成為他們的一種思維自覺,不可避免地會將儒學的價值觀和方法論運用于分析兵學問題。比如:曾國藩強調要以禮治軍,“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⑦《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391 頁。;左宗棠也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不可不隨時講究,心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⑧《督標中軍尚副將兆嘉稟閱過督標等營春操事竣并境內得雨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6 頁。,都帶有鮮明的儒學特色。左宗棠更說“能克己者,必能克敵”⑨《答王璞山》,《左宗棠全集·書信》(一),第125 頁。,將儒學中看重的個人修為與操守上升到了決定戰爭成敗的高度。湘軍統領不僅以儒學治軍,還以儒學指導作戰。羅澤南原是理學名家,“及其將兵,膽略俱壯,隨機立應,竟為宿將所不及”①《致嚴仙舫》,《左宗棠全集·書信》(一),第107 頁。。當被問及制勝之道時,他的回答是:“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數語,盡之矣。”②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17 頁。李續宜治兵,“只實做程、朱主敬存誠工夫,終日靜默,不妄言,不妄動,抱定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作主腦,其臨陣則全是以靜待動,謀定后發,慮勝后戰”③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9 頁。。
除兵學的儒學特色外,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治軍、選將、作戰等領域也提出了不少異于前人的深刻見解。比如:在訓練上,既強調技能訓練,又突出“訓”,即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訓作人之道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動”④《批統領韓字營全軍韓參將進春稟奉委招勇抵省立營管帶由》,《曾國藩全集·批牘》,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第246 頁。。在選將上,強調將領要“勤、恕、廉、明”,要有忠義血性。在作戰上,提出“先求穩當,次求變化”;戰略貴先,作戰貴后;水陸相依等原則。對傳統兵學范疇的認識也有所突破,如對奇正,認為“總以并力為主,穩打為主,此是奇兵也。奇兵而出之以穩,尤奇之奇也”⑤《致金國琛》,《胡林翼集》第2 卷,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443 頁。,“其實戰陣之事,有平實而無奇巧,從平實入者,雖無大功亦無奇禍。從奇巧入者,未有不貽誤者也”⑥《云臥山莊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21 頁。。可以看出,這些思想雖仍是在傳統兵學框架內的豐富或補充,但亦有所突破和創新。
(三)西方軍事理論的引入與兵學體系的重構
盡管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對傳統兵學進行了實踐化的充實,但對其原生缺陷卻無力進行根本性調整。所以盡管傳統兵學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運動中被證明行之有效,但在應對裝備有堅船利炮的西方列強時則捉襟見肘,傳統兵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在近代中國與西方的競逐中逐漸暴露出來。如:歷代關于選將的思想雖很多,但都無外乎孫子講的“智、信、仁、勇、嚴”五字。曾國藩、胡林翼雖提出了要用陶镕造就之法對將領進行培養和鍛煉,但亦缺乏嚴密、完善的培養機制,所以常有“有兵無將”的感嘆。關于訓練,歷代兵書中最有價值的是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除此以外的其他訓練思想,雖有價值但無實際的指導意義,因此胡林翼才會說:“千古兵書,以《左傳》為第一,此外則《資治通鑒》胡身之所注,亦大有所得,余人皆囈語夢話耳。”⑦《致李續宜》,《胡林翼集》第2 卷,第178 頁。淮軍大規模引入西式火器,卻找不到能夠對火器使用與訓練進行指導的兵書。李鴻章曾說:“中國制炮之書,以湯若望《則克錄》及近人丁拱辰《演炮圖說》為最詳,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度之談,而世皆奉為秘本,無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遠。”⑧《致總理衙門》,《李鴻章全集》第29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2 ~313 頁。
為彌補傳統兵學的諸多不足,19世紀70年代,隨著洋務練兵活動的展開,翻譯外國軍事著作被提上議事日程,并逐步演繹成一場引進學習西方軍事理論的熱潮。初期以翻譯介紹軍事技術書籍為主,如《制火藥法》《克虜伯炮彈造法》《步隊毛瑟槍說》等,后期選譯范圍逐步擴大,除繼續關注軍事技術外,也開始翻譯軍事訓練、作戰理論等方面的著作,如《行軍臆說》《臨陣管見》《水師操練》《輪船布陣》《防海新論》《陸操新義》等,甚至翻譯了介紹當時強國軍事制度的著作,如《列國陸軍制》《德國軍制述要》等。
這些譯著對傳統兵學的發展產生了顯著影響,主要有三:一是受西方海軍和海戰理論影響,中國近代海防思想得以建立。當時很多人對水師與海軍的區別認識不清,往往以辦江防的思路來理解海防,所以始終突破不了從海口到海面的這段距離。李鴻章的海口重點設防盡管算不上高明,但也是在普魯士軍事家希里哈的《防海新論》的影響下產生的。通過兩次海防大討論,海口重點設防的思想逐步被多數人接受,在后續的海防建設中得以實施,并最終形成了晚清海軍、要塞、駐口防軍三位一體的總體海防格局。二是陸戰戰術逐步擺脫了傳統的“鴛鴦陣”“三才陣”等冷兵器陣法,轉而提倡靈活機動、發揚火力,強調步騎炮兵協同配合的戰術。三是“選將以學堂為根基”①《武弁回華教練折》,《李鴻章全集》第8 卷,第515 頁。的觀念逐步得以確立,并陸續建成了天津武備學堂、江南陸師學堂等一大批近代軍事學堂,對于改變晚清武將知識結構,提升武將整體素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此外,受西方軍事譯著的影響,清末還出現了幾部結構內容上均與傳統兵書不同的新型兵書。聶士成主持編寫的《淮軍武毅各軍課程》,明顯吸收了西方軍事理論中的訓練方法,成為中國傳統兵學轉型的標志之一。徐建寅在吸收當時西方軍事理論最新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編寫了《兵學新書》。該書用較多篇幅講述了各種先進的技術問題,如后裝槍炮的構造與使用等,在戰術訓練上區分了進攻與防御、林地與要隘等不同類型的作戰形式,這些都是傳統兵書所沒有的。這兩部書對改革清軍作戰訓練方法,改造中國傳統兵學體系,均有重要意義。
這些新思想的引入,撞開了中國傳統兵學思想的沉重藩籬,同時也促使中國兵學家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基礎構架近代中國兵學體系,推動中國近代軍事思潮從傳統經驗性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兵學”向具有科學性的“軍事學”轉變。
二、主要兵學著述
近代兵學思想的呈現方式趨于多樣化,除一般意義上的兵書外,還有大量的訓練操典、軍事教材和有關招募、訓練和管理的章程或規定,以及散見于有關軍事人物文集中的零星兵學思想。具體而言,可分為以下幾部分:
(一)兵書
近代一般意義上的兵書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通論性的著述。如壁昌的《兵武聞見錄》,分為擇帥、選將、肅伍、整械、修守、安撫、行軍及善后8 篇。盡管該書所論較為粗略,且較少涉及戰略層面的問題,但比較貼近實際,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陳澹然的《權制》,是作者有感于清末中法甲申之戰、中日甲午之戰中清軍敗績而作,包括《軍地述》《軍勢述》《軍情述》《軍材述》《軍政述》《軍謀述》《軍本述》7 篇。盡管該書寫成于1898年,但從其結構和語言風格來看,仍可歸入傳統兵書一類。
甲午戰爭后,出現了一批吸收了西方軍事理論的新型兵書,如前文提到的《淮軍武毅各軍課程》《兵學新書》。此外,清末編練新軍后,官方頒定了一系列系統化的軍事教材。如由袁世凱主持編定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劉坤一主持編定的《江南陸師學堂課程》、張之洞主持編定的《自強軍西法類編》等,這些教材從內容到形式已與傳統意義上的兵書有很大區別,都大篇幅地介紹槍械構造和原理,對隊列訓練、技術訓練、戰術動作均有極為細致的介紹。書中也有大量以功名富貴相激勵和忠君愛國的訓詞,以封建家長制維系新軍內部關系的“道必師古,法必因時”②《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第1 冊,光緒二十五年本,第2 頁。的治軍思想。
另一類是專論性的兵學著述。這些論述或單獨成冊,或單獨成篇,編入著者文集當中。報紙和期刊出現后,其中討論兵學問題的文章也有不少。按照論述內容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海防類。魏源在《海國圖志》中的《籌海篇》,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以守為戰”的海防觀。徐稚蓀的《洋防說略》,除討論海防外,也討論了江防與陸戰的關系。鄭觀應的《易言》中有《論船政》《論水師》《論火器》《論練兵》等篇,對于海軍與海戰有較深刻的認識。還有薛福成的《籌洋芻議》和姚錫光的《籌海軍芻議》。此外,晚清幾部《經世文編》均設有兵政卷,其中討論海防問題的文章也有很多。
二是武器類。為改變清軍器械窳劣的落后狀況,近代科學家們努力探索新式火器的原理和制造方法,如:鴉片戰爭后,丁拱辰的《演炮圖說》,內容涉及火藥的配方、火炮的鑄造、炮臺的構筑,西洋炮臺、岸炮以及運炮器械的制造與使用等;龔振麟則改進了鑄炮技術,并將鑄炮經驗匯纂為《鑄炮鐵模圖說》;丁守存寫成《西洋自來火銃制法》《詳覆用地雷法》《造藥法》等著作;19世紀60年代黃達權譯、王韜整理的《火器略說》(后改名為《操勝要覽》),介紹了洋槍洋炮的制造方法;數學家李善蘭編寫的《火器真訣》,第一次把系統的彈道學原理引入了中國。
三是訓練操典類。湘軍時期有劉連捷的《臨陣心法》和王錱的《練勇芻言》,都帶有明顯的傳統兵書特色,除了強調技能訓練外,還包含練膽和練心的內容;劉長佑的《畿輔練兵營規》涉及直隸練軍的裝備、訓練、陣法、營規,內容頗為豐富。淮軍時期有周盛傳編寫的《操槍程式》,主要介紹槍支的使用與養護之法;丁日昌編譯的《槍炮操法圖說》,主要介紹基本的隊列訓練;潘鼎新編寫的《洋槍隊大操圖說》,則主要講陣法訓練。新軍時期有袁世凱主持編寫的《新建陸軍兵略錄存》,是編練新建陸軍過程中的文件匯編,其中有《臨戰要則》《發槍要則》《操法擇要》等篇,比較具有實用價值。練兵處成立后,陸續頒定了《炮兵暫行操法》《馬兵暫行操法》《步兵暫行操法》《輜重兵暫行操法》《工程兵暫行操法》,使兵種訓練有了可資參考的依據。
四是團練類。如朱孫詒的《團練事宜》、許乃釗的《鄉守輯要合鈔》、李柬的《鄉兵管見》。團練僅是低限度的武裝力量,組織松散,因此,此類兵書的兵學價值多不高。
除以上四類外,還有蔡標的《地營圖(附說)》,專講地營建法;李汝魁的《精神談》,專講軍人的榮譽感與愛國心;劉連城的《將略要論》,專論為將之道;丁日昌編訂的《百將圖傳》,主要介紹古代名將簡要事跡;等等。
(二)散見于奏折、書信等載體中的兵學論述
一般而言,兵書是兵學思想的主要載體,但近代有所不同,除上述兵書能夠部分地反映兵學發展脈絡外,尚有大量以奏折、書信、日記等形式留存于晚清重要人物的文集當中的零星兵學論述。盡管這些軍事論述是散漫的,但有相當一部分是經受過戰爭洗禮后的經驗總結,因此兵學價值較大。如李鴻章與丁日昌的信件中有較多關于海防的討論,其中一些思想成為后來北洋海軍及海防建設的主要思想來源。《海防要覽》是近代有關海防的一部重要兵書,內容其實就是丁日昌、李鴻章在第一次海防大討論時,對總理衙門提出的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項舉措的復議奏稿。李鴻章關于海防的主要思想,主要集中在《籌議海防折》《議購鐵甲艦折》以及其上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信件當中。因此,研究近代兵學,若將這些鮮活的思想略過不計,是不可能真實地反映近代兵學全貌的。
表面上看,這些信件中所保留的兵學思想缺乏關聯性,但因涉及內容相當廣泛,又具有實際上的一致性和系統性。蔡鍔編訂的《曾胡治兵語錄》,將曾國藩、胡林翼的言論分為將材、用人、尚志、誠實、勇毅、嚴明、公明、仁愛、勤勞、和輯、兵機、戰守等12 章,從這一分類大體可以看出,曾國藩、胡林翼兵學思想的內在一致性。
總體而言,這些零星的兵學論述呈現出與一般兵書不同的特點:一是不簡單重復舊說,盡管這些思想仍在傳統兵學框架之下,但對一些舊的錯誤認識卻有所校正和糾偏,且有比較多的創見。如曾國藩說“(兵事)總以質實二字為主”①《復宋夢蘭》,《曾國藩全集·書信》(二),第1641 頁。,左宗棠則說“兵事均須從質實處著想,不必弄巧”②《復史士良》,《左宗棠全集·書信》(一),第500 頁。,這與傳統兵學一般強調的用詐出奇、以巧搏大的基本精神是相對立的。二是這些思想皆來源于實踐,所論不再糾纏于一些概念或范疇的抽象理解,而是著眼于如何化解現實矛盾和解決實際問題,不作空泛之論,因此指導性更強。如左宗棠用兵極看重后路安全,于此相關的論述也很多,講解也頗為透徹,比如“戰陣之事,最忌前突后竭。行軍布陣,壯士利器厚集于后,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無余,設有蹉跌,無復后繼,是乃危道”①《官軍出關宜分起行走并籌糧運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94 頁。。無實戰經歷的文人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三是這些思考始終是發展著的,是有生氣有活力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新的認識和反思,不可能使傳統兵學中的不足充分顯露出來,西方軍事理論亦不可能順利被引入。
(三)有關制度規定
晚清的大量有關章程與規定,雖缺少一般兵書的思辨性,卻是思想的行動化,能比較充分地反映出支撐這些行動背后的思想,因此,其研究價值也不亞于兵書。比如《北洋海軍章程》,被視作北洋海軍建成的標志之一,是除北洋艦隊這一有形成果之外,清廷多年海軍建設的重要制度成果。通過章程,“既能強烈地感受到西方軍事制度的移植,又能清楚地看到中國傳統軍制的繼續沿用”②張一文:《〈北洋海軍章程〉及其軍事學術價值》,《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4 期。。還如《大清光緒新法令》軍政篇,收入了練兵處及陸軍部期間清朝關于軍事教育、營制餉章、校閱、獎懲、兵役等方面的重要法令和規定。再如保留于《東方雜志》中的《新定陸軍軍械章程》《經理修械章程》《經理檢查章程》《正副軍需官及各營軍需長領餉章程》《軍需長職守章程》等,這些是了解晚清軍隊裝備管理保障的重要文獻。
(四)傳統兵書的研究整理與輯錄
近代還有大量傳統兵學典籍輯錄和再整理本,對于傳統兵學經典的重新整理和發掘極具學術價值。如胡林翼召集幕僚汪士鐸、張裕釗等人撰輯的《讀史兵略》,采擷《左傳》《通鑒》的兵事部分,評價戰略得失;汪宗沂輯《汪氏兵學三書》,含《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陣兵法輯略》《衛公兵法輯本》三種;李廷樟重刊清初《武經三書集注》,改稱《武經團鏡》,以為辦團練者提供指導。此外,近代孫子學也有幾部比較重要的著作,如顧福棠的《孫子集解》是晚清第一部以新思路研究《孫子兵法》的專著;黃鞏的《孫子集注》有一些關于東西方兵學結合的思考③參見皮明勇:《中國近代軍事改革》,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00 ~201 頁。。
三、近代兵學的主要特點
兵學在近代,肩負紓困與自救的雙重任務。如果不能與社會現實相適應,不能有效地在解決現實危機中有所建樹,兵學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兵學在近代的改造主要是兩種方式:一是援實入兵,如同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所為,去除傳統兵學中的浮泛、虛飾之氣,將更具實際指導意義的思想充實到兵學體系中;一是援西入兵,即吸收西方軍事理論中有價值的成分,補足傳統兵學體系中的不足與缺項。在兵學發展史上,近代兵學的發展變化最為劇烈,其特點也最為顯著,主要有:
(一)文人論兵的式微
當國難當頭、內外交困之時,文人也想通過自己的積極行動,促使戰爭局面朝有利的方向發展,這是文人言兵原始的出發點。近代無實戰經驗的文人的兵學著作或論述,數量不少,但內容多較空洞,或論為將之道,或論人心決定勝負。也有談及海防和練兵的,但亦多不著邊際,為紙上談兵之論,嚴重脫離社會和戰場實際。所以盡管近代文人論兵者大有人在,但所論的軍事學價值越來越小,對于決策產生的影響則越來越弱。盛軍統領周盛傳在批評舉人廖連城所上的海防策圖時所說的一段話,頗能看出文人在討論軍事問題時如何隔膜。他說:“(該舉人)當海疆多事之秋,講求時務,自屬有心之士,但必須于海道廣狹、器械利鈍、經費盈絀考證精確,立言乃有折衷,若徒襲載籍陳言,妄相稱說,烏能見諸行事,惟鑒察焉。”④《周武壯公遺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56 頁。
在戰爭的大背景下,需要的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具體辦法,而非大而無當的空泛指導。左宗棠批評一名地方官調撥客軍的言論時說:“不思派撥客軍極非易事,無論機宜方略一一須有成算,即徑由之道路、運解之子藥軍糧均須預為籌策,乃保萬全,殊不易易也。該守于所屬道里山川形勢、賊蹤出沒之所,及采辦軍糧、雇用車馱一切辦法,漫無區畫,徒知上稟請兵,不知平日于地方情形,臨時于軍務情形亦曾留心否?”①《同州府延守愷稟賊竄郃陽一帶請兵防剿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9 頁。無實戰經歷的文人往往主觀地認為戰略運籌與實戰有較少的相關度,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坐而論道是文人論兵最致命的弱點。
(二)兵學逐步趨向專業化
湘軍時期,文人統兵的現象頗為普遍,一方面說明文人參與兵事的熱情很高,但另一方面也說明,軍事領域的專業化程度很低,領兵打仗不需要經過特別的訓練即可參與。淮軍以后,隨著裝備日益復雜,沒有專業化的知識,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日常管理和指揮。丁日昌在解釋水師提督李朝斌、彭楚漢為什么不能出任海軍統領時說:“該提督等平日所習之長龍、舢板,與外海之兵輪船絕不相蒙,外海波濤洶涌,旦夕萬狀,飛輪、硼炮變化無窮,非自幼衽席其間,熟諳其法,斷未有不改常度者。”②《遵議督操輪船事宜疏》,《丁日昌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4 頁。而要培養合格的領導者,必須依靠專業化的軍事學堂,“將才非累年培養不能有成,故現用之將才雖經選揀,而待用之將才亦宜預儲,必學堂精延教習,庶赴練船學習者有基;必練船勤加操演,庶出洋學習者有基”③《遵議督操輪船事宜疏》,《丁日昌集》上,第184 頁。。
李鴻章在《水師學堂請獎折》中列舉了學堂的主要課程,“欲其于泰西書志能知尋繹,于是授以英國語言翻譯文法;欲其于凡諸算學洞見源流,于是授以幾何、代數、平弧、三角、八線;欲其于輪機炮火備諳理法,于是授以級數、重學;欲其于大洋駕舟測日候星、積算晷刻以知方向道里,于是授以天文推步、地輿測量,其于駕駛諸學庶乎明體達用矣”④《水師學堂請獎折》,《李鴻章全集》第10 卷,第649 頁。。近代兵學的專業區分日趨明顯,可以說不具備專業知識,很難提出有針對性的、可行性的建議。
(三)兵學闡釋方式由虛向實
中國傳統兵學呈現出高度概括抽象、文字凝煉且意涵極豐的特點。這種闡述方式利于啟發思維,但從指導實踐的角度看,抽象的兵學思想要實現其指導實踐的價值,必須經過幾重改造,才能具有清晰和明確的指向性。《中西兵略指掌》的編者陳龍昌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談兵家者無慮百數,惟《孫子》十三篇,戚氏《紀效新書》至今通行,稱為切實。但孫子論多玄空微妙,非上智不能領取,戚書出自前明,雖曾文正公嘗為推許,其可采者,要不過操練遺意。”⑤陳龍昌:《中西兵略指掌》卷20,清光緒二十八年秦中官書石印本,第20 頁。
近代是中國兵學發展史上的特殊時期,與前代無實戰經歷的人撰述兵書不同,有過戰場經驗的人更傾向于從質實的角度理解戰爭,不做過分形而上的分析或想象。以奇正為例,近代更側重將主客的指代關系具體化,將過于靈活、難于把握的觀念,進行降格處理,使其指向軍事實踐中的某一種特定形態,明確規定何為奇、何為正。曾國藩在《兵》篇中詳細區分了不同情況下何為正兵、何為奇兵,“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游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御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于用兵之道思過半矣”⑥《兵》,《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兵麓書社,1986年,第385 頁。。
與曾國藩的兵學思想相比,左宗棠的兵學認識,現實指導性更強。比如,對于軍心士氣,曾、胡都有過這樣的論述,“夫兵,陰事也,以收斂固嗇為主;戰,勇氣也,以節宣提唱為要”⑦《復多隆阿》,《胡林翼集》第2 卷,第566 頁。,但左宗棠則更多的是將士氣高低與軍餉保障得力與否掛接起來,“進兵必先固后路,務令卻顧無虞,然后一意前驅,餉道常通,軍情益奮”①《與金和甫》,《左宗棠全集·書信》(三),第100 頁。,即糧餉無憂,軍心自然穩固。傳統兵學歷來強調先勝,即《孫子兵法》所講的“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這一說法很有啟發性,但籌劃到什么樣的程度是為先勝,卻是極難判斷的。左宗棠對此有不同的認識,他說:“兵事變動不居,隔一日、兩日之程,便與千里無異。若預為之制,曰賊如何、我如何,是教玉人琢玉,未免徒勞,且機宜亦必多不協。前周制軍天爵章奏中有曰‘我以速戰法,賊不如法而來’,至今傳為笑柄。元戎之職,在明賞罰、別功罪、一號令。其于戰陣之事,籌大局而已。若節節籌度,則明有所蔽,而機勢反滯礙而不靈。”②《答曾節相》,《左宗棠全集·書信》(一),第457 頁。因此,左宗棠對待戰爭的態度是慎以終始,“兵事利鈍非所逆料,然慎以終始,其要無咎”③《復陳布置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445 頁。。
曾、胡、左的兵學思想,很多是對傳統兵學的重新認識和重新解讀,是將已經嚴重脫離戰爭實際的抽象觀念,放回到戰場這個一切戰爭理論的最真實的檢驗場,并在軍事實踐中,發現傳統兵學缺失的成分。盡管這種探索仍然有限,但已經讓傳統軍事思維從虛空中重新落地,重新回歸兵學思想應有的本來面目。
越到晚清后期,泛論式的著述越少。徐建寅在闡述其撰述動機時指出:“泰西各國講求兵學,久有成法,愈新而器械愈利,兵學愈精。……中國士子,素未講求此學。古來兵書,半多空談,不切實用。戚氏《紀效新書》,雖稍述實事,而語焉不詳,難以取法。”④徐建寅:《兵學新書·凡例》,清光緒二十四年本,第1 頁。又說:“世俗迂儒,一誤再誤,諱講兵學,是以二千年來無人以兵學泐為成書者。即有古兵書,亦皆模糊影響,罔切實用。”⑤徐建寅:《兵學新書·后序》,清光緒二十四年本,第3 頁。這樣的說法雖有失偏頗,但基本反映了近代兵學家不迷戀往古、開創新學之風,并主張撰著對現實有“補救之方”的兵學著述傾向。
兵學歸根究底是要用于指導戰爭,面向戰場的。離開了這個根本點,兵學的意義就是失位的,若兵學僅有學術上的意義,而失卻其指導軍事現實的意義,兵學的發展就不可能是昂揚向上的,而只能是步步淪落。兵學的發展只有回歸戰爭這片土壤,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生根發芽。
四、結語
文化上的演進,并不總是遵循生物學上的由萌生到興盛,再到衰朽這樣一個過程。對于近代兵學而言,更像是由中心退隱的過程,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沖擊和西方軍事理論的光芒映照下,傳統兵學日益暗淡和無力,逐漸由中心退到邊緣,而西方軍事理論則逐步占據了中心位置。但傳統兵學的價值仍在,它已內化為一種特殊的軍事思維,仍然在指引著后世軍事家看待軍事問題的方式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