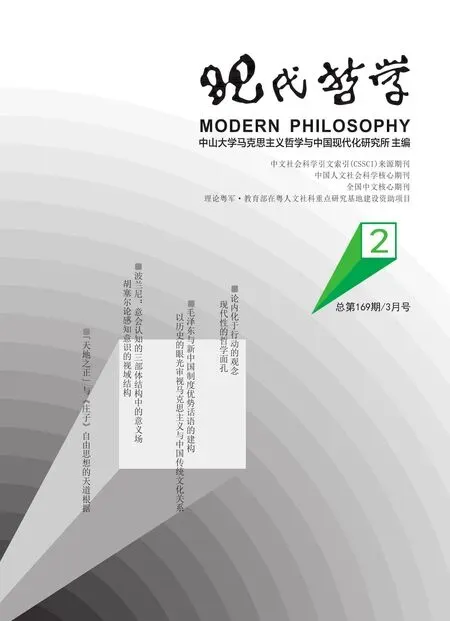論內化于行動的觀念
魯克儉
不同于思想史,觀念史涉及的是有別于思想的觀念概念。那么,什么是觀念?觀念與意識、思想有何異同?高瑞泉(1)高瑞泉:《觀念史何為?》,《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對此已經作過辨析。本文進一步就此作一探討。
一、觀念與思想和意識的區別
思想(2)思想可以是普通個體的thought(思想),也可以是學者的intellectual[學術或智識的(思想)]。思想史的英文是history of thought,而學術思想史是intellectual history,觀念史是history of ideas。可以說是作為結果的意識,就像馬克思所說“死勞動”那樣的死意識;而意識是當下的、活生生的心理現象,即活意識。觀念與意識都是活意識,它們的區別在于:意識是認識論(知識論)視角下的心理現象,而觀念是非認識論(知識論)視角下內化于行動的意識。簡言之,觀念是內化于行動的意識,是先于主客二分的實踐(3)參見魯克儉:《超越傳統主客二分——對馬克思實踐概念的新解讀》,《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行動主義)視角下的意識。
所謂認識論視角,就是非時間性的上帝視角。貝克萊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以上帝視角來看待外界事物的典型案例(4)貝克萊著名的“存在就是被感知”通常被看作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代表,但它并不意味著相對主義(休謨的經驗主義可以說是相對主義)。在貝克萊那里,盡管存在不是物質,卻具有和上帝一樣的客觀性。只有上帝視角的感知才能與存在劃等號,因此,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認識論上帝視角的典型例子,也可以說是主觀唯心主義與客觀唯心主義的混合物。。實際上,傳統認識論一直蘊含著上帝視角這一前提。在這一前提下,個體的意識自動成為類意識,而類意識也自動成為個體意識。換句話說,意識都是自我意識(個體的自我意識=普遍的自我意識),我的意識與他者的意識并沒有區別。認識論視角下的意識追求真理,總是存在意識與意識對象的關系問題。當代科學認識論雖強調“觀察滲透理論”,但針對的是洛克式的“白板”認識論,并不強調不同的認識主體由于“理論先見”的差異而對認識結果所產生的影響。換句話說,在當代科學認識論這里,“理論先見”并無個體的差異,科學實驗必須有可重復性。而觀念從根本上說是私人的,它關乎生活,本質上與真理無關,而與行動有關。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問題不在于解釋世界,而在于改變世界。
休謨的觀念與胡塞爾的觀念屬于非認識論視角的意識。休謨區分了觀念與印象,把觀念看作是復現的印象,又將印象分為原印象和反省印象。原印象是認識論視角的意識,而觀念和反省印象屬于非認識論視角的意識(5)休謨的觀念和反省印象是否非認識論的意識,可能存在爭議,因為休謨在觀念論中重點考察的因果性問題,似乎屬于典型的認識論問題。但回憶具有私人性,想象(不考慮因果關系)也更多與私人體驗有關。實際上,我們在胡塞爾的意識分析中,確實可以看到大量休謨理論的影子。。胡塞爾的觀念與休謨的觀念和反省印象很接近,不同在于,胡塞爾把原印象(原感知)也看作是非認識論視角的意識。
但我們的觀念與休謨和胡塞爾有一點根本的不同:休謨和胡塞爾的觀念都是靜觀的產物(盡管胡塞爾的靜觀具有意向性結構),而我們的觀念總伴隨著個體的活動。靜觀的直觀和活動中的直觀有根本區別。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對靜觀的唯物主義的批評,同樣適用于休謨和胡塞爾。活動一旦停止,一旦轉為反思(休謨的回憶和想象,以及胡塞爾具有意向性結構的構造),觀念就成為思想。這里所謂的活動并非指思維活動,而是人的現實的感性活動。觀念的主體(承擔者)是行動者(actor),而非思想者(沉思者)。我關于民主的思想(或理論)不等于我的民主觀念。我的民主觀念一定內化于我的行動中,成為我下意識的行動。
可以說,康德第一個明確將認識論視角與非認識論視角做了區分(6)休謨在《人性論》中試圖用一套理論整合認識論和情感論,因此,他沒有明確區分認識論視角和非認識論視角的意識。,即明確區分了實踐理性、審美理性(判斷力)與知性理性。這就是康德的著名“劃界”,但它并沒有改變“上帝視角”,即個體視角與類視角的同一。黑格爾繼承了康德的“劃界”,進一步將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區別稱為理論態度和實踐態度的區別。而且按照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精神哲學》的思路,實踐態度意味著自我意識的外化,即由主觀精神異化為客觀精神。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個體與類是相互影響和相互生成的關系,而不是像康德理論里的個體與類可以自動等同。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批判的,黑格爾的這種異化(對象化)運動只不過是思維內部的運動(勞動),與個體感性的對象性活動無關。而我們和馬克思一樣,強調的是個體現實的感性的活動及活動中如影隨形的觀念。
觀念內化于活動中,用休謨的話說,意味著活動與觀念有恒常的結合。因此,相應的活動會產生相應的觀念,相應的觀念也會有產生相應行動的傾向。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下意識。唯物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存在指的就是生活(活動)。生活包括個體生活和類(社會)生活。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7)馬克思經常用“觀念的東西”(das Ideelle)的說法。這里“觀念的東西”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3頁的譯法,后來的中譯文改為“各種觀念形態”。。把社會存在理解為物,包括物化形態的生產資料或經濟基礎,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極大誤解。
強調個體活動與觀念的關系,是20世紀以來哲學的新趨勢。皮亞杰和維果斯基都是觀念內化論者,盡管在社會關系的作用問題上二者存在分歧。維特根斯坦晚期哲學的游戲理論、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秩序理論(試錯理論)、胡塞爾生活世界理論及海德格爾的此在“在世界中”理論,都強調活動與觀念的不可分離。俞吾金把馬克思的哲學解讀成“實踐詮釋學”(8)參見俞吾金:《實踐詮釋學——對馬克思哲學與一般哲學理論的重新解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強調“從人的物質實踐活動出發去理解和解釋人的觀念”,“決不可能存在與人們的物質實踐活動相分離的、獨立的觀念”,實質上也是強調活動與觀念的統一。
二、觀念的六種用法
通過考察我們發現,以下六種含義的觀念經常在日常語言和哲學思考中被使用。
(一)作為常識理性(9)關于常識理性,參見魯克儉:《世俗化·大小傳統·常識理性》,《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的觀念
ideology字面意思是觀念學,也就是關于idea(觀念)的體系,即思想體系(意識形態)。它是法國思想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首創,馬克思將其改造成德文詞Ideologie。如果從現象學的懸置精神出發,不僅馬克思所說的人文社會科學,就連自然科學也屬于需要懸置的意識形態。“面向實事本身”也就是要去掉“-logy”,回到“觀念”。去掉“-logy”之后的觀念,首先是個體的觀念。觀念首先是私人性的。我在活動中自己眼睛看到的,才是“實事本身”(我的印象);我在活動中自己直觀到的普遍物(本質直觀),才是“真理”。我在活動中有我自己獨特的“視閾”,有不同于你的“先見”。當然,我的“先見”可能已經被意識形態所污染,因此我的觀念并非真正“純粹”,但這畢竟是我自己的“先見”。這時,個體的觀念就體現為常識理性。
作為常識理性的觀念是從意識形態理論到我的觀念的“還原”。我的看是行動中的看,而不是靜觀(沉思)。我的觀念直觀也是行動中的觀念直觀,而非科學認識。休謨將觀念還原到原印象,胡塞爾將觀念還原到原體驗,邏輯經驗主義將邏輯命題還原為原子事實,都是試圖尋求笛卡爾式原初奠基性的“自明性”。不過,在休謨和胡塞爾那里,原初自明性不能保證后續觀念不失真,因為直觀是可靠的,思維就可能不可靠了。但邏輯經驗主義基于真值表,可以由原子事實的真推出邏輯命題的真。我們所說的“還原”是指還原到我的內化于行動的觀念。觀念可以是簡單的,也可以是復合的,關鍵是“我”的。訴諸我的常識理性,也就是聽取我自己內心的聲音。
(二)作為社會意識的觀念
共同活動是交往的重要形式,首先體現為生產活動中的共同活動。在共同活動之外,交往還體現為經濟交往(交換)、社會交往(日常生活的交往)、政治交往(包括戰爭)等。在交往行動中,我的“觀念”與你的“觀念”會有沖突和碰撞,當然也會產生共識。成為共識的觀念可能會被傳播(主動傳播即教化,被動傳播即流行),從而成為大眾觀念(社會意識)。大眾觀念可以上升為思想體系(意識形態),也可以下降(接地氣)成為集體無意識(“心理積淀”為文化)。我可能會接受或拒絕大眾觀念。被接受的大眾觀念會轉化為我行動中新的“先見”。
伽達默爾將海德格爾關于領會(在世界中籌劃的領會)的解釋學循環發展成哲學解釋學,而海德格爾“在世界中”籌劃的領會更接近于所謂的個體行動中的觀念。領會以對前理解結構的先行把握即“先見”為前提,從而會有解釋學循環,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個體觀念與大眾觀念的雙向互動。
個體間觀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現象(主體際性)存在的原因,不僅在于交往(當然交往是前提),還在于既有的公共性,因為現實的交往不可能是魯濱遜式原子個體之間的交往(馬克思多次批評這種魯濱遜式社會虛構)。這種公共性包括共同的文化背景(包括習俗、思維方式等)、共同的世界(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共同的語言以及近代科學知識的普及等,這些因素構成個體“先見”的基本內容。而原創性的個體觀念也對這種公共性有貢獻(在程度上有個體的差異),二者是相互影響、相互生成的關系。
不同于個體觀念,大眾觀念也可稱為社會觀念。所謂“文明的沖突”是社會觀念沖突的一種形式。在社會轉型期,社會觀念沖突和斗爭非常激烈。另一方面,個體觀念與社會觀念的雙向互動,使得個體觀念可以成為社會觀念的全息單元觀念。因此,個體可以通過內省的方式(類似胡塞爾的先驗還原)把握到時代的脈搏。藝術家(特別是詩人、小說家等)的創作常常就是這樣。行動中的個體觀念是常識理性,既是社會觀念的基礎和原動力,也是意識形態的源頭。當然,藝術家也可以在民間“采風”,這就是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強調的“民間文學”。人民生活特別是勞動生產中的鮮活觀念(包括原生態藝術創造),是一切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的源頭活水。
(三)作為默會知識的觀念
內化于行動中的觀念常常體現為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所謂的“默會知識”(即“個人知識”)。默會知識更多與技藝有關,特別是技術“竅門”。在行動中,一個觀念到一個新觀念的躍遷依靠的是“干中學”(模仿),而非反思。休謨和胡塞爾都強調反思(包括記憶、想象等),這種反思也可能是非理性、非邏輯的,從而具有默會知識的特征,但反思獲得的知識不是從干中學到的,因此不會內化為人的肌肉記憶。作為觀念的默會知識,已經轉化為個體的能力。顯然,默會知識與純主觀的意識已經有很大差別,它已經有非大腦的物質即人的肉體作為載體。
默會知識是觀念映象,盡管不能邏輯地言說,但可以在頭腦中以映象形式體現出來。就像休謨強調基于觀念的反省印象,默會知識作為觀念映象具有活潑性、生動性的特點,伴隨著人的情感。休謨的反省印象主要是情感、情緒,這與作為默會知識的觀念有所不同。但休謨基于觀念的反省印象說法,是富有啟發性的。默會知識不同于可言說的邏輯化知識,后者超脫了個人,是沒有情感色彩的普遍知識,更多與反思性思維有關。
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以及維果斯基的人類心理社會起源學說,所探討的兒童心理發育很大程度上與個體活動有關。皮亞杰認為,心理起源既不是先天的成熟,也不是后天的經驗,而是動作,即動作是認識的源泉,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中介。這就是皮亞杰的活動中介論。維果斯基特別強調在人的發展過程中社會文化歷史的作用,尤其強調活動和社會交往在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認為,高級的心理機能來源于外部動作的內化,這種內化不僅通過教學,也通過日常生活、游戲和勞動等來實現。而且,內在的智力動作也外化為實際動作,使主觀見之于客觀。內化和外化的橋梁便是人的活動。顯然,皮亞杰和維果斯基所說的心理發展都涉及默會知識,并不僅僅是邏輯思維。
(四)作為人的活動形式的“觀念的東西”(10)蘇聯哲學家伊利延科夫特別強調馬克思的“觀念的東西”思想。他撰寫了蘇聯《哲學百科全書》第二卷“觀念東西”詞條,參見《蘇聯哲學資料選輯》第1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5—279頁。
人的活動特別是生產活動(勞動實踐),就是將自然界的質料賦予形式即塑形的過程。在黑格爾看來,塑形是自由意志的現實化。如果撇開黑格爾的主客二分思維,即以自由意志為邏輯起點的否定之否定邏輯,人的生產活動就是形式從現實到觀念和從觀念到現實的雙向互動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的過程,是合目的性活動。不管最初的目的多么粗糙、簡單,被欲望和沖動驅使的意志總要轉化成人的行動,從而在滿足最初生理需要的勞動中,使質料原有的形式得到改變,變成合目的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在反復勞動操作中,逐漸在人的頭腦中固化,成為人的活動形式即觀念的東西(觀念化)。
盡管不以自由意志為邏輯起點,個體在勞動中仍會通過不斷試錯而給勞動對象賦予新的形式,進而成為人的活動形式。正如哈耶克所強調的,秩序不是理性建構的結果,而是自生自發的產物。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人的活動“形式”的演變。自由意志追求“形式”的完美理性建構(先驗形式(11)康德無疑是這種理性建構主義的代表。不過,康德強調圖型作為連接先驗范疇與現象的中介,很有啟發意義。我們所說的形式就類似于康德的圖型。當然,我們不同意康德關于圖型先驗性的說法。),而“干中學”的試錯則突出人的活動本身。
隨著人的歷史的發展,由意志(指伴隨欲望和沖動的意志,而非自由意志)發端的新形式越來越成為人的活動形式的先導因素,類似于我們常說的“胸有成竹”。馬克思說“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特別強調“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并把這作為人與動物(比如蜜蜂)相區別的重要方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
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第96—97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說:
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
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做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第202頁。
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價值形式”的思想,就是一個“觀念的東西”(15)巴克豪斯稱之為“客觀的思維形式”(Objektive Gedankenform),馬克思自己就有這種提法。作為人的活動形式的典型例子。假定在人的經濟交往活動中,某一物(如貝殼)充當了一般等價物。人們接受貝殼作為交換的媒介,就在頭腦中產生一般等價物的觀念。在經濟學家頭腦中,可能只有貨幣的概念,抽象掉了貝殼的形象。但在現實活動的人頭腦中,呈現的是具有一般等價物職能的貝殼形象(觀念)。“觀念的東西”類似于康德的圖型,康德稱之為先驗直觀。馬克思說:
如果有人想象自己有一百個塔勒,如果這個表象對他來說不是任意的、主觀的,如果他相信這個表象,那么對他來說這一百個想象出來的塔勒就與一百個現實的塔勒具有同等價值。譬如,他就會根據他的想象去借債,這個想象就會起這樣的作用,正像整個人類曾經欠他們的神的債一樣……難道一個現實的塔勒除了存在于人們的表象中,哪怕是人們的普遍的或者無寧說是共同的表象中之外,還存在于別的什么地方嗎?(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頁。
馬克思對照康德說:
一百個真正的塔勒里包含的東西絲毫也不比一百個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東西多。確實,因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著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著物體及其假設本身,那么如果物體所包含的東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會表示整個物體,因而也就不會和物體相等。可是,當我有一百個真正的塔勒時,我的財產就比我光有一個它們的概念(即可能有的塔勒)時多。確實,在實際情況中物體不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且也被綜合地加到我的概念(它是我的財產的規定)中,而一點也沒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這一存在去增加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17)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7頁尾注35。
在馬克思看來,概念與觀念(馬克思此處用的是“表象”)是不同的。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學原理》中也曾把財產劃分為物理占有、觀念占有兩個階段。馬克思此處關于塔勒觀念(“一百個想象出來的塔勒”)的說法,應該說與康德的“觀念占有”是一致的。
不管是一般等價物由貝殼充當,還是由金銀、紙幣甚至虛擬貨幣充當,現實活動(特別是經濟交往活動)中的個體,不會做關于貨幣的沉思冥想,不會像經濟學家那樣在頭腦中呈現抽象的貨幣概念。個體面對感性的物(即使是手機中的電子記賬),呈現在頭腦中的是與現實活動相關的一定量的貨幣觀念。即使是對財產的“觀念”占有,也必須有契約或憑證(國家相關部門頒發的證書)作為個體面對(擁有)的感性存在物。貨幣也是如此。這類似于胡塞爾對“紅”的本質直觀。但胡塞爾的本質直觀就像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費爾巴哈的高級哲學直觀一樣,是非歷史的靜態直觀。而現實活動中個體的貨幣觀念,是個體在現實活動中習得并固化到頭腦中的客觀思維形式,是現實的個體活動中面對感性世界而在頭腦中呈現出來的觀念。不但如此,客觀思維形式并非認識論抽象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一般抽象勞動的歷史生成),是抽象辯證法(18)關于抽象辯證法,參見魯克儉:《抽象辯證法:唯物主義實在論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9年第1期。的結果。
(五)作為賦予意義和價值評價的觀念
個體會對活動中“上手”的具體物形成觀念(賦予意義)。休謨區分了印象與觀念,還專門指出洛克是把所有的知覺(包括印象和觀念)都看作是觀念。休謨之所以這樣做,是基于印象沒有個體差異,而觀念(涉及回憶、想象)具有個體差異。胡塞爾進一步將休謨所謂的“印象”個體差異化(這涉及胡塞爾的內時間意識理論),徹底破除了印象的上帝視角,從而使對物的“看”變成對物賦予“意義”(立義)。
在現實活動中,不同個體、同一個體在不同時間面對同樣的事物會產生不同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物是人非”。胡塞爾的“視閾”或伽達默爾的“先見”,都是意義形成的關鍵因素。對個體來說,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生活活動中的認識其實不是認識論(知識論)意義上的認識(即無差別的人類認識),而是個性化意義的不斷生成(賦予意義)。這不是純客觀的意識,而是帶有情感色彩的意義(觀念)。
在現實活動中,個體不但對單個事物賦予意義,而且因為個體活動本身就意味著在“在世界中”(海德格爾語),因此個體會對所在的周圍世界賦予意義。由于“視閾”或“先見”的個體差異,個體所在的世界也處于不斷變化之中。這就像攝像鏡頭在前后左右移動以及遠近變焦,面對同樣的事物和環境,不同攝影師會呈現出不同畫面。再次不同于胡塞爾,我們所說的賦予意義是在個體活動中生成的,而非在個體沉思中構造出來的。
個體還會對活動(特別是生產活動)的對象賦予價值(價值評價),包括效用評價、道德評價、審美評價等。價值評價具有私人性(多元性),與人的現實活動密切相關。
觀念雖然是私人的心理體驗,但不能像胡塞爾那樣把觀念看作是純粹私人的體驗流。類似于個體行動中外物在頭腦中“形式化”,個體在行動中賦予意義和價值評價的觀念也會形成相對穩定的、結構化的心理體驗,即所謂的“-觀”。比如,“睹物思情”這種心理體驗就具有可重復性。其中的物可以置換,盡管不同的物勾連起的畫面有所不同,但情緒(懷舊觀念)卻有相似之處。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強調“單元觀念”(unit-idea)是有道理的,其觀念史代表作《存在巨鏈》(19)[美]洛夫喬伊:《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張傳友、高秉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就是以存在觀念為研究主題。“-觀”是個體行動中“先見”的重要內容。
當然,作為個體觀念的“-觀”有別于理論化(即作為意識形態)的“-觀”,體現的是個體的常識理性。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思想被尊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特別是其道德說教,與普通百姓有不小距離,可以說很不接地氣。這在宋明理學那里達到極端。而民間流傳的價值觀念,體現在雜糅了各種思潮的《增廣賢文》。《增廣賢文》成書于明代,經過明、清兩代文人的不斷增補,可以說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是常識理性對意識形態的一次反撥。儒家思想不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的全部,而諸子百家的思想也只是學術思想,不等于個體行動中的觀念。當然,“諸子百家”特別是儒釋道都有虔誠的信奉者,思想也可以轉化為個體行動的觀念。但只有內化于行動中的思想,才是觀念。這時,觀念與思想的區別體現為常識理性與意識形態的區別。
(六)作為“思想具體”的觀念
思想具體屬于形象思維,而且伴有畫面感。有些形象思維無法言說(指邏輯地、概念式言說),但思想具體可以言說。中國傳統的形象思維大都屬于不可言說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感性實在(具體)到思維具體有過著名的辯證論述:
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43頁。
在馬克思看來,感性實在才是主體,并批判黑格爾把概念看作主體。比如,現實的社會(而非社會概念)是主體。以對社會實在整體的把握為例。現實的社會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即表現為關于社會的直觀和表象。頭腦以思維方式把握現實社會(社會實在)的過程,首先是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形成不同側面的諸規定性,比如關于勞動的一般抽象規定,以及資本、雇傭勞動、地產、國家、國際貿易、世界市場等關于社會內部結構的規定。這是對社會實在整體進行分析的過程,是從具體到抽象的知性思維過程,也是諸概念被加工出來的過程。然后,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就是將已獲得的孤立、碎片化的諸知性規定重新組裝起來。這是思維中的綜合過程,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其產物就是關于社會的思維具體(思維整體),也就是社會觀念。
馬克思關于思想具體的辯證法來自黑格爾,不過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做了頭足倒置(21)馬克思說:“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黑格爾在《小邏輯》中說:“我們以為構成我們表象內容的那些對象首先存在,然后我們主觀的活動方隨之而起,通過前面所提及的抽象手續,并概括各種對象的共同之點而形成概念,——這種想法是顛倒了的。反之,寧可說概念才是真正的在先的。”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批判,顯然是針對這段話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頁;[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34頁。)。思想具體是“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思想具體并不是解釋世界的方式,而是把握世界的方式。馬克思原文用的是“aneignen”,意即“占有”。因此,不能僅僅在認識論上解讀馬克思的“思想具體”。“思想具體”的形成過程(包括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是認識的結果,但已獲得的“思想具體”體現在個體的活動中,成為人的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22)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過“這個階級的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一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表現”的說法。馬克思應該是不加區別地使用“實踐-精神的”(praktisch-geistigen)和“實踐的觀念的”(praktisch-idealistischen)。(《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頁。)掌握(占有)方式。
這句話該如何理解?馬克思沒有展開論述。不過,可以從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關于知覺的理論中得到啟示。在《精神現象學》第一章“感性確定性”之后,緊接著就是第二章“知覺”。黑格爾關于知覺的論述和《小邏輯》第三篇概念論的“主觀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知覺面對的是感性個體,主觀概念討論的是個體概念。感性個體是具體,不過是表象的具體。感性個體首先是“這一個”,對應于概念的普遍性。從概念的普遍性到概念的特殊性(諸規定),對應于知覺的過程(物的多種屬性)。從概念的特殊性到個別性(單一性),對應于“屬性合并為單一體”(以“并且”聯結)。當然,知覺中對物(單一體)是領會式把握,而概念中對個體概念是概念式把握。思想具體就是對個體概念的概念式把握,這是對內容的本質直觀(有別于上述對形式的本質直觀)。從知覺(感性直觀)到思想具體(本質直觀)的飛躍并不神秘,因為物的屬性和概念的規定性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知性普遍性)。特別是在人的現實活動中,領會式把握是非概念的形象思維,而思想具體就是概念式把握的形象思維。這兩種形象思維在人的現實活動中各有其地位和作用。當然,對不同的個體來說,非概念的形象思維和概念式把握的形象思維所占比重會有個體差異。因此,作為觀念的思想具體是人在現實活動中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