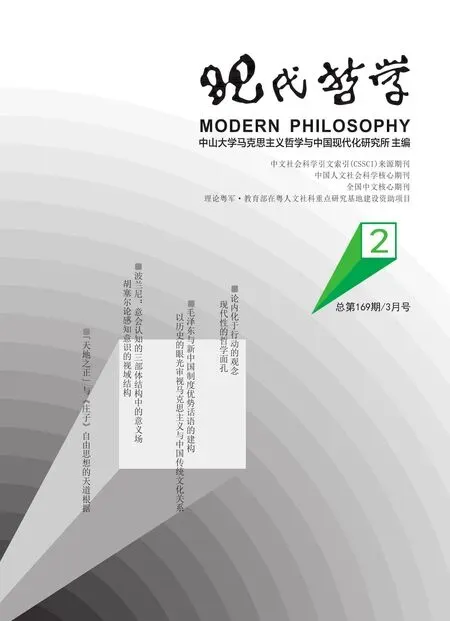五四后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實踐路徑、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
曾 榮 劉演杭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話語構建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話題。尤其是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接受、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基于掌握革命話語權的現實需要,通過話語方式的創新、話語內涵的擴展和話語能力的提升,逐步構建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既往研究多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樣一種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方法,當成眾所周知、不言而喻的理念,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一進入中國,就開啟了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時,關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問題,持不同政見者或同一政黨的不同派系之間,往往因其主張和目的之不同,表現出不同話語環境下話語內涵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一、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實踐路徑
五四運動前后,隨著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各類主義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社會大眾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尤其是知識界人士,展開了一場以學理對話為形式、以政治論爭為特征的“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8月17日,“主義派”代表人物李大釗向“問題派”扛大旗者胡適致函,旨在闡明“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質。在信函中,李大釗結合五四運動以來社會思想的變動情況,指出“適應實際”的特性是“主義的本性”,強調人們在運用“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際的運動”時,必須“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1)《李大釗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頁。。就此而言,“主義派”與“問題派”之間應是不相矛盾的,甚至是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而之所以存在爭議,或源于雙方對話語產生的具體環境理解上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與胡適為代表的“問題派”進行公開論戰時,李大釗對話語生成的具體環境頗為重視。1919年底,他在《新青年》刊發《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代表性文章,該文深入分析了中國革命形成與發展的內外環境,指出“一個學說的成立,與其時代環境,有莫大的關系”。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即革命時代的特殊環境造就了馬克思主義學說,而這種革命時代環境下形成的學說無疑具有特殊的性質以及特定的適用范圍和條件。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環境變遷,我們“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為此,李大釗勸告“問題與主義”論戰的對方,“我們批評或采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2)《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6頁。。
正是基于中國革命的時代背景、現實需要、環境特點的考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政治歧見,逐漸演化成一場學理對話。隨著五四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現實問題對接的客觀需要日益迫切,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歷史進程亦不斷深化。1920年,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參加過五四運動的革命者從北京來到廣州。他們集資創辦《廣東群報》,將其作為馬克思主義話語表達的重要載體,借以指導和推動廣東地區的革命運動。是年12月,陳獨秀受邀赴廣州,旨在創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推動馬克思主義在廣東的傳播。來粵后,鑒于當時“許多青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的革命現狀,陳獨秀以探索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為導向,呼吁各界人士“討論社會問題,要以實際問題為限;若是離開了實際問題,專門發空議論,就是天天談政治,天天鼓吹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也無人來干涉你”(3)《討論社會實際問題底引言(1921年2月12日)》,《廣東群報》1921年2月12日。。在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闡釋時,陳獨秀進一步將其演繹為“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兩大精神,借以鼓舞中國青年志士既“能以馬克思實際研究的精神研究社會上各種情況”,又能發揚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他強調“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兩大精神“都是中國人所最缺乏的”,但兩者相比較,后者更為重要(4)《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3、454頁。。換言之,廣大青年志士要以實際行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具體運用于中國革命。他甚至提出,我們“寧可以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干馬克思革命的運動!”(5)《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9、250頁。顯然,在他看來,將馬克思“實際研究”和“實際活動”精神轉化為中國革命的實際行動,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迫切需要與尚佳途徑。
與陳獨秀將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問題納入“革命行動”范疇不同,鄧中夏以營造革命良好氛圍為旨歸,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但是,“革命”話語的構建離不開寬松的政治土壤,理論的宣傳也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然而,在五四運動的起源地北京,因北洋政府的輿論管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受到嚴重限制。對此,鄧中夏指出,“北京是公認的所謂政治中心”,但“在茶館或是飯館里,常常碰到‘莫談國事’的告示。這種對國家政治問題的一切談論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對下層階級設置的社會監督”(6)《鄧中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1頁。。為營造中國革命的良好氛圍,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鄧中夏等人在北京發起并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廣泛搜集和整理了德、英、法、日、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舉辦一系列討論會、講演會、宣傳會等,深入研討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具體問題,并編譯和刊印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這種通過宣傳馬克思主義,激起“工人和貧民階級對政治感興趣”及“喚起群眾對政治事件的興趣”,借以“促使群眾從事革命工作”,從而營造中國革命的良好環境(7)《鄧中夏全集》,第121、122頁。的做法,其話語環境建構的方式與路徑雖與陳獨秀存在差異,但就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而言,二者可謂殊途同歸,他們均以實行(或從事)革命為旨歸,深入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方法,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而對于身在法國、正潛心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蔡和森而言,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應當有另一種闡釋,即用于指導成立革命的政黨——中國共產黨。1920年7月,蔡和森向從法國各地聚集到蒙達尼的新民學會會員提出“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方針。會后,蔡和森分別于8、9月向在國內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毛澤東致信,信函的核心要義就是組建中國共產黨。他強調:“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8)《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頁。值得一提的是,對于蔡和森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建黨的提議,毛澤東曾回信表示“深切的贊同”,并指出此舉將有助于推動中國“革命運動”,有助于“改造中國與世界”,因此“是贊成馬克思的方法的”(9)《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1917.11-1923.7)》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51頁。。
可以說,五四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基于對革命形勢、背景與基本條件的整體認知,在考察主義如何運用問題時,往往將具體的、客觀的實際情況作為重要因子,使諸如中國革命的時代背景、現實需要、環境特點等成為時人言說的重要基礎,彰顯了深入結合中國實際構建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實踐路徑。
二、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理論邏輯
在話語建構的歷史背景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將中國國情納入考察范疇,并視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否具體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為創新話語方式、擴展話語內涵、提升話語能力的重要標準,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早期構建,反映了不能照搬各種理論,而應根據具體的革命實踐加以靈活運用的理論邏輯與實踐特征。
1916年5月1日,孫中山抵達上海,開始長達近5年的寓滬生涯。此時的孫中山雖然在政治上處于暫時的失勢境地,但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尤其是五四后席卷全國的各類主義及其產生的思想潮流,都予以密切關注。1920年1月29日,他在一封致海外國民黨同志的信函中,高度稱贊“愛國青年”“熱心青年”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稱“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命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認為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各類抗爭,“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預言將來“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借此鼓勵海外國民黨同志順應時勢,“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蘗,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10)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223頁。。這顯示了他對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學生革命思想日漸成熟的高度重視,以及五四后中國革命需要日益迫切的基本認識。而在撰寫該信函的當月,孫中山與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張國燾進行了一次頗具深意談話,所談內容至少透露了三個信息:一是他具有接觸并了解歐洲社會主義各流派代表人物的經歷;二是他曾研讀有關各派社會主義理論的書籍,其中包括英文原著;三是他在“汲取”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主義各流派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創建了三民主義(11)《孫中山全集續編》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454頁。。前兩個方面已有學者做了專題研究,此不贅述;而第三個方面尚未引起學界重視,其中涉及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早期構建、形成與發展問題,是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體系構建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重要關鍵。
眾所周知,孫中山力倡民主革命思想,并以三民主義為其綱領。可以說,三民主義是孫中山關于中國革命實踐探索與基本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理論總結。值得注意的是,在談及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時,孫中山雖然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偉大及其理論的科學性,稱贊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是社會主義中的圣人”,但涉及是否接受或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問題時,孫中山毫不諱飾地表示,“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12)《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03頁。。為何孫中山對馬克思極為推崇,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給予高度評價,但為何在面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時卻表現出“師其意不用其法”的態度呢?(13)楊天石:《師其意不用其法——孫中山與馬克思主義二題》,《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這需要從中國革命的現實性和具體性來加以分析。
孫中山在構建三民主義理論體系之時,注意考察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并且嘗試將兩者有機結合,這應當是有所本的,即基于對馬克思經典作家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運用闡述的深入理解。一方面,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重要標志的《共產黨宣言》,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方法論。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五次提及“革命”概念,并通過對革命環境、革命措施、革命影響等的深入考察,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頁。。而在1886年11月29日致友人的信函中,恩格斯批評當時一些人陷入“教條主義”和“學理主義”的誤區,不懂得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走向“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應付一切”的另一個極端。對此,恩格斯鄭重提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革命“行動的指南”(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6頁。。顯然,恩格斯批判這一錯誤傾向的目的在于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同具體的革命斗爭、革命實踐密切結合起來。
早在1896年旅居倫敦時,孫中山就在大英博物館閱讀了《共產黨宣言》,是最先讀到這部著作的中國人。隨著中國知識人士以及來華傳教士等的譯介與傳播,《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斷被翻譯和介紹進來。據統計,僅1899-1919年間,涉及《共產黨宣言》譯本的文章就有17篇(16)陳紅娟:《〈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誠然,近代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各類社會主義思潮蜂擁而至,在此背景下,國內知識界對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理解尚屬表淺,一些譯作甚至出現錯讀誤解的情況。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進步人士已經意識到,中國具有與歐美等西方國家不同的國情、歷史與文化,因此在學習、接受和傳播相關理論時,注意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造。
尤其是19世紀初,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矛盾與沖突日趨激烈,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日益懸殊,這使中國進步人士在探索中國獨立富強道路之時,將“防患于未然”作為倡導“民生主義”的重要提前。同時,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國內雖存在較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工人階級尚未成為革命的主導力量,因此并未出現歐美各國資本主義與產業工人激烈矛盾與沖突的情形。可以說,正是基于對中國國情的考量,孫中山在構建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時,能從話語環境的變量出發,注意考察中國革命的外部環境與內在要求,并嘗試將兩者有機結合,這無疑是辯證地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后做出的正確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持不同政見者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各異,但在根據時代背景運用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的方法論上,時人是一致認同的。作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胡漢民曾東渡日本,在日本法政大學系統研讀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政治學說,歸國后不僅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實踐,還大力宣傳與倡導三民主義。當“問題與主義”論戰愈演愈烈時,胡漢民亦于1919年8月開宗明義地提出,“拿歐洲近代社會主義的主張,也不能完全適合于中國”,并強調包括“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內,各類社會主義學說均產生于特定的時代與環境,而特定時代與環境之下產生的學說,其“立腳點不同”,“所用的手段方法便也有不同”(17)《胡漢民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第104、105頁。。
三、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歷史邏輯
革命運動需要革命話語的支配,同樣,革命話語也要通過革命運動的實踐來加以豐富和完善。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對生死存亡的考驗,革命成為時代主題,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亦由概念提出和學理爭論,逐漸過渡到革命運動的實踐階段。這標志著革命話語生成的歷史條件逐步形成,革命的手段、方法、目標等要素亦逐漸明確。在此背景下,“社會革命”被納入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歷史進程,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基礎。
五四后中國革命聲浪日益高漲,“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一個亟待回答的時代問題。作為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李達認為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均具有深厚的“革命”內涵,一旦掌握革命的話語權,便掌握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1920年11月,李達在《第三國際黨(即國際共產黨)大會的緣起》中提出“革命的社會主義”概念,強調“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即革命的社會主義”,而實行革命的社會主義是“國際共產黨聯盟的主旨”(18)《李達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頁。以下各卷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贅述。。事實上,對“社會革命”理論的考察,是李達解答“革命”語境下“馬克思主義是什么”問題的重要路徑。次月,李達在《社會革命底商榷》中進一步指出,社會革命的要義在于“直接行動”。為此,他積極呼吁“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即“結合工人農民兵士及他種屬于無產階級的人,組織一個大團體,利用機會,猛然地干起大規模的運動來,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奪在我們手中,憑著政治上的勢力,實行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完全管理社會中經濟的事業”。可以說,李達基于掌握革命話語的客觀需要,將這種直接行動視為“社會革命的唯一手段”,旨在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實現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19)同上,第44頁。。此外,李達關于“社會革命”問題的考察,為解答“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途徑。1920年12月26日,李達《馬克思還原》一文指出,馬克思本人既“是理論家又是實行家,實具有二重資格”。該文論述的目標直指“馬克思所述社會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所推導出的結論則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性質,是革命的,是非妥協的,是國際的,是主張勞動專政的”(20)同上,第58、59頁。。
1921年,遠在法國求學的蔡和森就馬克思學說與中國革命問題,向正在國內緊張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陳獨秀致函。蔡和森認為,從學理上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資本論、階級斗爭說,“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意即馬克思主義具有“革命”屬性;而從話語環境看,革命時代產生的理論必然具有革命性質,就此而言,“馬克思的革命說完全立于客觀的必然論之上”(21)《蔡和森文集》,第79、81頁。。陳獨秀在回信中贊成蔡和森的觀點,認為“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骨髓”之一;同時指出馬克思固然主張革命說,但要防止陷入“自然進化說”的矛盾境地,因為“若是把唯物史觀看做一種挨板的自然進化說,那末,馬克思主義便成了完全機械論的哲學”(22)《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201、202頁。。
蔡和森在論及馬克思主義革命時,還注意到社會運動與社會革命的關系,認為“社會運動為社會革命之起點,社會革命為社會運動之成熟”(23)《蔡和森文集》,第82頁。。應當指出的是,這點與陳獨秀的觀點并不矛盾。尤其是陳獨秀根據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性質,指出馬克思主義為“社會革命的原動力”,并呼吁廣大青年志士以“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從事“社會的革命”或“干馬克思革命的運動”,其構建革命話語的實踐路徑以及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根本宗旨,應當與蔡和森并無二致(24)《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249、250頁。。此外,致力于農民運動的彭湃,從構建“新社會”的角度,提出“社會革命,社會運動,合社會人而運動,而革命之謂也。非個人或少數人,所能成就者。即使之成就,必不是真正之社會運動,社會革命也”,由此呼吁社會各階層人士互相團結、互相聯絡、互相扶助,“有不得不實行社會革命之決定”,構建一個全新的社會和時代(25)《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頁。。
1923年5月,中國共產黨已成立近兩年。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大會的代表,李達基于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現實需要,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認識,提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的重要命題。他認為,中國社會革命實際內涵是“應用馬克思學說改造社會”,其前提是明確“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革命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樣實現的?究竟在什么時機實現?”(26)《李達全集》第3卷,第108、109頁。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社會革命時機成熟的重要標志。盡管當時一些反動派認為“不應提倡社會革命”,但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意義,預示了中國革命新階段的到來。對此,李達號召中國無產階級人士抓住有利時機“實行政治革命”,一舉“奪取政權”,實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社會革命”(27)《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1917.11-1923.7》上冊,第193頁。。換言之,如果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和傳播是革命的中心工作,那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政治主張已公布,革命目標已明確,自然要“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28)《李達全集》第3卷,第108、109頁。。
革命進入新階段,必然面臨新形勢、新問題與新挑戰。尤其是國共兩黨關系的發展演變,使馬克思主義者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將“社會革命”納入考察范疇,并通過革命話語的構建,實現理論的對接和政黨的聯合。概言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基于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現實需要,逐漸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旨在建立強有力的同盟者。而第一次國共合作之所以可行,固然是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也基于三民主義的“革命”屬性。對此,惲代英《論三民主義》一文認為“三民主義為革命的主義”,一方面它是內憂外患的中國國情所需要的,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倡導民族自強、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非革命是不能實現的”,因此,“三民主義的革命”或者說“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最切實合于國情的”主張(29)《惲代英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1頁。。
李達亦持類似觀點。在《民生史觀》一文中,他對三民主義的革命屬性表示認同,強調“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解決民族、民權、民生問題。該文還揭示了三民主義革命與中國社會革命的關系:“三民主義是國民革命的理論,同時又是社會革命的理論,一方面適應現代中國的要求,一方面促進現代社會的進化。總括起來說,三民主義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發生出來的思想信仰和力量。”(30)《李達全集》第4卷,第195頁。
1928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后,因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共同盟合作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革命的前途與命運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在此情形下,“革命”話語的內涵發生新的變化: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其革命理論更徹底,革命信念更堅定;另一方面,隨著孫中山的去世,其所信奉的三民主義,顯然對國民黨而言有了不一樣的性質和色彩。對此,李達基于中國革命現實的需要,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革命與三民主義革命,指出在追求世界大同這一革命最終目的上,兩者是相同的,但在革命的出發點與實踐路徑上存在根本差異。概言之,“三民主義革命是以中國的半封建式的社會做出發點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是以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做出發點的”;而且三民主義革命“是要由半封建式的社會達到未來的新社會”,馬克思主義革命則“是直接要由資本主義社會達到未來的新社會”(31)《李達全集》第4卷,第227頁。。顯然,在李達看來,“革命的理論”是“革命的行動”的重要基礎。正如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然而,馬克思沒有為中國革命提供現在的理論,那么中國共產黨“對于應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的事實的革命理論既沒有建設起來”,“中國所需要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李達在理論探索中似乎找到答案,即“革命的三民主義”(32)同上,第274頁。。可見,“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已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使馬克思主義者對三民主義重新予以審視,借以阻止“反革命化的三民主義”傾向(33)《蔡和森文集》,第997頁。。因此,中國革命的世界性和特殊性,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構建的前提和基礎,亦使團結和聯絡各類文化社團人士的必要性得以凸顯。
可以說,“三民主義革命”或“革命的三民主義”既是中國革命客觀需要的產物,也是國共合作的重要基礎,反映了“社會革命”被納入革命話語體系后產生的重要影響。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條件逐漸成熟,“革命的三民主義”再次被人們提及。正如董必武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前夕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員可以而且應當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理論的基礎”,只有堅持和發揚“三民主義的革命”性質,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戰,才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原則與傾向(34)《董必武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2頁。。毋庸置疑,這一原則與傾向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民族危亡之際,革命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社會革命”也已被納入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歷史進程,由此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提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借以揭示革命對歷史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頁。。列寧則結合俄國十月革命的實踐,進一步指出革命話語構建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呼吁“革命黨的領導者也必須更廣泛、更大膽地提出任務,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走在群眾的革命自動性的前面,成為他們的燈塔,向他們表明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的無比宏偉和無比壯麗,向他們指出達到完全的無條件的徹底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36)《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1、602頁。。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辯證關系的闡述,在某種意義上揭示了革命話語構建的重要意義。五四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接受、闡釋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基于掌握革命話語權的現實需要,通過話語方式的創新、話語內涵的擴展和話語能力的提升,逐步構建起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體系,推動了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的深化和發展。而在“革命”話語構建的背景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與馬克思主義者不約而同地將中國國情納入考察范疇,并且視理論能否具體地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為創新話語方式、擴展話語內涵、提升話語能力的重要標準,反映了理論創新與實踐發展相互結合、促進的歷史面相,揭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現實需要,折射出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