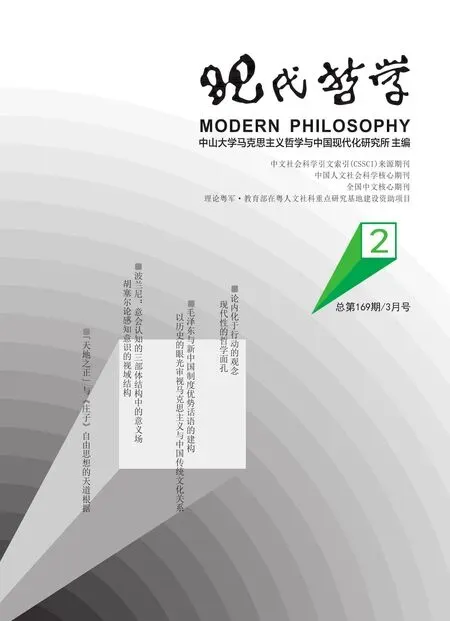胡塞爾論感知意識的視域結構
王鴻赫
胡塞爾用“視域”概念來描述意識行為的一個本質要素,其功能表現為:意識能夠超出自身當下所明確擁有的,去意指得更多(über-sich-hinaus-meinen, Mehrmeinung)(1)See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ge,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Stephan Strasser, Nachdruck der 2. verb. Auflage, Dordrecht: Kluwer, 1991, p. 84.。感知意識的視域性表現為:意識可以超出當下原本被給予之物,意指某種此刻并不在場的東西,將其當下化、意識到它。在這種意指和當下化中,被意識到的內容植根于過去的意識經驗。據此,胡塞爾說“視域”是一種“歸納”:“‘視域’意味著……本質上屬于每個經驗的且與其不可分離的歸納——我強調——作為每個經驗自身之本質組成部分的原始歸納。”(2)Edmund Husserl,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16-1937), Hrsg. Rochus Sowa,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p. 137.(下文簡稱Hua XXXIX.)
目前學界對感知意識之視域結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內視域、外視域,以及作為所有外視域之普全整體的“世界視域”,附帶有所提及作為“我能”的權能性視域(3)See Laszlo Tengelyi, “Husserls Begriff des Horizontes”, Horizonte des Horizontbegriffs. Hermeneutische, ph?nomenologische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Hrsg. Ralf Elm,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 2004, pp. 137-161; Tze-wan Kwan, “Husserl’s Concept of Horizon: An Attempt at Reappraisal”, Analecta Husserliana 31, 1990, pp. 364-376; Carleton B. Christensen, “The Horizo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Logical Analysis 16, 2013, pp. 116-140; Saulius Geniusas, The Origins of the Horiz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Dordrecht/ Heidelberg/ New York/ London: Springer, 2012.。這些研究者所依據的文本主要是已出版很久的胡塞爾著作,如《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笛卡爾沉思與巴黎演講》《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經驗與判斷》《第一哲學(第二卷)》。本文則主要依據新近出版的胡塞爾全集第39卷《生活世界》和第42卷《現象學的臨界問題》的相關論述,結合洛瑪(Dieter Lohmar)對伴隨感知的“弱想象”意識活動的新近研究成果,對感知意識的視域結構做更全面的論述。
由于胡塞爾有時也在“背景”的意義上使用“視域”概念,為了使論述清晰一致,這里有必要將兩者嚴格區分開來。在胡塞爾看來,在注意力的作用下,感知域可以分為“前景”和“背景”。以視覺為例,視覺領域本身所具有的清晰性并非均勻分布,通過注意力朝向的轉換,一個之前模糊的顯現物可以變得清晰,與此同時,剛才被注意到的東西則變模糊。每次被注意到的東西就是視覺領域的前景,未被注意到但處于視覺領域的東西則一起構成視覺領域的背景。這種劃分同樣適用于由各個感官域一起構成的整個感知域:當我注意觀察某物時,我同時聽到周圍環境或大或小的聲響,這些聲響連同我的視覺領域中未被關注的物體一起構成我的感知域的背景。由此,不難看出“背景”與“視域”的區別:背景跟前景一樣都是現前在場的自身被給予之物,而以視域的方式被意識到的則此刻并不在場、自身并未被給予。下面我們來看看胡塞爾是如何具體分析感知意識中視域結構的。
一、由“滯留”和“前攝”構成的視域
“滯留”是一種意識活動,可以將剛剛感知到的、在意識流中剛剛逝去的原印象以一種變異的方式保留下來。這里,變異是指滯留并非對原印象(例如整個視覺領域)的全盤復制,滯留的直觀性充盈要比原印象貧乏很多,并且這種充盈在意識流中會迅速減弱降至為零。處在同一時刻的滯留和原印象彼此處于直接的內在關聯中,兩者的關聯具有一種綜合作用。對于感知主體而言,前后相繼的兩個原印象在直觀內容上相似和相同之處多于相異之處,因而,這種綜合作用通常表現為一種相合綜合(Deckungssynthese),即對剛剛過去的原印象的滯留與此刻的原印象在直觀內容(充盈)上相一致,由此構造出感知內容的同一性。在感知進程中,意識不斷以被動的方式進行這種相合綜合,并在同一性的基礎上,構造出對于感知主體而言的被感知對象的延續性(Dauer)。滯留的基本功能是,通過與原印象的相合綜合作用,構造出感知內容的同一性和延續性。
依胡塞爾的分析,在功能上與滯留相對應的意識活動是“前攝”,它是對尚未到來但即將到來的感性內容的先行把握,例如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對綠燈的前攝。需要注意的是,前攝不同于“期待”。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區別兩者:(1)前攝的內容被意識設定為馬上就要出現的,期待的內容則被設定為發生在(或遠或近的)未來;(2)前攝的內容完全基于當下的原印象并與之有本質聯系,期待的內容則不是必須與當下的原印象相關,且通常與之沒有本質聯系,比如在等紅燈時浮現的晚餐情景屬于期待,而不是前攝;(3)前攝不是獨立的意識行為,而是感知行為的不獨立的組成要素,前攝不會影響感知行為的順暢進行,而期待屬于獨立的意識行為,我們若要在感知的同時進行期待,就必須把注意力從感知域撤離并轉移到期待行為,感知行為由此便從意識域的前景中被排擠出去。
滯留、原印象和前攝構成感知行為的基礎結構。其中,原印象是感知體驗的核心,滯留和前攝猶如核心的“兩翼”,正是借助這兩種意識活動,我們具有“剛剛過去”和“即將到來”的意識體驗。如果不考慮注意力產生的影響,滯留內容會經歷“從有到無”的漸進過程,而前攝內容的“從無到有”一下子便可完成,無需漸進式的構造,所以滯留這一“側翼”比前攝“側翼”長一些。又由于意識流動的單向性,感知結構從整體上看便具有一種“彗星”式的構型。當然,這些只是比喻,這里所說的滯留翼“長一些”并不是空間性的,也不首先是時間性的,而是指意識活動作用的效果。
按照本文開頭對感知視域的界定,即視域是對當下原本被給予之物的超越,意識到某種此刻并不在場的東西,那么滯留(對剛剛逝去的原印象的意識到)和前攝(對即將到來的原印象的意識到)正是感知中的視域意識活動。胡塞爾將滯留稱為“后視域”(Nachhorizont),將前攝稱為“前視域”(Vorhorizont)(4)See Hua XXXIX, p. 375.。由于滯留和前攝是感知行為之基礎結構的構成要素,所以感知的基本結構具有視域性,滯留和前攝構成視域意識結構和功能的基礎。
二、身體權能的視域性
除了滯留、原印象和前攝的顯現內容,感知行為還有一個本質性的構成要素,即感知主體的身體性。下面將考察胡塞爾對身體權能(Verm?gen)所具有的視域性的分析。
在感知的進程中,主體不僅是在進行感知的主體,更是出于意欲或職責在行動的主體。前攝可以把某種即將發生的事物進行當下化,表明自身是感知意識中主動的、具有創造性的要素。然而,“對于與尚未實現的諸實踐意向構成的視域相關、即將到來且處于直接視域中的行動階段而言,并不存在‘它將到來’、‘它將發生’這種單純的意識,而是自由的‘我能’意識”(5)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nomenologie und ph?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Hrsg. Marly Biemel,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2, p. 257.。這里,“我能”指的是身體的權能性。在胡塞爾現象學,身體是由動感構成的,所以對身體權能視域性的分析須從動感入手。
作為身體運動的感覺,動感具有兩個要素,即“動感的位置要素”和“力的‘張緊性’要素”(6)Hua XXXIX, p. 397.。“前者以一種位置流形(Mannigfaltigkeit)的形式而具有變化的諸可能性;另一個要素則具有強度的特征,即零與極限狀態。”(7)Hua XXXIX, p. 397.通過位置要素可以區別相似的動感,如兩只眼睛轉動的動感、兩條腿跑動時的動感;力的要素則在身體的實踐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兩種要素都與系統相關:“‘位置處于動感系統中’[這一含義]本來就已蘊含在‘位置’這個名稱中;一如力的張緊亦與系統相關,當我們具備一個已經形成的系統時,才會在意識方面有作為要素存在的位置。”(8)Hua XXXIX, p. 397.由于身體的每個部位都有很多的運動可能性,若把力的張緊性要素也考慮進來,每個部位的動感可能性便愈加繁多。因此,每個身體部位都可以被視為一個動感系統,身體作為整體則可以被視為總系統,或者說許多動感分系統的統一體。
根據“在多重劃分的動感所構成的動感系統統一體中協同作用的方式”,胡塞爾區分了動感的兩種基本功能:“1)純粹在感知方面起作用的動感……2)在實踐方面起作用的動感”(9)Hua XXXIX, p. 396-97.。一方面,在感知意識之構造的底層,即感覺材料層面,動感已與素材(Hyle)(10)在本語境中,素材與感覺材料同義。處于直接關聯中。“一個由自我操控的動感進程‘決定了’……純素材領域中的一個進程”(11)Edmund Husserl, Sp?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 (1929-1934): Die C-Manuskripte, Hrsg. Dieter Lohmar,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 52. (下文簡稱Hua Mat VIII.),即動感的進程不可避免地使素材跟著發生變化,比如眼睛的轉動不可避免地使視覺顯現域也跟著變化。不過,動感變化與素材變化之間的這種相互關聯只是一種一般性的關聯,即某一確定的動感并不專門地與某一確定的素材相關聯。換言之,動感與素材間的關聯式共存當然可以具體化,但任一具體的關聯都不是必然的、本質性的關聯。另一方面,并非素材的每個變化都是由動感的變化引起的,素材也可以自己發生變化。胡塞爾把這樣一種變化方面的單方依附關系解釋為“如果-那么”:“動感-素材的一直共存具有一種‘意義’,即把動感-素材(自我-非我)聯系起來的因為(Weil),或者說,如果-那么。”(12)Hua Mat VIII, p. 52.即便素材沒有發生變化,也有其動感方面的前件:身體姿勢保持靜止,這種靜止要歸因于肌肉的某一張緊狀態。
每個動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處于一個或幾個分系統中,這些分系統由很多的動感可能性組成。雖然所有可能性不會一下子都被激活,但至少那些緊接著可直接實現的可能性會被激活。在這個意義上,每個動感都有其作為運動之(位置和力的變化)可能性的本己視域。在“如果-那么”的關系中,這種動感的可能性也相應地帶來素材方面有所變化的或新的顯現,這些顯現可以被視為當下被給予的素材的視域(13)“動感-素材的一直共存……自身帶有一個由相關k(“動感”德文詞的首字母——作者注)的自我-動感之諸可能性構成的視域,以及一個相應的、由‘所隸屬’且被決定的素材之諸可能性構成的視域,或者說,k0-h0的共存具有從那里輻射出去的、關于什么的諸顯現(Erscheinungen-von)的諸可能性構成的視域,這些顯現是與其相應的k的、且在k的某一進程中的諸后件。”(Hua Mat VIII, pp. 52-53.)。動感本身并不具有意向功能,所以動感的視域性并不是一種超出當下的意指,而是對接下來可實現的動感可能性的激活。
處于共存中的動感與素材是感知的本質要素。在素材這個基礎性的構造層次,對象無疑尚未構造出來,因而,動感在此并未涉及朝向對象的實踐活動。與之相對,在已完成對象構造的高一級層次,并非所有的動感都是“純粹在感知方面起作用的”(14)Hua XXXIX, p. 396.。例如,當我口渴伸手去拿水杯時,我伸出的手和手臂的動感顯然不是為了去獲得水杯的最佳視覺呈現,也不是為了去獲得對水杯的觸覺體驗,而是為了把水杯拿到嘴邊來喝水止渴。純粹在感知方面起作用的動感與在實踐方面起作用的動感,兩者并不是“動感的相分離的兩個種類,而是動感……協同作用的兩種方式”(15)Hua XXXIX, p. 397.。
兩者在協同作用方面的一個區別是:一個實踐行為往往同時涉及幾個對象,需身體的多個部位參與,這就要求每個參與實踐的身體部位協調好相互合作、在使用物體時根據目的掌控好力度;與之相比,一個單純的感知行為(如專注地看風景)則通常不需要身體與對象相接觸,也就不會產生身體部位之間協調相互配合的要求。
我的行動是“在眾多熟悉的動感系統中進行的,這些系統聯結成一個相互配合的總系統”(16)Hua XXXIX, p. 365.。上述動感協同作用的兩種方式與兩種活動相對應:“我們區分……感知活動……和行動著的實現活動、塑造實在存在的活動。”(17)Hua XXXIX, p. 381.前一種活動的動感顯然是純粹在感知方面起作用的動感,后一種活動的動感則在自身中同時包含兩種動感,因為實踐活動是在感知中進行的。沒有主體在實踐中不需任何感知便可行動。因此,實踐中的感知被視為“原始行動的必不可少的組成要素”(18)Hua XXXIX, p. 381.。由于感知行為本身也是一種可獨自進行的活動,胡塞爾稱之為“原實踐”,區別于實際行動中發揮作用的實踐:“顯現和顯現系統本身重又意味著一種原實踐,它并不依目的去改變已經‘在’的物體,而是完成對這些物體凸顯性的構造:我必須在感知方面進行活動,以便認識物體……這個實踐是實際實踐的基礎……每個實際的實踐必須由具有最佳真切性的感知模式來奠基。因而,感知實踐始終先行。”(19)Hua XXXIX, p. 383.
此外,胡塞爾還指出從純粹感知向實踐行動的過渡,即作為行動之觸發的“感知中的朝向目標”(20)Hua XXXIX, p. 381.。“感知作為原本意識(在此意識中一個實在之物……被展示為自身在此的)尚不是作為行動的感知,這個行動朝向目標并以感知的方式加以實現”(21)Hua XXXIX, p. 382.。
不管是純粹在感知還是在實踐方面起作用的動感,“具體說來始終已是復合的并構成了一個唯一的總體流形,這個總體流形首先作為系統構造起來,進而在每一當前復合的動感那里,這個總體流形始終被意識為權能性的視域”(22)Hua XXXIX, p. 397.。這個權能性便是身體方面的“我能”。
三、視域意向性與身體權能性視域的共同作用
感知有兩個本質要素:動感和顯現。上文已跟隨胡塞爾分析了每個要素的視域性:由滯留和前攝構成的視域涉及的是意識方面的顯現;身體權能性的視域則關涉動感。下面將考察這兩種視域是如何在感知中相互作用的。
上文已述,視域意識被刻畫為一種超出自身的意指。意指具有意向性特征,嚴格說來,只有意向行為才具有視域性,胡塞爾用“視域意向性”(Horizontintentionalit?t)來刻畫意向行為的本己特征。在感知行為中,其意向性表現為意識有所選擇的關注,即“注意力”,而被關注的區域構成感知域的前景。因而,這種內容上超出自身的意指是基于感知域(整個原印象域)的前景進行的,“超出”在此是對前景感知內容的超出。
胡塞爾區分了動感的兩個基本功能,與此相應,下文將從純粹的感知行為、實踐行動兩方面描述視域意向性與身體權能性視域的共同作用。
前文已經探討了在感知構造的底層,即在感覺材料的層次,動感與素材之間的相互關聯(k0-h0),此時的動感還不涉及實踐性的“我做”,因為在這個感知結構的構造底層,對象尚未構造出來,便無從談起主體朝向對象的實踐活動。不過,在這個底層得到揭示的“如果-那么”關系作為基本規律顯然也適用于高一級的構造層次,即已構造出對象的層次。在此,動感與對象顯現之間具有“如果-那么”的前后件關系(k0-g0)。關于其視域性,胡塞爾闡述如下:“通常,物的顯現與動感這樣地相聯結,即,當我正處于某一動感位置,且不管處于哪一動感位置或身體處于哪種姿勢,與此同時我都擁有某種顯現,比如一個視覺顯現。由此,對于連續動感進程中每個將進行的動感方向,我已預先勾勒了某種對顯現者有所知悉的綜合,這種綜合是某種被喚醒的綜合視域。”(23)Hua XXXIX, p. 365.據此,在視域方面,“將進行的動感方向”作為前件起作用,得到勾勒的“對顯現者有所知悉的綜合”則作為后件出現。
在對象構造的層次,動感與顯現共同作用構成的視域可以進一步細分。對此,胡塞爾以一個處于注意力中心的對象作為出發點,或者說作為分析的樣板。在此,意識方面發揮視域作用的是超出此刻被注意到的東西的意指。一方面,這種意指可以是對被關注對象的真切看到的那個面的超出,不過得到意指的仍然屬于同一對象,比如它的其它的面、被看見的面但未被注意到的細節等。而且,這個在視域中得到意指的、作為后件受身體權能性視域的制約:只有通過身體的運動我才能看到另外的面;只有當我向物體再靠近一點時,才能觀察到更多的細節。通過動感與顯現的這種共同作用,我們關于對象的經驗得到充實、擴展和豐富。胡塞爾稱這一過程為“展顯(Explikation)”(24)See Edmund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redigiert und hrsg. von Ludwig Landgrebe, Hamburg: Meiner Verlag, 1972, § 24.。這種對一個對象可不斷繼續下去的展顯過程,構成這個對象的“內視域”。另一方面,視域中的這種意指也可以是對整個被關注對象的超出,即意指此刻另一個僅是附帶被看到或尚未被注意到的對象。這個對象可以處在當前感知域的背景區域,也可以在當前尚未但即將被感知到。不論哪種情況,都需借助身體的運動(如眼睛和頭的轉動、軀體的移動),才能使這個被意指的對象進入意識的注意力區域。這類處于感知域背景中的諸對象,以及此刻尚不在感知域但隨即便可進入感知域的諸對象,一起構成了此刻正被關注的對象的“外視域”。
內視域與外視域的區別可以概括為:在對象極方面,一個被關注的物體正處于現前原印象域的前景;在意識活動方面,與其相關聯的是一個具有視域的意向。在這個意向與身體權能性視域的共同作用下,產生了兩種視域性(超出性)意指的可能方向,即向內(繼續關注這個對象)或者向外(整個地越過這個對象),由此便形成內視域和外視域的區別。但參與這兩種視域的動感都是純粹在感知方面起作用的動感,相應地,身體的權能也只是涉及感知行為,而不涉及實踐行動。
再看在實踐行動中視域意向與身體權能性視域是如何共同作用的。“每個行動、每個實踐在本質上都具有一個‘實踐視域’,一個在視域上被我意識到的境遇中我能做什么的視域。”(25)Hua XXXIX, p. 366.這種“我能”指的便是“在給定的時刻活躍的能視域(K?nnenshorizont)、被我意識到的掌控范圍、確實被我意識到的我的權能”(26)Hua XXXIX, p. 367.。身體的這個權能性視域受主體當下具體境遇的制約,它是“一個活躍的權能視域(一種標示著某一能結構〈K?nnensstruktur〉的權能,這個能結構由此時此地所熟稔的經驗構成)”(27)Hua XXXIX, p. 372,黑體為筆者所加。。
通常在實踐行動中,某種有用的東西處于感知注意力的中心,同時視域意向超出這個被關注之物,朝向一個目的的終點:“在實踐中,我指向一個作為實踐道路之終點的目的,這個目的處于作為實踐朝向性的視域中。”(28)Hua XXXIX, p. 367.這種出于意欲(或職責)的目標設定,引導(或規范)著主體的感知進程和身體活動。“在感知進程中我所‘謀求’的目標作為實踐道路的終點,它連同這條道路以視域的方式處于感知行為本身的每個階段。”(29)Hua XXXIX, p. 367.這里,胡塞爾區分了兩種行為:“或是指向最終目標的獨立(或相對獨立)行為,或是服務型的不獨立行為。后一種行為指向服務目的的手段,指向(關涉最終目標的)中間目標。前一種行為作為統攝性的行為貫穿于諸服務型的行為。在意向活動方面,可以區分瞄向最終目標和瞄向中介性目標;在意向相關項方面,可以區分最終目標(目的)和手段、中間目標。”(30)Hua XXXIX, p. 372.
不過,胡塞爾還是強調瞄向中間目標和瞄向最終目標的統一性:“唯一的一個目標連續貫穿于整個[實行]過程,這個目標是我在先并且不斷欲求著的。這個對最終目標的瞄向貫穿于所有在過程的不同階段相繼進行的單個行為、單個的目標瞄向。每一個這種單個的目標瞄向……都不是孤立的,單個目標的終結并不是事情的了解。單個的目標瞄向自身便帶有對最終目標的瞄向,而且后者不是與前者有所不同的東西,后者就是在前者中得到了校準。”(31)Hua XXXIX, p. 373.這種貫穿于所有中間階段的對最終目標的瞄向,可以區別作為行動必不可少的要素的感知與純粹的感知行為。因為純粹的感知行為缺少這種對最終目標的瞄向,更準確地說,它的最終目標無法實現,即無法徹底、完全、無余地感知一個物體。因為隨距離的遠近、角度的不同、日光(或燈光)的變換,物體每次顯現都有所不同,這樣每次關于這個物體的經驗都或多或少地含有一些新內容。不僅如此,對物體的展顯過程也是無窮無盡的,因為展顯不僅涉及物體外在的各個面,也可以涉及它所有的縱切面和橫切面。在此,比“最終目標”更合適的說法應該是一個起主導作用的目標,即盡可能全面和細致地感知一個物體。與這種內視域不同,實踐視域中的視域意向性朝向一個尚未實現的最終目標。實踐主體無需對某一物體不斷加以展顯,而是滿足于物體的某一最佳呈現。至于從什么角度、在什么距離、具有何種程度精確性的呈現才會被認作是最佳的,則是由相應的中間目標和最終目標所決定。
對目標的瞄向總是基于主體自身的權能性,不管“權能性分多少層次,以及相應的作為諸中介之終端的目標分為多少層次,抑或自我的‘意向’多么簡單和素樸”(32)Hua XXXIX, p. 357.。多層次的權能性指的不僅是身體的權能性,還包括智力的權能性、交流的權能性以及其它技能和能力。可能我的能力實現不了被設定的目標;在目標實現過程中的某一階段,也可能遇到外在或內在的阻礙。“我能(Ich-kann)會受到質疑,付出了努力也會失敗,事實會與預想的、預先設定的、追求的不同。”(33)Hua XXXIX, p. 357.
視域意向與身體(在實踐行動方面)的權能視域一起構成一個實踐視域。這個視域不僅向前指向未來,也可向后回溯喚醒過去:“行動意向有其原涌現的現在,有其由此出發、伸展至最終目標的一個自我性的未來視域,即由現在須做的事情、正使其成為現實的事情構成的期待視域。另一方面,行動意向……從這個原現在(原涌現的意向性階段)出發也具有一個自我性的過去視域,這個視域是由在實踐上已解決的事情、已使最終目的得到滿足的事物、基于我的能力已完成且與該能力相稱的事物構成的。”(34)Hua XXXIX, p. 374.
四、情景式想象的視域
不只實踐視域,至此已探討的所有視域種類都植根于處于現在點的原印象:滯留和前攝構成的視域、身體的權能性視域、內視域、外視域。最后,我們再考察一種不植根于感知原印象的視域類型:情景式想象的視域。上述具有意指功能的視域意識雖然超出原印象,但其所意指的內容仍基于原印象,與之相關。此外,視域意識還能以一種更積極主動的方式,借助想象將與當下原印象完全無關的對象當下化,并且被當下化的不限于一個單獨的對象,也可以是一處場景、變化著的情景等。這種想象的發生和進行都伴隨著感知行為,它由此區別于獨立的想象行為。洛瑪將這種想象稱為“弱想象”(35)Dieter Lohmar, Ph?nomenologie der schwachen Phantasie. Untersuchungen der Psychologie, Cognitive Science, Neurologie und Ph?nomenologie zur Funktion der Phantasie in der Wahrnehmung, Dordrecht: Springer, 2008.。這種情景式的弱想象也是一種對當下原本被給予之物的超越,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廣義感知意識中的視域意識。在此,廣義上的感知是指非單純的感知行為,它包含了弱想象的成分。
在延續時長和想象內容的充盈性、完整度方面,這種情景式想象是可變的。接下來,各舉一例說明它的兩個基本樣式:(1)在一次從容的散步途中,我陷入對一個事件(比如對即將到來的面試)的想象。這種情景式的想象可以在總體上是連續的,內容上也相對比較完整和清晰。(2)在面試當天我驅車前往面試地點,我在感知中專注開車的同時,也可以在弱想象中設想面試的場景;但這種想象是片段式、不連續的,內容上也不完整、有缺漏。在開車途中,我可能僅能把面試的若干重要環節粗略地加以圖像化。
這兩個例子大致勾勒了情景式想象在延續和強度方面的可變幅度:它可以從瞬間的閃現,經片段的呈現,一直到情景式的敘述。這種變化在本質上取決于對這種想象活動所投入的精力(注意力)。胡塞爾列舉了幾種可能的“閃現”內容,如“對一個回憶場景的閃現、對一個科學思想的閃現、對一種實踐可能性的閃現”(36)Hua XXXIX, p. 366.。這類閃現可以引發主體進一步的活動:“我轉而……去弄明白,去更清晰地回憶,去把有關實踐可能性的‘模糊表象’弄清楚、明確為對我而言是可能的(作為可能性去實現它)。”(37)Hua XXXIX, p. 366.
胡塞爾指出了這種“弄清楚”可能起到的作用:“接下來它可能引導繼續不斷地重新奠基的諸意向,并引導使其成為現實的諸行動。”(38)Hua XXXIX, p. 366.此類“對一種實踐可能性的閃現”所具有的引導功能可以被一般化,即每個對實踐之可能性的情景式想象都可以具有這種引導功能。根據洛瑪的分析(39)Dieter Lohmar, Denken ohne Sprache. Ph?nomenologie des nicht-sprachlichen Denkens bei Mensch und Tier im Licht der Evolutionsforschung, Primatologie und Neurologie,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6, § 4.1.,這種朝向未來的情景式想象可以服務于對目標的實現、避免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權衡幾種可能性及其后果,等等。大多數情況下,情景式想象描畫了一種行動上與對象或事件的遭遇,與此相應,情景式想象作為視域大多服務于實踐視域。我們可以以情景式想象的方式進行籌劃和權衡,主體由此能夠做出一個合適的決定并有效地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實踐視域的內容與情景式想象視域的內容融合在一起,而非彼此分開并行。只有通過兩者內容上的分離,才更容易區分這兩種視域。
胡塞爾給出的一段描述可用作區分兩者的例子:“需要去散散步,在‘我想出去走走’中‘被動’跟隨這種需要。與此同時,腦子還在思索、還在專注思考,并且被動地踏上了‘習以為常的’道路,沒有進行選擇,沒有特別指向這條道路的意志決斷。不過也沒有違背我的意志”。(40)Edmund Husserl, Grenzprobleme der Ph?nomenologie: Analysen des Unbewusstseins und der Instinkte, Metaphysik, sp?te Ethik.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08-1937), Hrsg. Rochus Sowa und Thomas Vongehr, Dordrecht/ Heidelberg/ New York/ London: Springer, 2013, p. 96.(下文簡稱Hua XLII.)在此,主體一方面在習慣的道路上“被動”地散步,另一方面則陷入沉思。其中,感知中的視域意向和身體的權能性視域共同作用,構成散步的實踐視域。對于沉思的內容,不妨舉一個具體例子:借助想象的圖形來證明幾何命題。這種借助想象的圖形進行的幾何思考,構成情景式想象的視域。在此,主體從事著兩件事:感知非主動地參與其中的散步;借助圖形想象主動進行的幾何證明。兩者可以同時進行,因為兩者涉及的是兩種不同的活動,即行動與思維。也就是說,主體在此并未同時進行兩個不相干的行動,也沒有同時進行兩個想象活動,而是同時進行一個身體行動和一個想象活動。這二者可以互不沖突地并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圖形想象上,而對于這條“習以為常的道路”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在每個岔路口根本無需停下來張望一番并思量究竟該走哪條路:“視夏日的溫度而定,我時而喜歡走這條路,時而走那條,一開始便有所思量。天熱時,我習慣走這條路,等等。此刻[即我專注思考時]天熱了起來,我不加思索地踏入了成蔭的、看起來涼快些的道路。就是說,并非特意而為之。”(41)Hua XLII, p. 96,黑體為筆者所加。也就是說,我只需分給感知很少的注意力,散步便可順利進行。胡塞爾也把這種沒有特別指向什么的意志決斷稱為“意志的被動性”(42)Hua XLII, p. 96.。當意志處于被動,或者說,當感知意識中的意向處于非主動狀態時,身體便似乎只是在做機械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并非視覺感知,而是這種身體運動本身主導著散步這一實踐活動。可見,這里主要是身體已習性化了的權能性視域在向前推進實踐行為,而不是處于非主動狀態的視域意向性。由于身體的權能性視域不具有意向性、不是超出當下被給予物的意指,所以這種視域以及它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實踐視域可以被稱為近視域(Nahhorizont);而那種例如指向最終目標的視域意向則可以被稱作遠視域(Fernhorizont)。我可以一邊出于純粹的習慣在散步,一邊專注于情景式的想象。由于我的注意力要同時分配給感知和想象,所以這兩種意識行為會為了“爭奪”意識活動的主位而處于一種競爭關系之中。
情景式想象的視域在內容上與當下的感知原印象無關,也與當前的身體運動沒有必然聯系。通常而言,情景式想象的視域與身體的權能性視域之間沒有互動(43)想象中的情景有時會對當前的身體運動產生直接影響。比如,我趕著去赴約,當我腦海中浮現那位正等我的人難掩慍色的臉時,我的腳步會不由得加快。但這種影響是單方面的,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共同作用。。由于在想象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被當下化,所以這種想象視域大大地拓展了當下經驗所能擁有的體驗范圍。
至止,我們考察了感知意識中視域的各個面向,有前視域與后視域、內視域與外視域、近視域與遠視域、實踐視域等,分析了它們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從中可以感受到胡塞爾意識分析的細致與嚴謹。這種非教條式的工作哲學的特征正是胡塞爾現象學最吸引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