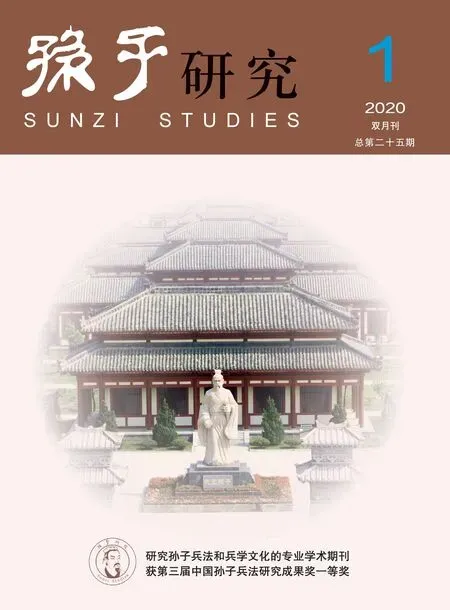在中國特色強軍路上闊步前進
——兼論新時代強軍思想中的中國傳統兵學智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胸懷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革故鼎新,厲行新政,以大氣魄大擔當治黨治國治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的歷史起點上,在我國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歷史階段,習近平同志從謀民族復興偉業、布富國強軍大局、立安全與發展之基的戰略高度,圍繞強軍興軍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科學籌劃了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的戰略布局,深刻揭示了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的特點規律,實現了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與時俱進,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軍事篇”,成為新時代引領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實現強軍興軍偉業的“魂”與“綱”。任何一種思想理論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其理論的傳承性、鮮明的歷史性和特殊的時代性。習近平新時代強軍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汲取中國傳統兵學文化的智慧,與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
一、蘊含深邃內涵的強軍戰略思想體現了政略與戰略的和諧統一
習主席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對軍隊來說,就是強軍夢。習主席鑒于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強調中國堅決摒棄“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強調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目標下加以推進,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和民族最高利益;強調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堅強力量保證。這與中國傳統兵學中始終強調要將“道”置于運籌和指導軍事問題的首位是一脈相承的。《易經》當中也提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意思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要去掉武器,但不要忘記防備。習主席曾多次引用《司馬法》中的“國雖大,好戰必亡”的名句闡明窮兵黷武的危害。因此,一定要正確認識和處理軍事和政治的關系,這是事關國家命運,事關戰爭和軍事斗爭指導全局的根本問題。
(一)著眼實現中國夢的戰略高度運籌國防和軍隊建設
在習近平新時代強軍思想中,實現中國夢、強軍夢與中國特色強軍之路是辯證統一的。軍事力量的提升與發展是實現中國夢和強軍夢的基礎和保證。習近平主席籌劃新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戰略考量就是著眼實現中國夢,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重要戰略支撐和堅強安全保證,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爭取更大的戰略空間和更多的發展時間。把國防和軍隊建設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下來認識和推進,服從和服務于國家和民族最高利益,這也與《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和政治價值取向是一致的。孫子認為戰爭的目的是“安國保民”“安國全軍”,是“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可以說,安國全軍之道是其最高戰略指導原則,而安國保民則是其軍事戰略的政治價值基礎。戰爭從屬于政治,其目的不是為戰而戰,而是為實現安國保民的最終目的。創新軍事戰略指導,就要把實現中國夢作為根本著眼點,堅持從國家利益的高度謀劃軍隊建設,從政治大局的高度思考處理軍事問題。習近平主席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提出中國夢,僅10 天后,在戰區考察時又提出強軍夢及強軍之魂、強軍之要、強軍之基。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將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放在治國理政大格局、國家改革大棋盤中來布局;四中全會作出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定,把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專列一節,納入依法治國大業同步協調;五中全會作出“十三五”規劃建議,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專列一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協調統籌。著眼中國夢運籌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充分體現了習近平主席宏大的戰略視野、高遠的戰略考量和高超的戰略運籌。
(二)立足由大向強發展關鍵階段擘畫國防和軍隊建設
強大的軍事實力始終是支撐國家強大的“骨骼”,是增強國家應對國際風云變幻的底氣所在,是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突破國家崛起“安全困境”的保底手段。強國必須強軍,既是國家強盛之道,也是大國崛起的規律所在。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往往在兩個時期面臨的外部壓力最大,一個是積貧積弱之時,另一個是發展振興之時。現在,我國就處在由大向強發展這樣一個關鍵階段。我們發展得越快,對外部的影響沖擊就越大,受到的戰略反彈力就越強,正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
由大向強發展關鍵階段所面臨的新形勢,正是習近平主席思考謀劃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現實邏輯。一方面,我國綜合國力、核心競爭力、抵御風險能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世界更加關注、重視中國,我們的戰略回旋空間不斷擴大。另一方面,世界體系進入大變局時期,圍繞權力和利益再分配,新興國家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日趨激烈,大國關系進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階段。中國塊頭大、分量重,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系影響深刻。面對中國這樣的強勁發展勢頭,西方守成大國處心積慮地制造各種矛盾和問題,試圖在我“將強未強”之際遏阻、搞垮中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強,一些西方國家的焦慮感進一步上升,他們加大力度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丑化等“屠龍”戰略,企圖分裂、瓦解、孤立中國。尤其是一年多以來由美方挑起來的貿易戰,美國政府企圖以極限施壓手段迫使中國屈服。其實,貿易戰是表象,其實質是阻扼中國發展進步。接下來就是科技戰、貨幣戰、金融戰甚至軍事戰。美國的目標就是一個,稱霸世界,號令天下。誰挑戰他的霸權地位,他就與誰開戰。盡管我們再三聲明,我們無意挑戰美國霸主地位,永遠不稱霸。但是美國不信,美國人的邏輯是:發展可以,但要在美國控制范圍內發展。只能生產低端產品,為美國當打工仔,不能生產高端產品,任何方面都不能超過美國,“美國第一”。面對強國進程中這些無法回避的挑戰,習近平主席指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為國家核心利益和戰略底線的終極力量,作為確保“中國號”巨輪破浪前行的“壓艙石”,責任重大、任務艱巨。正如《孫子兵法·形篇》中所講,“先為不可勝”,“能為不可勝”,必須通過國防和軍隊建設保證先立于不敗之地,方能具有和平崛起的實力與底氣。
(三)順應世界新軍事變革大趨勢謀劃國防和軍隊建設
進入21世紀,以信息化為核心的世界新軍事革命正在加速發展。面對這場新軍事革命,世界主要國家紛紛調整軍事戰略,加緊軍事轉型,以信息化為核心重塑軍隊組織形態,重構軍事力量體系。面對這一股改革浪潮,世界各主要大國競相調整軍事戰略,紛紛加緊推進軍事轉型。美軍在積極推動“二次轉型”;俄羅斯圍繞建設“職業化、常備化、精干化”軍隊,鐵腕推進武裝力量“新面貌”改革;日本加快推進軍事改革,企圖實現從靜態威懾的“基礎防衛力量”向動態威懾的“機動防衛力量”轉型。英國、法國、印度等其他國家也不斷推進軍事改革,調整軍事發展方向。
面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巨大變化,習近平主席提出,世界新軍事變革加速發展對加強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目前,我軍現代化水平與國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還很大,與世界先進軍事水平相比差距還很大。同時,我軍現代化水平與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軍事能力與履行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2016年4月20日,習近平主席視察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時,對全軍官兵提出,要堅持底線思維,強化危機意識,擔起歷史重任,適應國家安全戰略需求,緊跟世界新軍事革命潮流,抓住和用好國防和軍隊改革這個歷史性機遇,深入研究信息化戰爭制勝機理,研究現代化戰爭作戰指揮規律,構建具有我軍特色、符合現代戰爭規律的先進作戰理論體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入研究和破解發展難題,努力開創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新局面,在搶占世界軍事斗爭制高點中贏得主動,成為習近平主席思考謀劃強軍夢迫切需要解決的時代性課題。
二、實現強軍興軍偉業的行動指南體現了強軍與富國的統一運籌
富國與強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兩大基石,新時代如何處理經濟與國防的關系,關乎國之興衰、民之福祉。習近平主席指出,“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本依托,只有國家經濟實力增強了,國防建設才能有更大的發展。國防建設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只有把國防建設搞上去了,經濟建設才能有更加堅強的安全保障。”“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與強軍相統一,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把軍民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是新時代實施富國和強軍相統一的重要途徑,有利于加快形成強大的軍民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
(一)富國強軍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
“富強”,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也是一個民族傲然自立的根本。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理論家管仲率先提出了“富強”的概念。《管子·形勢解》中講,“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一個國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強調“國防建設要服從經濟建設”。為了支持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很少,1997年軍費支出僅占GDP 的1.03%,為新中國歷史最低點。但通過改革開放的積累,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進入新世紀,中國軍費逐年增加。至2017年,中國國防經費預算突破1 萬億元大關。但是,中國人均國防支出僅相當于美國的1/22、日本的1/5,而且我們軍費預算的2/3 是用于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等日常消耗性費用,能夠拿出來用于國防現代化建設的費用是有限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孫子兵法·形篇》早就認識到國土資源、軍隊數量以及戰斗力之間的關系。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強國的其他要素還不完備,國家尚處于“大而不強”“將強未強”的關鍵發展階段。建設一支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我國發展利益相適應的軍事力量,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為民族復興的關鍵階段發揮重要作用。強大的軍事實力不僅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而且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的拉動作用,對國家的政權穩定和國際話語權有重要影響,對提升綜合國力具有杠桿效應乃至系統聚合效應。
(二)軍民融合是實現富國強軍相統一的重要途徑
習近平主席強調,“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們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發展和安全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應對復雜安全威脅、贏得國家戰略優勢的重大舉措。”走軍民融合式道路,是對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和戰略升華。只有發揮好軍民融合對國防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向支撐拉動作用,既以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又最大限度地發揮國防和軍隊建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拉動作用,才能實現安全與發展兼顧、富國與強軍統一。
現代國防安全,本質上是靠國家整體實力支撐起來的大國防體系安全。信息時代的戰爭樣式由平臺對抗向體系對抗轉變,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其根基已經深深植入經濟社會的沃土中。面對戰爭形態的深刻變化,只有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充分挖掘使用經濟社會母體中蘊含的巨大經濟、技術、信息、人才等能量,才能有效解決我軍現代化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問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用融合之力鑄就現代國防安全之盾。國防和軍隊建設不僅維護國家生存權益,而且增創國家發展利益;不僅生產“安全產品”,而且創造“發展紅利”。實現強軍目標,必將推動軍事高科技發展和高素質軍事人才培養,進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為強國提供強大的科技和人才支撐。實現強軍目標能夠極大提升國防實力,并通過杠桿效應提升綜合國力,產生巨大的綜合性溢出效益,大大提升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影響力,從而使我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三)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要堅持富國與強軍相統一,強化統一領導、頂層設計、改革創新和重大項目落實,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統籌謀劃、整體推進和一體運用,從而實現國家總體戰略效益最大化。
國家戰略體系是一系列國家戰略構成的有機整體。經過多年來的探索,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集中布局了一批國家戰略,比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海洋強國戰略、航天強國戰略、網絡強國戰略、制造強國戰略,等等,形成了一個指導國家總體發展、區域發展、各領域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體系。國家戰略能力是國家組織、協調和運用內外戰略資源和戰略力量,預防和應對各種重大威脅,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的能力。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能力,是將各種相互關聯的軍民力量集成為軍民一體、總體增效的國家能力。正所謂“上下同欲者勝”“民齊者強”。發揮軍民一體化的強大力量是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戰略的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路徑。國家發展的各大戰略系統,從表面上看是自成一系、彼此不同,但從實質上講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近幾年,經過堅持不懈的探索實踐,一個以“六大體系”融合為主體支撐、以“新興領域”融合為突破重點、以“走出去”融合為拓展延伸的軍民融合發展布局漸趨成形。“六大體系”融合指的是基礎領域資源共享體系、中國特色先進國防工業體系、軍民科技協同創新體系、軍事人才培養體系、軍隊保障社會化體系、國防動員體系。“新興領域”融合聚焦海洋“遠邊疆”、太空“高邊疆”、網絡空間“無形邊疆”,加快形成多維一體、協同推進、跨越發展的新興領域融合發展布局。“走出去”融合,著眼有效維護我國不斷拓展的海外利益,統籌力量走出去,著力提升維護海外利益安全核心能力。
三、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志舉措體現了大變局競爭的時代需要
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和重要標志,是實現強軍興軍的戰略舉措。習近平主席從加快推進強軍進程、更好贏得我國軍事發展優勢的高度,發出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時代號令。基于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以及我軍改革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習主席強調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一場回避不了的大考。軍隊在這場大考中必須自覺經受考驗。改革是強軍的必由之路,必須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制度。習近平改革強軍戰略思想是實現新時代黨的強軍目標的戰略先令。為實現強軍興軍布了長遠局、下了先手棋,為人民軍隊未來制勝與發展贏得了關鍵一招。
(一)軍隊組織架構實現革命性變革
習近平主席指出,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決定軍隊組織功能和作戰效能,是這次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中之重。“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新格局的建立,實現了我軍領導指揮體制的重大歷史性變革,是最大的改革成果。
首先,打破了傳統的作戰指揮和領導管理職能合一的領導指揮體制。現代戰爭作戰指揮的復雜性空前增長,指揮活動涉及的兵種達數百種,聯合性進一步凸顯,任何單一軍兵種都不可能包打天下。這要求作戰指揮必須超越軍種界限,褪去“建用一體”時代的軍種特色,根據現代作戰的規律特點,構建獨立的作戰指揮體系,對所有作戰部隊和作戰單元實施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這輪國防和軍隊改革,打破了大軍區體制,調整劃設了五大戰區,建立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把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放在戰區,把部隊建設管理的重心放在軍兵種,建立了作戰指揮職能和建設管理職能相對分離的體制,切實提高作戰指揮效能和軍隊建設效益。其次,重塑了軍委機關。原來的司政后裝四總部制體制不僅職能泛化,而且客觀上延長作戰指揮鏈,對實現聯合作戰指揮不利。新的軍委機關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把軍委機關改為一廳、六部、三個委員會、五個直屬機構共十五個職能部門。這樣調整組建,使軍委機關真正成為軍委的參謀機關、執行機關、服務機關。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軍委機關調整組建,是整個領導指揮體制改革的龍頭,是這輪改革中最具革命性的改革舉措,是對我軍戰略領導、戰略指揮、戰略管理體系的一次全新設計。”再次,構建了“軍委—戰區—作戰部隊”聯合作戰指揮鏈路。此次軍改,健全了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組建了戰區作戰指揮機構,基本上構建平戰一體、常態運行、專司主營、精干高效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軍委聯指中心主要擔負軍委的戰略指揮職能,戰區則由軍委賦予本區域、本戰略方向上指揮的全權,專司主營戰區聯合作戰指揮。
(二)軍隊力量體系實現整體性重塑
戰爭的時代特征,決定了軍事力量體系的建設標準。運用精銳力量實施精確作戰,成為現代戰爭的一個突出特征。當前,我軍軍事力量體系正處于機械化即將完成、信息化全面發展的初級階段,總體上還屬于國土防御型、人力密集型、陸戰主導型,整體水平還落后于世界軍事強國。這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把部隊搞得更加精干、編成更加科學,努力打造以精銳作戰力量為主體的軍事力量體系”的建設要求還有較大差距。這輪軍改是著眼打造精銳作戰力量,優化規模結構和部隊編成,推動我軍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對軍事力量進行的整體性重塑。
一是規模適度。“兵少不足衛,兵多則不勝其養。”構建軍事力量體系要從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需要出發,結合國家經濟實力,合理確定軍事力量的規模。我們國家塊頭大、國境線長、鄰國多,周邊安全形勢錯綜復雜,軍事斗爭和維穩任務重,軍隊需要保持較大規模。但是,230 萬的總員額是有些偏大的,還須繼續“消腫”。《孫子兵法·行軍篇》有云:“兵非貴益多。”此輪軍改,我軍再裁減30 萬人,確定維持200 萬人的總規模,這是與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需求相適應的,對國家政治外交大局也是有利的。二是優化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把“瘦身”與“強身”統一起來,推動軍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壓減陸軍部隊,適度發展海軍、空軍、火箭軍,尤其是海軍要擴大規模、大力發展,使我軍軍種比例適應現代作戰需要。三是新型作戰力量快速發展。縱觀世界軍事史,新型作戰力量往往成為軍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這輪軍改注重將新型作戰力量放在突出位置予以重點發展,加強了太空力量、網絡戰力量、預警偵察力量、無人化作戰力量、戰略威懾力量、遠程投送打擊力量和海上作戰平臺等的建設。
(三)形成成熟的中國特色現代軍隊政策制度體系
習近平主席指出,軍隊政策制度,關系官兵利益,是提高軍隊戰斗力、激發軍隊活力的重要途徑。政策制度不僅在規則層面對固定改革成果具有重要意義,對教育引導廣大官兵積極投身改革實踐,更具有深遠導向意義。
一是健全完善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強軍興軍,要在得人。”古往今來,對人才的重視程度與一支軍隊的強大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果軍人職業沒有構成相對凸顯的比較優勢,且各種政策制度銜接配套不到位,就會造成大量才俊投身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意愿不強。因此,這輪軍改著眼提升軍人職業的比較優勢,在政治榮譽、薪酬福利、住房保障、保險醫療、家庭優撫等方面給予較為優厚的待遇和政策支持,以發揮政策制度的激勵、杠桿、導向作用。二是制定更為完善的軍費管理制度。《孫子兵法·計篇》對統籌軍事問題提出了“五事七計”,其中的“法”指的是“曲制、官道、主用”。軍備物資、軍事費用的供應管理制度對國防和軍隊建設進程和成效有著規制性的影響。所以在軍費管理上要以戰斗力為導向,切實樹立“績效為本”的管理理念,形成預算—編制—執行—監督—反饋的閉合回路,做到需求充分論證,劃撥科學統籌,用錢精打細算,用好每一個“銅板”。
新時代改革強軍思想是著眼于奪取未來軍事競爭戰略制高點,蘊含打造世界一流軍隊的戰略設計。面對當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全黨全軍智慧,經反復醞釀、反復研討、反復修訂,精心制定了頂層設計科學、總體框架合理、內部功能鏈路清晰、政策機制配套的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總體方案,形成了既著眼現在又前瞻未來的新時代改革強軍思想。這一戰略思想,是我軍實現“彎道超車”的強勁引擎,是保持與世界軍事發展潮流同步的戰略布局,奠定了我軍未來發展壯大的基本輪廓,科學有力地引領指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偉大變革與歷史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