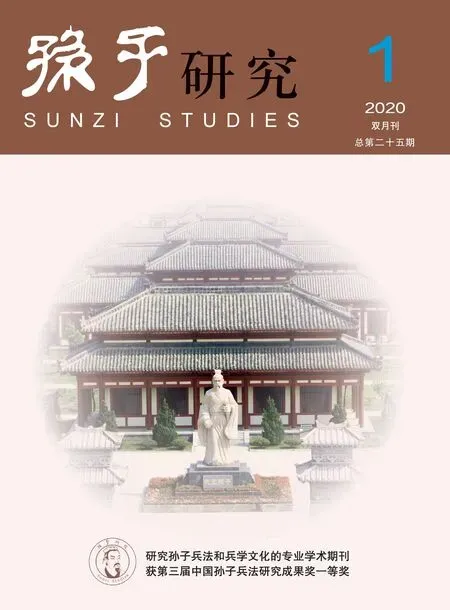孫子論兵要地理
兵要地理是《孫子》十三篇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孫子兵學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行軍篇》到《地形篇》,再到《九地篇》,孫子對這一論題逐漸深入,用墨越來越重,充分顯示出其重視程度。遺憾的是,這些重要論述被部分學者視為“層次較低”。①鈕先鐘:《孫子三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66、95頁。《九地篇》更是被當成“內容雜亂”②鈕先鐘:《孫子三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66、95頁。,系拼湊而成。既然如此,我們也很有必要就這一論題再進行一番探討。
一、地理與駐軍
《孫子》在進入《行軍篇》之后,開始對治軍問題進行討論。《行軍篇》篇題中的“行”,讀“杭”,意指行列。《周禮·夏官》鄭玄注曰:“行,謂軍行列。”從篇題就可以大致判定該篇會對軍隊部署及駐扎等問題有所探討。駐扎軍隊,必然要考慮地理因素,并且也不可避免會對治軍問題有所涉及。就“處軍之法”,孫子總結了四種不同方案,分別為“處山之軍”“處水上之軍”“處斥澤之軍”“處平陸之軍”。
“處山之軍”是總結穿越山嶺地帶的各種注意事項。孫子認為,必須要靠近有水草的溪谷,兵駐扎于向陽的高地。而且,如果敵軍居高臨下,就避免對其仰攻,這就是“戰隆無登”(《孫子·行軍篇》)。此處“戰隆”,簡本作“戰降”。古人經常將“隆”和“降”混用。降,下也。戰于山下,敵人可能誘我上山,但此時一定不可登山迎敵。“處水上之軍”則總結了準備渡河時軍隊駐扎的若干注意事項,其核心為“遠水”。很顯然,這是就駐扎軍隊而言,否則就于理不通:既然是渡過江河,為什么還要遠離江河?孫子的本義應為,大軍渡河之前,安營扎寨一定要遠離江河,防止被河水所傷。就迎戰來犯之敵來說,注意半渡擊敵。另外也要“無附于水而迎客”(《孫子·行軍篇》),也即不要背水而接敵,避免無路可退而導致全軍覆滅。總之,一定要“視生處高,無迎水流”(《孫子·行軍篇》),不僅要占據高處,向陽而處,而且不可在下游駐軍,不能面迎水流。如果是“處斥澤”,那就必須迅速離開,不可久留。這種地形對于交戰雙方而言都非常不利,進退都非常困難,更別說打仗。在孫子看來,大概只有一種方法相對可行:“依水草而背眾樹。”(《孫子·行軍篇》)因為這種地方,地質相對較硬,部隊可以稍作伸展,便于將士機動。“處平陸之軍”是指平原地帶的駐軍方法。這種地方車馬易行,應選擇視野開闊之地,便于部隊機動。而且要注意將主力部隊駐扎在地勢較高之處,即“右背高”(《孫子·行軍篇》)。這里的“右”,應遵從吳如嵩、鈕先鐘等學者,解釋為“主要側翼”。①吳如嵩:《孫子兵法新說》,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1月第1 版,第153頁。鈕先鐘:《孫子三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88頁。至于“前死后生”,則稍微難解。王皙懷疑此句當為“前生后死”②王皙曰:“凡兵皆向陽,既后背山,即前生后死。疑文誤也。”見《十一家注孫子·行軍篇》。,但簡本與傳本保持一致,傳本并未寫錯。杜牧注曰:“死者,下也;生者,高也。”如果保持這種陣型,顯然利于部隊出擊。李筌曰:“前死,致戰之地;后生,我自處。”這里依據的是對“死地”的理解——“死地則戰”,“向前”則與敵疾戰。向后則背處向陽之地,因為有所依托而能自由處置。
對于自己所總結的四種“處軍之法”,孫子非常自得,認為這樣便可得“四軍之利”,而且也是“黃帝之所以勝四帝”的方法。(《孫子·行軍篇》)黃帝是傳說中的遠祖。孫子引古以爭,強調自己所建構的理論非常有用。銀雀山出土簡文《黃帝伐赤帝》對此有專門解釋。③詹立波指出,《黃帝伐赤帝》那一部分,有一些文字是在解釋《孫子·行軍篇》中的“黃帝之所以勝赤帝也”。見詹立波:《略談臨沂漢墓竹簡〈孫子兵法〉》,載《文物》,1974年第12 期。當然,該篇文字較為繁復,而且較多沾染了兵陰陽家的色彩,顯得更加費解,也與孫子“不可取于鬼神”(《孫子·用間篇》)的精神背道而馳。
孫子總結的“處軍四法”,其基本原則是“趨利避害”,不僅要達成“四軍之利”,而且努力占據“地利”,追求的是“兵之利,地之助”。如果占據有利地形,如“好高”“貴陽”“養生”之地,那就可以占據居高臨下的優勢,不僅便于部隊機動,也利于后勤補給,士卒也會百病不生,從而為戰爭獲勝創造有利條件。
“處軍”過程中必然要遇到治軍問題,孫子于是結合地理問題論及治軍,也順帶提出了精兵原則:“兵非益多。”孫子說:“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孫子·行軍篇》)“兵非益多”,簡本作“兵非多益”,意思更為明確。十一家注本作“兵非益多也”,“益”和“多”二字顛倒。曹注本在“非”后又加“貴”字,顯得冗繁。
治軍理論是孫子兵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子在《行軍篇》最后部分提及,而且在《地形篇》《九地篇》逐漸展開,明顯也是結合地形論述。在《行軍篇》,孫子提出了治軍的總原則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孫子·行軍篇》)。對于此句,人們習慣理解為,主用“文”的一面來教育士卒,用“武”的一面約束和管制士卒。簡本作“合之以文,齊之以武”,可以促進我們的理解更進一步。筆者認為,這里運用了“互文”的修辭格。④熊劍平:《〈孫子兵法〉“互文”修辭格的運用》,載《濱州學院學報》,2012年第5 期。“令”,或可校正為“合”,簡本更佳。孫子主張文武兼用、寬嚴相濟,“文”和“武”都是治軍必要手段,而且應當互相配合。換句話說,使用寬厚和仁恩的方法能使其心悅誠服,但同時也要加強刑威,保證部隊紀律嚴明、步調統一。“文武并用”,其實就是仁恩和懲處相結合,尤其需要把握“度”。如果士卒和將帥沒有親近感,距離很遠,實施處罰則會將距離拉得更遠。這就是“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孫子·行軍篇》)。如果士卒已和將帥非常親近,甚至導致將帥不能下手處罰士卒的錯誤行為,即“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孫子·行軍篇》),同樣也是非常危險。必須通過合適的治軍方式,實現“治眾如治寡”(《孫子·勢篇》)和“齊勇若一”(《孫子·九地篇》)的目標,保證軍隊的整齊劃一,達到“攜手若使一人” (《孫子·九地篇》)的效果。可見,治軍理論雖在孫子兵學思想中不占據主要位置,但也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治軍問題及有關軍事地理等論述,并非“層次較低”的小問題。
孫子論治軍,先在《行軍篇》提出了“令文齊武”的總原則,接下來便在《地形篇》提出了偏于“文”的一面:“視卒如嬰兒”與“視卒如愛子”。他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將士卒視為“嬰兒”或“愛子”,與孫子的仁義思想保持一致。孫子認為,這樣才能保證作戰之時三軍用命,達成“可與之赴深溪”和“可與之俱死”的效果。(《孫子·地形篇》)
當然,仁愛也需注意“度”。如果超過了“度”,也即“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那就是嬌生慣養的“驕子”,派不上用場。孫子于是也有對于“武”的一面,集中體現于“愚兵之術”,主要見諸《九地篇》:“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在關鍵時候,要蒙蔽士卒,讓他們順從。甚至要造成無退路的感覺,逼其奮勇作戰。這一點在死地作戰時顯得尤其重要,與“令文齊武”的總原則并不矛盾。就治軍而言,《行軍篇》《地形篇》《九地篇》恰好也構成一個有機整體。《行軍篇》總論“令文齊武”,《地形篇》和《九地篇》則分別論述“文”與“武”。
二、地理與情報
孫子認為,要想做好“處軍”,必須做好“相敵”。換句話說,“處軍”和“相敵”緊密聯系在一起。《行軍篇》因此在討論“處軍之法”后,便將主要筆墨轉向“相敵之法”。他不厭其煩地將所能想到的各種偵察敵情的方法進行了羅列,多達三十余種。這些內容,既是古代戰爭經驗的總結,同時也能對戰爭實踐起到指導作用。“相敵之法”主要是為偵察敵情,為指揮員判斷戰場情況、下定決心和指導戰爭提供基本依據,和《計篇》的“廟算”思想、“形人之術”和用間之術等,共同組成了一整套豐富而嚴密的情報理論體系。其中某些方法,直至今天仍不失實際運用價值。現代戰爭固然需要掌握和擁有大量新型高技術偵察裝備,包括大量衛星、雷達及遠程紅外偵察裝備等,但孫子所總結的這些“相敵之法”并非完全沒有意義。在前線陣地的接敵偵察行動中,執行任務的偵察分隊同樣會遇到諸如“鳥集”和“揚塵”等現象,根據孫子所總結的各種方法來快速判斷敵情,固然非常原始,但仍有實際運用價值。
《行軍篇》所總結的這些“相敵之法”中,有一些是根據敵人的言辭和行動來判斷敵軍行動方向,如“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等。也有一些是根據鳥獸、草木及塵土情況來判斷敵軍動向,如“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等。這兩類占據了絕大多數。
當然,孫子所總結的“相敵之法”,有個別未必準確。比如“敵近而靜”,孫子認為是敵軍“有險可恃”便值得商榷。敵方抵近且不動聲色,很可能另有預謀,或組織更大規模的進攻戰斗,未必是“有險可恃”。而且各本“相敵之法”具體條目數字存在差異。從“敵近而靜”到“來委謝”,十一家注本為“三十一法”,武經本則為 “三十二法”。其中“粟馬肉食,軍無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一句,武經七書本作“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故而多出一條。考察簡本,似與十一家注本保持一致。武經本“軍無糧也”更像是“殺馬肉食”的注解文字衍入。①世人或稱“相敵三十三法”,應是在武經本的基礎上又加上“軍旁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處也”一句。
孫子總結“相敵之法”,首先強調“軍旁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處也”,重點要對這些地理情況進行偵察,孫子設計戰法等也依據地形出發,這便為《地形篇》集中論述“知地”作了鋪墊。在《地形篇》,孫子主要探討利用各種地形條件克敵制勝。這些內容,今天屬于軍事地形學的范疇。銀雀山出土的簡本《孫子》篇題木牘有《□刑》,疑為《地形篇》篇題,但簡本并無該篇簡文出土,只留下殘缺嚴重的《地形二》,疑為《地形篇》的注解文字。孫子構建了“先知后戰”的理論體系,在《地形篇》重點論述的是“知地”。由“廟算”開始,孫子已經建立了“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的“知論”。到了《地形篇》重點討論“知地”,是其大情報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子對“知天”很少論及,懷疑古人對天存有敬畏之情,由于科技水平有限,古人對“天”的了解也很有限。但是對于其他幾方面,孫子都有詳細論述,對“知彼”和“知地”探討最多。
在《地形篇》的結尾,孫子大段論述“知”,最終還是回到了“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的“四知”:“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戰,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孫子以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一語作為《地形篇》結尾,完全是基于“知地”在情報理論體系中的地位認識,同時也與“先知后戰”的兵學理論體系呼應。孫子非常重視情報工作,因此構建了“先知后戰”的兵學理論體系,這從《地形篇》中更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特點。這也與《計篇》以“五事七計”為主要內容的“廟算”完全呼應。出于對“知地”的重視,孫子不僅在《地形篇》大段論述“知地”,也在《九地篇》花費大量筆墨探討和總結各種地形條件下的戰法。可以說,“地”與戰術設計和戰術執行都密切相關,對戰爭勝負也構成了直接影響,地理與情報便由此而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孫子指出,“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孫子·地形篇》),對于“知地”的重視可謂溢于言表。
就情報觀而言,孫子與當下我們部分學者將情報僅界定為“彼方情況”或“敵軍情報”的做法有著明顯不同,卻與當今西方尤其是美軍相近。美軍的情報觀非常重視“彼己”的對比,又重視“天地”的支持。美國蘭德公司《戰爭中正在變化的情報角色》認為:“關于己方部隊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準確情報的需要,和知敵同樣重要。”②原文是:As important as knowing the enemy is the need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capabilities,limitations,and location of one’s own forces.轉引自張曉軍《武經七書軍事情報思想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頁。這一主張明確表達出對己方情報的重視,幾乎是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翻版。從美國《國際軍事與防務百科全書》有關“軍事情報”條目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美軍對地理情報等的重視。美軍認為:“軍事情報是針對外國、外國軍事組織和可能成長為軍事作戰地區的地理而進行的所有上述情報活動。”①熊劍平、儲道立:《孫子的戰略情報分析思想》,載《濱州學院學報》,2011年第1 期。作者將“作戰地區的地理情報”提到重要地位,也與孫子在本質上保持一致。從美軍有關情報的論述,我們可以不難發現孫子的情報觀已經迎來歷史回歸,地理與情報也正建立起日益密切的聯系。孫子從“知情”的角度出發,冷靜總結和分析了地形的作用,進而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孫子·地形篇》),將掌握地理情報與“料敵”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顯然并非過時之論。
三、地理與用兵
從篇章的安排情況來看,《行軍篇》討論的是如何“處軍相敵”,這就必然牽扯地形問題,《地形篇》則對如何“知地”和挖掘“地利”展開深入探討,《九地篇》則進一步結合兵要地理環境探討戰略戰術,以充分發掘軍隊的戰斗力。這其實也是非常合理而順暢的邏輯展開過程,體現出布局謀篇的巧思。
孫子對如何有效利用地理條件克敵制勝進行了深入探討,所論之“地”基本為“陸地”,對空、海作戰并無提及,這與孫子所處時代直接相關。其時并無海戰和空戰,戰爭基本都在陸地進行。圍繞“地理與用兵”這一主題,孫子有著不同形式的總結。
在《行軍篇》,孫子對無法滿足“處軍”的地點進行了總結,簡稱“六害”:“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諸如絕澗、天井、天牢等地,都非常不利于駐扎軍隊,即便行軍路過,也容易被敵軍包圍而陷入絕境,因此必須組織部隊迅速撤離。而且,這種地方對敵不利,對我也不利,高明的指揮員可以設法將敵軍逼向這一地帶,獲取主動局面。這便是“吾遠之,敵近之”的戰法。這里的“六害”,是就地理與用兵問題進行的初步總結。在《地形篇》和《九地篇》,孫子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
在《地形篇》,孫子將不同地形條件下的作戰之法總結為六種,總稱“六地”,同時也對容易導致部隊吃敗仗的混亂情況進行概括,總稱“六敗”。孫子反復叮嚀,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無非是希望對地理與用兵問題有著更為科學的總結。西方著名地理學專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曾說:“戰場的自然特點及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對進行謀算的軍事家而言具有重要意義。”②(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的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 版,第5頁。
其中,“六地”包括通、掛、支、隘、險、遠。所謂“通形”,指“我可以往,彼可以來”。道路四通八達,敵我雙方都可以自由來往,那就一定要占據地勢較高之處,居高臨下,視野開闊,容易占據主動。所謂“掛形”,是指“可以往,難以返”。這種地方固然可以進入,但難以返回,所以要認真觀察,切不可貿然出擊。所謂“支形”,是指“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這種地方其實是“相持之形”,尤其要注意不受到敵軍引誘。所謂“隘形”,是指咽喉之地。這是大軍出入的要道,如果搶先占據,就一定要派出重兵把守。一旦被敵軍占據,就不要貿然攻打。所謂“險形”,是指險要地形,一定要搶先占據視野開闊的高地。如被敵軍占領,就應立即撤離。所謂“遠形”,是指“勢均”之地,因為距離較遠而不利于兵力投送。要想勞師遠征,就會造成兵馬疲憊,難以取勝。
在分述“六地”之后,孫子總結道:“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孫子·地形篇》)孫子將掌握不同地形情況,按照地形條件靈活用兵,視為將帥的基本要求,這顯然是非常務實之舉。因為兩軍作戰是勝是敗,與地形條件始終息息相關。
接下來,孫子由此論題而深入,就如何避免“六敗”進行深入探討。所謂“六敗”,分別指“走、弛、陷、崩、有亂、北”。第一種是“走”,在敵我雙方占據差不多對等的戰爭條件時,如果將帥以少擊眾,以一擊十,那就只能招致失敗。第二、第三種分別為“弛”和“陷”,均就官兵關系而言:“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孫子·地形篇》)在孫子看來,如果士卒強悍,管理他們的軍官卻懦弱無能,就會導致部隊紀律松弛,缺少戰斗力。反之,如果軍官能力強,士卒能力弱,同樣也是缺陷。士卒完全沒有創造力,必然也會造成戰斗力的喪失。第四種是“崩”。這是就指揮體系或將帥關系而言,將領如果不服從管理,擅自出戰,將帥卻不知其真實才能,就會造成部隊的崩壞。第五種是“亂”,是“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孫子·地形篇》)引起,這是就管理問題而言,既包括對士卒的管理,也包括了對軍官的管理。身為將帥,如果性格懦弱,無法對部隊實施有效管理,士卒和軍官都不遵守紀律,排兵布陣必然雜亂無章,會就此導致部隊混亂局面,部隊喪失戰斗力。第六種是“北”。如果不能很好探知敵情,或以少擊眾或以弱擊強,或缺失戰斗力很強的沖鋒隊,都會導致戰爭失敗。
“六敗”既然放在《地形篇》加以總結,想必多少也與地形有關。在孫子的設計中,“六敗”是順應“六地”而推出。這種設計,其實按照“知論”的邏輯體系加以解讀,就顯得順理成章。出于對“知彼知己”的重視,孫子始終強調的是大情報觀。《行軍篇》的“相敵之法”論“知彼”,《地形篇》論“知地”,“六敗”則強調“知己”。在完成上述總結之后,孫子以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作為結尾,初步完成了其情報認識論的闡釋。“知”或“不知”,對戰爭勝敗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孫子認為將帥必須認清這些致敗的緣由,認為這是“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孫子·地形篇》)。在孫子看來,將帥情況不明、處置不當就必然會造成敗局,這其實也是對“失敗”進行的討論。鈕先鐘批評孫子“對于失敗的原因,以及應如何避免失敗的方法,都不曾給予足夠的重視”①鈕先鐘:《孫子三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274、5頁。,這種批評實在是不著邊際。之所以出現這種失當批評,也許正是因為他將《地形篇》等視為“層次較低”的內容,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
結合《地形篇》的“知地”,孫子對“戰道”進行了總結。在孫子看來,發動戰爭與否,主要依據“戰道”:“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孫子將國君的命令與“戰道”進行衡量,認為后者更為重要,更應作為將帥發起戰爭與否的主要依據,這是尊重戰爭規律的表現,也是基于地理與用兵的考察。受條件限制,國君和戰場距離較遠,如果在不知敵情的情況下還要保持對戰場的遙控指揮,便會帶來各種問題,吃到敗仗,損兵折將,便是勢在必然。因此,遵從“戰道”,從打贏戰爭的角度出發處理用兵問題,便是一種務實之舉。
四、地理與戰略
清人顧祖禹有云:“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②《讀史方輿紀要·總敘二》。應當說,這是一句非常中肯的評價。從《行軍篇》到《地形篇》,孫子對于軍事地理的論述漸次深入,到了《九地篇》已進入更高層次。其中不少內容,均可稱戰略地理學或地緣政治學。因為其中所論,均為研究戰略環境所不可或缺,如果認為其“對于戰略研究的重要性也較低”③鈕先鐘:《孫子三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274、5頁。,可能是在戰略學研究內容上與我們存在著某些差異。
在《九地篇》,孫子基于作戰態勢的不同,對地理環境進行了多種劃分,共為九種: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圍地和死地。第一種是“散地”,是指在本國境內與敵作戰。散,意為離散和逃散,是軍心渙散的表現。在家門口作戰,士卒容易分神,容易產生畏戰情緒,故稱“散地”。第二種是“輕地”,是指雖進入敵境,但仍在淺近地區作戰。由于距離己方大本營不遠,士卒可進可退,因而軍心并不專一。“輕”,既可以說士卒戰斗之志并不堅定,也可視為距離本國的國境線尚且不遠。二者之間也直接因果。第三種為“爭地”,敵我雙方誰先占領則對誰有利,因為爭地具有特殊的戰略價值,是雙方必爭之地。“爭地”既有戰略層面,也含戰術層面。就戰略層面來看,諸如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及各種要害地區等,都是爭地;就戰術層面而言,諸如交通要道、險要關隘等,都是爭地。這些地方,誰搶先占據就會對誰有利。第四種為“交地”,是指敵我雙方都可以自由出入之地。這里的“交”,既可以指邊界交接,也可指交通發達,出行比較便利。由于敵我雙方都可自由出入,隊伍容易被切割成塊,故需要保持陣型的完整和隊伍的連貫。第五種為“衢地”,是指同多國接壤,誰先占據就可以得到更多支援。春秋時期的鄭國和宋國就是處于這種地帶,也可稱四戰之地,容易迭為戰場,飽受戰爭之苦。就這一點而言,孫子的討論已經有點類似西方的地緣政治學,注意“基于地理因素考慮而制定安全政策規劃”①(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的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 版,第6、7頁。,且“不可避免地牽涉地理意義上的各國領土關系”②(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的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 版,第6、7頁。,注意結交鄰國,尋找支援。孫子所論,未嘗不可稱之為古代地緣戰略論。第六種為“重地”,是指深入敵境,三軍背后的城邑已經很多。如果和“輕地”進行對比,可以不難對“重地”有所體察。第七種為“圮地”,是指山高水險、林木茂密、水網縱橫之地,這些地段因為道路毀壞而難以通行,三軍進退維艱,容易遭到對手沉重打擊。第八種是“圍地”,是指前進道路狹窄,退兵之路難尋,敵軍較為容易以少擊眾。我方很容易被對方包圍,處境非常危險。第九種是“死地”,只有疾速奮戰才可以存活。身處“死地”,求生艱難,只有拼盡力氣,向死求生。
上述關于戰爭地理的分類,所依據的標準基本是與己方大本營的距離遠近,關注的是作戰條件對己方有利與否,而且層次清晰,逐級深入。“九地”放在今天,基本都可視為戰略層面的內容。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進行列舉,也想說明其中并不存在“層次較低”的內容。至于“死地”放在最后,是為了突出和強調。《九地篇》重點論述的就是死地作戰,是長途奔襲的“為客之道”。吳如嵩說:“《九地》主要論述的是戰略進攻問題。”③吳如嵩:《孫子兵法新說》,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1月第1 版,第166頁。有關這一點,我們已有專門論述。
針對不同的地理條件,孫子也分別提出不同的處置方法或戰法。對于散地,孫子要求統一部隊的意志;對于輕地,必須保證部隊前后緊密相連;對于爭地,則需迅速出兵抄到敵人側后;對于交地,需要懂慎布置防守;對于衢地,要注意鞏固與諸侯的同盟關系;對于重地,要注意保證軍隊的給養;對于圮地,需命令軍隊迅速通過;對于圍地,需要注意堵塞缺口;對于死地,必須要顯示出必死的決心。所有這些,都是依據軍隊在不同戰場環境之下的心理變化,所以夸贊孫子為軍事心理學的大師毫不為過。
孫子高度重視軍事地理,并將其與戰略戰術問題聯系在一起,這對中國古代軍事學術史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古代兵家一向關注兵要地理,并且就此論題有著深入探討。這一現象在明代兵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明代萬歷年間,軍事地理學與兵學研究聯袂興起,備受矚目。《籌海圖編》等著作的出現是最為顯著的標志。《武備志》也有大量討論軍事地理的內容。茅元儀提出了邊防、海防、江防并重的戰略思想,以多卷篇幅詳細記載了明代地理形勢、關塞險要、海陸敵情等情況,從軍事學角度考察戰略地理形勢,孫子的軍事地理學由此而得到發揚光大。基于明代后期軍事斗爭形勢的考察,茅元儀更加重視海洋地理,認為求得百歲之安,關鍵就在于“拒之于海”①《武備志》卷209《海防》。,不僅要充分掌握海防特點,還應根據海岸線特點和海洋地理特點進行布防。《籌海圖編》等書同樣深度探討海洋地理,結合海岸地形和邊疆海防討論海防戰略并總結防衛經驗等。到了明末清初,軍事地理研究更是發展到高峰期,系統論述軍事地理的著作《讀史方輿紀要》便于此時誕生。因為立意和主題都是軍事地理,顧祖禹在寫作過程中著重記述的是歷代興亡、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系,進而試圖從中推導出地理與戰爭勝負的聯系。清代張之洞評價該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②《書目答問》卷3。,并將該書列入兵書之中,對這部書的軍事價值給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