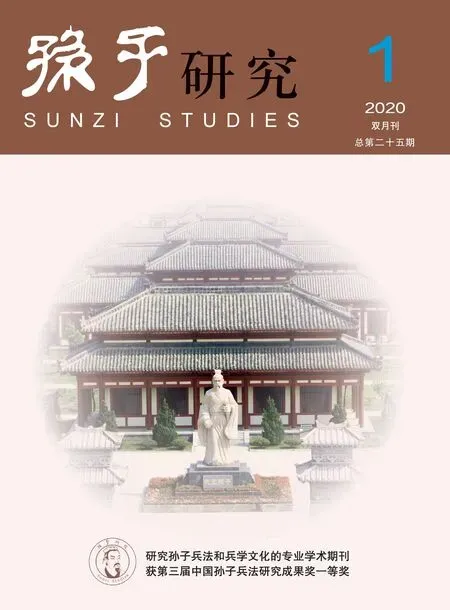《孫子兵法》軍事倫理思想略論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兵書,被譽為“百世談兵之祖”。《孫子兵法》內涵豐富,體系完整,論述深刻,影響深遠。關于《孫子兵法》思想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就其軍事倫理思想而言,研究還相對薄弱。本文擬對《孫子兵法》的軍事倫理思想進行總結和歸納,希望更多學者共同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一、孫子軍事倫理思想主要內容
孫子生活在諸侯爭霸、戰爭頻繁的春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社會最動蕩、變革最劇烈的時代,也是中國思想文化奠基的時代。中國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如《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都產生于這一時期。和西周時期相比,春秋時期在軍事上、戰爭上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戰爭指導者重視運用謀略,強調“伐謀”“伐交”,注重巧妙用兵,主張“兵者詭道”“兵以詐立”。
《孫子兵法》是春秋時期的產物,是春秋時期戰爭經驗的總結。《孫子兵法》十三篇,六千余字,主體內容是論述戰爭的戰略、戰術及治軍問題,但幾乎在每一篇中,都有關于軍事倫理的內容。概而言之,《孫子兵法》的軍事倫理思想,主要包括戰爭倫理思想、作戰倫理思想、治軍倫理思想和將帥倫理思想等內容。
(一)《孫子兵法》的戰爭倫理思想
《孫子兵法》的戰爭倫理思想,主要表現為重戰、慎戰、備戰、勝戰并重的戰爭觀念,表現為“自保而全勝”的戰爭目標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理想。
《孫子兵法》開篇寫道:“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篇》)孫子指出,戰爭是關系到國家存亡的頭等大事,統治者必須重視戰爭、慎重對待戰爭。重視戰爭,謹慎對待戰爭,不輕啟戰端,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是《孫子兵法》全書一以貫之的思想。正如孫子所言:“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用間篇》)
基于戰爭的重要性和危害性,孫子強調做好戰爭準備。“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篇》)孫子強調戰爭的危害,同時也認識到正義戰爭的積極意義,因此,他不一概反對戰爭,而是主張通過正義戰爭,達到“自保而全勝”“勝敵而益強”的目的。
“自保而全勝”是孫子的戰爭目標。孫子認為,將領指揮作戰,首先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戰勝敵人,而是如何不被敵人戰勝。具體地說,就是“先為不可勝”,即盡可能減少己方的弱點、短板、破綻,使敵方感到無機可乘、無懈可擊,“以待敵之可勝”,即耐心等待敵方弱點的出現和暴露,尋求和不放過任何敵方可以為我所勝的有利條件和時機,從而到成“自保而全勝”的戰爭目標。
孫子認為,戰爭的勝負是由道、天、地、將、法這五個方面因素決定的。這五個方面涵蓋了從事戰爭的政治因素、天候因素、地理因素、將帥因素和法制因素等內容。這些因素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籌劃戰爭、準備戰爭和贏得戰爭,要從這些因素入手。
孫子的戰爭理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認為,高明的戰爭指導者應該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百戰百勝”并不是最好的選擇,戰爭的理想是“屈人之兵而非戰也”,不費一兵一卒,通過“伐謀”“伐交”,用強大的兵威懾服敵人,“兵不頓而利可全”,“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的戰爭倫理思想,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他大膽突破西周以來“以仁為本,以禮為固”的戰爭觀念,從利害的角度看待戰爭,主張“兵以利動”。在“春秋無義戰”的時代背景下,孫子汲汲追求的不是“義戰”,而是勝戰、“自保而全勝”。這是春秋時期的國家生存之道,也是當時人們對戰爭的理性思考。
(二)《孫子兵法》的作戰倫理思想
“兵者詭道”“兵以詐立”是《孫子兵法》用兵作戰的重要原則,也是《孫子兵法》作戰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
孫子提出了著名的“詭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計篇》)目的是隱真示假、“示形動敵”,“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勢篇》) “形人而我無形”,“形兵之極,至于無形”。(《虛實篇》)進攻時,如同“動于九天之上”,防守時,如同 “藏于九地之下”,變化莫測,敵人不知所蹤,從而達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戰勝敵人的目的。
孫子的“兵者詭道”思想,反映了春秋時期戰爭從以“禮”用兵到變詐之兵的發展進程,揭示了軍事斗爭的客觀規律,推動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但這一思想,與儒家學說相沖突,因此,引起了后人對孫子的非議和批評。如班固在《漢書》中對孫子本人及其“任詐力”的觀點大加斥責,甚至說他“身誅戮于前而國亡于后”(《漢書·刑法志》),是應得的報應。實際上,孫子的詭詐理論講的是軍事問題,適用于軍事和戰爭。并且,孫子既講詭道,也講仁信。以詭道求勝,以勝求仁,這才是孫子詭道思想的真正含義。
(三)《孫子兵法》的治軍倫理思想
在治軍方面,孫子也多有建樹,提出了以“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為特色的治軍思想和治軍倫理思想。
孫子說:“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行軍篇》) “令之以文”,是指通過教化手段達到軍令暢通的目的;“齊之以武”,則是說通過法規約束的手段,達到部隊整齊劃一的目的。孫子認為,在治軍問題上,文、武二者不可偏廢。“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形篇》)對待士卒,一方面,孫子強調要關愛士兵,“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行軍篇》)。將帥對待士卒如同對待嬰兒,士卒就可以跟隨將帥赴湯蹈火;將帥對待士卒如同對待愛子,士卒就可以與將帥同生共死。“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如果不關愛士兵,士兵就不會服從,不服從就無法使用。另一方面,孫子也強調嚴格紀律,嚴明賞罰,“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孫子重視軍隊紀律,把“法令孰行”作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因素之一。
孫子強調,“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行軍篇》)。軍隊管理必須要抓好平時的養成教育,認為軍隊平時法令不行,戰時就很難服從統一指揮、形成戰斗力。他認為,令能“素行”的關鍵在“與眾相得”,即將官與士卒上下同心,用今天的話說,叫官兵“團結融洽”。官兵是否“相得”,關系是否融洽,是形成軍隊戰斗力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孫子認為,治軍做到了“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就會戰無不勝。
(四)《孫子兵法》的將帥倫理思想
孫子認為,戰爭關系著國家的存亡和軍民的生死。將帥統兵作戰,是“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責任無比重大。一名優秀的將帥不僅要具備“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計篇》)這“五德”中,孫子以“智”為首,多謀善斷是將帥的首要素質;“信”,既是說將帥要言而有信,又是說要令行禁止,在士卒中擁有威信;“仁”,是指將帥要具備仁愛的品德;“勇”,勇敢精神是將帥必備的素質;“嚴”,是“仁”的補充,要求將帥既要嚴于律己,又要軍紀嚴明、嚴格治軍。這為將之“五德”,相互聯系,相互補充,是孫子對將帥道德修養提出的總要求。
孫子在提出“五德”的基礎上,又提出“五危”:“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變篇》)孫子認為,“必死”者會中敵人之計被殺;“必生”者會被俘虜;“忿速”者會失去理智;“廉潔”者會遭到侮辱;“愛民”者會被敵人煩擾。以上五點,都是將帥容易犯的過錯,也是用兵的大忌。將帥修養上的這五種缺陷必然導致“覆軍殺將”的嚴重后果,不可不認真對待、引為鑒戒。“五危”是對“五德”觀念的深化和進一步闡發。
孫子指出,將帥不但要具備“五德”、戒除“五危”,而且要精通指揮、善于用兵。“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九變篇》) 孫子指出,軍事上有“走”“弛”“陷”“崩”“亂”“北”六種必敗的情況。孫子認為,以上六種情況,是導致作戰失敗的原因。將帥對此負有重要責任,不能不認真考察研究。
孫子認為,將帥不但要業務過硬,還要品德高尚,淡泊名利,忠于國家和人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地形篇》)在戰場上機斷指揮,勇于進退,敢于負責,一切從戰場實際出發,堅決按戰爭的規律決定自己的行動。根據作戰規律有必勝把握的,即使國君說不要打,堅持打也是可以的;根據作戰規律不能取勝的,即使國君說要打,不打也是可以的。“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在對我有利的情況下,進兵求戰,不是為了沽名釣譽;在不利的情況下,退兵避戰,也決不推卸應負的責任。這樣的將帥,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二、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的理論特色
(一)客觀冷靜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人們客觀地認識世界的方法。在先秦諸子中,《孫子兵法》無疑最具客觀理性精神。
孫武反對迷信鬼神天意,他對“天”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計篇》),認為“天道”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從而打破了人們對“天”的迷信與崇拜,“天”不再是天下萬物的主宰,而成為一種客觀的自然的存在,和當時把“天”視為人格神的宗教思想劃清了界限。孫武進一步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反對采用陰陽雜占等迷信手段預測戰爭,提倡基于客觀事實分析戰爭、籌劃戰爭,把戰爭的勝負歸因于物質條件的準備和主觀性的發揮。
此外,《孫子兵法》中有許多以征引“五行”觀念來論證戰爭的客觀物質性的內容。如《勢篇》說:“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在這里,孫子把“五行”看作物質世界的基本屬性,并將世間萬物的發展演變歸結為“五行”的本質內涵。
從《孫子兵法》關于戰爭的謀劃、用兵原則、戰爭主動權、爭取先機、機動作戰、行軍駐扎、軍事地形、火攻之法的論述,不難發現,客觀的理性精神是《孫子兵法》印記鮮明的思想特色。這樣的理性精神和認識方法,在中國軍事思想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都具有十分寶貴的價值和意義。
(二)鮮明的功利主義傾向
在春秋以前的西周時期,重視禮樂,講求仁政,主張“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為正”(《司馬法·仁本第一》)。認為治國治軍,都需要“以仁為本”;對待諸侯國,也講求仁義禮讓,如“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成列而鼓,爭義不爭利,舍服,知終知始”(《司馬法·仁本第一》)等。戰爭是為了維護周王朝的統治,“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單純地追求國家利益而已。
到了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戰爭的目的轉為打敗對手,稱霸諸侯。孫子明確提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軍爭篇》),戰勝敵人,壯大自己。用兵作戰,要“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軍爭篇》)。為了要減少戰爭的消耗,孫子主張“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智將務食于敵”“取敵之利者,貨也”(《作戰篇》)。正如孫子所說,“兵以利動”,利益才是國家從事戰爭的動力和目標。歷史地看,孫子功利主義的戰爭倫理觀,符合當時新興勢力的要求,與社會發展潮流一致,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
(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孫子兵法》研究戰爭,是以戰爭中的對立矛盾為核心而展開的,如力量的強弱、人數的眾寡、軍隊的治亂、將帥的賢愚、士卒的勇怯、謀算的得失、部署的虛實、兵力的專分、人員的勞佚、戰勢的奇正、戰法的攻守、時間的速久、道路的迂直、地形的死生、處境的安危等等。這些兵學范疇,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并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
孫子強調分析問題,要立足矛盾的雙方,兼顧事物的兩面,如:“知彼知己”,“知得失之計”,“知動靜之理”,“知死生之地”,“知迂直之計”,等等。明確提出了“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了解事物的兩面性,目的是促其轉化,為我所用。孫子主張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使戰爭態勢朝著于我有利的方向發展,為奪取戰爭勝利創造條件。
孫子對戰略、戰術問題的論述,也充滿了辯證的思想智慧。孫子既高度重視客觀因素對戰爭勝負的決定性作用,又極其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伐謀伐交,靈活用兵,積極爭取勝利;既提出“勝可知而不可為”,強調客觀條件的重要性,又認為“勝可為也”,主張發揮主觀能動性以獲取戰爭勝利;既主張“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又反對“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等等。這些觀點,看似相互矛盾,實質上內在統一,體現了孫子思想的辯證特點。
(四)濃厚的民本主義色彩
春秋時期,民眾多寡,民心向背,往往決定著國家的興衰。因此,當時許多的思想家都提出重視人民、以民為本的思想。這一思想在《孫子兵法》中也有大量體現。
孫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計篇》)又說:“上下同欲者勝。”(《謀攻篇》)他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正”(《形篇》);“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行軍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地形篇》);等等。很顯然,孫武將戰爭的勝負同政治清明與民心向背聯系起來。即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上下同欲”“與眾相得”,為此,要“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這些都體現出孫子思想濃厚的民本主義色彩,也是孫子理論超越時代、具有歷史進步性的表現。
毋庸諱言,孫子的軍事倫理思想存在著歷史的和階段的局限性。如忽視戰爭的道德支撐和制約,過于強調戰爭的功利目的;無視戰爭的侵略性質;主張“愚士卒之耳目”“若驅群羊”的愚兵思想;等等。對孫子的這些思想,需要仔細甄別,揚長避短,絕不能全盤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