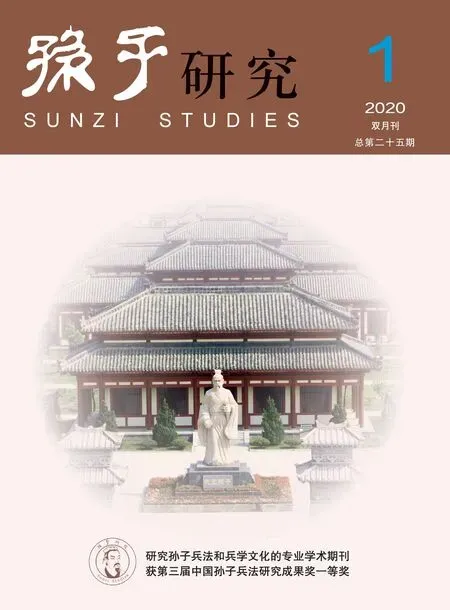太平天國敗亡的兵學考量
1851年1月11日,如狂飚自九天而落,在廣西桂平縣偏遠的紫荊山下的金田村,爆發了名為太平天國的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數以萬計的拜上帝信徒,呼嘯著經永安沖向廣西省會桂林,然后沿著奔流北上的湘江,沖過湖南省會長沙,直下岳陽。1852年1月,順利攻占湖北省會、號稱“九省通衢”的武昌。再后水陸并進,沿長江東下,一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猶入無人之境,當年3月即占領東南重鎮、清朝兩江總督駐節地南京,改名天京,安放下這個政權的首都。至此,僅僅經過一年零三個月,太平軍就縱橫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六省,發展成超百萬的大軍,建立起與清朝對峙的政權,使朝野驚詫,令世界刮目。
一個由不第秀才領導,由一群名不見經傳、幾乎都是文盲組成的隊伍,何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創造了如此驚人的奇跡,讓大清帝國近二百年的看似鐵打的江山震顫不已?原因說來極其簡單,一是太平軍領袖關于“天國”的許諾使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看到了翻身的希望,紛紛加入造反隊伍并冒死拼殺;二是承平歲月養尊處優造成的清朝各級官吏及其軍隊八旗、綠營腐敗無能,難以抵御太平軍勇猛的重擊。彼時清朝各級官員和軍隊不僅無統一指揮和調度,而且幾乎個個貪生怕死、愚蠢愚昧,最典型的例子是:兩江總督陸建瀛居然在太平軍圍攻南京的危機時刻躲進總督衙門,誦經拜佛,祈求神靈的佑護渡過難關。顯然,面對太平軍的拼死沖殺,清朝從皇帝到各級官吏、將帥兵丁,全都懵懵然、訝訝然,驚嚇得目瞪口呆,無所措手足。待到少數清醒者如曾國藩組織團練以謀對策的時候,太平天國的軍旗已經獵獵飄揚在南京城頭了。
然而,進入南京的太平天國盡管在此后三年還能擴大戰果,但在1856年9月發生“楊韋事變”的內訌后基本上終止了前期順利發展的勢頭。它日日陷于同清軍尤其是其中的勁敵湘軍和淮軍的苦戰中。當年12月武昌失守。自此,太平軍開始走下坡路。戰場上敗多勝少,屬地得少失多。1864年7月天京陷落。四年以后,太平軍余部最后被撲滅。當太平軍的各路領袖和將帥一一走上斷頭臺的時候,清朝皇帝和各級官吏也伴著自我標榜的“同治中興”彈冠相慶,誤以為清帝國夕陽的余輝是又一次壯麗的日出。
太平天國面對的是一個已經歷時近兩百年、內憂外患、腐敗墮落、暮氣沉沉、病入膏肓的封建政權,它為什么在與之激烈較量十四年后最終敗亡,奏出了《薤露行》的哀哀悲歌?其實,盡管太平天國敗亡的原因十分復雜,但只要從兵學上認真加以解讀,其敗亡之必然性也就顯現無遺了。
一
《孫子·計篇》: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撇開屬于自然環境方面的天、地因素,我們分析太平軍在“道”“將”“法”等方面的局限和失誤,對比敵方的相應之策,基本上能夠找到它敗亡的必然之因。
我們姑且將太平天國的“道”擴而大之為政治理想、制度設計、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等方面,看它究竟較之清朝優長了多少?
太平天國是以拜上帝的宗教信仰武裝群眾,以地上“天國”的許諾引領群眾對未來的期望。而這兩者,在實質上,一是麻醉民眾的鴉片,二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都經不住時間的考驗。請看經常被學者引用的洪秀全的兩則“革命理論”:
《原道救世歌》:
天父上帝人人供,天下一家自古傳。
積善之家有余慶,積惡之家必余殃。
順天者存逆天亡,尊崇上帝得榮光。
《原道醒世訓》:
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人,盡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
前者僅僅是摭拾西方基督教義的余唾,后者不過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大同”理想的表述,根本談不到什么創造性。這些理論和理想絕對敵不過中國傳統文化多年凝結的忠、孝、節、義、仁、禮、智、信的價值觀和民本、仁政、好皇帝、清官等的政治理念。特別是,太平軍一路上毀廟破寺,砸孔子牌位,焚燒經書,將江南貯藏《四庫全書》的三大閣(揚州大觀園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和杭州圣因寺文瀾閣)燒得只剩下杭州圣因寺文瀾閣的半閣,又將歷代典籍篡改得面目全非,這不僅引起廣大知識分子的忌恨,而且也難以為多數民眾所接受。它舉行的開科取士應者寥寥就是明證。曾國藩看準這一點,在《討粵匪檄》中大肆渲染: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圣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官,毀宣圣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朝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顯然,曾國藩描準了太平天國的軟肋,其義正詞嚴的封建衛道宣示,更能契合一般百姓的理念。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宗教意識的淡薄使廣大百姓很難堅定對上帝的信仰。特別是,洪秀全宣揚的天國理想與他實際上的制度設計完全相反,被裹挾的民眾很快就會產生上當受騙的感覺。太平天國的政治理想突出體現在《天朝田畝制度》和后來洪仁玕撰寫的《資政新篇》中,但兩者都不具備實踐的品格,始終停留在紙面上。而它實際上實行的是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封建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參加太平軍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很快發現,所謂“天國”只不過是洪秀全等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奢侈享受的安樂國,而作為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最吃虧的成員,他們的命運在太平天國并沒有真正改變。
太平天國自永安建國起,即根據《周禮》加以損益建立起自己的政治體制。定都南京后,進而擴充整備為更為龐大復雜的官僚機構。據記載,僅僅是天王府的屬官即多達1600 余人,屬官之下又有屬吏達萬人,且級別都很高。一個為天王捧茶打雜的童子擔任的侍臣,竟相當于軍中統帥萬人的檢點。其他王府也都建立起具體而微的機構。最盛時,整個中央機構的官員多達300 萬人,是天京居民的10 倍。它同時建立起最嚴格的等級制度。在頒發全體軍民周知的《朝天朝主圖》中,明確規定統治集團分三圈:一是里圈超等者,天王、王長兄次兄、子侄、駙馬、幼東王、幼西王。洪秀全9 歲的兒子封幼天王,稱“天孫”,配4 個幼娘娘。洪仁發、仁達的兒子都封王,有的剛生下來,如洪仁發的兒子垌元即封王。二是中圈二等稱“胞們”的一群人,洪仁玕、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特爵”。三是外圈的“列爵王”。再后是兩檔,一是參加金田起義的“開朝王宗”,二是最初跟隨洪秀全進入天京10年間的“開朝勛臣”。花縣同鄉凡洪氏族人來天京投奔者,一律封王。到后來,為了滿足將士升官發財的欲望,不斷胡封濫賞,最后封到2700 多個王爵,造成官多民少,將多兵少。例如,廣西人、為洪看門的吉有余,年過70,被封為“夢王”;一字不識的宰殺雞鴨的廚師安慶人董金泉,也被封為“夢王”。最后天京被湘軍攻破時沒有出來的王爺就有上千人。而每個王府都設一套六部辦事機構,有數以千百計的人為之服務。例如陳坤書在常州做護王,屬于最低級的列王,其王府就設有六部,有數以百計的官員為之服務,出門即乘8 人抬大轎,由正典鑼鳴鑼開道。于是,官越設越多,任命越來越濫。丞相開始是高官,后來在其上新設的官職越來越多,各王府的丞相就降為如后世連排級的小官了。在太平天國統治區,等級最末端的依然是農民,他們成為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被統治者。所以它對官員的重要懲罰手段之一就是“黜為農”。
不同的等級有法定不同的權利和義務,高等級王爺的奢侈享受絕不比清朝皇帝和其他達官貴人遜色,最基層小吏的享受也不比清朝的鄉村小吏差。你看,自永安起,洪秀全與各級官員開始坐轎,王府均設典輿衙,轎頭是指揮級官員。只管25 戶的兩司馬也乘坐四人抬的小轎。凡參加永安建國的各類人員均獲得“世食”的功勛,可以世襲官位。天王和其他諸王屬于“國宗”,享受特殊待遇。天王在永安時已經有了36 個妻子,進入武昌,又選了60 名絕色女子為妻,再后各路將領不時進獻,達到南京后即數以百計,統稱月亮,為了便于管理,就編號以示區別。這種配備已經遠遠超過清朝皇帝。別以為洪秀全說過“天下多女人,盡是姐妹之群”,天國女人就能獲得與男人平等的地位。在天王府里,月亮們只能是絕對服從他的性奴和玩物。他給小月亮定下的杖責戒律就使人大開眼界:
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夫主三該打,問主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凈五該打,說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嘴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①轉引自盛巽昌《實說太平天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頁。
其他封王的高級官吏與天王一樣擁有數以十計的妻妾,而在太平天國的基層實行的是嚴格禁欲的男女分營的制度。
洪秀全的飲食起居從永安建國起就有了帝王的氣派。在進軍南京的船上,他每飯十簠,山珍海味,樣樣俱全。進饌時有8 個鼓手奏樂,兩人站船頭敲大鑼百響。到了南京,天王禮拜及上食,鳴鉦64 聲,奏樂三次。侯、丞相鳴鑼48 聲,檢點、指揮36 聲,總制、監軍24 聲,軍帥20 聲,師帥16 聲,旅帥12 聲,卒長10聲,兩司馬8 聲。為此,天王府設典天樂300 員,典天鑼48 員,東王府設典東樂240 員,典東鑼32 員,其他依次減少。天王府前建有兩座黃琉璃瓦的鼓吹亭,其他王府亦有此類建筑。天王及各級地方官員“每餐必鼓吹”“食必用樂”。
與洪秀全和其他高級官吏奢侈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太平天國的基層士卒是在“圣庫制度”下過著有時甚至連溫飽都難乎為繼的生活。
太平天國一開始通過沒收清朝府庫和富人財產,也包括劫掠一般百姓的家資維持“圣庫制度”,解決經濟問題。但這種辦法只是實現財產轉移而不能創造財富,所以后來它在自己較穩固的統治區就推行與清朝基本相同的稅收制度,在農村也基本維持原有的經濟關系,如地主和佃戶的租地交租制度。被史學界刻意宣揚的“我交長毛租不交地主租”似乎是廢除了封建剝削,其實充其量也只是將地主置換成了太平天國的官府,并且不久又將已有的租佃關系視為合理合法,甚至派軍隊下鄉幫助地主催逼佃農交租。太平天國晚期,屬地苛捐雜稅眾多,據《避寇日記》記載,嘉興地區就有房捐、火藥捐、柴捐。海寧百姓外出經商需剃頭,要交剃頭費。還有禮拜捐、海塘費等。《難中記》記載,杭州市民還要交“出灰捐”(造火藥用的草木灰費)。另外,建造王府也要百姓捐錢,官員生日、晉升、赴任都要百姓交錢。這表明,太平天國所到之處,并沒有改變封建的經濟制度。
太平天國的腐敗比之清朝政府同樣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是制度腐敗:規定它的官僚群體有奢侈享受的權利,一方面是各級將領和官員利用特權肆意掠奪、貪污受賄,在極短時間內積聚起巨量財富。洪秀全在天京十多年,已經積聚了數不清的金銀財寶,但他永無厭足,1863年,當蘇州危機、李秀成要求前往救援時,他竟要求李交出10 萬兩銀子作為離開天京的條件,李在湊足7 萬兩并保證欠款以后補齊后才得以出京。1864年,天京饑荒,要求離開的百姓每人須交5 兩銀子才能放行。天京其他王府,星羅棋布,同樣積聚了大量錢財,湘軍攻入后,肆意搶劫,得銀10 萬兩以上者達百余人。像提督蕭孚泗帶著劫掠的巨額財物辭官回家享福。曾國荃將所劫掠財物用幾十條大船運送回鄉,受到沈葆楨彈劾,他也索性辭官回家。就是被史家倍加贊譽的李秀成,在蘇州也是紙醉金迷、花天酒地,忠王府造了三年尚未完工。李鴻章評價這座王府:“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秀成在天京和蘇州的王府皆蓄有眾多妻妾。每逢生日,屬下必進金銀財寶和漂亮女人。他還索賄受賄,永昌劣紳徐佩瑗一次就向他獻白銀6萬兩和兩個漂亮女人。蘇州城破,淮軍看到的忠王府庫金銀財寶無算,還有藏書10 萬余卷,多屬稀世珍本。另有名硯300 余方,其中就有顏真卿的歙硯“卿云捧日硯”。李鴻章得到李秀成的象牙床和沉香木床,對其珍貴奢華也驚異不置。太平軍所有王爺和各路將領,根本無視“圣庫制度”,紛紛私設小金庫,積聚金銀財寶。1863年12月17日,湖州守將陳殿選開城納降,小金庫竟有60 多萬兩銀子。雖不能要求太平天國的領袖和將帥個個都是苦行僧,也不能要求他們的物質待遇絕對與士卒保持一致,但他們一開始就如此追求物質享受,如此奢侈腐敗,如此展示暴發戶的貪欲,較之歷史上的其他農民起義軍領袖和將帥們顯得特別突出和另類。在他們身上,根本看不到一般貧苦農民勤勞節儉的生活作風,更多顯現的是流氓無產者“今日有酒今日醉,何懼明天就斷頭”的心態和行事風格。
以往的不少歷史著作,都贊揚太平天國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保持了民族尊嚴,似乎與清朝的屈辱妥協形成鮮明對比,這也是一種刻意美化。其實,太平天國從上到下,幾乎所有人對外國侵略者都缺乏明確的認識,且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1858年11月,英國特使額爾金乘軍艦進入長江,溯流而上,造訪太平天國統治區,希圖從那里獲得中英《天津條約》攫取的權益。太平軍安徽太平守將熊光明寫信給他,“請求洋兄弟給予全力協助,消滅妖船妖軍”。蕪湖守將侯裕田照會說:“弟與麾下原系天父上帝之子,均是天兄耶穌之弟,彼此情同手足,誼切同胞。”英艦經浦口時遭到太平軍炮擊,洪秀全給額詔書,承認失誤,并稱“已將全部無知歹徒斬首”。詔書中有如下內容:
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穌真天兄,爺哥帶朕坐天國,掃滅邪神賜光榮,西洋番弟聽朕詔,同頂爺哥滅臭蟲。
天國爾來今既來,西洋番弟把心開,朕前上天見爺排,萬國扶朕上天臺。爺排定定今來到,替天出力該又該。替爺替哥殺妖魔,報爺生養戰勝回。
西洋番弟朝上帝,爺哥帶朕坐山河。朕今實情詔弟等,歡喜來朝報爺哥。朕據眾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詔眾臣禮相待,兄弟團圓莫疑狐。(《太平天國文書匯編》)
真實的歷史昭示,如果說清政府對外國侵略者是仇視、屈辱、妥協甚至是賣國的,那么,太平天國則將外國侵略者當成了具有一致信仰的志同道合的親兄弟,說它的認識比清王朝更糊涂應該符合事實吧?!
以上事實表明,太平天國的所思所想、所設所立、所作所為,絲毫都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定義不沾邊。它實質上不過是與清朝統治集團一樣的封建的軍事政治集團。它所堅持的“道”與清朝的“道”沒有本質的區別,與曾國藩宣揚的“道”相比,倒是差了一個層次。這樣的“道”,能夠“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嗎?不必諱言,面對清王朝,太平天國并沒有登上“正義”的道德高地,在“道”上,它已經輸給了曾國藩!
二
太平天國與清王朝的軍事斗爭堅持了14年,其間,曾經打了不少漂亮仗:順利進據長江南北,掃蕩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幾次打敗湘軍的精銳之師,逼得老謀深算的曾國藩三次羞愧自殺,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勝利,同時鍛煉出楊秀清、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出類拔萃的將帥。然而,通觀整個爭戰進程,以《孫子兵法》的“將”“法”和各種戰術原則盱衡,再對比湘軍、淮軍的戰略謀劃、情報收集和戰場指揮藝術,不能不說太平軍從頭至尾都存在致命的缺陷。
太平軍僅用一年的時間即拿下武昌、安慶、南京,占據了中國東南半壁的財富之區。輕易獲得的勝利使它的領袖們產生了嚴重的輕敵麻痹思想,從而引來一系列戰略決策和戰術指導的嚴重失誤。首先,太平軍最大的失誤,是它從頭至尾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規劃,沒有一個徹底推翻清王朝、奪取全國政權的頂層戰略設計。在僅僅占領長江流域少數城市鄉村、還沒有大面積鞏固根據地的情況下,就貿然派兵北伐,而后又未能全力以赴支持北伐軍的作戰,致使北伐軍在冀、魯、津、晉等清朝統治最牢固的地區艱難轉戰,招致全軍覆沒,大大消耗了力量,嚴重影響了士氣。中后期,盡管局勢變得越來越對太平軍不利,卻仍有挽回的余地。這時的關鍵是確保武昌、安慶不落敵手,確保長江中下游連成一氣,為日益殘酷的爭戰保有穩固的人、財、物的供應基地。可是在武昌、安慶形勢危殆的時刻,太平軍忙于掃蕩清軍的江南江北大營。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最兇悍的敵人是湘軍和淮軍,而不是戰斗力日趨弱化的江南江北大營。更認識不到,江南江北大營的存在恰恰能夠導致清軍內部八旗、綠營和團練之間互相牽制,頻繁扯皮,指揮不一,可以給自己造成許多致勝空間。而江南江北大營的掃蕩,正好幫了曾國藩的大忙,使他得以拿到夢寐以求的兩江總督的位子,統一清軍的指揮和后勤供應系統,大大增強了力量。最后,當天京被湘軍長期圍困、城破指日可待的情況下,洪秀全斷然拒絕李秀成“讓城別走”的戰略轉移計劃,失掉了最后一線轉危圖安的生機,敗亡的時日也就大大提前了。正因為缺乏整體的戰略規劃,數支太平軍各自為戰,一直沒有主攻方向,缺乏戰略和戰役的密切協同。有些戰役,往往勝利之門已經開啟,卻功虧一簣。其次,太平軍第二個最大的失誤是始終沒有明確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它從廣西出發,邊打邊走,奪取的地方隨占隨丟。兩湖、皖、贛、蘇、浙人口密集,生產發展,商貿活躍,經濟繁榮,稅負幾乎占全國之半。身處如此得天獨厚的財富之區,太平軍卻沒有在占領之后迅速建立地方政權,恢復秩序,以求牢固掌控,而是每經一個地方,隨即大肆劫掠,然后裹挾部分人口離開。致使尾隨的清軍能夠迅速重建政權,恢復秩序,訓練民眾,增強軍事力量,導致太平軍回攻時付出更慘重的代價。如武昌、九江、南昌、安慶、廬州、蕪湖等沿江重鎮,都是先占后棄,然后再花重大代價回攻。北伐進軍更是孤軍深入,邊占邊丟,后援不繼,陷于四面皆敵的困境。沒有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最大危害是沒有穩固的戰略后方,也就難以保證源源不絕的支持戰爭的資源,“圣庫制度”也就難乎為繼。到了晚期,太平軍的根據地意識雖然有所增強,但時不我待,面對猛撲過來的湘軍、淮軍和外國侵略者組織的多支洋槍隊,奪一城,守一地,都要付出血的代價。當最后一點點根據地喪失凈盡的時候,天京淪陷的時日也就屆臨了。再次,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文化素養都不高,軍事素養更低,他們指揮作戰,全憑悟性和耳食的那點《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軍事知識,盲目沖動,歪打正著,全仗血氣之勇和人海戰術拼殺。盡管在對付腐敗懵懂的八旗和綠營時還能夠較多取勝,但在對付精于治軍和戰略戰術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指揮的湘軍和李鴻章等指揮的淮軍時,就只能是捉襟見肘、勝少敗多了。洪秀全根本不懂軍事,也沒有到前線指揮過任何一場戰役。但由他掌控全局,隨意發出許多昏妄愚蠢的指令。如天京保衛戰的關鍵時刻,他自作聰明,制定“圍魏救趙”之策,命令李秀成進軍皖北和湖北,走了一步攸關天京存亡的臭棋。因為皖北和湖北經過兵燹之后,經濟凋敝,人口銳減,根本不是敵軍必爭之地,只能徒然增加出征太平軍的消耗。結果是李出兵三月,內外交迫,一事無成,三月后只得悻悻撤回。而湘軍正是乘此時機攻下維持天京對外聯系的唯一支點長江江心島九洑洲,徹底切斷了天京與外界的一切聯絡。進入南京后,洪秀全倒是意識到將領們需要提高軍事素養,于是在1857年指示刪書衙將《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編為《武略》,在刪改289處后,頒發給各級將領學習之用。按照洪秀全的原則,凡他認定妨礙自己專斷集權的內容一律刪掉。如將《孫子兵法·九變》改為“八變”,刪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同書《地形篇》中,刪去“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這樣刪削后的兵書究竟能夠提高將領們多少軍事素養,只有天曉得。再說,太平軍的將領們幾乎日日苦戰,時時面對生死抉擇,同時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哪里還有工夫學習古代兵書呢!可以說,太平軍的將領們一直沒有達到自覺學習和運用中國古代兵學遺產的水準,也就一直無法改變他們用兵作戰的盲目性。他們“勇”則勇矣,但多數是匹夫之勇和血氣之勇。如果照真正“智”的要求他們恐怕至多是入門而已。這樣的一群將領,在一個專斷的領袖掌控下,盲目決策,胡亂決策,率領著一批今日入伍、明晨作戰、缺乏嚴格軍事訓練的士卒,面對熟讀兵書的曾國藩和訓練有素的湘軍淮軍,能夠取得一點勝利已屬僥幸,遑論徹底戰勝。太平軍將領軍事素養之差還表現在對軍隊合理結構和情報工作的忽視。太平軍一直在長江流域作戰,這里水網縱橫,江河湖泊相連,沒有一支強大的水師,軍隊的調動和作戰必然處處受限,不僅難以取得戰場上的勝利,而且也難以保證后勤供應線的暢通。太平軍卻始終沒有意識到建立水師的重要性,他們的水師只是改裝獲得的民船稍加武裝而已,根本不敵湘軍刻意建立和訓練的水師,作戰中屢屢吃虧受損。當曾國荃打下安慶率水師利用長江水道直抵天京城下時,沒有強大水師的太平軍只能干瞪眼看著卻束手無策。與此同時,太平軍對武器裝備的革新,特別對新式武器的裝備和應用也缺乏自覺。鴉片戰爭之后,清朝洋務派目睹外國侵略軍的船堅炮利,開始籌辦洋務,購買和制造新式軍艦和熱兵器。太平軍的領袖和將帥卻沒有及時認識新式兵器的重要性,直到最后,除了李秀成的麾下裝備了一點洋槍洋炮外,其余太平軍基本上還是使用冷兵器作戰。面對湘軍,尤其是淮軍和洋槍隊的后膛炮和來福槍,只能以血肉之軀抵擋,能夠有多少勝算呢?太平軍一直對情報工作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始終沒有建立起準確窺探破解敵情的情報網絡,對敵軍、敵占區缺乏準確細密的了解。如北伐軍進入冀、魯、津、晉時,派出的情報人員都是南方人,文盲居多,語言不通,所到之處,連清朝官府公開張貼的布告文書都看不懂,只能將得到的一些道聽途說的信息作為情報匯報,這就使得太平軍在作戰時很難準確掌握敵情,雖知己而卻嚴重不知彼,這必然增加決策的盲目性,使自己經常處于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狀態。這樣一來,作戰的勝負就只能靠運氣了。
太平天國自“楊韋事變”后,內部裂痕不僅始終沒有愈合,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洪秀全只信洪家幫,大權獨攬,不時發出昏妄的詔令,卻再也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能夠令行禁止的指揮中心。胡封濫賞的結果,更是制造越來越多的互相掣肘的權力中心。本來,太平天國初起之時,就存在嚴重的宗族團伙,到后期這種宗族團伙更進一步強化。李秀成、陳玉成等各路將領都自組團伙,領有一支武裝,視自己占據的一塊地盤為禁臠,反對他人染指。他們的小金庫已經積聚了可觀的財富,形成強固的局部利益。他們只想維護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服調動,對援助其他將領和地區作戰缺乏積極性。對上級的指令陽奉陰違,消極怠工。李秀成后期援助陳玉成不力,一心進攻和經營江、浙和上海的財富之區。他們貪戀已有的享受,害怕打仗,更不愿打硬仗,暮氣沉沉,貪生怕死。1856年底的二郎河之戰,陳玉成、李秀成指揮的20 萬太平軍竟敗于鮑超指揮的3 千湘軍。1862年10月13日開始的天京保衛戰,李秀成指揮的30 萬大軍,竟不敵湘軍3 萬疲憊之師。原因在于,他害怕自己指揮的軍力遭受損失,他身在天京前線,心在自己的老巢蘇州,所以在湘軍幾乎陷于全軍覆滅之時徹圍而走,使湘軍得以獲喘息之機,絕處逢生。而其他參加援救天京的太平軍也都是各打自己的小算盤,不愿冒死拼殺。曾國藩即一針見血地評論:“城寇與援寇相環伺,士卒相死勞敝,然罕搏戰,率持炮者相震駭。蓋寇將驕優,亦自重其死。”(王闿運《湘軍水陸戰紀》卷5)因為只重視自己團伙的利益,所以任人唯親、賞罰不明的情況會經常發生。還在“楊韋事變”前,全盤主持天國軍政事務的楊秀清已是如此。1854年10月武昌被湘軍攻克,責任全在草包統帥、石達開的族兄石鳳魁。而楊秀清竟然將此時主持湖北民政事務、在武昌城破時有條不紊撤退有功的黃再興一同處死。晚年的洪秀全更是剛愎自用,事事專斷,將軍事上的失誤一一諉過下屬。如安慶失守,他將責任完全推給在第一線指揮的陳玉成。天京未能解圍,他就嚴責李秀成指揮失當,措置不力,多次革除他的爵位。李秀成也任人唯親,包庇汪有為蘇州叛亂集團和通敵有據的內奸錢桂仁、徐佩瑗等,使太平軍蒙受巨大損失。
太平軍的將領和士卒參加起義隊伍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改變自己的命運,起碼能夠獲得衣食之資,免除凍餒;進一步是向高處攀登,升官發財,得到榮華富貴。一批升至高位的將領的確積聚了大量財富,享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錦衣玉食的生活。但軍旅是一種時時刀口舔血的危險職業,待到面對生死存亡時,他們就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未來。除一些忠義思想牢固者為太平天國拼死殉節外,也有相當多的高官顯爵者選擇投誠清朝,以求保住自己的生命和既得利益。太平天國后期,數以十計的具有王爵和掌管一方軍政大權的高官投降了清軍。如1855年在連鎮降清的北伐軍將領詹啟綸,1859年10月在安徽池州降清的韋志俊,1862年降清的童容海,同年投入清營的周興隆,1864年在江西金溪降清的陳炳文等,在清朝都做到總兵官。1861年在安慶降清的程學啟,也官至總兵,成為李鴻章淮軍麾下第一大將。1858年投降勝保的李昭壽官至江南提督。1863年以后,降官降兵如潮。1863年6月,常熟守將駱國忠投降淮軍,使蘇州門戶洞開。10月,奉王古隆賢以皖南石埭、太平、旌德三縣降。同年天將楊英清以江蘇溧水降。1863年12月,納王郜永寬、寧王周文嘉、天將汪有為以蘇州降。12月17日,平湖守將陳殿選降。12月22日,乍浦守將熊建勛降。1864年2月,比王錢桂仁以杭州降。同年,聽王陳炳文在金溪降。1864年8月,祜王藍成春在黑石渡降。同年11月,天將倪隆準以黑石降。1865年8月,天將林正揚在廣東長樂降。同年,列王黃朋厚在江西降。高官如此,士卒投降者更多。據記載,蘇州被圍困時,李鴻章一紙招降的大字布告貼出后,每天出城投降的太平軍士卒就達300 多人。降兵降將之多而形成潮,表明其內部已經分崩離析,走向敗亡應該順理成章吧!
《孫子兵法》強調“法”的重要意義,其中特別強調軍隊必須有嚴明的紀律。太平軍的紀律有其嚴明的一面,對各色人等的衣食住行都有嚴格規定,如廢除“王”姓,不準穿紅色衣服,不準戴帽,不準剃發,不準喝酒,不準傷害百姓等。進入武昌,楊秀清就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傷”。太平軍分設男女營,實行嚴格的禁欲主義,即使夫妻也不準過夫妻生活。進入永安后,西王蕭朝貴的母親和繼父蕭玉勝就因為違規偷偷湊到一起過夫妻生活被處決。1854年3月,太平軍進入南京已經一年有余,又發生了東王府又正丞相陳宗揚和東王府首席尚書、鎮國侯、東王表兄盧賢拔私下違規過夫妻生活的案件,結果是陳宗揚夫婦被斬首,盧賢拔被革爵。這盡管可視為一樁嚴肅紀綱的典型案例,但也展示了太平軍禁欲主義非人道的一面。太平軍的領袖沒有階級觀點,由于圣庫主要通過劫掠官府和富人的財產維持,所以一般百姓的財產也必然成為劫掠的對象。進入武昌后,雖然頒布了不可傷及無辜的紀律,但實際上不僅大小官員及其家財沒收,人殺盡,一般百姓的財產也同樣遭受劫掠。特別是,太平軍規定凡加入其隊伍者財產交公、房屋焚燒,這必然傷及一大批被裹挾的無辜者。而故意殺人放火的情況也一再出現。如李開芳、林鳳祥的北伐軍在山西平陽府(今臨汾)和滄州因遇到激烈抵抗,就曾下令屠城,僅滄州就殺死漢回民萬余人。1853年9月胡以晃進攻安徽桐城,遇到在籍工部侍郎呂賢基所組織團練的頑強抵抗,進城后,嚴令搜殺“呂妖”,士卒誤聽為“女妖”,于是從早晨至中午,就殺了3500 多無辜婦女!濫殺無辜的現象后期愈來愈多,這勢必引起廣大百姓的反感,促使他們或固寨自保,或投靠清軍與太平軍為敵,如浙江諸暨的包村,是一個只有百余戶人家的小山村,他們就自動組織團練拼死抵抗太平軍。太平軍前后投入近20 萬人,經過8 個月的反復沖殺,在戰亡數千人后才將這個小村踏平。面對被越來越多百姓敵視的困境,李世賢致東陽佐將陳榮(或陳壽)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認說:“自我思之,皆因眾兄弟殺人放火,勢逼使然,非盡關百姓之無良。”①轉引自盛巽昌《實說太平天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9頁。在戰爭中,由于槍炮不長眼睛,難免傷及無辜,但視生命如草芥,并且有意識地將槍刀對準無辜的百姓,就是不可原諒的。逐漸失掉民心,這恐怕是導致太平軍最后敗亡的根本原因。
太平軍在對清軍作戰的過程中,將帥們有時也能運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避實擊虛”“以少勝多”等戰術原則,展現出卓越的指揮藝術。如1852年1月進攻武昌時,陳玉成窺破敵人的薄弱環節,率500 勇士縋城而上,守軍即一哄而散,順利奪取該城。同年,石達開封鎖湖口,將湘軍水師攔腰截斷,使之遭受一次重大損失。1856年11月,陳玉成利用曾國藩悍將李續賓驕橫輕敵的錯誤,引誘其督率湘軍七營進入三河鎮,成為一支遠離湘軍主力的孤軍。之后,太平軍先挖開河壩,使三河鎮周圍形成一片汪洋,斷絕其退路。接著在李秀成的配合下,陳指揮五路大軍猛攻敵營,將被圍湘軍全部殲滅,李續賓也成了太平軍的刀下鬼。李秀成也指揮太平軍運用誘敵深入、以多勝少的戰術,打了一些致敵于死命的漂亮仗。如以“圍魏救趙”之策攻破江南大營,在青浦兩次擊敗淮軍和洋槍隊。然而,從總體看,太平軍將帥們的戰場指揮藝術并不高明,自覺的戰術意識差,基本上是跟著感覺走。尤其在后期屢屢犯兵家之大忌,失誤連連。如李秀成的部將陸順得占領松江后,孤軍深入,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進攻上海,結果是一敗涂地,松江也被華爾的樣搶隊攻陷。李秀成親往前線指揮,他對上海的敵情也根本不了解,還受騙認定外國侵略者這些洋兄弟會幫助他奪取這個商貿中心,結果遇到的是外國侵略者密集炮火的迎擊,座轎被炮彈擊中,他也被彈片擊傷。1860年底,為了解安慶之圍,太平軍派出兩路大軍救援。江北一路由陳玉成統率,經安徽直趨湖北;江南一路由李秀成統率,經皖南、江西向武昌進擊,約定三月會師武昌。但是雙方不久就失去聯系,只能各自為戰,無法進行戰略戰役的協同。當時武昌空虛,守軍僅兩千余人,已經占領黃州(今湖北黃岡)的陳玉成只要西向進攻即可拿下該城。可他在關鍵時刻聽信了英國參贊官巴夏禮的勸告,以妨礙英國商貿利益為由停止了進攻。李秀成一軍也很快進至鄂東,但由于雙方信息不通,他在得到李世賢江西吃敗仗的消息后也撤軍東返。武昌未能打下來,救安慶的戰略目標也就難以實現。安慶失守,太平軍面臨的形勢進一步惡化。1861年,李秀成進軍浙江,前敵指揮陸順得統率的10 萬大軍竟然為彈丸之地的包村民團阻擊達8 個月,不僅延誤了奪取浙江的時日,給左宗棠的湘軍造就了充分反擊的機會,而且大量犧牲了太平軍的有生力量,實在得不償失。其實,太平軍完全可以置包村于不顧,全力進攻杭州,實現自己既定的戰略目標。但由于激于義憤,走出了這樣一步錯棋。
中國是一個儒學傳統深厚悠長的國家,自秦朝之后,即崇尚中庸理性,鄙薄怪異鬼神。統治者雖然也不時利用宗教,但宗教向來只能作為儒學的補充而存在。歷史上以宗教信仰為旗幟的農民起義沒有一個成功創建新王朝。《孫子兵法》更是堅持實踐理性,倡導“不可取于鬼神”(《孫子·用間》)。洪秀全創建拜上帝會,裝神弄鬼,一再使用“天父下凡”的騙術欺蒙他的屬下和將士,最后竟違背基本常識要求天京圍城中饑餓的將士和百姓以天降的“甜露”(野草)充饑,還吹噓說他將上天領來天兵天將保衛天京。一用再用的騙術敗露后,虛幻的信仰必然破產。太平天國后來政治、經濟、軍事的迅速崩潰,顯然與信仰的破產是連鎖的。
從一定意義說,太平天國是成也拜上帝會,亡也拜上帝會。取于鬼神者,絕對與最后的成功絕緣。
三
反觀太平天國的對立面清朝政府及其軍隊,尤其是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統帥的湘軍和淮軍,后者在戰略戰術上比太平軍就高了不止一個層次。你看,清朝的八旗和綠營盡管腐敗已極,幾乎喪失戰斗力,但它一直黏住太平軍不放,步步緊隨,監視其一舉一動。太平軍進入南京,它即在距南京近在咫尺的雨花臺建立江南大營,又在揚州建立江北大營,對太平軍形成高壓態勢。湘軍訓練成軍后即從湖北沿長江由西向東推進,既不斷殲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更奪取太平軍占據的城鎮鄉村,尤其是武昌、安慶等關鍵戰略要地,切斷天京與外界的聯系,特別是它的糧食運輸通道,使天京軍民因饑餓損失戰斗力。淮軍勾結外國侵略者,通過上海扼守長江出海口,由東向西進擊,攻取鎮江、常熟、無錫、蘇州等中心城市,與湘軍形成對南京的東西夾攻之勢。左宗棠統帥的湘軍則深入浙江,在太平天國的東南方向堵住它向滬、杭、甬地區的發展之路。三者互為犄角,將太平軍牢牢卡死于天京為中心的蘇、皖、浙交界地區,使之陷入首尾難顧、四面受限、動輒得咎的被動境地。曾國藩更高明的一著棋是謀求整個圍剿軍隊指揮權的統一。他知道清朝皇帝及其周圍的滿族臣僚對漢臣掌兵心存疑忌,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授予漢臣指揮軍隊全權的。所以只要江南江北大營存在,清朝皇帝就不會讓他執掌圍剿軍隊的指揮權,他的行動就會處處掣肘,整個戰略意圖也難以實施。有鑒于此,他多次冒著抗命不遵的罪名拒絕執行皇帝救援江南江北大營的詔令,幸災樂禍地看著江南江北大營被太平軍圍殲。借太平軍之手消除了這個障礙之后,逼使清朝皇帝將兩江總督的大印交到他的手上,由此取得了蘇、浙、皖、贛四省軍政事務的最高指揮權,也就使清軍取得了對太平軍絕對的戰略優勢,加速了太平軍末日的到來。曾國藩深得理學動心忍性之精髓,他穩如泰山的戰略定力、屢敗屢戰的堅韌精神、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知人善任的馭將統兵能力,都是太平天國領袖們難以企及的。如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兩路猛攻江西、湖北,破城以十計,威脅武昌,逼其回軍。但他絲毫不為所動,揪住安慶不放,加大圍攻力度,破解了太平軍的“圍魏救趙”之策,最終拿下安慶,取得了戰略上的重大突破。在他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對這一戰略決策作了簡潔的概述:
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之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云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凎、永豐等屬,皆所以分我兵力。
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于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力求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曾文正公全集·家訓上·諭曾紀澤》)
湘軍、淮軍陸師水師齊備,訓練有素,武器裝備優良,后勤供應充足,道路交通順暢,情報收集、用間策反、戰役組織、戰場指揮藝術都較太平軍優長得多。就是軍隊紀律,也不比太平軍差。請看曾國藩為湘軍寫的《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
第一扎營不偷懶,莫走人家偷門板。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
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間去打館。筑墻莫欄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鞭(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擄人當長夫;一個被擄挑擔去,一進嚇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
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愛民歌》顯然不能以“欺騙”解讀,它至少反映了曾國藩主觀的真誠。這里規定的紀律雖然湘軍不見得完全遵守,但總是對它的一種約束,而在相當程度上,湘軍的軍紀是優于其他清軍和太平軍的。這就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百姓的擁護。當然,湘軍攻入天京后肆無忌憚地劫掠是不容掩蓋的事實,但也請注意:它劫掠的主要是太平天國的府庫及其王爺等達官顯貴的府第,這與太平軍劫掠清朝官府有何不同呢?
以往的歷史著作,也包括一些戲曲和電視連續劇,論述太平天國歷史時最大的失誤是,先將它置于“革命”的祭壇上,作為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加以濃墨重彩的歌頌。然后尋找能夠夠得上革命的資料,或能夠解釋成革命的資料,加以精心鋪排。對有悖革命的資料則故意隱蔽,或謚之為“敵人的誣蔑不實之詞”予以否定。這都不是嚴肅科學的唯物史觀的態度。我們應該如實地將太平天國放到與清王朝對等的同為封建政治軍事集團的位置上進行觀察和論列,只有如此才能展現太平天國的歷史真相,讓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在更宏闊的視野下健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