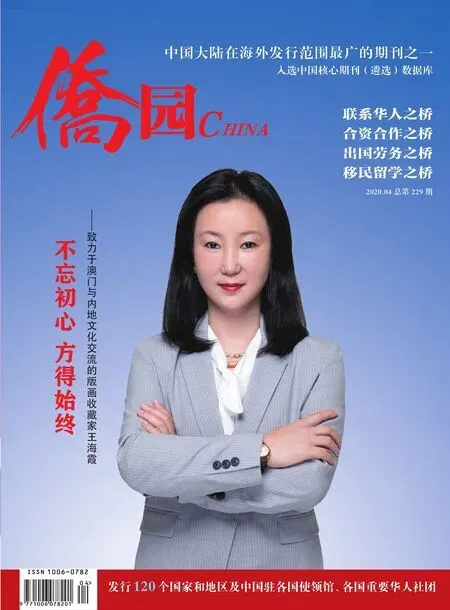西方現代悲劇觀對傳統悲劇觀的顛覆與反叛
關琦 徐宏宇(齊齊哈爾大學)
被后世稱為經典的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學說,一直到今天都被人津津樂道。他提出的傳統美學觀點,在之后的兩千余年間,一直領導著人們的思想。在之后的時間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在黑格爾時代得到了更新,黑格爾提出了以矛盾的觀點來詮釋悲劇的概念。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他們對悲劇的理解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但這也是基于對過去的美學觀念的傳承與發展。
在19世紀末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悲劇的解釋都是建立在傳統觀念的基礎之上,但是在19世紀之后,悲劇觀出現了新的方向,并且對傳統的悲劇觀產生了沖擊。到了20世紀,悲劇作為一種隆重的戲劇演繹方式,濃墨重彩地走上了演繹舞臺,并且在主旨的表達上出現了很多與傳統觀念相反的現代思想的沖擊。在更新的悲劇觀念中,對傳統悲劇觀的反叛以及沖擊的思想方式并不代表對過去思想的摒棄,而是歷史浪潮中的產物。20世紀的很多戲劇家,他們筆下的悲劇作品都非常一致地反映了強烈的與傳統格格不入的現代悲劇色彩,這也是歷史變遷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一、悲劇實體的轉變
在古希臘,其悲劇往往是主人公的命運悲劇,這種悲劇主義色彩貫穿了整個戲劇,而莎士比亞的悲劇則是體現在人物性格方面,注重對悲劇色彩的性格的刻畫,再者就是,易卜生等人創作的悲劇,反應的是可悲的社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翻天覆地改變。到了20世紀,西方的悲劇逐步向異化的方向發展,體現一種以異化為主題的具有哲理的悲劇。這樣的發展過程也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人類不斷進步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二、西方現代悲劇的實踐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既是西方國家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時代也是社會動蕩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對當時的人們來說也是巨大的沖擊,隨后的工業化和網絡化的發展,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巨大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的急速變化下也發生了巨大改變。科技的發展使得長久以來信奉上帝的人產生了相反的觀念,人類精神世界里的神話世界分崩離析,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信仰,一時間無法適應這個改變,精神世界產生空虛之感。現代悲劇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人類沒有精神歸宿的不安全感以及自我否定自我懷疑都被體現在現代悲劇之中,這種以異化為主題的現代悲劇不斷發展。在現代悲劇的探索道路中,西方悲劇開辟了嶄新的道路,并且和傳統悲劇劃分了明顯的分界線。用戲劇的方式展示了當時人們心中的恐慌,在困境中艱難生存的心情。這種“精神覺醒的痛苦”被充分融入進現代悲劇的創作之中,并且這種創作思路也為后續的文學作品提供了新的方向。
三、從塑造英雄人物轉向描繪人類
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喜歡塑造神話形象,描繪英雄人物。悲劇的主人公常常是擁有突出常人的能力或者直接取自希臘神話中的神明。亞里士多德悲劇中會將神描繪成具有傳奇色彩的領導者,這種創作思路引領了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的悲劇創作,悲劇也因此更加偏向于“貴族化”。后來在文藝復興時代,各大思想家主張關注人性,悲劇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平民和貴族開始同臺演出。慢慢地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思想的開化,悲劇的主角逐漸從神明變成了普通人。萊幸創作的市民悲劇,在當時的時代還是非常前衛的,因此不被人們認可,直到很多年后,才得到人們的贊同。他在悲劇中描繪的就是平凡人的悲劇,在他眼里,普通人的不幸才顯得更加不幸,王侯貴族的不幸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遠。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多的小人物小角色走上了悲劇舞臺。到了19世紀之后,悲劇開始走下了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壇,變得親民和親近生活。非常多的悲劇藝術家,都努力在日常生活、平民生活中尋找創作對象。不僅使戲劇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學作品也是一樣,20世紀的西方文學作品變得更加平民化,甚至作品的主人公并沒有名字和職業,而是某一類人的代名詞。因此現代悲劇常常是極為普通的場景,對劇情發生背景的描繪也更加簡潔、平淡。
總而言之,“二戰”對人類思想影響是巨大的,人類感受到了物質力量的強大,慢慢認識到了自己的渺小,對悲劇的描繪也轉向到對自身的懺悔。悲劇藝術家也更加注重對內涵的表達,人物的身份不再受到限制,很多作品表達的都是一種類型的人,只剩下代表這種人的影子和符號。更加注重表達人物的內心抗爭,更加關注作品的內涵,是現代悲劇創作的新潮流。西方的悲劇創作隨著時代的變遷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過去的情節沖突表達,到現在的內向情緒的體現,表達了人類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突破自我的艱難過程。這是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是社會異化的側面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