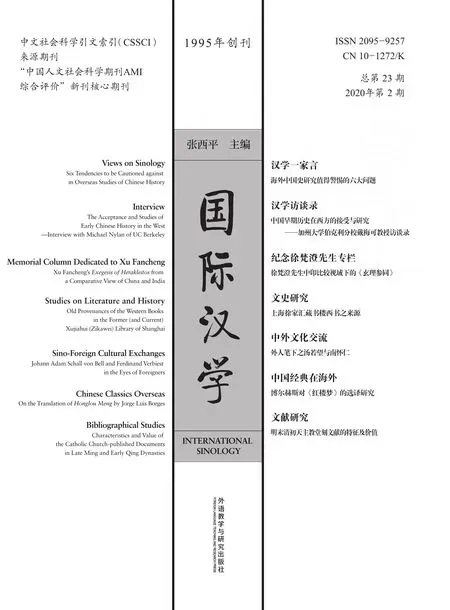徐梵澄先生中印比較視域下的《玄理參同》*
趙 波
徐梵澄先生一生所治為精神哲學。何為精神哲學?可視為玄理或形而上學。與尋常哲學重概念、方法不同,它純憑靈感和直覺,多象征而少直指,重直觀、體驗或實踐,求“精神”證悟之“是”,非求“物理”進步之“新”。這宗學問也稱為“內學”,原指真理端由內中修為省悟而得,“而人人皆稟賦有此靈、此心、此性、此情、此體、此氣,中西今古不異,則可謂只有所見之方面和所表之形式不同而已”(1)徐梵澄:《玄理參同·序》,武漢:崇文書局,2017 年,第4 頁。。這“靈”“心”“性”“情”“體”“氣”,徐先生又統稱為“性理”,超出普通智性,乃至大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之“理性”。他說:“在宋學中,這理智也是‘心’,但說為‘理性’,或‘性理’。后者范疇似較前者為大,‘性理’統攝整個人性之理,則其間非事事皆合理性,統之曰‘心’,所以此‘心學’又稱‘性理’之學。”(2)徐梵澄:《陸王學述》,武漢:崇文書局,2017 年,第102—103 頁。這“性理”之學的內容與氣質若譯成印度思想,便與圣哲室利·阿羅頻多(Sri Aurobindo,1872—1950)之“新韋檀多學”或曰“大全瑜伽學”相呼應了。徐先生指出:
鄙人之所以提倡陸、王者,以其與室利·阿羅頻多之學多有契合處。有瑜伽之益,無瑜伽之弊。正以印度瑜伽在今日已敗壞之極,故室利·阿羅頻多思有以新蘇之,故創“大全瑜伽”之說。觀其主旨在于覺悟,變化氣質,與陸、王不謀而合。姑謂為兩道,此兩道誠有文化背景之不同,皆與任何宗教異撰。亦與唯物論無所抵牾,可以并行不悖。今人總好光怪陸離之論,重外來之新論,而不重自己之家珍,倘于舊物拂拭整齊,當豁然于其聲光之弘麗。五中有主,外邪不侵,治身則然,立國亦爾。(1)揚之水、陸灝 :《梵澄先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年,第131 頁。
徐先生至晚年,仍“殷殷耗日力于此”。“此”,參同玄理或形上之理,旨在義理之互證,學術之會通,然后求世界之大同。這理想多么高遠,同時又多么渺茫,然“舍從此基地前進,亦別無其他途徑可循”(2)《玄理參同·序》,第9 頁。。“其他途徑”或可獲得經驗和知識的進步,但這條路卻是德性與精神的提升。孔子之“小康”“大同”說,應在此一義度上理解。
徐先生在20 世紀50 年代,以翻譯韋檀多學古典(《薄伽梵歌》《五十奧義書》等)和今典(阿羅頻多和“母親”[即“密那氏”(Mira),全名Mirra Alfassa,1878—1973]的著作)為主;在60 年代,以紹介漢學思想菁華(小學、孔學、佛學)為主;至70 年代,以學術會通為鵠的。第三個時期之代表作是《玄理參同》這本小冊子。《玄理參同》原名《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阿 羅 頻 多 撰 寫 于1916 年2 月 至1917 年6 月,其啟因乃讀印度學者蘭納德(R. D. Ranade,1889—1957)之英語論文《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蘭氏論文只17 頁,發表于1916 年2 月,阿氏以同名撰稿,登載于《圣道月刊》(Rrya,亦即《阿黎耶》)上。圣哲之作,意在借題發揮,其論述已超出哲學知識的范限,進入印、西之精神畛域的探討,如“神秘道”“永生原則”“一與多”“變易與不變易”等等。徐先生將之譯出并附以疏釋,又斟酌內容改名為《玄理參同》,于1973 年在修院出版。就文字而論,徐疏裒大于阿氏,實則他是攜一大橛中國背景而來,參與比勘與會通,其目的不外是構建“心同理同”的人類平等對話的平臺,正如其所言:“學術生命實與民族生命同其盛衰,互為因果。”(3)《玄理參同》,第3 頁。其實,他又是站在了“巨靈”的肩膀上,將視野向極處拓展了。他要證明,這思想學術會通的工作,非得有中國一維參與不可,蓋緣我們的文化從未中斷過,其重心也從未外移過,果若將其種種勝處導揚,正可參與引領世界和平發展之大合唱。因此,實有必要重溫之,闡發之。依筆者閱讀此書之體會,徐先生至少著意在三個方面:第一,疏解名相;第二,統釋人生;第三,篤論圣境。
首先,要弄清“精神”概念的確切含義。一般認為“精神”與“物質”對舉,為二元,但在阿氏和徐先生的語境中,“精神”將“物質”包舉,為一元之二元或多元。徐先生曾談到,道家講精、氣、神三者,蘇子瞻之徒嘗論“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能出能守,必有氣力之充滿與貫通,這“氣力”也即生命力。徐先生說:
而人,在生命之外,還有思想,即思維心,還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體。基本還有凡此所附麗的身體。但在最內中深處,還有一核心,通常稱之曰心靈或性靈。是這些,哲學上乃統稱之曰“精神”。但這還是就人生而說,它雖覺似是抽象,然是一真實體,在形而上學中,應當說精神是超乎宇宙為至上為不可思議又在宇宙內為最基本而可證會的一存在。研究這主題之學,方稱精神哲學。這一核心,是萬善萬德具備的,譬如千丈大樹,其發端初生,只是一極微細的種子,核心中之一基因(gene),果殼中之仁。孔子千言萬語解說人道中之“仁”,原亦取義于此。(4)《陸王學述》,第15 頁。
這“精神”是生命力的整個,又是生命力的核心,如說“宇宙是一大生命的充滿與潤澤”(牟宗三),是說“精神”與“大梵”“上帝”“道”“太極”同義,但其著重者,還在“心靈”或“性靈”,這是“精神”之上焉者,如孟子之是非之心,屬于知覺性之德;而“精神”之下焉者,便是食、色、性,屬知覺性之本能。阿氏多用“知覺性”(consciousness)表精神,也即“力”(force),我國宋儒頻用“知覺”一詞,卻少與“性”聯用,但古人有“氣”概念,英人白尼斯(Baynes,1883—1977)徑直譯為“力”,徐先生甚為贊許,“在宏觀中,它是無所不在的生命能量(力);在微觀中,它是其生命氣息(氣)。它相當于梵語的般若(Prajna)”(5)徐梵澄著,孫波譯:《易大傳——新儒家之入門》,《國際漢學》第11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71—76 頁。。
在《玄理參同》中,徐先生談到“氣”為一宇宙原則,正與赫拉克利特之“火”及印度之“火神”阿祇尼(Agni)同,皆表一宇宙權能或一“神圣知覺力”。阿羅頻多問:赫拉克利特說的“永遠活著的火”是什么呢?他認為是世界的原始不滅的本質,即永恒的“變是”(Becoming),能見之者為見道,古印度稱“詩人”或“見士”,他們是用了詩化的語言,欲要發掘宇宙的奧秘,乃成其神秘道。又因其尋求“光明”,故曰“光明的神秘道”。徐先生說:“此一‘神圣知覺力’之于物質界,乃形成或毀滅一切事物,它攻入、籠括、改造、重創,那么,又是物質及其形式下的潛在者。——作如是觀,已頗涉入精神哲學境界了。”(1)《玄理參同》,第34 頁。徐先生指出,我國古代,未如希臘初期哲人將宇宙萬物本因歸結為“水”或“火”,也無印度之神話學,卻有超上之玄學,周代即有火德之稱,將“火”收攝于“德”,已有“概念的共相”(亞里士多德)。漢代則有“五常之行氣”說,這“氣”實則“是一精神運動,仍統攝于陰陽二元之一元”(2)同上,第36 頁。。在此基礎上,于一圓周上劃定四方又配以八卦,中央復配以五行,重之六十四卦,附之以天干地支和算數,幾乎將宇宙萬象的基本原則涵括無遺了。這一復雜而系統的玄學圖型已是理智的產物,但又非純思想。換言之,此系統是憑證驗和體會,出自靈感和直覺,如《易經》之占卜。可以說,中國人的思維至今未能走上純思想之路,這是其不足亦是其優長,因其“理智”關注的是“生命”,而“生命”之奧秘,終是宇宙之“未知”或“不可知”。徐先生說:“系統化的玄學,代替了上古的神話,理智已參入其間,便見不出神秘道了。”(3)同上,第37 頁。如道家自漢、唐以服食求長生失敗后,轉入內丹煉氣一途,以人身譬若鼎爐,謂“火”為身體中之“陽氣”,與印度之赫他派瑜伽不甚相遠,這是生命之“火”,推及仍是一知覺性。徐先生指出,道家、韋陀都經過了這一“由外轉內的思想運動”(韋陀轉向韋檀多),即“對象化之外神,亦轉為主體化之內性”(4)同上,第42 頁。。
“火”表一“神圣知覺力”,亦表一“永生原則”,赫拉克利特將這“永生原則”給予了“人”,他說:“天神皆有生死,人則永生。”阿羅頻多認為,赫氏已認識到永恒者與暫時者不可分離的道理。“人則永生”,是原則上的,也即價值與意義上的,“死而不忘者,壽也”,乃謂“精神不死”;至若在現象上,要引入一“類”概念,《詩經》云:“宜爾子孫繩繩兮”,似以“火”支撐著世間的“光明”。不論從價值意義還是從現象上說,人都是天地之“主”,徐先生說:“依《易經》所論,宇宙由三個根本權能組成,即‘天道,地道,人道’。‘天’即是‘上帝’,與‘地’合,即為‘自然’,‘人’為兩者間之一極。再進一步可引出這樣的信仰,即人是天地之圓成,可影響天地,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是宇宙之主。”印度之“大我”(Atman)哲學最能理解這一點,“既然人內中具有神圣本性,就可以知覺到自己能夠轉化為神圣”(5)徐梵澄著,李文彬譯:《孔學古微》,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117—118 頁。。這么說來,人自身就是一“神圣存在”,亦是一“永生”者,因為他有“心靈”,而“心靈”雖流轉,卻是以現象的不斷熄滅又生起而保持著的,即“死亡”為“生命”開辟了道路,赫氏將其視為“火”或“戰爭”原則,故說“戰爭為一切之父,一切之王” 。《奧義書》亦言,世間一切生命和存在,皆是為充作“死亡”的食物而創造的。現代地質學也證明“大滅絕改變了生物群落結構,是生命演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正是恐龍滅絕為哺乳動物的生存打開了希望之窗,一個全新的紀元——新生代由此產生”(6)《生物大滅絕是如何發生的?》,《南方周末》2018 年07 月12 日。。另句“天神皆有生死”,佛教保持了這一信仰,認為諸天果若成佛,便得入此世間經過輪回。入此世間,乃得“心靈”,而天神卻未有之,此“心靈”與至上者合契或同體為一,即是得到永生。“為一”“永生”,乃謂“一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這是暗許生死一體,非是教人只管生便夠。后儒解此“一體”為“本體”,而“本體”既明,則一切皆通。又解“本體”為“太極”,“太極”一,“陰、陽”二,萬物三(多),莊子則謂“通于一, 萬事畢”,謂之“道”。
赫氏言“人則永生”,阿氏亦言“永生的原則在人中內在”(1)《玄理參同》,第42 頁。,蓋因人能明“道”,能體驗“本體”,能見到“性靈”,并與之結合,成為君子。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兇……”此又與瑜伽學相契,“瑜伽”的字義便是“結合”,佛家之超出生死,亦是與“涅槃”結合,莊子所謂“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大宗師》),與佛家同然,因明了生、死、存、亡原是一體,故“吾與之友矣”。但有一個問題,似為佛、道兩家所不足,即缺少一“本位”,它們對“永生”原則的體悟是智用型,而非心靈型。牟宗三先生說:“道家經過虛靜之工夫即可至此圓用之境者,然而道家之心顯然不即是此誠體(心靈)寂感之神用。”(2)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93 頁。徐先生也指出,道家修為之焦點全在“虛無窟子”,而儒家卻不離“人”這一“本位”,因為人中天地而立,無論上之“諸天”或下之“鬼神”,都不能脫出他的“本體”之外。人與天地同體并為之“主”,故大于“諸天”和“鬼神”。如此,赫氏之“天神皆有生死,人則永生”便好理解了。徐先生說:“在人類中起了‘永生’的追求。因為取‘永生’為一基本,所以死、生現為流轉。”(3)《玄理參同》,第48 頁。說“死、生”,乃指自然現象,凡物皆新陳代謝,春生秋殺;說“流轉”,是指變化,此《易》道最能明之,一方面陰陽相蕩擊、兼并,另一方面亦彼此相需、相成,所謂“相克相生”,阿氏稱前者為“交易”,后者為“互易”,實則是一原則,曰“相戰斗”“相成全”。若細加體會可知,小到人事之微,大到世界戰爭,皆逃不出此一“生命的理實”,這是一深埋在人類歷史命運中的悖論。徐先生亦提醒我們“相戰斗”亦是一契機,什么契機呢?是重新認識、重新建構自身價值與意義的契機。他在《薄伽梵歌·譯者序》中說:“出于至親骨肉相殘之際,亦人生由外轉內之機也。”
于此可一問,其“內”者何?成圣成賢;其“外”者何?建功立業。依儒家語曰“內圣外王”,正是《薄伽梵歌》中主人公阿瓊那(Arjuna)的人生要求。阿瓊那戰陣憂傷,幾欲退卻,其師克釋拏(Krsna)鼓勵其棄除雜念,勇往克敵,克敵乃復國,復國乃正義之戰,正義之戰乃無私之戰,因為勝利屬于“大梵”“天道”。此義克釋拏對阿瓊那反復陳說,其實整個故事并無過多戰爭場面的描寫,而以師生二人的對話貫穿。此書為印度之《圣經》,是精神生活之大全,內容大抵有三:知識瑜伽、行業瑜伽和敬愛瑜伽。其中,知識瑜伽為“高棲”,敬愛瑜伽為“冠冕”,行業瑜伽為“基礎”。該書特彰“行業”精神,即“工作中的自我皈順”。阿羅頻多說:“《薄伽梵歌》之第一行為律則,作事,無任何欲望——無愿望之行業——多么簡單的規律,多么困難的事情!”(4)徐梵澄:《徐梵澄文集》第11 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183 頁。這“第一律則”又涵攝三觀念,即平等、舍棄和奉獻。此三觀念又合三重性格,即知識(智——平等)、行業(勇——舍棄)、敬愛(仁——奉獻)。故徐先生說《薄伽梵歌》之精神“合于儒”“應乎釋”“通于道”。“合于儒”,因皆是內圣外王之學,皆是體天立人極之學,孔子言絕四,毋我、毋意、毋必、毋固,孟子言“義”乃天生職分,如戰陣無勇,則視為“不孝”。“應乎釋”,本為一物,前引后承,其名相皆從此出,正如儒、墨、道、法源頭為同一;佛陀去“有”說“空”,倡平等被弘慈,與阿瓊那之戰場無異。“通于道”,“道”乃“太一”“無上大梵”,又可謂“天地根”;老氏所謂“德”,乃“薩埵性”;其中最合者,曰“為無為,事無事”,有為無為,兩皆無執;又言為道之方,皆高等知覺性之謂。如此,印度的圣典就完全可作中國故事來了解。
這“故事”欲講明什么道理呢?它是在說人(類)精神的進步,需造就典型人物以為人眾之“標的”。此進步當屬內中之心理經驗,而非屬外在之物理經驗,其目的是變低等自性為高等自性,這是“上帝對人之道”,印度稱“瑜伽”(結合)之道,也即“天人合一”之道。這“結合”是此間與彼世、“無明”與“明”的結合,而結合之“主”,在“彼世”在“明”,可謂一清清凈凈的“心靈”,赫拉克利特稱之為“干心靈”,與“濕心靈”相對。蘭納德是在理智層面理解“干”與“濕”,以為“干心靈”是一清醒人的理智,“濕心靈”是一醉酒漢的非理智,而阿羅頻多指出,赫氏所言非智識(nous)而是心靈(psuche)。故赫氏之“干心靈”略相應于純潔化的“情心之知覺性”或曰“清凈心”(suddha citta 或heart)。而“濕心靈”則是為那不純潔的酒而攪動者,指人的生理情欲,屬“情命”,即自然本能,它把“心靈”給包裹住,使其不能透出光亮來。若稍稍變換概念,中國人則不說“干”“濕”,而說“清”“濁”,以“清”代“干”,以“濁”代“濕”,既講究又明白。“心靈”亦是此“心”,“清凈心”是一明明朗朗的心知之境界。儒家常說“清明在躬”,是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的境界,可謂是“先天的”。而“濕心靈”,則是“后天的”,它不清凈,可推之為“物欲”,久之養成了“習氣”,則“心靈”種子生發之可能性便被窒息了,其歸極為“死神”,而“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與“死神”哈迭斯(Hades)是同一神,便解釋通了。
精神的進步,也謂“進化”,但不是科學的進化論。科學的進化論是回溯的,由今返古,就自然史而建出理論;而精神的進化,是推測未來,預言理想,這源自于古代見士與哲人對宇宙原則的深沉視見。赫氏認為宇宙原則為“火”的本質和力量,它發出“風”“水”“地”之次一等原則,正如“陰陽”原則生出“五行”之次一等原則。然阿氏說,赫氏只顧及“向下”的進程,卻未“向上”返回到萬物生成的源頭,即不能如“陰陽”一樣返回“太極”,故其平衡觀與和諧觀只能止步于二元之“相戰斗(反)相成全(正)”。“向上”亦是“內轉”,義即“隱沒”,佛典譯為“非現者”;“向下”亦是“外發”,義即“顯現”,佛典譯為“現前出者”。徐先生說:“此由外而推內,倘若不是原來有其內在者,經過了一番內入作用(involution),如何能有其外發和進化(evolution)?”(1)《玄理參同》,第102 頁。這“內在者”原在,頗合儒家之“人性本善”,善為內在,為固有,即心靈之性,其極歸為“至善”者,云“太極”“道”“大梵”“上帝”皆是。如何能“至善”?端在擴大吾人之知覺性,亦嘗如孟子所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里,“氣”指“生命之氣”,為身體中生命流轉之系統,徐先生稱為“生理實體”,而非“物理有體”。《孟子·公孫丑上》中公孫丑問“浩然之氣”,孟子答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這是說“浩然之氣”需“道”的維持與養護,浩然之氣充滿宇宙,已超出言表之外,卻是一精神事實。說到底,“‘道’為一終極的內中經驗”(2)《孔學古微》,第203 頁。。設若將“道”置換為“仁”,就構成“十”字形的兩原則,“‘仁’是一條下降(或上升)的縱線(‘經’),‘義’是一條向兩端伸展的橫線(‘緯’)”(3)同上,第180 頁。。“縱”表“一”,“橫”表“多”,縱橫交會處,即“天地之心”。誠如阿羅頻多言:“‘一’與‘多’,亦縱亦橫。……這兩種傾向之和諧,是一切所欲達到真為神圣底之條件。”(4)室利·阿羅頻多著,徐梵澄譯:《神圣人生論》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第43 頁。
赫氏把“多”也表為“一切”,他說:“‘一’出自一切,一切出自‘一’。”阿氏問,赫氏是將“一”當作“多”的結果呢?亦或是將“多”當做“一”的結果?他說蘭納德認為赫氏否定“有體”(“一”),肯定“變是”(“多”),有如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1844—1900) 和 佛教徒,認為“一”,只是一“永恒變易”原則而已,非是“多”或“一切”的“不動”的終極因。那么,這“永恒變易”之后之上“是”什么或“有”什么呢?是“虛無”嗎?于此,又論及“空”與“無”。老氏說“無”,佛陀談“空”。徐先生說老氏論“道”,其實“道”本“無”可名之(一“名”便有限),表萬物之始,有“道”存焉,所謂“先天地生”者,也即宇宙之因,故王弼言老氏是“有”者。如果將“有”視為正極的表述,那么“無”就是“有”的負極表述,“有”為“陽”,“無”為“陰”,合之乃“太極”,乃“道”。佛家分“空宗”(般若學)“有宗”(唯識學),然般若學為其共法,與道家之“無”相當,只是推及更遠,連“無”的觀念也“空”掉了;唯識學承認“心有”,“心有”則佛性存,“心靈”存,已暗許“一”或“有”。赫氏說“火焰”說“水流”,此“焰”非彼“焰”,此“流”非彼“流”,這是牒述世間之物理現象,未點示其上其后的宇宙“真實”,阿氏說:“倘若火焰之形只由恒常底變易而存在,毋寧說這是芯炷之本質,變換為火舌之本質,可是必有其間為共通的一存在原則,這么變換其自體,而‘火’的原則常是同一,常是產生同樣底能力之結果,常是保持同樣底度量。”(1)《玄理參同》,第84—85 頁。赫氏喻萬事萬物為“火”,其本質必在超上一維,并與此間原則為同一,因物理“真實”是一,精神“真實”亦一。雖然赫氏未加“點示”,其眼光實已越出“變易”之外,因為這“一”(希臘文曰esti gar hen,梵文曰asti hi dkam,即唯“是”或“有”此“一”而已,也即“萬物為一”)恰恰是所謂的“有體”。(2)同上,第92 頁。他又說,佛教徒安立了“羯磨”(Karma,即“業”)宇宙原則,尼采承認“是為意志”,這與《奧義書》中“意志能力即是大梵”有何不同嗎?這么說來,“用”即是“體”,“體”即是“用”,一如阿氏所問:“這,除了是永恒底‘本體’外還(能)是什么(呢)?”(3)同上,第80 頁。
阿羅頻多評說赫氏,已觸及韋陀和韋檀多思想邊緣,他見到宇宙原則之二項,即知覺性權能的兩方面,一是無上的明智,屬“內”之“非顯了”者,如“陰”,表“能知”;一是無上的能力,屬“外”之“顯了”者,如“陽”,表“所知”。此二項在超上大梵知覺性中是“智”的兩權能,正如“陰”與“陽”之交會(“用”)等于“太極”。但印度思想的眼光推之此二項之外,見到了第三方面,即“樂”(“阿難陀”——悅樂、美與仁愛)。不妨將“真”“智”“樂”看作一超上“圖形”,即“體”“用”和“目的論”。設問:為什么要“存在”?答曰:是為了“創造”;再問:為什么要“創造”?答曰:是為了“悅樂”。阿氏說西方的思想未追蹤到這最后的微妙處,而能攝持者,只有靈感的哲學和宗教。此一問題甚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悅樂、美與仁愛”這一目的論,知覺性之二項就只能處在較低層次,即“交易”或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阿氏說赫氏應把眼光再往前推,見到力量平衡時,爭沖雙方“發生了恒常底互易,而且這互易的需要一旦見到,便興起了一可能性,以理智修改且代替戰爭,以之為互易的決定原則”(4)同上,第161 頁。。嘗如康德為人類制定“和平條款”,那是理智的產物,其中亦有各自利益的考量,但最終目的卻是謀求“永久和平”,也即天下“大同”。同理,阿氏要我們再升到最高處,以相互的依倚代替冷靜的平衡,即從“互易”躍至最高理念“通易”。阿氏指出這是人生的深隱之秘,是一神圣的極樂之門,惜乎赫氏未能及之,但他有一語幾乎觸到了這秘密的核心,即“天國是他們(兒童)的”。阿氏說:“而完善底人是一神圣孩子!他是一個心靈,醒覺到神圣游戲……在精神底一純潔性中,將自體奉獻于‘神圣者’。”(5)同上。阿氏將這“神圣孩子”稱為“超上飛鴻”。徐先生指出,宇宙本體“悅樂”為印度所獨創,此非吾人經驗之與“苦”相對之“樂”,而是超上之大寧靜與大酣暢,此一境界,只可求之于孔子之“仁”,“可謂二千五百余年前,孔子已勘破之秘密。但未此以為教,凡人所謂仁與義,是下推了一層,要上到宇宙萬事萬物皆寓乎一大‘仁’,則‘阿難陀’出現”(6)同上,第164 頁。。也就是說,“真”“智”“樂”之基因,已然全部包涵在“仁”的種子中。最后,徐先生站在了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的遠大之愿景的立足點上,結論到——“論博大為萬世法,終無過于孔子”。(7)《徐梵澄文集》第8 卷,第30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