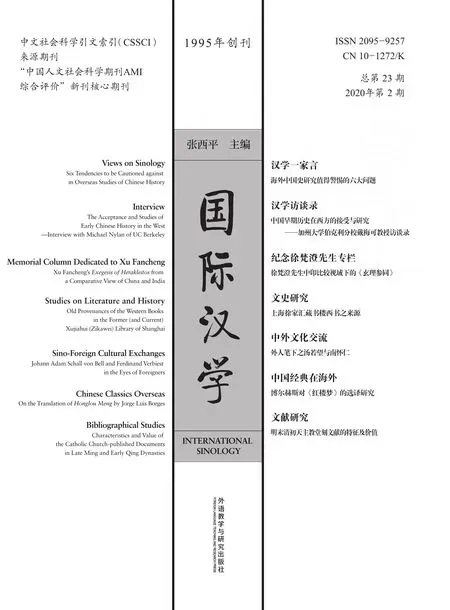作為國際學術事業(yè)的漢學研究
張西平
梁啟超先生當年談到研究中國的三種境界:“在中國研究中國”“在亞洲研究中國”“在世界研究中國”。今日之中國已經是世界之中國,海外漢學(中國學)的存在標志著中國學術的國際化,作為世界之中國,很自然應將這種域外的中國學問納入自己的學術視野之中。嚴紹璗先生在談到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傳播時,對這個領域的歷史及學術意義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說:“中國文化向世界的傳遞,歷史古遠、區(qū)域寬廣,曾經在亞歐廣袤的區(qū)域引發(fā)了程度不等的對‘中華文化’的憧憬、熱忱和思考,在文化學術史上被稱之為‘漢學’的‘學問’由此而誕生。……無論是在‘漢學時代’還是進入了‘中國學時代’,這一學問涉及的地域之廣闊,歷史之悠久,積累的智慧與資料之豐厚,從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立場上考察,它始終是一門與世界文明密切相關聯(lián)的‘大學問’,它的生成和發(fā)展,始終表明了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國際化的中國學術研究呢?本期的論文從兩個方面做了回答。
首先,中國學術界應該和域外的中國學術展開對話和討論,汲取其獨特的視角,關注其不同的研究方法,重視其開拓出的新材料,從跨文化角度去理解這種對中國學術的異域解釋與言說,從而在世界范圍內探究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互動與演進。
在這個過程中,展開學術的討論與爭鳴,在對話中闡明中國學術的基本立場,在研討中指明漢學家知識的不足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本期汪榮祖先生的長文《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值得一讀,哪怕是再著名的漢學家,當其著作在中國出版以后,都將會受到中國學術界的研讀與討論。當年楊聯(lián)陞等學術前輩在美國常常發(fā)表這樣的批評文章,從知識論上,乃至方法論上糾正漢學家們的錯誤,被譽為“學術警察”。今天,在討論域外漢學研究時,指出漢學家們在基本常識上理解的不足與錯誤,批評其完全離譜的解釋,這是很自然的。在上一期的《國際漢學》上,我發(fā)表了《建立一種批評的中國學》一文,也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期盼更多的像汪先生這樣的“學術警察”,對漢學家的著作展開正常的討論。
與漢學家展開學術理念上、理論上的討論是另一個重要的方面。長期以來,一些漢學家認為中國學者只能提供材料,而理論的框架需要由他們提供,這種看法已經完全過時了。漢學家們“以西釋中”的研究方法未嘗不可,但在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解釋上,中國學者應該闡明自己的學術立場,展開有益的學術討論,如汪先生對“新清史研究”的評論。對這些大的、原則性的學術問題不展開討論,只是全盤將其翻譯出來是不妥的,那就真成了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了。
域外漢學(中國學)的存在極大地拓寬了我們的學術視野,中國學術正是在同不同觀點、不同風格的漢學家們的討論中,重新認識自身,在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中,鍛造自己的國際學術能力。
本期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在于,在研究范圍上大大擴展了。尹錫南的《當代印度漢學家的中國歷史研究》、李學昭的《博爾赫斯對〈紅樓夢〉的選譯研究》,以及幾篇研究儒學在朝鮮、越南的傳播和影響的論文,顯示了作為國際學術的漢學的特點。長期以來,國內的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者絕大多數在研究歐美漢學、日本漢學,對其他國家的中國文化研究關注較少。平心而論,在世界各國的漢學研究中,毫無疑問日本與歐美學術成就最大,但今日之中國,乃世界之中國,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胸懷,更寬闊的眼光,去關注亞洲、拉美、非洲的中國文化研究。
著名的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漢學書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saire biblio- 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和其后的袁同禮《西文漢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是治漢學研究的兩大基礎性書目,有巨大的價值,涵蓋了西方從古代到1957 年間發(fā)表的西方漢學專題著作。但很遺憾,這兩套書目仍是西方漢學的研究書目,甚至連俄羅斯?jié)h學的研究成果都沒有涵蓋其中,更不要說日本漢學成果了。
《國際漢學》 以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的研究為宗旨,它的研究對象理應是世界性的。順便說說,由我主編的“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19 卷,2019 年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其中8 卷本的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海外傳播編年是這套書的重要貢獻,如《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美國的傳播編年》《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英國的傳播編年》《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法國的傳播編年》《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中東歐的傳播編年》《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東南亞的傳播編年》等。為便于中國學者閱讀,所有書目均為外文與中文對照,這是考狄書目和袁同禮書目所沒有的,也是漢學史上第一個編年體的漢外雙語書目。在語言范圍上也大大超越了“考狄書目”和“袁同禮書目”,他們的編目主要集中在西方幾個大語種上,而我們這個書目擴展到27 種語言,以往被忽略的日本、韓國、東歐、東南亞的漢學研究成果都包括其中。可以說,這是世界學術范圍內第一個囊括27 種語言、涉及43 個國家的漢學研究文獻編目,無論在漢學史的研究上,還是在中國文獻學的研究上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主要做基礎文獻目錄的編年,而任大援教授所領銜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文化域外傳播百年史(1807—1949)》”則深入多國漢學史的研究。該項目涵蓋了英、美、法、德、意、俄、阿拉伯、東南亞、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注重研究中國文化19—20 世紀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傳播的特點,關注文化的多樣性,以文明互鑒理論為基礎,研究多元文化的相融與互動。我期待著他的項目的順利完成。
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追溯中國學術國際化的歷程,自然,這是一個充滿跨文化對話的歷程,正是在這樣的歷程中,我們的學術被豐富,我們的視野被擴展,我們的文明開始彰顯出世界性的意義,這也是本刊的學術理想與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