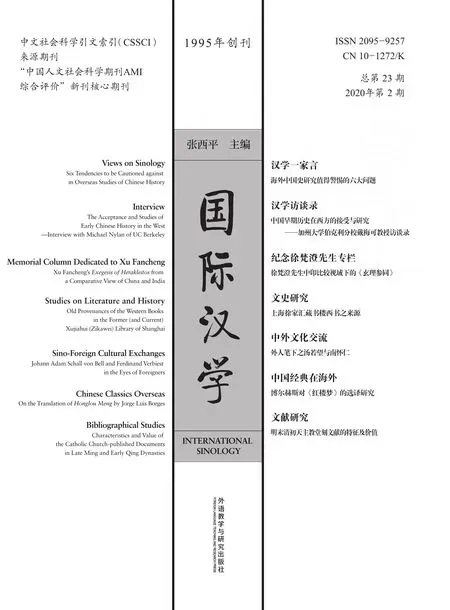葛蘭言漢學研究中的中國古代婚俗與祭禮
孫 越
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20 世紀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漢學家,師承漢學家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社會學家涂爾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致力于運用社會學理論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宗教和禮俗。
葛氏發表的兩篇博士論文——1919 年《古代中國的節慶和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和1920 年《中國封建時期的媵嫁制度和續娶妻妹傳統》(“La Polygynie sororale et le sororat dans la Chine féodale”),(1)收錄于1953 年出版的《關于中國的社會學研究》(Marcel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aris: PUF, 1953)中。分別探討中國上古時期農民與貴族迥異的婚俗和祭禮(2)在其第一篇博士論文中,葛蘭言主要探討了古代鄉間“節慶”活動中的祭祀、祈愿、歡愛等儀式性活動,側重于“儀式”層面;在其第二篇博士論文中,葛氏既考查了貴族婚姻制度,也探究了相應的婚禮儀式。出于行文簡潔考慮,筆者將這些與兩性交往和婚姻相關的活動及其習俗、儀軌統稱為“婚俗與祭禮”。及其原因;兩篇論文中談祭禮的部分又分別成為《中國人的宗教》(La Religion des Chinois, 1922)中第一章《農村宗教》(“La Religion paysanne”)和第二章 《封建宗教》(“La Religion féodale”)的基礎。此外,以婚俗和祭禮的研究為突破口,葛蘭言在20 世紀20 年代至30 年代初又撰寫了一系列談中國上古社會禮制的文獻,(3)如《中國語言和思想的某些特點》(Quelques particularités de la langue et de la pensée chinoises,1920)、《生與死——中國古代的信仰與學說》(La vie et la mort: croyances et doctrines de l’antiquité chinoise,1920—1921)、《置嬰于地——古代意識和神秘裁判》(Le dép?t de l’enfant sur le sol: rites anciens et ordalies mythiques,1922)、《言語的痛苦——對中國古代葬禮的考察》(Le langage de la douleur, d’après le rituel funéraire de la Chine classique,1922)、《論早期道教》(Remarques sur le Tao?sme ancien,1925)、《中國宗教的精神》(L’esprit de la religion chinoise,1929)等,收錄于1990 年出版的《關于中國的社會學隨筆》(Marcel Granet, Essai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aris: PUF, 1990)中。其中流傳較廣的是探討祭祀與封建貴族“聲望”的專著《古代中國的舞蹈和傳說》(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1926)。葛氏最終將其對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宗教和禮俗等方面的研究總結為兩部綜合性專著《中國文明》(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929)和《中國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 1934)。可見,葛蘭言關于婚俗和祭禮的兩篇博士論文是奠定其學術大廈的基石。
以下將從《古代中國的節慶和歌謠》(以下簡稱“《節慶》”)和《中國封建時期的媵嫁制度和續娶妻妹傳統》(以下簡稱“《媵制》”)出發,從舉行的背景、發生的動機、展現的方式、演變的根源四個方面,通過對葛蘭言相關論點和論證的梳理和歸納,就上古城鄉兩種婚俗及其所涉祭禮之間的異同做比較研究。
一、舉行的背景——農村與城市
葛蘭言所研究的婚俗和祭禮的時代,即法國漢學所謂“古代中國”(la Chine antique)至“封建中國”(la Chine féodale)時期;前者大體相當于中國史的上古至夏、商,后者大體相當于西周和春秋。此時的中國先民,從絕大部分定居在鄉村,逐漸發展到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并存。(1)商代開始才有像樣的國都,但頻繁遷移;參見呂思勉:《中國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第352 頁。周代殷以后才眾建諸侯,而“營造城市成為封建王朝的重要標志”;參見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aris: Albin Michel, 1982 (Un document produit en version numérique par Pierre Palpant), p. 206。通過對涉及先民生活的相關古典文獻的考察,葛蘭言注意到鄉村與城市的區別乃是婚俗與祭禮問題研究的首要分野,故其博士論文分兩篇撰寫。據葛氏的文獻整理,大體來看,《詩經·國風》中的許多詩篇是研究上古鄉村禮俗的優質素材,(2)參見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p. 212—214。而《儀禮》《禮記》《春秋》和《史記》里的一些記載則是考據封建貴族禮俗的絕佳旁證。(3)參見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aris: PUF, 1953 (Un document produit en version numérique par Pierre Patenaude), pp. 31—53。
據《節慶》,彼時的鄉村社會,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隔絕;為了暫時擺脫這種苦悶的生活狀態,他們虔誠地參與到神圣的節慶中去,也通過這種方式給子女(4)原始婚姻制度下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不完全從血緣來界定,是一種群體性的親緣關系,參見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55。進行公共生活和性生活方面的啟蒙。(5)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p. 189—190.一方面,此類節慶在名山大川處舉行,使天地人相溝通,具備祭祀的性質;另一方面,節慶采用歌舞、競賽(joute)、歡飲(orgie)等交流形式,使青年男女相互了解,消除彼此間的對立與隔閡,最終相戀,盟誓,直至結合。
而彼時的城市,已成為王公(princes)、領主(seigneurs)和貴族(nobles)(6)葛氏文中的“nobles”一詞有時用作廣義,泛指所有貴族;這里指王公和領主以外的中下層貴族(士大夫、普通官吏等)。的獨有領地,獨立的家庭單位(unité domestique)已經形成——居于核心的是一位領主,其他成員是其仆從(vassaux);領主是神圣種族的代表,具備獨特的德性(la vertu),也具有至高無上的影響力。(7)參見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53。因此,整個貴族階層(8)這里泛指一般貴族、領主和王公。采取了一種與鄉村社會迥異的婚姻制度——“媵嫁制度”,即一位貴族男子娶同一個家族的數位姐妹,其中一位為“正妻”(épouse),其余為“媵女”(suivantes)。
據《節慶》,鄉下農民雖理應舉行婚禮,但因典籍中無明確描述,葛氏在文中也語焉不詳;抑或是因為上古農民婚俗存在許多有違后世儒學禮教之處,故《儀禮》《禮記》等儒家經典刻意避而不談。(9)《儀禮·士昏禮》談貴族婚儀,而《禮記·昏義》也是對前者的解釋,均未談及鄉村婚俗。而城市貴族的婚禮已從集體場所走向私人空間,其儀軌已相當詳盡、確鑿。(10)參見《儀禮·士昏禮》(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25—54 頁)。鄉村的戀愛(更確切地說是“婚前活動”)和婚姻源自兩群男女在自然環境中的直接溝通,明顯具有群體性;而城市的婚姻主角需要在伴郎、伴娘的協助下展開交流,(11)詳見本文第三部分的第二段引文。婚禮具有私人性。此乃葛氏婚俗研究的出發點。
二、發生的動機——經濟與政治
盡管鄉村與城市的婚俗存在群體性和私人性的區別,但二者均需要符合一定的儀軌。在葛蘭言看來,“禮”的采用說明婚姻不是基于某種心理動機或個人情感的活動,而是社會性的行為;不光是在城市,在鄉村亦是如此。(1)葛蘭言舉例說:“(節慶中)不合時宜的舞蹈是丑聞的首要原因”,見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 148。又:“性愛啟蒙和訂婚在眾人注目下進行,受集體控制,遵守傳統規范”,見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 202。因此,葛氏始終將婚俗和祭禮的研究合二為一,認為農民的原始婚姻制度和貴族的媵嫁制度均是祭祀的產物,抑或本身就是祭祀的一環。
在《節慶》中,葛蘭言認為“節慶和婚姻之間必定存在聯系”(2)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 159.,又具體分析了四季交替同節慶、婚姻的關系:
在晴熱的季節里,男性在田間從事繁重體力勞動,女性就在園中采桑葉,在室內養蠶;在天氣寒冷到無法從事田間勞動的季節,男性只能做一些修補房屋的活兒,而女性則忙于繅絲織緞。于是,男人和女人們按季節交替的規律交替勞作……但在全年當中,兩性隔離已成為規律;在男女各自的小團體中,生活單調乏味……只有當生活狀態出現變化的時候,才會有社會生活——這將是一場廣泛的聚會,整個社群重新恢復團結。春季聚會的特點是性愛狂歡(orgie sexuelle)……而秋季聚會的特點是飲食狂歡(orgie alimentaire)……(3)Ibid., pp. 200—201. 楷體字引文系筆者直接從法文版本譯出,未參考其他有關中譯本,下同。
可見,群體婚姻與節慶的關聯不是偶然的、隨意的,而是兩性的分工和農業生產方式決定的。在夏、冬兩季,男性女性分別在不同的場所勞作,生產環境的差異造成了兩性的天然隔離和對立;(4)也有學者(如民國時期的丁文江)認為葛氏所持的“男女隔離”觀點只是儒家的固有觀念,參見王銘銘: 《葛蘭言(Marcel Granet)何故少有追隨者?》,《民族學刊》2010 年第1 期,第8 頁。而在春、秋兩季,勞動分工相對不明顯,男女兩個生產群體之間也需要借機消弭對立,故以性愛狂歡和飲食狂歡的形式維持整個社群的團結。
而生活在城市的貴族階層已脫離農業生產,貴族婚姻的動機無法從生產方式角度來分析。在《媵制》中,葛蘭言首先歸納出媵嫁制度的兩個基本原則:“一位貴族只能從一個家族娶若干位女子,他原則上也只能結一次婚;而嫁女的家族必須一次性嫁去若干位女子,數量取決于嫁女家族的地位。”(5)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62.即“允許多妻,禁止多婚”的原則。對于這種現象,葛氏根據社會學上的“供給原則”(les prestations)作出解讀:貴族嫁娶是雙方家族結盟的方式,而“一次嫁多女”既是嫁女家族誠意的體現,也是雙方聯盟(6)葛氏原文用的是“alliance”這個詞,兼有“聯盟”和“聯姻”的意思。重要程度的體現。(7)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69.此外,共嫁的姐妹來自同一個家族也確保了日后不會因出自不同家族的兒子之間相互敵對,而使家庭成為政治爭斗的場所。(8)參見Ibid., pp. 64—65。但媵嫁制度也并非眾妻平等,姐姐必須成為唯一的“正妻”,其他的妹妹或侄女(“娣”)均為“媵女”。對此,葛蘭言解釋為“封建時代婚姻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丈夫提供宗廟祭祀時不可或缺的合作女伴(collaboratrice)”(9)Ibid., p. 66.,而更深層原因在于宗廟里祖先牌位的放置規則:
要祭拜的各祖先的牌位按輩份分開排列,父輩和曾祖輩在廟堂的一邊,祖父輩和高祖輩在另一邊。這種文獻上稱為“宗廟順序”的排列方式說明親緣關系被分成兩組,上下輩成員永遠不可能出現在同一組。……因此,一個男人無法獨自向其全部祖先獻祭,只可能向祖父輩和高祖輩獻祭,因為按親緣關系他們排在同一邊;但如果他正常結婚,妻子是其姑媽的女兒,那么她(必然屬于她舅舅那一組,亦即她公公)就完美地成為祭拜夫家父輩和曾祖輩的合格人選。……為保證妻子是正宗的祭祀合作者,她必須是丈夫的同輩,兩人必須在規定年齡結婚……(1)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68.
總之,城市貴族媵制婚姻的動機一是雙方家族的政治結盟,二是本家宗廟祭祀的需要;而主持宗廟祭祀的權力與作為貴族的家族統治權密不可分。(2)葛蘭言在《中國文明》中認為,祭祀權力和領主權威都依據長子繼承制(primogéniture)來傳承,參見M. Granet,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Paris: Albin Michel, 1994, p. 347;詳細分析見本文第四部分。從大的歷史背景上看,城市貴族已脫離農業生產,城市本身就是政治發展的產物,故家族內外的政治需要就是媵制婚姻的根本動機。而在廣闊的農村,與自然密切相關的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節慶的方式和儀軌,后者是鄉村婚姻和祭祀活動的結合。
三、展現的方式——交流與交易
婚姻動機的差異造成了兩種婚制在展現方式上的差異。葛蘭言對鄉村節慶中與兩性相關的活動做了詳盡的描述:
節慶于特定季節在鄉間舉辦,面向全民。時而在山麓,時而在河邊;水流、山坡、采花、束薪都非常重要。(3)“流水” “山坡”即葛氏強調的節慶“圣地”(lieux saints),而“采花”和“束薪”分別象征定情和結婚。有很多人來見證,各種儀式活動也很多;本地青年是主角;對歌和飆舞構成節慶的主要部分,來自不同村莊的男女青年因為歌舞活動而面對面。在一段單對單的即興吟詩之后,男女便成雙成對。盟誓過后是與性有關的儀式,整個節慶以歡飲告終。(4)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 157.
無論是對歌、飆舞還是吟詩、盟誓,鄉村男女在一系列的交流活動中結識與結合。這些交流是直接的,無需中介人或引導者,最多只需要一些簡樸的信物(如鮮花、柴薪)。而城市貴族們在婚前無接觸,僅通過中間人(entremetteur)行“納采之禮”;(5)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123.到婚禮時雙方依然缺乏直接交流,需要通過伴郎、伴娘作為“儐相”來行禮:
盡管獨處,兩位準新人或許還無法成功地行夫妻之實(rapprochement matrimonial);為此,兩人分別需要伴郎和伴娘的協助……伴郎為新娘、伴娘為新郎倒水盥洗(lustrations préparatoires);(6)“lustration”原指古羅馬人的撒圣水凈化儀式,這里主要指洗手。參見《儀禮譯注》,第33 頁之注釋4。伴娘為新郎、伴郎為新娘分別把婚宴坐席鋪好,伴娘協助新郎寬衣,新娘再將新郎脫下的衣服交給伴郎。(7)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82.
更關鍵的是,盡管根據媵制婚姻的原則一個貴族只能通過一次婚姻娶走一個家族嫁出的一定數量的女性,以換取雙方結盟;但某兩個家族間也不可通過婚姻來結成過于緊密的聯盟,即雙方不能交換嫁娶本族內所有的適齡女性。對此,葛蘭言的解釋是,貴族家族之間既需維持傳統關系,也要各自保持相對的自由,以便提高聲望,擴大影響。(8)Ibid., p. 75.換言之,兩個家族之間避免排他性的婚姻交換使得貴族間的關系更為復雜、微妙,婚姻交易中的女性已完全成為維持或締結兩個家族間政治關系的工具。(9)當然,葛氏也認為原始社會兩個鄉村家族的婚姻也含有“人質交換”的意味,以此維系某種“團結”(solidarité,參見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 199)。但和貴族聯姻相比,原始的鄉村婚姻的政治目的要少得多(因為“alliance”一詞政治意味較濃,而“solidarité”一詞包含集體情感因素);再者,原始的鄉村婚姻中男女均可能成為“人質”,男性相對女性而言并無豁免權。
另外,葛蘭言在《節慶》和《媵制》兩文中都沒有提及上古婚戀中兩性的情感狀況。但從《節慶》中有關“對歌飆舞” “性愛狂歡”等細節推斷,鄉村男女的結合無疑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礎;盡管這類感情偶發,或許也不太專一。而據《媵制》,貴族婚姻祭祖和結盟的雙重動機很難讓夫妻(媵)之間產生真正的感情,而妻媵之間姐妹有別、長幼有序的現實也是削弱男女間感情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上古鄉村農民的婚戀中男女均具有一定的主體意識;而城市貴族婚姻中的男女沒有任何感情基礎,女性完全淪為男權家族之間交易的客體。
四、演變的根源——平等與權威
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農民原始婚姻制度和貴族媵嫁制度雖可能在上古特定的歷史階段并存于華夏世界,但總的來說,媵嫁制度是從原始婚姻中萌芽并逐步取而代之,上古文獻也能佐證。(1)《節慶》采用的書證主要為《詩經·國風》中的詩篇,而《媵制》采用的書證既有少量《詩經》中的詩篇,更多的則為記載較晚風俗史實的《儀禮》《禮記》《春秋》《史記》等。葛蘭言在《媵制》中借《儀禮》里“馬車夫”(2)《儀禮》中原文為“御”。的例子來說明貴族婚俗中殘存的原始婚姻禮俗是如何式微的:
在貴族媵制婚姻時期,伴娘是新娘的妹妹,伴郎不過是從丈夫的家仆中選出來的一員,通常為馬車夫。正是他駕著新娘的馬車從娘家駛往夫家。根據中國古詩中記載的民間風俗,“與君攜手同車”在古時就是結婚的象征。……后來,隨著封建文明賦予男性的尊嚴越來越多,丈夫不再在新娘面前扮演下屬的角色;他讓一位仆人替代自己,他自己只象征性地駕一下車,車輪轉三轉即可。(3)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83.
與強調家族榮譽的“聲望”(prestige)一詞不同,葛氏原文中的“尊嚴”(dignité)亦有爵位、頭銜等意思,強調男主人與男仆人間的地位差異。如果說,伴郎和伴娘的存在是原始婚姻制度的印跡,那么當伴郎的角色開始由車夫扮演時,新郎便完成了對新娘和隨嫁女(伴娘)的獨占。
但為何原始婚姻制度最終走向媵嫁制度(la polygynie sororale,直譯“姐妹共夫制”)而沒有走向“兄弟共妻制”(la polyandrie fraternelle)?據葛蘭言分析,每個原始婚姻制家族中都會出現一位有資格代表家族的首領,通常是直系長男(premier-né des ascendants),只有他能憑借自己個人的婚姻來維持本族與外族的聯盟;娶多位姊妹的目的在于保證正妻去世后仍有媵妻能陪同自己完成宗廟祭祀。(4)有趣的是法文中的“suivante”一詞既有“隨從”的意思,也有“下一位”的意思。兄弟間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兄弟共妻制無法形成,連“叔娶寡嫂制”(le lévirat)都被禁止。(5)詳細的分析參見M. Granet, é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p. 85。總之,原始婚姻形式演變到媵嫁制度的關鍵在于族內權威(autorité domestique)的建立,(6)Ibid., p. 84.即長男只有先建立起相對于本族兄弟的內部權威,才能享有對外族女子的婚姻權。
葛蘭言對中國古代貴族婚姻提出的“直系長男權威說”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對世界其他民族上古婚姻制度的分析有不謀而合之處。恩格斯認為古羅馬家庭的本質是繼承,即父權按遺囑在每一代的長男之間傳遞,(7)書中恩格斯援引了一句古羅馬成語:familia, id est patrimonium(家庭,即遺產),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54 頁。形成“家長制家庭”。所謂宗廟祭祀,也是中國古代貴族父權制強大的集中體現。而韋斯特馬克(E. A. Westermarck,1862—1939)認為,男性在家庭的權威源于雄性動物保護和撫養雌性和幼崽以維持物種繁衍的本能,“男子是家庭的保護者和撫養者,女子則是他的助手和子女的養育人;這種習性首先由習俗所認可,繼而得到法律的承認,并最終形成為一種社會制度”(8)愛德華·韋斯特馬克著,李彬等譯:《人類婚姻史》(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第34 頁。。歸根結底,是父權及其代際傳遞造就了媵嫁制度,并形成了媵制婚姻下丈夫對妻、媵和其他家庭成員的統治。
對于父權的產生過程,恩格斯認為在世界各民族中男性通過對畜群的馴養和繁殖獲得了最早的私有性質的生活資料,即“謀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歸了男子,婦女參加他的消費,但在財產中沒有她的份兒”(9)《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165 頁。。而在《節慶》中討論的時代,華夏世界的鄉村里男性耕田造屋,女性采桑紡織;同便于畜群繁衍的歐亞草原地帶相比,這種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不利于私有財產的迅速出現。而“男戶外、女室內”的勞動分工正好與中國古人的陰陽觀念相契合——男性代表南向、陽光、夏季,女性代表北向、陰暗、冬季;春秋兩季的野外節慶便是兩性結合的機遇與儀式,也象征了陰陽和諧,四季交替。(1)M. Granet,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 205.可惜,男女兩性的群居生活不可能永遠保持平等、和諧,“當對女性的蔑視迫使女性自我封閉并遠離一切社會生活……此類年輕男女的節慶便退出了民間習慣的行列”(2)Ibid., p. 208.。
綜上所述,葛蘭言的兩篇博士論文揭示出,在中國上古社會,農村和城市的婚姻在制度和儀軌方面都有著本質差別,其根源在于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生活所處的自然環境的差別。當然,我們不能全憑葛氏的研究成果去斷言中國上古農民或貴族完全遵守某種婚姻制度,或完全采用某種儀式,抑或因某種動機去遵循該制度或儀式……但應當看到,葛蘭言婚姻研究的獨創性在于從上古文獻的梳理出發,利用社會學原理,先設了鄉村/城市、農民/貴族、經濟/政治、交流/交易、平等/權威等一系列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其“史學—社會學”的上古婚姻研究范式建構于其上。這種方法對我國的上古婚姻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