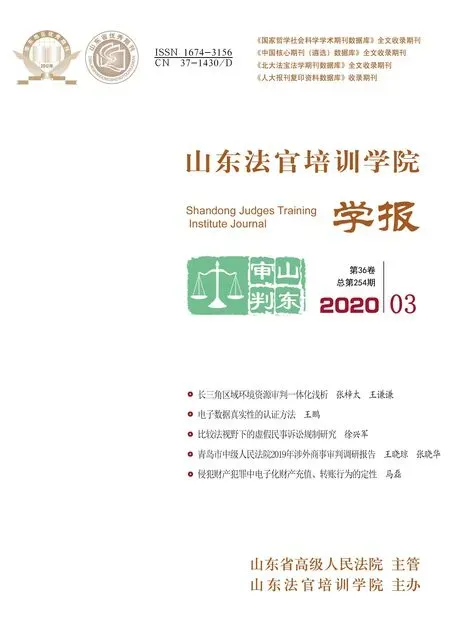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淺析
張梓太 王謙謙
一、背 景
隨著公民環境意識的加強,環境類糾紛出現了“井噴式”增長。由于環境侵害所表現出的潛伏性、長期性、風險的不確定性、損害的不可計量性和隨時擴大性、跨區域性、與科學緊密相連性等特征,導致其與傳統審判機制難以有效契合。同時,環境侵權的二元性特征導致一個環境污染或破壞行為關涉私益與公益、有形主體與無形主體、個人損害與生態損害、直接利益與間接利益、實際損失與未來風險等多重因素。傳統侵權法對這類糾紛中復雜的因果聯系、難以計量的損害后果、行為的不可譴責性等難題無力應對。①參見呂忠梅等:《環境司法專門化:現狀調查與制度重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頁。因此,必須打破現有體制機制的障礙,實現環境司法專門化。自2007年10月貴陽市清鎮設立全國首個環保法庭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環境審判組織與日俱增,直至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的落成,中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了專門的環境審判機構體系,實現了以“三審合一”或“四審合一”為主要模式的環境司法專門化。
隨著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推進,“專門化”無論是從橫向還是縱向上,均不再僅僅局限于在原有的行政區劃和審判層級內設立環境資源審判組織。2019年5月15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會議,全面部署環境資源審判機制改革,以生態功能區為單位設立與行政區劃適度分離的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包括設立南京環境資源法庭與9家按照流域劃分管轄區域的專門法庭、跨行政區劃對環境資源案件進行集中管轄和專業化審理,②具體而言,江蘇將在南京設立西南低山丘陵區域環境資源法庭,在蘇州設立太湖流域環境資源法庭,在無錫設立長江流域環境資源第一法庭,在南通設立長江流域環境資源第二法庭,在淮安設立洪澤湖流域環境資源法庭,在鹽城設立黃海濕地環境資源法庭,在連云港設立灌河流域環境資源法庭,在徐州設立淮北丘崗區域環境資源法庭,在宿遷設立駱馬湖流域環境資源法庭。指定設立環境資源法庭的法院集中管轄全省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環境資源第一審案件,其余基層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審理環境資源案件。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南京環境資源法庭,集中管轄上述9個生態功能區法庭所審結案件的上訴案件和全省中級法院管轄的環境資源案件。建立環境資源“9+1”審判機制等具體措施,旨在通過實行生態功能區全流域集中管轄,解決司法保護碎片化問題。
近年來,環境司法專門化跨出較大一步——不僅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行政區劃和審判層級,也不再局限于本省行政區域內,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流域系統性著眼,建立流域司法協作機制以及跨區域環境審判機制,江浙滬皖四地高院對此作出了積極探索。2018年6月,四地12家法院簽署了《長三角環境資源司法保護協作備忘錄》;2019年6月,上海和江蘇5家法院共同簽署《長江口生態環境司法保護合作框架協議》;同年9月,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法院簽署了《服務保障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建設司法協作協議》,在環境資源司法保護協作方面作了積極探索。
2019年11月5日,第十一屆長三角地區法院司法協作工作會議召開,江浙滬皖四地高院簽署《長三角地區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協作框架協議》(以下簡稱《協議》)《長三角地區人民法院聯合發布典型案例推進法律適用統一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協議》為進一步提升長三角洲三省一市區域環境資源審判協同性,為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保障發揮引領作用,在環境資源審判領域對2018年11月習近平主席于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提出的“將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作出回應,同時進一步推進了環境司法專門化的進程。
二、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的必要性
(一)一體化的題中之義
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其本質是實現資源要素的無障礙自由流動和地區間的全方位開放合作。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要打破行政壁壘,讓各城市的資源充分發揮作用,協同發展,各地區任何政策的出臺都要考慮到左右鄰居。
《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中指出,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是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完善我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打造我國發展強勁活躍增長極的重大戰略舉措。①參見《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地區人口密集、經濟活躍度高、生態環境壓力大。因此,生態環境保護是一體化建設的重點領域。長三角生態環境保護應該納入一個大的區域概念中,建立良性生態環境保護機制,實現共建、共管、共治。《綱要》在發展目標一章中明確,到2025年,長三角一體化將取得實質性進展。而實質性進展在生態環境方面的體現便是聯治能力的顯著提升。這便需要基本形成跨區域、跨流域的生態網絡,逐步推進環境污染聯防聯治機制的有效運行,使得區域突出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治理。
同時,在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聯合推動跨界生態文化旅游發展,加強跨界江河湖蕩、丘陵山地、近海沿岸等自然與人文景觀保護開發,是推進跨界區域共建共享的重中之重。跨界江河的共同開發必然會帶來新的跨區域環境問題,傳統的環境審判組織模式無法快速有效地解決這類問題,于是需要跨區域的環境審判組織的出現,來實現生態功能區為單位的跨區域環境共同保護。
(二)環境資源審判工作規律的內在要求
加強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司法協作是環境資源審判工作規律的內在要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長三角區域四省市唇齒相依、山水相連,生態環境休戚相關,客觀上要求環境資源司法保護必須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加強環境保護司法協作。環境要素的流動性、擴散性導致四地生態環境呈現污染行為和環境修復的雙重跨區域性,跨域排放、異地傾倒、鄰避現象等復雜問題,區域內環境資源案件裁判尺度、量刑標準統一難的問題,亟待解決。江浙滬皖四地高院簽署《協議》目的就是建立省級層面環境資源審判協作機制,攜手破解環境司法難題,共同提升審判整體效能。
筆者通過收集相關文獻與數據發現,盡管環境司法專門化工作在全國范圍內一直在穩步推進,環境資源專門審判組織的數量日益增多,但“庭多案少”和“等米下鍋”現象普遍存在——《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2019)》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環境資源專門審判機構1353個,其中環境資源審判庭513個(包括26家高級人民法院,118家中級人民法院及368家基層人民法院),合議庭749個,人民法庭91個。①參見《中國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2019)》。統計數據顯示,環境資源審判組織的結案率不容樂觀,以2013年的辦案情況為例,河北11個環境資源審判機構有24名法官,一年環境案件結案總量為24件,平均每人一年結案1件;江蘇省5個環境資源審判機構一年共結案5件;浙江2個環境資源審判機構一年共結案3件;北京、上海、天津、廣西、河南、山西、陜西、廣東、內蒙古、湖南、新疆、寧夏、西藏、湖北等省市的結案率為零。②參見孫佑海:《對當前環境資源審判若干問題的分析和對策建議》,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9月17日,第8版。根據貴州省高院研究室的調研,“貴州省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件年均只有20件;行政方面的環保案件沒有超過5件。”③《中國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2016-2017)》。江蘇省5個環保法庭2013年全年結案5件。昆明中院環保審判庭自成立后的五年內僅受理六件公益訴訟案件,環境案件總數不足百件。
以上情況表明,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推進的近十年里,“庭多案少”和“等米下鍋”現象極為嚴重,以至于學界與實務界均有質疑之聲:“環境法庭還有存在的必要嗎?”“環境法庭的旗幟還能打多久?”筆者查閱相關資料,其實不然。究其原因,其中重要一條是環境訴訟受本地方各種因素干擾,造成起訴難、受理難等現象。以四川沱江污染事件為例,盡管事件發生后有許多律師躍躍欲試,但當地司法行政部門很快發出紅頭文件,明確要求律師一律不準代理沱江污染案件,法院以此為由,拒不受理相關案件,從而失去了一個通過環境審判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的良機。④參見孫佑海:《對當前環境資源審判若干問題的分析和對策建議》,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9月17日,第8版。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與環境資源審判的特點正相契合。為此,應當積極探索設立以流域等生態系統或以生態功能區為單位的跨行政區劃的審判機構,實行對環境資源案件的集中管轄,逐步改變目前以行政區劃分割形成的行政區域管轄模式,解決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與保護的分散性之間的矛盾,以及國家環境資源法治的統一性與執法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江蘇環境資源審判“9+1”模式及《協議》《辦法》,便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要求的具體回應。
(三)“一體化”與“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把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一分部署,九分落實。上海、江蘇、浙江、安徽要增強“一體化”意識,把規劃綱要確定的各項任務分解落實,明確責任主體,加強各領域互動合作,將長三角地區打造成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標桿區域,為全國發展大局作出更大貢獻。推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影響的不僅是一城一地,將帶動整個長江經濟帶和華東地區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集群。
而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落實到環境資源審判領域,則是為了推動環境資源案件審判的高質量發展。如上所述,環境資源審判發展至今天,仍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以“庭多案少”與“等米下鍋”最為明顯),而一體化在環境資源審判領域的實踐,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強調一體化,就不再是一個市、一個區的單打獨斗,而是要形成協同創新、信息資源共享的鏈條。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抓好統籌協調,完善合作機制,進一步破除壁壘,確保各個環節暢通,形成有利于實現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推動環境資源案件審判的高質量發展,以此推動長三角區域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重大戰略目標。
三、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的可行性
(一)長三角地區自身優勢
回溯歷史,長三角區域全方位的合作機制由來已久——從1992年建立長三角15個城市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制度算起,已走過26年。長三角是我國區域一體化發展起步最早、基礎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區,更是增長質量好、經濟規模大、內在潛質佳、發展前景被普遍看好的經濟核心區。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口約2.2億,經濟規模約占全國25%,被譽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的經濟中心、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是我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區域,也是全球第六大世界級城市群。
多年來,在滬蘇浙皖和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效,各方面呈現良好態勢:一是省級統籌加強,形成了決策層、協調層、執行層“三級運作”機制,以及交通、產業、科技等12個方面的專題組。二是協同創新加強,大型科學儀器設施實現了共建共享。2017年底“長三角大儀網”已集聚2192家單位的2.8萬臺(套)大型科學儀器設施,總價值近300億元。三是互聯互通加強,滬通鐵路一期、商合杭鐵路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基礎設施加快推進,寬帶用戶規模、光纖寬帶接入端口、4G網絡覆蓋率均位居全國領先地位。四是聯防聯控加強,推動區域環境質量不斷改善。五是市場和公共服務融合加強,信用信息共享互動、社會保障互聯互通等不斷強化。①參見《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載搜狐網2020年5月15日,https://www.sohu.com/a/273504991_100014721。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率先探索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優勢、從項目協同走向區域一體化制度創新,示范引領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二)江蘇省環境資源審判“9+1”模式的先進經驗
如前文所述,自2019年5月15日以來,江蘇省法院系統啟動以生態功能區為單位設立與行政區劃適度分離的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全面部署環境資源審判機制改革。江蘇省環境資源審判“9+1”的司法聯動模式,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流域區域制度管轄的優勢,進一步加強了環境資源司法與行政執法體系之間的協調性,提升了環境資源的綜合治理能力,緩解了環境資源審判中固有的“主客場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破解了地方保護主義對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沖擊。環境資源審判“9+1”的聯動模式,使“法治”真正成為江蘇的核心競爭力——充分利用了案件集中管轄制度的優勢,確保環境資源審判中法律與政策的有效融合。創造了可復制和可擴展的專業審判經驗,打造了環境資源審判領域的“江蘇品牌”,實現了環境司法專門化由“點”(傳統行政區劃內各級環境資源審判組織)到“面”(江蘇省以生態功能區為單位設立的“9+1”跨區域環境審判司法聯動模式)的轉變,同時也為由“面”到“體”(長三角地區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協作框架)提供了“江蘇經驗”,打下了堅實基礎。
四、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的路徑分析及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一)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的路徑分析
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建設方面,原則上應遵循以下路徑或基本原則:
1.共抓大保護
在長三角地區各級人民法院之間建立規范化的司法合作機制,提高長三角地區環境資源審判的整體水平,打造“長三角”環境資源審判品牌,共同維護整個長三角的生態和環境安全,為生態文明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
依托長三角“一網通辦”政府服務平臺,探索建立區域案件審判和執行司法協助機制,加快跨境環境資源案件立案工作。對于當事方提起的環境資源案件,應當由長三角其他省份的法院管轄的,當事方可以向當地法院申請異地起訴。建立區域內重大爭議事項的協商制度。對于跨省的重大、敏感、困難和復雜的案件,三省一市的高級法院可以通過案件咨詢和其他形式來組建聯合工作隊伍,以協調和解決地區沖突。
2.標準統一化
建立區域法院環境資源案件判決統一機制。促進環境資源刑事案件判決標準的統一,優先處理環境污染犯罪,非法捕撈水產品等常見犯罪,促進本地區刑事案件證據判決標準和量刑標準的統一。總結經驗,統一區域內新型環境資源民事案件的具體標準和自由裁量權的尺度,促進區域內環境資源民事案件判決規則的完善。①參見《打造環境資源審判“長三角”品牌》,載人民網2020年5月1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862935468456223&wfr=spider&for=pc。
加強對環境資源案件證據標準和法律適用規則的研究,統一長三角環境資源案件判決標準。建立區域環境資源典型案例發布機制,重點保護長江,太湖,淮河,新安江等重要水域,保護東海生態資源。在上海,江蘇和浙江的管轄范圍內,共同發布相關典型案例,以促進法律的統一適用并擴大長三角地區環境正義的社會影響力。
3.協作守“紅線”
《協議》指出,四地區法院應充分發揮司法職能,在加強司法合作和保護生物多樣性,加強生態補償機制的司法保障,深化跨省生態司法合作等方面加強合作。長三角地區各級法院要充分發揮環境資源審判的職能,繼續深化環境資源審判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積極探索跨區域集權管轄。根據流域和自然保護區等生態功能區的環境資源案例,不斷深化長三角環境資源試點合作機制。加強區域內各法院主要共同司法政策和司法事項的共同協商、研究和解決,以及重大、復雜的法律適用問題,形成委托服務、委托取證、委托執行和信息通報的機制,以實現信息在流域各地法院之間更好地共享。
(二)長三角區域環境資源審判一體化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項新的政策與制度,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必然會存在一些問題,如與傳統訴訟模式的沖突、難以突破“區域司法合作”層面、跨行政區劃設立審判組織突破了現有立法等。
1.訴訟程序方面
根據《協議》與《實施辦法》的有關內容,不難看出,環境資源審判區域一體化,就是在長三角地區設立跨行政區域的環境資源審判機構,而非僅僅開展司法合作,統一審判標準。這勢必要涉及級別管轄和審判層級的問題。在江蘇省“9+1”的環境資源審判模式中,因涉及的區域仍在一省之內,尚可將所設立的環境資源審判組織的層級作為中級法院看待,不服其判決上訴至省高院。而環境資源審判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中所新設的區域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地位,是否可以理解為等同于高級法院,不服其判決結果是否直接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均值得商榷。
2.難以突破“區域司法合作”層面
根據南京中院、上海市三中院等落實《協議》所做的工作方案,筆者感受到,環境資源審判區域一體化目前在實踐層面仍停留在“區域司法合作”層面。如南京中院的工作方案共18條,重點還是從協作機制、信息共享、統一裁判標準、司法聯動等方面落實環境資源審判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這與“9+1”跨行政區設立審判機構的模式所追求的目標還是有一定距離的。
3.設立方式與現有立法間存在沖突
環境資源審判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除在江浙滬皖三省一市間開展司法合作、形成區域司法聯動外,還將參考江蘇“9+1”環境資源審判模式,突破原有行政區劃,以生態功能區為單位設立與行政區劃適度分離的環境資源審判機構。上海市對于環境資源審判區域一體化的落實,又主要采取了由上海市三中院歸口管理、集中管轄的模式。無論是跨行政區劃管轄還是集中管轄的模式,均與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有關審判組織的規定存在一定的沖突,而這又與《立法法》及有關規定中“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原則不相一致。盡管當前環境資源審判區域一體化僅在長三角區域試點,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定,但在不久的將來,設立方式與現有立法間的沖突,會進一步凸顯出來。而這一問題,不僅在環境資源審判區域一體化中存在,在整個環境立法與相關司法解釋等領域中均有所體現,必須認真研究,盡早拿出解決方案。
綜上所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在環境資源審判領域的實現之路還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