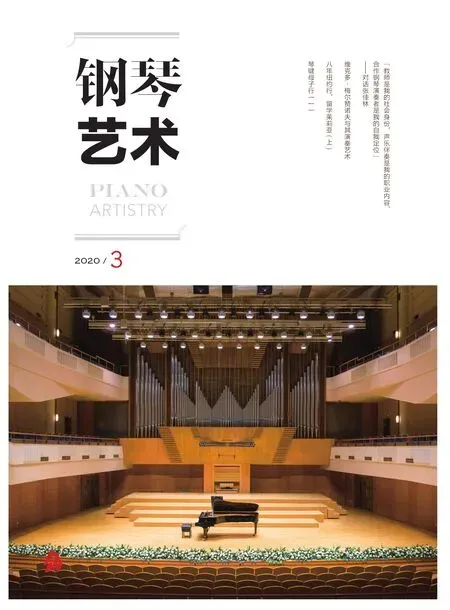朵朵花瓣,沁人心脾
——習張朝系列《兒童鋼琴組曲》所感
文/張 凱
引
在中國鋼琴音樂創作方面,張朝教授是一個不能不被提起的兼具“鋼琴家——作曲家”雙重身份的民族音樂家①。他的鋼琴作品,憑借獨到的和聲、豐富的情感、鋼琴化的技術,形成了獨特的音樂風格。一曲《皮黃》(1995),用鋼琴一展京劇韻味,在一氣呵成的篇章中吟唱出對人生喜怒哀樂的生命體驗;鋼琴小品《滇南山謠三首》(2002),在一幅幅絢麗多姿的民俗畫卷中抒發童年情景的回憶;詩情畫意般的《音詩》(2002),透過哈尼族、彝族音樂的音調,其內在所展現是父輩們對理想情懷的追尋和對人間親情、愛情的詮釋。此外,宏偉壯麗的《我的祖國》(2009),洋溢著英雄主義色彩、情節跌宕起伏的《敘事曲——歌唱二小放牛郎》(2013),以及《梅娘曲》(2013)等一系列鋼琴改編曲,都是作曲家對經典歌曲題材的回顧與鋼琴化創作實踐。2018年初,在“三亞國際音樂周”上,《自然一號》(“冰雪的冥想”——“烈焰的音詩”)這首動靜相宜、由強烈反差美學而帶來磅礴震撼效果的鋼琴作品中對演奏新技術的挖掘再造,展現了作者探索鋼琴新音響的不斷思考。還有很多耐人尋味的鋼琴小品、樂曲,等等,這些作品常被選為專業鋼琴教材和音樂會演奏曲目。不斷出新的鋼琴音樂創作,一方面與他兼具“鋼琴家——作曲家”雙重身份有關,專業演奏與創作相輔相成;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鋼琴音樂創作所追求的終極目標——“鋼琴的中國夢,讓鋼琴發出中國的聲音,表達中國的內容”。
本文對作曲家新近創作的《兒童鋼琴組曲》②進行介紹,力圖展現作品的藝術魅力,同時也借此表達和闡述筆者對中國鋼琴音樂創作以及兒童鋼琴教育的一些拙見。
追根求源
激發作者創作初衷的是他注意到在數量眾多的中國鋼琴作品中,為幼兒可彈,且具有藝術深度的作品并不豐富。中國作為鋼琴大國,琴童數量巨大,理應有更加多元化的兒童鋼琴作品,特別是帶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鋼琴曲。他認為:音樂可以開啟兒童的天性,陶冶情操,增進他們心理、生理的健康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燦爛多彩,若是在兒童時期就接觸到具有各民族特色的音樂,通過音樂領會其中的獨特內涵,就能夠使他們既領略了音樂的魅力、增加了彈琴的樂趣,又接受了多元文化的熏染。在幼年時期通過鋼琴彈奏接觸民族音樂,于潛移默化中植入民族音樂的種子,開啟音樂心靈 。獨樹一幟的視角,激發了作者的創作熱情,經過多年的采風調研,作曲家將民族音調加以改造和創新,融合多種素材和手法,創作出富含民族風情與時代氣息,融形象性、藝術性和技術性于一體的系列《兒童鋼琴組曲》。
多彩神韻
全作包含《兒童新疆組曲》《兒童西藏組曲》《兒童云南組曲》《兒童內蒙古組曲》《兒童東北組曲》《兒童廣西組曲》《兒童湘西組曲》《童年日記》等近三十首新穎別致的音樂小品。縱觀其貌,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在標題方面,既有帶形象性標題為指引的組曲,如《童年日記——晨、風、湖、趣》;也有以不同的速度術語為引導的組曲,如《兒童新疆舞曲》《兒童西藏舞曲》等。
在技術課題方面,這幾十首作品中盡可能地涵蓋了鋼琴技術要點,并以簡潔的方式進行表達,通過巧妙的技術刻畫,使兒童在視奏階段就能快速上手,技術提升后再進行內涵性的強化練習,直至音樂熟練入心,深刻地凸顯出以兒童接受為核心、不以技術繁復為目標的創作理念。樂曲織體清晰,語言簡練,音響變化豐富,有著生動樸實的感染力,著實突出了為兒童而創作的本意。
在曲式結構方面,布局樸素,篇幅短小,大多為一段式或帶擴充再現的二段式、多段式,充分顧及兒童的能力特點和接受力,不追求以長度來容納深度,以小見大而蘊含完整的思想意境。一曲終了,既可以感受到作曲家的精心構思,又有一種即興而作的感覺,在小而美的曲體中發揮想象,舒展民族音樂的韻味。
在和聲調性方面,和聲簡潔又考究,充滿靈動的色彩,音樂思維以旋律為主導,聲部旋律化,可唱性的樂句感強。在和聲上保持傳統的元素,同時又大膽突破,在不復雜的形態下盎然有趣,飽滿有張力。每一首曲子都運用了轉調,有時在意料之中,有時又頗具意外,使演奏者于聲音的塑造和聆聽中受到民族音調的浸染。
在音樂內容方面,組曲音樂素材廣泛,曲調多樣,取材范圍北至東北三省,南至湖南、廣西,西至新疆、西藏,并涵蓋了多地少數民族區域,恰是一幅遼闊壯麗的少數民族音樂地圖,新穎的音樂語言與個性化樂意處理,是新時代下對少數民族音樂新的氣質形態的闡釋。
這些在多年實踐中打磨出來的兒童音樂小品,凝聚了作者的創作智慧,將自己的藝術理念付諸實踐,在實踐中走出自己的創作風格之路,看似隨筆式的寫作實為精準的凝練,民族風格突出,鋼琴技術精巧,不僅是兒童,成年人在彈奏時亦不覺其淺顯,更有回味無窮之感。
循音探樂
鑒于篇幅原因,本文選取其中的三套組曲進行分析解讀。
《兒童西藏組曲》(2018)由三首無標題小曲組成,以速度術語和表情術語作引導,由“快——慢——快”的結構組成,在速度與情緒上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樂曲中,作者運用藏族民間音樂的音調加以發揮,表現出藏族音樂的風格韻味。第一首“Allegretto”,是一種藏族儀式中類似“神童的舞蹈”的描繪,氣氛莊重而沉穩,帶著宗教的神秘感,聽聞旋律,即被帶入到一種獨特景境。其中最富特色的是左手重音的刻畫,被強調的重音好像是某種“奇特”的東西突然跳出來,令人感到意外,這種表現手法,是為了再現藏族宗教儀式中獨特的手勢動作特點。曲中觸鍵多是斷奏,涉及半連音、跳音、保持音、二連音等多種奏法,猶如藏族民間音樂中的鼓點、舞步特征,六十七小節的長度一直保持著音樂情緒的變化,盡管音符不多,但旋律線條清晰,音響效果動人,通過特色手法達到了音樂色彩上的對比。
第二首“Moderato”,長線條的旋律給人以寬廣寧靜感,音樂起伏平緩,但主題音調在高、低音域中做對唱,展現出藏族音樂所具有的高亢悠遠之特點。在這樣的音響中,使人仿佛置身于遼闊的西藏高域,在一望無際的天際線、蒼穹下,深深地呼吸,盡情地歌唱。通過這樣純凈、樸素的意境,令兒童在彈奏時獲得情緒上的啟發,在體味音樂的同時得到心靈的熏陶與洗滌。在分句特點上,樂句長度的起伏與演奏者的呼吸長度基本是一致的,一呼一吸,仿佛人琴合一,使兒童在彈琴的過程中既訓練了歌唱性奏法,又自然地融入旋律線條的走向。
第三首“Allegro Felice”,全曲始終保持一種快樂的幸福感,上下環繞的小音程式的旋律精短且富有強烈的律動,時而低音婉轉,時而高音悠揚。作曲家借鑒了藏腔中聲音短促、有力的特點,并加以切分節奏的強調,形成一種自豪灑脫的“堆諧”風格的旋律音調④,“踢地” 式的邊歌邊舞,生活的幸福感、滿足感通過音樂躍然而出。樂曲中左手低音部分是歐洲古典音樂中阿爾貝蒂低音的變形,沒有停頓,作者結合音樂內容的需要,再運用藏族民間音樂的某些特征,創造出符合樂曲思想、情感表達需要的低音織體,并在反復行進中做巧妙的變化。兒童在重復彈奏的過程中得到肌肉強化和技術訓練,更從中獲得演奏的樂趣和幸福感,這種幸福感是彌足珍貴的,對其心靈起到了潤物細無聲的滋養。
《兒童新疆組曲》(2013)融合了新疆風格曲調的諸多要素,民族手法突出,三首小品中彌漫著濃郁的新疆音調。第一首“Allegro”,在短小的篇幅中,小二度、純五度、增四度、減五度等多色彩和聲,通過巧妙的組合與微妙的音調變化來加強音響層次感與旋律表現力,描繪出獨特的新疆音韻,曲中用波音、同音反復的旋律手法,模仿維吾爾族鈴鼓、木卡姆彈撥樂器清脆、明亮的聲音,并在重復時輔以復調手法的裝飾,在大小調的交替演奏中,渲染出豪邁灑脫的民族氣質。
第二首“Largo”,該曲樂思之豐富讓聽眾“吃驚”,以浪漫主義手法的表現特點抒發了深刻動人的情感,音樂細膩委婉,三十二小節的長度容納了豐富的內涵。樂曲一開始顯現出舒緩優美的主題,相比第一首的舞蹈性質,這一首仿佛是人們在草原上停舞高歌。中間部分,多種音程變換行進,都融入了具有新疆特色的音調,簡潔洗練的旋律與生動的復調思維,營造出一種“寧靜的流動”的境界。一曲終了,使人不禁聯想起舒曼的《夢幻曲》,令演奏者反復品味,沉浸其中。
《兒童云南組曲》(2020)又名《佤山童謠》,由五首具有佤族民歌特色的小曲組成,分別是:《晨歌》《山歌》《獵歌》《夜歌》《木鼓歌》。五首小曲連貫而成,連續演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是組曲與多段體相結合而成的一種新形式,追求于完整、連貫的樂意中強調形象內容的變化,五個樂段貫穿發展,聯系緊密,既有獨立的樂思,又順循著內在的發展脈絡。就整體而言,樂曲描述了山寨中人們美好快活的一天;分開來看,也可以理解為生活中的五個場景與畫面。既抽象又具象,以此啟發兒童的想象力。
歡快的《晨歌》為引,速度為 =130,八分音符動機構成的主題在高、低聲部間三次輪唱,仿佛山間晨時一片生機勃勃,伴隨著悅動的節奏,人們開始了新的一天。主題的三次再現都建立在不同的和聲變化上,三度、五度音程形成了生動的音響色彩。接著,曲風一轉,進入悠揚流淌的《山歌》,速度為 =66,《山歌》由短短十七小節的兩個樂句組成,樂曲中高低音區的音距與雙手旋律間的和弦差異,塑造出特有的空間感與音色美感。主題的第二次重復中,低聲部由動態的單聲織體變為靜態的和聲烘托,仿佛山間歌聲隱隱回響。之后,一天當中最令人激動的打獵活動開始了,《獵歌》的速度為 =186,節奏律動短促有力,低聲部五度、六度音程貫穿而終的頓音演奏猶如行進中鏗鏘的步伐。中間經過一個小小的移調,增加了音樂的趣味性和畫面感,熱烈的情感在《獵歌》中得以暢快地宣泄。臨近結尾,以單音的延長自然過渡到了《夜歌》。《夜歌》的速度為 =60,音樂表達饒有特色,低聲部兩小節的旋律烘托反復循環至終,旋律中二度、四度和五度構成的上行進行,和聲別致,具有一種寧靜的期待感。在二十五小節的長度中,右手的主題旋律在五次吟唱中完成,然而,每次都是這一樂句的變化重復,巧妙的旋律變體令聽覺上不覺古板單調,體現出音樂簡約而不簡單的意圖。暮落時分,歸家,村寨回歸到傍晚的寂靜安寧。最后,組曲在歡騰熱烈的《木鼓歌》中結束,渲染出村民圍著篝火歡快起舞的場景。《木鼓歌》中速度回至 =134,與《晨歌》達到幾乎一致的速度。在曲式上采用的是回旋曲式,樂曲的主題特性在這一結構中得到強調,其中快速交替的切分和弦形象鮮活,富有動力。在插部中,左右手以卡農二聲部手法和連、跳奏的區別,形象表現出“跟歌仿唱”的情景,第二插部則是第一插部卡農織體的變體,增添了更多抒情的意味。作品巧妙地將回旋曲式結構以凝練的因素來展現,使兒童在變化發展的音樂情境中掌握該曲式特點。
終
兒童期是人生成長過程中最關鍵的時期,這一階段所受到的音樂熏陶與音樂教育會對其終生音樂素養的形成起到重要影響。通過對作品的演練和解讀,促使兒童在早期鋼琴學習中接觸民族音樂而建立起母語審美,較之于成年后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縱觀近幾年我國兒童鋼琴教材,在作曲家群體的辛勤耕耘下已碩果豐實,兒歌樂曲、民歌小曲、彈唱歌曲、創作類樂曲等繁多種類,極大地充實了兒童鋼琴音樂文獻,為琴童的學習成長提供了條件。從中國鋼琴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應更多地觀照兒童鋼琴教育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鋼琴文本、鋼琴教學法、演奏實踐等,以及最為重要的中國鋼琴作品創作、中國鋼琴教育。以上幾者之間是互為融合發展的關系:有意義的作品會推動教育、演奏的積極發展,好的教育和演奏會催生更好的作品誕生,幾者的良好互動促進了鋼琴教學法的全面提升,相信最終會推動有特色的中國鋼琴學派的形成。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著絢麗多彩的文化,在中華民族大花園中綻放著各自獨特的魅力。對琴童而言,應該有充足的音樂作品伴隨他們的學琴生涯,這樣會有助于他們形成中國特色的多元審美能力。作為中國人,彈奏的是代表著西方音樂文化和歷史的鋼琴,在音樂、技巧的學習中,如果缺失了中國音樂的元素,練琴就變得單一,也缺少了民族之魂。因此,在彈鋼琴的早期階段,從娃娃開始抓起,使其在多元文化的音樂環境里學習和成長,建立起民族音樂的母語意識,從長遠的歷史時空來看,一定會推動未來在世界范圍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風格的鋼琴藝術文化。
注 釋:
①在百年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歷史中,很多具有鋼琴家身份的作曲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創作的鋼琴作品歷久彌新,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這種具有雙重身份的作曲家群體,我們用“鋼琴家——作曲家”這一特定名稱來稱謂他們。
②《兒童鋼琴組曲》是作曲家系列鋼琴曲集之一《兒童集》中的作品。
③摘自本文作者與張朝于2019年6月的訪談記錄,未刊稿。
④藏族的一種民間歌舞,因舞蹈中有較多的踏地動作,也被稱為“踢踏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