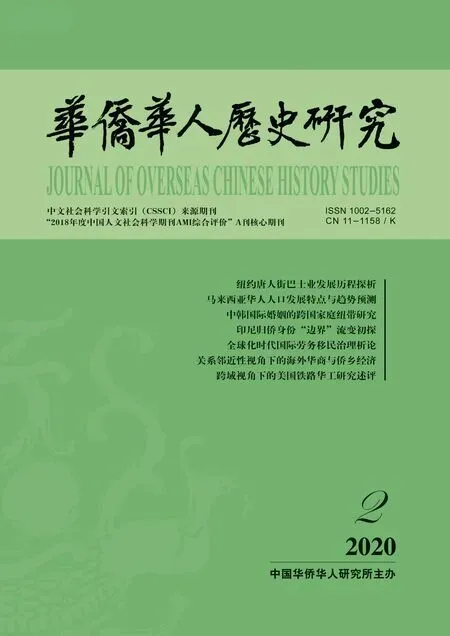抗戰期間廣東省銀行溝通潮梅匯路之研究*
袁 丁 秦云周
(中山大學 歷史學系,廣東 廣州 510275)
潮梅地區是潮屬地區(汕頭、潮安、潮陽、揭陽、普寧、澄海、豐順、南澳、大埔、饒平、惠來)和嘉應五屬(梅縣、興寧、平遠、蕉嶺、五華)的合稱,其范圍相當于如今汕頭市、潮州市、揭陽市及梅州市所轄地區。[1]潮梅地區在我國僑匯經營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每年華僑匯款,“匯往潮梅一帶者,多集中汕頭,約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全國僑匯總額——筆者注)”。[2]然而,這一巨額的僑匯資源卻長期掌握在民營僑批業手里。抗日戰爭爆發后,僑匯作為一種重要的外匯資源,成為中日雙方在華南爭奪的焦點。為切斷我國的對外交通線,掠奪豐厚的僑匯資源,日軍于1939年6月侵占汕頭并封鎖潮汕沿海,致使大批僑匯滯留香港,潮梅匯路梗阻。潮梅匯路暢通與否,不僅直接關系著數百萬僑眷的生計,更是關系到華南抗戰的成敗。如何溝通潮梅匯路,就成為國民政府及廣東地方政府為舒緩僑困并爭取海外僑匯資源而必須解決的重大金融問題。針對該問題的深入探討,對理解戰時國民政府僑匯管理政策及華南抗戰格局的最終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有關潮梅匯路的研究,張慧梅探討了1939—1945年潮汕與東南亞之間的僑匯流通及背后的金融與傳統人文網絡;[3]焦建華集中探討了太平洋戰爭前潮汕淪陷區僑匯業的變遷;[4]泰國學者黎道鋼論述了暹羅銀信局公所為溝通潮梅匯路所做的努力;[5]袁丁認為,汕頭淪陷后,國家行局(主要是郵政局)的僑匯業務依然在運作,國統區與淪陷區之間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僑匯合法流通。[6]學界對該問題雖然做過一定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國家行局和民營僑批業,針對廣東省銀行的研究仍然薄弱。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集中考察1939年6月汕頭淪陷后廣東省銀行(以下簡稱“省行”)溝通潮梅匯路的成因、成效及局限,進而分析其對華南抗戰的作用及貢獻。
一、汕頭淪陷前省行潮梅匯路經營概況
廣東省銀行的前身是1924年8月15日孫中山親手創辦的中央銀行,第一任行長是宋子文,享有發行紙幣、代理國庫及代募公債等特權。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另設中央銀行于上海,廣東省的中央銀行于1929年3月1日奉令改稱廣東中央銀行,該行繼承前中央銀行全部資產負債,由省庫撥足資本1300萬,從此變為地方銀行性質。由于對前中央銀行發行之紙幣負有兌現之責,故仍加上“中央”二字;由于其資產由省庫撥付,純屬省立銀行,為循名責實,劃清界限起見,1932年1月1日再次奉令改組為廣東省銀行。1936年7月廣東“還政中央”以后,孔祥熙親信顧翊群為行長,宋子文之弟宋子良為董事。此廣東省銀行既不同于1912年成立的廣東銀行,也不同于1920年成立的省立廣東省銀行。[7]1939年6月汕頭淪陷之前,廣東省銀行雖然有較好的經營網絡,但在廣東僑匯中仍處于“從屬”地位。
(一)汕頭淪陷前省行潮梅僑匯經營網絡的構建
僑匯是廣東經濟的重要支柱,直接決定著廣東經濟的興衰。省行作為廣東地方金融的樞紐,發展僑匯業務不僅是自身業務商業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順應廣東地方經濟“外向型”特征的內在需求。隨著抗戰局勢的緊張,“吸收僑匯已成為粵省當局施政計劃之重要部分,其執行機關則為廣東省銀行,廣東省銀行年來皆以吸收僑匯為主要業務”。[8]為擴大匯路,在廣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省行積極向海外擴張。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省行海外僑匯經營網絡構建的關鍵一環即是新加坡分行的設立,這使得省行在粵僑集中的南洋地區有了經收南洋各埠僑匯的樞紐。此外,省行還在廣州灣、澳門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對于未能直接設立行處的暹羅及法屬安南,省行派員赴潮僑集中的暹羅辦理通訊及僑匯事宜。[9]省行還在法屬安南設立了海防通訊處,該處的設立,不僅可以和已成立的香港分行、廣州灣辦事處等行處遙相呼應,而且對于辦理法屬安南、英屬緬甸僑匯極為有利,“是時仰光僑款由批局帶至海防轉匯回國者為數甚巨,本行在僑胞中有甚深之信賴”。[10]截止1939年6月汕頭淪陷以前,省行的僑匯經營網絡已初步形成了集南洋攬收、香港中轉、省內解付于一體的格局,呈現出省內解付優勢明顯而海外分支機構明顯不足的特點。但省行作為華南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機構所構建的海內外僑匯經營網絡、積累的僑匯運營經驗及相應的人才儲備,決定了其可以在華南抗戰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汕頭淪陷前省行在廣東僑匯中的地位和作用
僑匯是數百萬僑眷的主要生活來源,“潮人仰賴批款為生者幾占全人口十之四五”。[11]據吳承禧研究,就潮梅僑匯來源來說,暹羅占50%,英屬馬來占30%,法屬安南占10%,荷屬東印度占6%,南洋其他地區占4%。[12]鑒于潮梅僑胞多集中于南洋,潮梅地區又是我國重要的僑匯區,省行一開始即把南洋及潮梅地區作為僑匯經營的重點區域。到1939年6月汕頭淪陷前夕,省行在潮梅地區已形成以汕頭分行為中心,以潮安、梅縣、興寧等行處為輔助的僑匯經營網絡,但這些分支機構均集中在汕頭及縣一級,而未能深入廣大僑眷居住的偏遠地帶。從其海外僑匯經營網絡來看,雖在潮梅僑匯最大來源地暹羅設有通迅處,但要有效吸收暹羅僑匯,直接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將是省行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對于潮梅僑匯另一重要來源地之新馬地區,省行在新加坡已建立有分行,輔以眾多的通匯處,吸收新馬等地僑匯顯然不成問題;在法屬安南和英屬緬甸,雖可以通過海防通訊處聯絡批局吸收兩地僑匯,但省行在上述兩地未能直接設立分支機構,制約省行吸收兩地僑匯的成效。顯然,省行潮梅地區及海外分支機構數量過少且布局不均衡,是制約省行吸收僑匯的重要原因。
據統計,省行吸收的潮梅僑匯從1937年的不足200萬元法幣劇升到1938年的1156.8萬元。[13]但相對于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僑批局和水客而言,依然“微不足道”。據統計,1937 年潮梅僑匯共計法幣6200萬元,而民營僑批業累計吸收的僑匯就高達5700萬元(其中僑批局4000萬元法幣,水客1700萬元)。[14]由此可見,汕頭淪陷前,無論是海內外的僑匯經營網絡,還是僑匯經營的成效,省行在潮梅匯路中均處于“從屬”地位。
(三)國民政府既利用又限制的僑匯管理政策
抗戰之前,廣東與南京國民政府關系不甚緊密,國家行局在廣東分支機構有限,省行遂成為廣東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機構。民營性質的僑批業則是閩粵地方僑匯經營的重要力量。僑匯作為國民政府外匯的重大來源和抗戰資金的主要構成要素,對于平衡國際收支、購置抗戰武器裝備、維系僑鄉經濟和上千萬僑眷生活有重大意義。最大程度集中僑匯成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外匯管理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有效集中僑匯,國民政府轉而采取爭取和團結閩粵兩省地方銀行和僑批業的政策,“一面充實僑匯機構,一面擬定僑匯合作辦法,督促各經營僑匯機構切實合作,形成一吸收僑匯之金融網,并責成中國銀行總其成,聯絡閩粵兩省銀行、閩粵省僑批業、郵政分支局,以廣吸收”。[15]但這種爭取和團結是以國家行局主導僑匯經營為前提的,它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兩重性,即國民政府鼓勵、支持國家行局,使之成為僑匯經營的領導和主干,對閩粵兩省地方銀行則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一方面要限制其向海外拓展,以免成為國家行局吸收僑匯的強勁對手;另一方面鼓勵、支持其在本省推設分支機構,以便更好地為國家行局的僑匯經營服務。由于國民政府嚴格限制閩粵兩省地方銀行海外拓展的政策直到1939年1月28日財政部公布《吸收僑匯合作原則》和《銀行在國外設立分行吸收僑匯統一辦法》才予以明確,在此之前,因政策相對寬松,省行得以構建起以南洋為重點,以香港分行、新加坡分行、澳門支行為樞紐的海外僑匯經營網絡。尤其是香港、新加坡兩分行的設立,使得省行可以借助近代以來形成的以新加坡——香港為主要渠道的亞洲地區金融網絡,[16]擴大和強化海外僑匯經營網絡。
二、海內外各方為溝通潮梅匯路建言獻策
1939年6月汕頭淪陷后,因日軍封鎖潮汕沿海致使潮梅匯 路梗阻,中國銀行、省行等公辦行局后撤內地,使得僑款轉駁困難、僑匯頭寸缺乏,再加上地方不靖,導致匯路安全缺乏保障。在此形勢下,數百萬僑眷嗷嗷待哺,海外僑領在致廣東省政府的函件中大聲疾呼,“茍不設法救濟,前途寧堪設想”。[17]然而環顧當時潮梅匯路的各種經營機構,長期主導潮梅匯路的僑批業因日軍入侵遭到了沉重打擊,幸存的僑批業又無力單獨解決批路安全等問題;國家行局在該地分支機構本來就不多,且已撤至內地;因此,溝通潮梅匯路的重任就自然而然落到了省行身上。為此,海內外各方迭次請求廣東省政府及省 行早日溝通潮梅匯路。
(一)國民政府要員、海外僑領及僑批業推動溝通潮梅匯路
1939年6月汕頭淪陷后,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出于維護中行的經營利益,要求廣東省政府及第四戰區維護批路安全。1939年6月24日,他致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廣東省主席李漢魂,“擬懇請駐潮梅駐軍派兵保護批局分發各縣僑款,以冀安全。”[18]爾后,長期經營潮梅匯路的僑批業通過 跨國網絡和機制化運作,進一步謀求借助廣東省政府及省行的力量,以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因暹羅是潮梅僑匯的最大來源地,暹羅銀信局公所率先作出反應。6月24日,該公所致電李漢魂及財政部駐港專員,尋求僑批投遞,最終無果,于是決定自6月30日起暫緩配往香港僑批。[19]隨之,旅港潮梅商幫紛紛要求省行設法救濟。[20]8月15日,代表僑批局利益的汕頭市商會主席陳煥章致電李漢魂:“懇商國家銀行著南洋各埠分行與批局妥定匯兌分發辦法,救民倒懸,至各縣分發批款盡可由各批局辦事處由縣負護送責。”[21]新加坡潮幫各匯兌商則提議妥速在揭、饒兩地增設行處,其中饒處擬設黃岡,揭處擬設棉湖墟。[22]
暹羅、新馬地區是潮梅僑匯的主要來源地,面對潮梅僑匯梗阻的困境,兩地僑團紛紛展開救鄉活動,其中以暹羅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影響最大、成績最著。他祖籍廣東澄海,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感和桑梓情結,面對家鄉的淪陷,多方尋求解決之道。7月20日,他致函僑委會委員長陳樹人,系統闡明了僑匯對僑鄉、僑眷及國家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溝通潮梅匯路的具體舉措,“擬請政府在香港設一僑匯機關,或指定銀行辦法,一方與南洋各地華僑銀信局聯絡,將所有僑批悉在香港集中,然后由香港轉道淡水惠陽送入內地,或由航空輸桂林轉韶關,再輸入內地,并以興寧或梅縣為僑批內地集中處,然后由駐防軍護送至各縣各鄉。以策安全。總之,一方宜盡量采用現有民信局深入民眾之辦法,一方宜統籌統辦,以求經濟快捷與安全。僑眷生活與外匯吸收,實深利賴。”根據暹羅中華總商會的建議,7月21日,他再次致函陳樹人,“現在救急辦法須由廣東省銀行迅為廣設縣辦事處接發僑批”,并懇請陳樹人轉呈行政院電飭省行照辦。[23]至此,蟻光炎明確形成了由廣東地方政府保障批路安全,省行主導溝通潮梅匯路的構想。這一構想集中反映了國民政府集中僑匯的政策和救助廣大僑眷的愿望,頗具前瞻性和可行性,得到了陳樹人、廣東地方政府、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馬來亞潮州公會聯合會主席戴澍霖、檳榔嶼潮州會館等海內外各方的積極響應。
(二)地方政府、潮籍要員及第四戰區對于溝通匯路的各自考量
潮梅匯路梗阻,僑眷生計無著,直接關系著當地的社會穩定和華南抗戰。因此,潮屬地方政府、潮籍要員、第四戰區紛紛要求早日溝通潮梅匯路。應該說,在潮屬地區增設行處,是普遍共識。但在具體行址的選擇上,則各有其利益考量。潮屬地方政府關注的是本地利益和社會穩定,因此多希望省行在自己轄區或靠近自己轄區的地方設立行處。1939年7月9日,普寧縣長杜邦致電李漢魂,建議省行在普寧當地設立行處。[24]潮籍要員劉候武因長期工作、生活在暹羅,和暹羅頗有淵源。他提議省行在普寧鯉湖設處以接發暹羅僑匯。[25]因南山管理局靠近普寧,杜邦的建議得到了南山管理局局長黃端如的積極響應。[26]8月2日,揭陽縣長陳友云提請省行在毗鄰揭陽的普寧或湯坑設立辦事處。[27]潮梅匯路持續梗阻,將直接影響華南抗戰的順利開展。第四戰區特派員林雁峰在巡視東江途中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8月18日他致電李漢魂,“乞飭省行或商中行迅辦南洋各埠匯兌,并在潮、揭設分行,以濟燃急。”[28]其后,這一情況上報至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為此,他于8月30日電告李漢魂,要求妥速籌辦具報。[29]其后,根據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何春帆提供的情報,9月7日他再次電告李漢魂,要求從速解決糧食恐慌和僑款阻滯問題。[30]張發奎作為負責兩廣對日作戰的最高指揮官,其電文的分量不言而喻。其后,廣東省臨時參議會(簡稱省臨參會,作者注)吳鼎新議長、同屬潮籍的省臨參會 議員許觀之及同盟會元老方瑞麟,也積極為溝通潮梅匯路建言獻策。
顯然,圍繞潮梅匯路的溝通,海內外各方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又有利益的差異性,這與各自的站位及代表群體的利益密切相關。在由廣東地方政府力量保障批路安全的基礎上由省行主導溝通潮梅匯路,是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利益的差異性則主要體現在新增行處處址的選擇上。地方各方的互動,也推動了省行早日溝通潮梅匯路的落實。
三、省行溝通潮梅匯路的保障與實施
抗戰爆發后,因中央銀行在廣東分支機構過少且實力較弱, 省行事實上又承擔著領導廣東全省對日金融戰的重任。因此,打通潮梅匯路就成為省行戰時的重大使命。而要溝通潮梅匯路,就要從維護批路安全、保障頭寸接濟、便捷僑款轉駁等多方面著手。
(一)潮梅匯路安全的有效保障
批路安全是僑批業正常開展僑匯經營活動的前提和基礎,要溝通潮梅匯路,首要任務就是維護批路安全。由于戰時國民政府執行的是爭取和團結僑批業的政策,中國銀行作為國家行局經營僑匯的主力,因在潮梅地區分支機構有限,當地的僑批業遂成為其僑匯解付的重要依托。為此,宋子文要求廣東省政府及第四戰區為當地批局提供安全保障。由于他長期位居中樞,對其要求,李漢魂自然不敢怠慢。1939年7月12日,他復電宋子文,稱已分別責令保安處轉飭駐潮梅各部隊,第五、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轉飭所屬各縣政府切實維護批路安全。[31]此外,省行依托自身優勢,積極為僑批業提供批路安全、轉駁僑款等服務。有信銀莊(批局)司理芮詒壎曾在回憶文章中指出:“廣東省銀行在國統區各縣前線設點,接應批款,繼而不辭艱險,武裝押運。后來還請準將所屬批局解送批款員工穿著軍裝,荷槍實彈解款,由汕頭僑批公會理事長萬興暢批局經理許自讓充當隊長。”[32]
(二)省行潮梅僑匯經營網絡的擴大與完善
僑委會為國家僑務管理的最高機關,團結僑領、維護僑胞利益是其重要職責。陳樹人和廣東有很深的淵源,熟悉省情和僑情,因此他積極支持蟻光炎的主張。在僑委會、廣東省政府、暹羅中華總商會多重壓力和敦促下,省行將蟻光炎的建議一一落實。1939年8月11日,廣東省政府函復僑委會:“今后潮梅各屬僑胞匯款,當依照原定計劃盡量吸收,先集中于香港分行,然后以梅縣、興寧兩分行為中心,大埔、松口等辦事處為協助,并擬于蕉嶺、丙村及潮屬各縣未淪陷之適中地點增設辦事處,盡量充實頭寸,以期輸送迅速,便利僑胞。”[33]鑒于省行既有的行處多集中于梅屬地區,因此在潮屬之揭、饒兩地增設行處將是省行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根據蟻光炎、劉候武及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的建議,省行當即派員前往揭、饒兩地籌備。[34]作為應急措施,省行還打算將普寧省分金庫改組為辦事處。[35]為加快揭、饒兩地籌設行處進程,劉候武還通過李漢魂對省行施 加壓力,“若再不設法,恐怨聲隨起,并將影響宣慰專員工作”。[36]隨著省行在上述兩地增設行處的成功實施,11月6日,潮梅匯路得以完全溝通。[37]
(三)省行與僑批業關系的調整和改善
私營僑批業長期根植于南洋和閩粵僑鄉,在多年的市場競爭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經營模式和不可替代的優勢。因此省行要有效地溝通潮梅匯路,一方面需要聯絡海外僑批業以擴大匯路,另一方面需要依托當地僑批業以有效解付僑匯。為便捷僑款解付,省行一度考慮與郵局合作,但郵局輻射范圍有限且收費昂貴,省行轉而與僑批局合作。以與省行建立特約代理匯款關系的陸豐吉祥莊為例,最明顯的成效就是省行可以依托吉祥莊長期經營僑批形成的良好社會信譽,以較低的成本快速將僑匯網絡進一步延伸至河婆及附近鄉村。[38]通過這些特約代理匯款店,省行將僑匯解付網絡由市縣一級進一步延伸到揭陽河婆,豐順留隍,梅縣白渡、銀市、畬坑、宮市、西陽、中部墟、長沙、南口、太平墟,普寧棉湖、五云洞,大埔之大麻、湖寮及揭陽縣城等地。[39]對于僑眷集中的偏遠地帶,則進一步發揮水客的作用和優勢。
擴大匯路是省行溝通潮梅匯路的應有之義。為此,省行一面與海外同業訂約通匯,一面聯絡海外僑批局和水客。在南 洋一些重要商埠,“如星加坡(大坡、小坡)峇珠巴轄、吉隆坡、關丹、昔乜加、金保、美里勞勿、文德甲、怡保、居鑾、古來等埠,亦先后覓得通匯處與代理點二十余家。并為推廣荷印僑匯起見,特委托實武牙埠廣成公司通匯處,又與荷屬張立端批局訂約吸收僑匯”。[40]而要有效吸收僑匯,非假手水客不可。因此省行要求東江各行處及新加坡分行與各地水客緊密周旋,妥為招待。[41]通過聯絡海外僑批業,省行得以將僑匯攬收網絡覆蓋到南洋廣大地區,這是省行擴大匯路并增加僑匯的重要基礎。
四、省行溝通潮梅匯路的成效
省行在溝通潮梅匯路的過程中,在潮梅、東興、昆明、重慶等地遍設行處,形 成了完善的經營網絡。這一優勢使得新馬等地淪陷后,越、老、柬及暹羅等地的僑批業能夠將收集的僑匯通過省行東興辦事處轉駁到粵東、閩南等地,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944年11月。據統計,1939—1941年,省行累計吸收潮梅僑款將近2590萬美元;到1942年底,省行東興辦事處直接吸收的僑匯高達法幣3900余萬元。[42]這對于維系數百萬僑眷生計并爭取人心,為改善廣東地方財政和厚實抗戰資源,為贏取華南抗戰的最終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日方也不得不承認,“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方在華僑匯款方面獲得之外幣極少,而法幣卻因獲得間接滋潤支持而對國民政府之抗戰經濟產生正面維護作用。”[43]
省行之所以能溝通潮梅僑匯,首先是省行具有銜接海外僑居地社會和國內僑鄉社會的網絡優勢。從法理上說,省行既是國家金融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廣東地方推行國家僑匯政策的主導力量,因此省行得以在海外建立起以南洋為重點,以香港、新加坡兩分行為軸心的海外僑匯經營網絡,從而最大程度將僑匯攬收網絡擴展到南洋僑居地社會。在潮梅僑鄉,省行一面普設機構,一面通過聯絡僑批業,打通了僑匯解付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起深入僑眷的僑匯解付網絡。其次是省行具有溝通廣東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身份優勢。“國父手創”的金字招牌和中央銀行的“高貴出身”,是省行與中央政府長期保持密切聯系的歷史基礎。從職能上看,省行除兼代國庫外,還代理省庫和縣庫,這是省行得以溝通中央政府和廣東地方政府的職能基礎。最后是省行所具有的地緣優勢和靈活務實的經營策略。省行長期作為廣東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和廣東地方淵源頗深,省行上下又以粵籍為主,相對國家行局來說,發展僑匯業務更易獲得當地的認同和支持。省行作為廣東地方金融的樞紐和華南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機構,正是憑借上述特色和優勢,在溝通潮梅匯路的過程中得以發展壯大。
由于省行的地方屬性,1939年1月28日財政部公布政策,限制地方銀行海外拓展后,省行無法向海外拓展,“本行原擬在美洲、南洋各地普遍推設行處,以利僑匯之吸收。因財政部對各省地方銀行在國外設立行處限制甚嚴,以致未能實現”。[44]這使得省行僑匯來源相對單一,直接制約了省行吸收僑匯的效果。而作為國家行局的中國銀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卻在海外增設了18個行處,[45]僑匯來源廣泛而多元。此外,英、法、荷等國在南洋屬地實施的外匯管制以及英美對中國資金的封存,對省行吸收僑匯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據統計,僅因香港凍結中國資金關系就導致省行僑匯減少了約1000萬元法幣。[46]
五、結語
抗戰以前,隨著中央集權和經濟壟斷的逐步推進,南京國民政府力圖限制和取締私營僑批業,但成效并不顯著。華南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采取團結閩粵兩省銀行和僑批業的政策,體現的是經營僑匯的思路,潮梅匯路得以溝通,從而為我們從地方層面認識戰時國民政府的僑匯政策及抗戰救濟提供了新的視角。這一匯路之所以得以溝通,離不開戰時的特定環境和海內外各方的積極推動。在此過程中,省行能夠順應時局發展,合理聽取海內外各方的意見,并及時改善了與僑批業的關系,由此實現了互利共生、合作共贏。
1939年6月汕頭的淪陷,為省行溝通潮梅匯路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在此過程中,省行依托自身優勢,積極聯絡僑批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國民政府嚴格限制省行海外拓展的政策和自身分支機構相對不足的局限,在溝通潮梅匯路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而在特定的戰時背景下,長期主導潮梅匯路的僑批業遭受重創,省行作為公辦行局所具有的經營網絡和政府背景,相比民營僑批業,更契合廣大僑胞匯款尋求安全的心理需求。在辦理僑匯業務環節,不同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注重吸收大額商業匯款,省行以辦理小額家用匯款為主,從而避免了和國家行局在吸收僑匯上的正面競爭。[47]由于“華僑小額家用匯款確是近代僑匯中的主體和極具穩定性的部分”,[48]因此,省行溝通潮 梅匯路不僅直接惠及了數百萬潮梅僑眷生計,進而為配合和支持國家行局辦理僑匯,為厚實抗戰資源,贏取華南抗戰的最終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國民政府的限制政策及戰時的影響,也制約了省行在潮梅匯路中發揮更大作用。
[注釋]
[1] 謝雪影:《潮梅現象》,汕頭:汕頭時事通訊社,1935年,第1~5頁。
[2] 童蒙正:《中國戰時外匯管理》,重慶:財政評論社,1944年,第303頁。
[3] 張慧梅:《戰爭狀態下之金融與傳統人文網絡——1939—1945年潮汕與東南亞間僑匯流通研究》,《潮學研究》第11輯,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
[4] 焦建華:《太平洋戰爭前潮汕淪陷區僑匯業研究(1939.7—1941.12)》,《南洋問題研究》2014年第1期。
[5] [泰]黎道鋼:《汕頭淪陷初期暹羅銀信局公所恢復批路之努力》,廣東省檔案館編:《僑批故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5~271頁。
[6] 袁丁:《國統區與淪陷區之間的僑匯流通——抗戰中的廣東僑匯研究》,錢江、紀宗安主編:《世界華僑華人研究》第一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7] 歐陽衛民主編:《嶺南金融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5年,第391~452頁;廣東省銀行編:《廣東省銀行史略》,廣州:廣東省銀行,1946年。
[8] 云照坤:《戰時廣東僑匯》,《廣東政治》1941年第1卷第1期。
[9] 《暹羅中華總商會證明書》(1947年5月3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 41-3- 3312。
[10]《關于本行恢復及增設海外機構并兼營存放款業務事項由》(1946年3月),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270。
[11]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實業志六·商業》,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年,第1312頁。
[12] 吳承禧:《汕頭的華僑匯款》,《華僑半月刊》1937年第99、第100期合刊,第13頁。
[13] 《近年來廣東省銀行辦理僑匯之概況》(1941年),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 41-3-4240之二。
[14] 姚曾蔭:《廣東省的華僑匯款》,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39頁。
[15] 《錢幣司關于擬定英美經濟運輸使節來華工作項目計劃大綱及抗戰以來辦理金融幣制情形說明書簽呈》(1941年1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51頁。
[16] [日]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24頁。
[17] 《李漢魂致顧翊群函》(1939年9月6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2221。
[18] 《香港中國銀行來電照抄》(1939年6月2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19] [泰]洪林、黎道鋼編:《泰國僑批業資料薈萃》,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73頁。
[20] 《本行積極辦理僑匯情形案》(1939年7月27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33。
[21] 《陳煥章致李漢魂電》(1939年8月15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22] 《港訊處致省行函》(1939年10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2221。
[23] 《僑務委員會公函荒渝己字第1929號》(1939年7月2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財政廳檔案4-2-10。
[24] 《杜邦致李漢魂電》 (1939年7月9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25] 《曾曉峰致李漢魂電》(1939年7月9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26] 《黃端如致李漢魂電》 (1939年8月9日), 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27] 《陳友云致李漢魂、顧翊群電》(1939年8月2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28] 《林雁峰致李漢魂電》(1939年8月1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29] 《張發奎致李漢魂代電》 (1939年8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30] 《張發奎致李漢魂代電》 (1939年9月7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31] 《李漢魂致宋子文代電》(1939年7月12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 4-2-10。
[32] 芮詒壎:《有信銀莊(批局)瑣憶》,陳訓先:《潮汕先僑與僑批文化》附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4頁。
[33] 《廣東省政府致僑委會函》 (1939年8月1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34] 《籌設揭陽、饒平等辦事處案》(1939年8月2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 41-3-34。
[35] 《李漢魂致杜邦代電》(1939年9月2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 4-2-10。
[36] 《曾曉峰致李漢魂電》 (1939年10月1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財政廳檔案4-2-10。
[37] [泰]洪林、黎道鋼編:《泰國僑批業資料薈萃》,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5~86頁。
[38] 《普寧辦事處致省行總行函》(1940年7月16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 41-3-3390。
[39] 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譯室編:《廣東金融》,曲江:廣東省政府秘書處,1941年,第20頁。
[40] 廣東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廣東經濟年鑒續編》(三十年度),曲江: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1942年,第F43頁。
[41] 《省行致東江各行處及星行函》(1939年12月17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2215。
[42] 云照坤:《一年來之廣東金融》,《廣東省銀行季刊》第3卷第1期,1943年3月。
[43] 楊建成主編:《三十年代南洋華僑僑匯投資報告書》,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69頁。
[44] 《關于建設廳黃廳長吸收僑匯意見各項辦理情形由》 (1941年8月13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2215。
[45] 中國銀行行史編輯委員會:《中國銀行行史(1912—1949)》,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554頁。
[46] 黃卓豪:《戰時廣東金融問題》,曲江: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1942年,第50頁。
[47] 《擬議廣東省銀行在海外華僑自由聚居地點自由擇設分支行處意見請核示辦理由》(1947年9月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銀行檔案41-3-284之三。
[48] 袁丁等:《民國政府對僑匯的管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