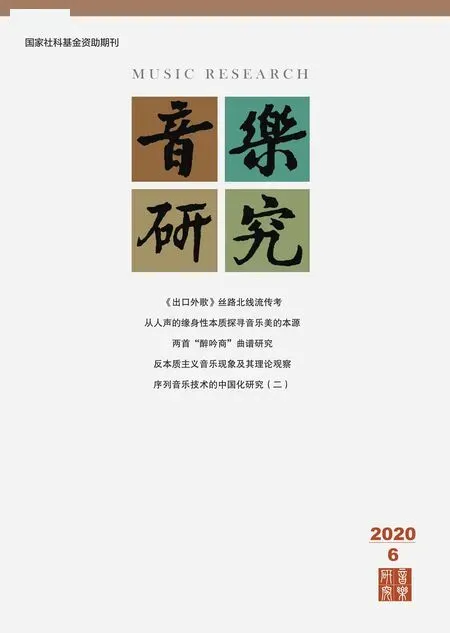孫繼南音樂史學思想研究
文◎馮春玲
引 言
孫繼南(1928—2016)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音樂史學家、音樂教育家。他的音樂史學研究與其音樂教育實踐緊密相連,特別是他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學堂樂歌,以及黎錦暉、李叔同等音樂家的研究,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其“學風之嚴謹,史料之翔實,評價之公允,在近現代音樂史學界有口皆碑。”①楊成秀《孫繼南學案》,《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5 年第1 期,第71 頁。綜觀孫繼南的音樂史學成果,可以發現,雖然他未曾就音樂史學研究的元理論問題做出過專論,在涉及相關問題的訪談中也沒有展開過具體的闡述。但是,作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大家,其學術研究必然蘊含著豐富的史學思想。因此,對孫繼南的音樂史學思想加以深入的學習與總結,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史料為本的音樂史學觀
史學觀,是史家對史學的根本認識,那么,音樂史學觀,是音樂史學家對音樂史學的根本認識。音樂史學家具有怎樣的音樂史學觀,通常會對其史學實踐產生深刻影響。從孫繼南的自述可知,他的音樂史學觀,深受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思想的影響。他在一次訪談中曾坦率地說:“我很贊同傅斯年‘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觀點。”②曲文靜《史料是史學的精髓——孫繼南采訪錄》,《中國音樂學》2015 年第3 期,第5 頁。
將史學定位為史料學的觀點,在今日的史學研究中已不為學界所完全贊同,但是,“史學即史料學”的治史觀念,卻指出了史料在史學研究中無可替代的價值。沒有堅實史料基礎的史學研究無疑如空中樓閣。孫繼南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強調了史料在音樂史學研究中的首要意義。因此,對于傅斯年、梁啟超和胡適等人注重史料的史學研究,孫繼南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認可。他結合自身的音樂史學研究提出,“史料意識”是歷史研究者必須具備的史學觀念,翔實的史料是史學研究最為關鍵的基礎,是否具有史料意識和辨別史料真偽的能力,往往決定了史學研究的成敗。③參見注②,第5—11 頁。事實上,他在許多文論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這一史學觀念更是在其史學論著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筆者將孫繼南的這一史學觀總結為“史料為本的音樂史學觀”。但是,這種以史料為本的音樂史學觀,并非僅是史學思維上的理論認知,只有通過艱辛的研究實踐——史料的發掘、考證、辨析、運用,才能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印證與統一。縱觀孫繼南的治史實踐,史料為本的史學觀念與治史原則,始終貫穿于他的音樂史學研究當中。
孫繼南在音樂史料發掘與考證方面所做的努力與貢獻,可以從他的研究經歷和研究成果來略加感受。比如,他經過長達十余年的搜尋,終于將登州文會館志中刊載的十首樂歌完整地呈現給音樂史學界,改寫了學堂樂歌的歷史;④孫繼南《我國近代早期“樂歌”的重要發現——山東登州〈文會館志〉“文會館唱歌選抄”的發現經過》, 《音樂研究》2006 年第2 期。經過他的費心和努力,1984 年日本友人實藤惠秀將李叔同1906 編的《音樂小雜志》復印本贈予中國學界;通過他的細心考證,使我們得以了解清末官修樂歌教本——1907 年《樂歌教科書》的面貌,這本目前所見最早的官修樂歌教科書,包括與楊蔭瀏所填岳飛詞大致相同的樂歌《滿江紅》;⑤孫繼南《中國第一部官方統編音樂教材——〈樂歌教科書〉的現身與考索》,《音樂研究》2010 年第3 期。經過他的執著查尋、嚴謹考證,李叔同創作的兩首歌曲《廈門大學運動會會歌》《誠》,得以拂去歷史的塵埃,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⑥孫繼南《音樂史料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師〈廈門市運動大會會歌〉版本考為例》,《中國音樂學》2013年第3 期;孫繼南《〈誠〉:李叔同百年樂歌新發現——兼及周玲孫唱歌教材與李叔同歌曲史料研究》,《音樂藝術》2016 年第2 期。經其詳加查證李叔同的傳世之作《送別》,使我們認識到,《送別》經歷了從“一瓢濁酒”,到“一斛濁酒”,再到“一壺濁酒”的長期訛誤,以致被傳唱為“一壺濁酒”。⑦孫繼南《還歷史歌曲以原貌——〈漁光曲〉、〈送別〉詞曲辨正》,《中國音樂教育》2000 年第4 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編著的《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紀年》一書,從初版到增訂本,再到新版,經歷了一個史料不斷豐富與充實的過程。該書最后一版(新版)共編寫條目850條,圖片202 幀,后附史料選錄、條目索引、人名索引和圖片索引,可謂史料宏富翔實、圖文并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工具書。本書從初版問世以來,澤被學界眾多從事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學者與莘莘學子,其學術價值熠熠生輝,可謂功德無量。
為了搜集史料,孫繼南不但自己處處留意,輾轉各處;同時,還經常拜托學界友人代為查閱一些難以親力親為的音樂史料,對此他總是要在相關文章中記下史料的來源并致以謝忱。更令人感佩的是,孫繼南從不把史料作為私藏品,而是經常慷慨地提供給有需要的人。筆者十余年前撰寫碩士論文研究黎錦暉的流行歌曲創作時,孫先生曾在史料線索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并且,他還主動將自己發現并查閱到的有關濟南“五三慘案”的新史料提供給馮長春教授,于是才有了筆者與馮長春合作完成的《勿忘〈國恥〉——關于“五三”慘案的幾則音樂史料》一文。⑧馮春玲、馮長春《勿忘〈國恥〉——關于“五三”慘案的幾則音樂史料》,《中國音樂學》2014 年第3 期。
對于音樂史料的處理,孫繼南是將其置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學科發展的高度來加以審視的。他在一篇有關“重寫音樂史”的爭鳴文章中指出,學界關于“音樂史料學”的討論“少之又少,不無遺憾”,繼而結合自己的音樂史學研究指出:
經過長期音樂資料的搜集、整理和應用,筆者愈益深刻地認識到:“史料”不等同于“資料”。亦即“資料”在未經考證前,一般不能作為嚴格意義的“史料”,它需要一個先“疑”、后“考”、再“信”的過程。考證之初,多出于懷疑;考證翔實,方具可證性,用之于史學研究,才會有“信史”產生。⑨孫繼南《音樂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師〈廈門市運動大會會歌〉版本考為例》,《中國音樂學》2013 年第3 期,第6 頁。
在《佛曲〈三寶歌〉源流始末考》一文 中,孫繼南又對史料的考訂提出了“細”和“精”的要求:
所謂細,是指條分縷析,細節不惑;所謂精,是指考據精深,源流分明。⑩孫繼南《佛曲〈三寶歌〉源流始末考》,《音樂藝術》2015 年第4 期,第11 頁。
這短短的幾行文字,可視為孫繼南治史觀念的濃縮,也概括了他由音樂史料學構筑而起的音樂史學觀之根本。不管音樂史學獲得怎樣的發展,這一樸素卻具真知的史學觀念,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其理論指引的力量,反而歷久彌新。
郭樹群先生通過深入解讀孫繼南著重史料考證的部分論文,認為孫先生提出的音樂史料工作之“疑”“考”“細”“精”“信”的要求,可謂“五字箴言”,“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11]參見郭樹群《幾個學習有得的中國音樂史史料研究個案》,《中國音樂》2016 年第4 期,第63 頁。劉再生先生在論及孫繼南的治史貢獻時則這樣寫道:“先生史料之扎實功底,史觀之獨立精神,史識之卓越超群,在老一輩近代史學家中極為少見。”[12]劉再生《低調人生學界楷模——孫繼南學術人生追思錄》,《人民音樂》2017 年第2 期,第26 頁。可見,孫繼南對音樂史料發掘與研究的貢獻與卓見,得到了同人們的高度評價與認同。
二、人本主義的音樂史觀
郭乃安先生的呼吁—“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至今猶在耳畔。這一呼吁,不僅意味著對過去音樂學研究中見“物”不見“人”之現象的批評,同時,也意味著音樂學研究由視角轉換而帶來的某種學術轉向。因為“人是音樂的出發點和歸宿”,“把目光投向人,不僅意味著在音樂學的研究中關注人的音樂行為的動機、目的和方式等,還意味著在各種音樂事實中去發現人的內涵,或者說人的投影”。[13]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中國音樂學》1991 年第2 期,第16 頁。筆者以為,這樣一種基于人本主義的音樂史觀,在孫繼南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極為鮮明的體現。這樣的音樂史觀,完全不同于以往建立在階級分析方法基礎上審視音樂與音樂家的歷史觀;而是通過對音樂家及其音樂行為的全面考察,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將音樂家與音樂還原到特定的歷史階段與文化語境,并結合當代人對歷史音樂文化的理解與闡釋,對音樂家及其音樂行為做出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其核心思想是對音樂家主體性的充分肯定,對音樂家藝術勞動的充分尊重。因此,這一帶有鮮明人本主義色彩的音樂史觀,進一步提升了音樂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價值。人本主義的音樂史觀,貫穿于孫繼南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全過程,其中,關于黎錦暉和李叔同的研究,最能體現這一音樂史觀。
眾所周知,在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黎錦暉在音樂史上的形象一直是“黃色音樂”創作的代表人物。由他創作的那些引領一代時尚的“流行歌曲”,長期遭到批判和禁止。這些使他曾經享有無上風光的歌曲作品,成為他后半生難以抹去的“不光彩”標簽。“談黃色變”的慣性思維,也使有關黎錦暉的歷史研究也變得復雜而敏感。回到20 世紀30 年代初抗日救亡和左翼“新興音樂運動”的歷史語境,當然不難理解對黎錦暉的批評與責難。但是,黎錦暉創作那些“摩登曲”“家庭愛情歌曲”等時代曲的初衷,是為了追逐商業利益而丟卻了藝術情操的不齒之舉嗎?他的大量愛情歌曲是否具有“黃色音樂”的內容與形式呢?
孫繼南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這樣的答案,并非只是他站在今天五花八門的音樂環境中,對黎錦暉的流行歌曲加以比較后輕易得出的歷史寬容;而是建立在對黎錦暉音樂人生,“時代曲”之時代的音樂觀念沖突,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反思等多方面,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其中所表現出的史識、史德與學術勇氣,令人感佩。這也正成就了孫繼南對黎錦暉研究做出的重要貢獻。從20 世紀90 年代初的《黎錦暉評傳》[14]孫繼南《黎錦暉評傳》,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年版。,到21 世紀初的《黎錦暉與黎派音樂》[15]孫繼南《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 年版。,兩部敢為學界之先的姊妹篇著作,不僅展示了黎錦暉及其“黎派音樂”得以正名的史學歷程,同時,也反映了孫繼南人本主義音樂史觀逐漸明晰、確立的心路歷程。《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一書,除了更為充盈的史料和更為全面的音樂分析之外,最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黎錦暉歷史形象做出的有血有肉的塑造和刻畫。這種塑造和刻畫,當然不是文學性的筆法,而是建立在對他的藝術人生、音樂創作、音樂觀念等進行全面研究的基礎之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對黎錦暉關于救亡歌曲創作的深入論述,是以往有關黎錦暉音樂創作的研究中所很少見到的,該著對他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的貢獻,給予了合乎歷史的定位與評判,讓世人重新認識到,近百年前的黎錦暉,就是高舉“平民音樂”大旗,在音樂創作的內容與形式等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探索印記的先行者。從“黃色音樂”和“黃色音樂的鼻祖”的貶斥否定,到“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創作的先驅”的高度肯定,這兩種天壤之別的歷史評價,體現了一位嚴肅而又充滿人本主義情懷的音樂史學家忠實于歷史的高度責 任感。
需要指出的是,孫繼南對黎錦暉的歷史評價,絕非為了“撥亂反正”而走向另一個贊美的極端,他深知“棒殺”和“捧殺”都是不符合唯物主義史學觀的。因此,《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一書,沒有回避對黎錦暉人性弱點、歷史局限的評說,不虛美,不掩惡,如其所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顯示了作者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正如項陽先生在書評中所言:“對他(黎錦暉)的爭議,究竟是他自身的問題,還是時代的問題,間或是社會的問題,透過孫先生的書,都一一給出了答案。”[16]項陽《黎錦暉:時代弄潮與世紀悲情》,《中國音樂》2007 年第4 期,第60 頁。
在《黎錦暉與黎派音樂》一書結尾,孫繼南不無欣喜地寫道:“一位歷史真實的黎錦暉,正在向我們走來。”[17]同注[15],第243 頁。筆者相信,認真讀罷此書的讀者,亦會有相同的體會,一定會真切地感受到:一位歷史真實的黎錦暉,透過一位史學家栩栩如生的音樂敘事,正在向我們走來。
弘一大師李叔同及其音樂創作與活動,也是孫繼南用力最多的研究對象。很多人未必知道,李叔同在日本創辦的中國第一本音樂期刊《音樂小雜志》,得益于孫繼南的執著與努力,日本學者才贈予復制的珍貴音樂文物—那幅由李叔同親自繪制的、令人過目難忘的彩色封面,才能走進中國音樂學者的視野。如前所述,孫繼南研究李叔同的文章,都在史料的挖掘、考訂方面做出了令人贊嘆的努力。如果我們更為深入細致地研讀這些文字,就會發現,這些文章仿佛是孫繼南與弘一大師的一種歷史“對話”。正是在這種充滿人文情懷的歷史研究中,弘一大師那超凡而又入世的歷史形象才被勾畫得血肉豐滿,李叔同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絢麗多彩的藝術創作、悲欣交集的心靈體驗,才得以清晰體現。作者對弘一大師人格的敬仰,并沒有因為研究對象的宗教色彩而發生改變,這也反映了人本主義音樂史觀對作者的深刻影響。
三、視域融合的歷史認識論
“視域融合”,是德國哲學家、美學家伽 達 默 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提出的,有關藝術理解與歷史闡釋的闡釋學理論。伽達默爾認為,藝術的意義在于理解,而理解既包括了帶有“前見”的歷史上的理解,也包括當下的新的理解,這特別體現在具有“再創造”特點的音樂藝術當中,因此,音樂的意義是向著未來敞開的。伽達默爾特別指出,“每一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種復制的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將歷史視域和當下視域相互融合,即他所謂的“視域融合”。基于這樣一種關于藝術本質的認識,伽達默爾提出了一個根本的歷史認識結果——“效果史”:“歷史學的興趣不只是注意歷史現象或歷史流傳下來的作品,而且還在一種附屬的意義上注意到這些現象和作品在歷史(最后也包括對這些現象和作品研究的歷史)上所產生的效果。”[18]〔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 頁。
孫繼南并沒有關于歷史認識論的專門論述,也從未表明其治史過程中受到伽達默爾闡釋學思想的影響。但細讀他的音樂史學論著可以發現,他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對歷史音樂的賞鑒,都帶有比較鮮明的“視域融合”特點。他對黎錦暉與“黎派音樂”的研究尤其體現出這一特點。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關于黎錦暉及其音樂創作的歷史評價,一直延續了20 世紀30 年代帶有“左翼”特征的歷史觀點,這可謂是歷史視域中所謂的“前見”。孫繼南在論述黎錦暉研究的歷史發展時,對這種歷史視域給予了充分的理解,指出這既是由黎錦暉音樂創作的自身特征所決定,也是當時思潮涌蕩時代引發批評的必然:
黎氏在創作實踐中,雖有追求“雄壯”“熱烈”“開展”之意,卻不脫“黎派音樂”固有創作思想及藝術形式、風格之局限,隨著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熱情的高漲,那種“輕歌曼舞、婉麗和諧”已不合時宜,尤其那些與救亡無關的軟性歌曲依然流行于社會,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界的批評與指責。[19]同注[15],第221 頁。
立足當代,孫繼南之所以為“黎派音樂”正名,又是由于他對黎錦暉時代曲的歷史評價融入了新時代的理解與闡釋。以歌曲《毛毛雨》為例,孫繼南認為,《毛毛雨》在當時遭到批評,與黎明暉的演唱水平亦有關系,1926 年初出茅廬的黎明暉演唱藝術尚不成熟,1934 年的錄音版本就反映出更高藝術修養的表現。因此,他強調:“時代曲‘二度創作’對其風格情調的影響很大,此乃音樂藝術本身所決定,一切音樂作品莫不如此”。孫繼南認為: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毛毛雨》,其中“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銀,只要你的心”的立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五四”女性突破長期封建思想的覺悟。……由于歌曲本身就是“舊的音樂形式”、民俗小調,又是嘗試之作,藝術、格調都未盡完善,各種不同的評議,見仁見智,并不異常。但若將其視為“淫靡”之作,則未免有失偏頗,何況這首歌曲畢竟具有自身的藝術價值。[20]同注[15],第160 頁。
上述的中肯評價,相較于以往的種種貶斥與否定,不可同日而語。這種對歷史音樂的批評與新的認識,無疑帶有視域融合的特點。筆者相信,只要我們對當代音樂生活中令人眼花繚亂的流行音樂現象,與黎錦暉當年的“時代曲”稍作比較,就會發現,所謂“黎派音樂”與“黃色音樂”,沒有任何實質的相同,新的音樂創作與審美體驗,一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對歷史音樂的認識和評價。這樣一種視域融合的歷史評價并非個例。無獨有偶,繆天瑞先生在談到黎錦暉的流行歌曲創作時曾不無感慨地說過:“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批判黎錦暉,認為他的音樂形式是黃色的,還有演唱的聲音方面……其實現在看來不是什么黃色音樂,《毛毛雨》那首歌一點兒都不黃,比現在的好多流行歌曲健康多了。”[21]馮長春《口述音樂史與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藝術論衡》(中國臺灣)復刊第9 期,2017 年11 月,第60 頁。毫無疑問,當年也曾批評過黎錦暉的繆天瑞,他對《毛毛雨》的新的理解和歷史評價,同樣帶有鮮明的“視域融合”特點,與孫繼南的歷史認識可以相互呼應。
筆者認同音樂研究中“視域融合”及“效果史”的歷史認識觀念。孫繼南音樂史學論著中自然呈現出的這一歷史認識論思想,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歷史音樂和音樂家研究的認識與理解。
四、歷史斷代帶來的思考
最后,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孫繼南在新版《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紀年》中,將此前兩版書名中的“近現代”改為“近代”,一字之差,反映了怎樣的音樂歷史觀呢?作者在“新版補記”中曾一筆帶過地提及該版的修訂與“易名”之事,但并未交代易名的原因及相關學術理念論述。在為《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紀年》而作的一篇書評中,書評作者寫下了帶有猜想色彩的一句話:“進入新世紀之后,學界有人主張把整個20 世紀稱為近代,看來不無道理。可能出于這種原因,作者把第三版《紀年》中的‘現’字去掉了。”[22]林寅之《鉤沉輯佚自辛勤——讀〈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史紀年〉一、二、三版》,《人民音樂》2012 年第8 期,第77 頁。
限于眼界,筆者對于“學界有人主張把整個20 世紀稱為近代”的觀點無從查證,但以治學嚴謹著稱的孫繼南,在新版《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史紀年(1840—2000)》中,將自鴉片戰爭以降至20 世紀末的音樂歷史統稱為“近代史”,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長期以來,關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歷史分期一直存在幾種不同的劃分,常見的幾種是:其一,1840—1919 年為近代史,1919—1949 年為現代史,1949 年至今為當代史;其二,1840—1949年為近代史,1949 年至今為現代史;其三,1840—1949 年為近代史,1949—1978 年為現代史,1978 年至今為當代史。此外,亦有學者以“新音樂”的誕生與發展作為歷史主脈,將近代以來的音樂歷史稱為“新音樂史”。上述種種不同歷史分期的觀點,見諸大量的學術論著,此不一一舉例。但是,如上所述,將鴉片戰爭后至整個20 世紀統稱為“近代”者,音樂學界目前只見孫繼南一人。他在晚年對近現代音樂史斷代的觀念更新,是否引起學界的認同抑或質疑,尚不得而知。筆者的理解是,作為音樂史學家,更由于《中國近代音樂教育史紀年》在學界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或許孫繼南將歷史的眼光投向了長遠的將來,也許在歷史轉折的某一時刻,以往的“現代”與“當代”都將成為后來人的“近代”。至于他對近現代音樂史的斷代是否另有深意,現在我們無法確知,也無需做過多揣度。總之,孫繼南先生在晚年以一字之變帶來的新的歷史觀念,值得后來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