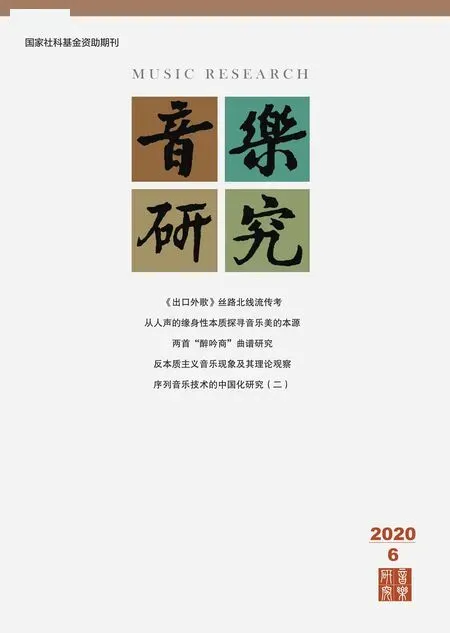新中國十七年電影音樂的理論探索
文◎蔡 夢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音樂文化事業(yè)也開啟了新的征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十七年間(1949—1966),音樂界圍繞各個方面展開的論辯方興未艾而干勁十足,諸如聲樂領域的“土洋”問題、創(chuàng)作領域的“立場”問題等辯論,成為當代中國音樂發(fā)展歷程上的重要史事,學界亦有深入探討與基本共識。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筆者發(fā)現,對于“電影音樂”這一新興的音樂體裁,音樂界曾進行過深入研究與廣泛討論。初步統(tǒng)計,其主要以《人民音樂》《電影藝術》為平臺,參與人數之多、持續(xù)時間之長、涉及內容之廣、影響范圍之大,應視為這十七年音樂界的重要史事之一。
一、1949—1966:新中國電影音樂文論概覽
新中國十七年間,發(fā)表電影音樂文論的刊物主要有:《新電影》《大眾電影》《上影畫報》《電影文學》《上海電影》《電影藝術》《人民音樂》等,其中以《人民音樂》《電影藝術》最為集中,發(fā)文超過60 篇。從刊文論題看,隨著1955 年對《遠航歸來》等抒情歌曲的論辯和1956 年《電影藝術》創(chuàng)刊,電影音樂成為一個新論題。1962—1966 年,是電影音樂討論的高潮期,僅《人民音樂》《電影藝術》兩刊的年度發(fā)文量總計在10 篇左右。從參與探討的群體看,既有作曲家、音樂學者,也有非音樂界人士。其中,音樂界人士呂驥、趙沨、李佺民、夏白、宋昭運、何士德、李煥之、徐徐、王云階、李偉才、婁彰后、黃準、向異、張棣昌、簡其華、伍雍誼、范西姆、譚冰若和陳聆群等,均有專文予以探討。
這一時期的電影音樂文論,既有時代語境下的政治表達,也有著眼創(chuàng)作的藝術探討。如王云階《電影音樂大躍進》①載《中國電影》1958 年第4 期。指出,在“大躍進”運動中,作曲工作者打破原定創(chuàng)作指標,全面規(guī)劃,調動積極性,在保證創(chuàng)作數量大躍進的同時,深入群眾與生活,不僅在思想、情感方面得到鍛煉,提高了專業(yè)技巧,也為電影作曲隊伍培養(yǎng)了新生力量;伴隨“大躍進”的浪潮,電影音樂演奏、演唱隊伍中,以往存在的創(chuàng)作效率低下,以及管弦樂隊隊員輕視民族音樂、民族樂器和民樂隊隊員的不良傾向有所緩解,整體呈現質與量的飛躍;通過“雙反”運動,作曲與樂隊、導演錄音的合作關系得以改善,這種面貌為電影音樂的大躍進提供了全面保證。
趙沨《從電影音樂的特點談起》②載《電影藝術》1964 年第1 期。從美學層面剖析電影音樂特點及其與電影的關系問題。作者認為,電影音樂具有交響性,但由于音樂通常在整部電影中多呈現不連貫特征及其依劇情發(fā)展而具有的多方面描述功能,交響性應指狹義層面,旨在使電影音樂具有更強的動力、節(jié)奏和邏輯力。圍繞音樂與電影的關系,作者認為,音樂作為電影表現結構的重要部分,只有在服從電影創(chuàng)作整體構思與需求前提下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發(fā)揮作用。同時,電影需要各種藝術表現手段并進行高度融合,又為音樂創(chuàng)作提出新要求。針對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的特殊性,作者主張不應過分拘泥于電影音樂形式的獨立意義,但也不意味著電影音樂只應停留在滿足一般性音響效果的地步,關鍵在于創(chuàng)作過程中怎樣運用藝術手法和在什么條件下運用。為使音樂更好地融于電影結構,作者提出,為了適應電影劇本要求,二者的統(tǒng)一、協調,不僅表現在電影音樂對時代和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畫,以及與地方特色和劇情發(fā)展需要的適應上,也要表現在音樂創(chuàng)作藝術手法的選擇上。
以上兩篇文論,代表了這一時期電影音樂討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前者是政治認識下的自我改造與規(guī)劃,后者是藝術認識下的創(chuàng)作思考與探討,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有著基于“統(tǒng)一認識”的集體主義觀念。這種觀念在這一時期極為普遍,并滲透在各種討論當中。如徐徐《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幾個問題》③載《人民音樂》1959 年第12 期。肯定了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取得的成就,認為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在使作曲家得以鍛煉的同時對其提出了更高要求。作者指出,由于影片題材的多元化,作曲家應力求掌握多方面知識,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充分了解客觀事實并通過影片合理體現客觀事實,提升影片暗含的思想性;由于電影的播放,音樂得以拉近其與觀眾的距離,要求作曲家應通過創(chuàng)作傳達個人對現實生活的責任感,以及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作曲家還應盡可能使用樸素、簡潔的語言表現深刻的思想內容,力求避免音樂的庸俗化和簡單化;音樂作為電影綜合藝術的組成部分,作曲家創(chuàng)作時應加強與其他藝術家的交流合作,以期使音樂在整部電影中更有效地發(fā)揮作用;電影藝術的樣式和片種比較多元,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須充分發(fā)揮各方面的才華;電影音樂由于受到影片場景內容限制,表現空間有限,要求作曲家能以精準的語言表達復雜的情感,塑造人物形象,同時熟悉并掌握各種音樂形式,力求突破單一形式的限制。
陳聆群《聶耳創(chuàng)作〈賣報歌〉的啟示》④載《人民音樂》1963 年第7 期。就當時部分作曲家不能通過深入群眾捕捉生活信息來獲取藝術創(chuàng)作靈感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細致的剖析。作者認為,這種情況的根源在于思想上存在問題,并以聶耳創(chuàng)作的《賣報歌》為例,指出“如果真正具備了為革命斗爭、為群眾服務的思想,堅決與工農兵緊密結合,那么有專門深入生活的機會固然可以得到更多收獲,即使沒有,也能像聶耳一樣主動、千方百計地關心群眾生活、接近群眾生活”。作者呼吁音樂工作者端正思想,堅定地認為只有深入群眾與生活,才能寫出新的、好的音樂作品。
向異《電影音樂的時代氣氛》⑤載《電影藝術》1962 年第2 期。圍繞電影音樂如何準確反映時代特征,并具有濃厚時代氣氛的問題展開探討。作者認為,藝術創(chuàng)作能否深刻反映時代特征,是否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氛,是衡量其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而音樂作為電影綜合藝術結構的組成部分,在烘托時代氣氛方面同樣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作者以《青春之歌》為例,分析了音樂在電影中烘托時代氣氛的成功經驗,如適當選擇和運用膾炙人口的群眾歌曲,且能將借用或創(chuàng)作的各種材料創(chuàng)造性地融為一體,提高音樂與場景的契合度等。同時指出,盡管相關人員開始思考如何利用電影音樂烘托時代發(fā)展的氛圍,增強濃郁的民族風格的問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經驗,但較之電影藝術發(fā)展與人民群眾日益提升的欣賞水平還遠遠不夠。圍繞電影音樂如何呈現時代特點這一重要且復雜的問題,作者的文章意在引起業(yè)內人士的廣泛關注,為國家電影音樂事業(yè)的發(fā)展群策群力。
李煥之以自己為電影《魯迅生平》作曲為切入點,從作曲者的視角出發(fā),認為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要注意民族形式,但并非一定使用民族樂器,提出注重電影音樂民族性的同時,更要注重音樂的形象性刻畫,認為電影音樂形象性刻畫不足有時比民族性不夠后果更要嚴重,強調音樂的民族性不能與其形象性分割,缺乏形象性的民族性是不動人的,缺乏民族性的形象性則不能準確真實地反映生活與情感。電影音樂既要在民族化方面做出努力,也要在刻畫深刻動人的藝術形象方面做出努力。⑥參見李煥之《即興曲——電影音樂隨筆》,《電影藝術》1956 年第3 期。李煥之還對呂其明作曲的兩部電影《鐵窗烈火》和《黃寶妹》進行了評價,指出《黃寶妹》的音樂民族特點非常鮮明,《鐵窗烈火》則包含了具有典型性的“時代音調”,并進一步闡述了“時代音調”在電影中的應用問題,認為電影音樂在運用“時代音調”上還做得太少、太弱,作曲家更關注個人的原創(chuàng)音樂。作者認為,以“時代音調”為基礎,有效使用交響手法對之加以處理,也許比新創(chuàng)作的音調更有力。⑦參見李煥之《從兩部電影的音樂談起》,《電影藝術》1958 年第2 期。
李煥之的電影音樂討論,代表了新中國十七年電影音樂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從創(chuàng)作經驗出發(fā)嘗試進行理論提升與歸納總結,同時又主動將這種理論總結與現實創(chuàng)作相對照。這種理論探討的做法與實事求是的作風,為當時電影音樂在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研究兩個方面的繁榮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基于同樣的訴求,除政治話語表達之外,這一時期的電影音樂評論也多具樸實之風。如向異以《青春之歌》《萬水千山》為例,對音樂烘托時代氣氛的重要意義進行闡釋。作者認為,《青春之歌》之所以在烘托時代氣氛上取得較大成功,是因為作曲家適當選擇和運用了膾炙人口的群眾歌曲,且能與其他類型的音樂達到前后呼應、風格協調一致。《萬水千山》則差強人意,由于音樂在構成上存在一些不足,且有幾段樂曲僅以西洋傳統(tǒng)的音階式進行為基礎,其藝術表現準確度不高,缺乏內在感染力;譜曲一味借鑒西方早期音樂風格與手法,與電影內容不協調。通過對兩部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特點的分析,作者進一步闡釋了音樂對于烘托時代氣氛的特殊意義。⑧參見注⑤。又如對電影《紅色娘子軍》的音樂評論,潘霞認為其音樂不僅發(fā)揮了配合劇作結構的作用,在速度、節(jié)奏方面與電影畫面的蒙太奇效果也達成了有機統(tǒng)一,創(chuàng)造出具有“獨特的、有高度感染力和深刻思想涵義的音樂與視覺結合的形象”⑨潘霞《〈紅色娘子軍〉中的音樂形象》,《電影藝術》1961 年第5 期,第59 頁。。而向異在對這部電影的肯定之外,還直指其不足,指出電影《紅色娘子軍》音樂還沒有被鮮明地樹立起來,對反面形象的塑造也不夠準確,某些音樂缺乏與影片內容相適應的力度與深度,一些音樂結構的缺失則又降低了全片音樂的完整性,配器上西洋樂器占比較大,造成風格的不協調等問題。⑩參見向異《電影〈紅色娘子軍〉音樂的成就和問題》,《人民音樂》1963 年第Z1 期。
除聚焦故事片電影的音樂討論之外,紀錄片電影的音樂創(chuàng)作也成為一個論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我國的紀錄片也掀開新篇章。1958 年新聞紀錄電影遍地開花,李寶樹結合自身的工作體會,闡述了對紀錄片音樂創(chuàng)作的感想,呼吁電影音樂工作者參與討論,交流經驗。作者認為,紀錄片音樂的表現方法、處理方式極為豐富,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不但有更加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對于影片主題思想的完成需求度也更高;此外,在結構方面,音樂主題一般貫穿全片,加強了整部電影的連貫性。針對紀錄電影中的歌曲問題,作者認為聲樂作品在紀錄電影中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體裁形式較為單一;要充分使用群眾歌曲和其他形式的聲樂作品,努力提高紀錄片歌曲的創(chuàng)作質量。[11]參見李寶樹《紀錄片音樂創(chuàng)作隨筆》,《中國電影》1958 年第10 期。即使在今天看來,電影紀錄片仍屬“冷門”,紀錄片的音樂創(chuàng)作論題則更少為人所重視,然而早在1958 年,面對新中國剛剛興起的電影紀錄片,音樂界已經敏銳地注意到其中的音樂創(chuàng)作問題,提出了較為深入的思考,且很多觀點對今天仍具有啟發(fā)參考意義,這是非常可貴的。
二、國家主導下的兩種語境
從新中國十七年電影音樂文論的內容看,分明可以感受到側重政治、藝術的兩種不同語境,同時,這種不同又是有著統(tǒng)一認識的集體訴求,其中每位參與者都表現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強烈責任感和高度使命感。
伴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電影音樂開啟了隨電影創(chuàng)作取向而發(fā)生變化的一個特定時代。1949 年7 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明確文藝發(fā)展的宗旨是服務于人民,開展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與落腳點是服務于工農兵;1953 年9 月,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呼吁藝術工作以抓創(chuàng)作為主,鼓勵藝術家創(chuàng)作出更多更好的藝術作品。兩次會議的召開,為其后的電影創(chuàng)作提供了導向與支持。
1956 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并在與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會見時發(fā)表了談話,一定程度上為解放音樂批評觀念提供了思想基礎。文學藝術界開始學習貫徹“雙百方針”,并呈現出相對活躍的局面。寬松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促使包括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在內的文藝創(chuàng)造一度出現繁榮景象。同年,電影事業(yè)管理局召開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會議,提出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問題及今后規(guī)劃,并在《人民音樂》刊登簡訊。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全國開展“整風運動”與“反右斗爭”,在其后的一年間,“反右”成為音樂界的主要任務。1958 年,在“反右”“拔白旗”的政治氛圍下,電影音樂工作者又卷入“大躍進”洪流。粗暴的批判使音樂創(chuàng)作需要的活潑氣氛、創(chuàng)新思維受到禁錮,特別是抒情性較強的電影音樂首當其沖成為眾矢之的。如《九九艷陽天》引發(fā)的爭議:《人民音樂》1958 年首先刊登《對〈九九艷陽天〉的兩種不同意見》,一石激起千層浪,迅速引發(fā)學界對于一些抒情歌曲創(chuàng)作問題的大辯論;隨后,從1958 年第4 期開始,《人民音樂》又連續(xù)三期為《九九艷陽天》設專欄進行討論,在形成廣泛影響的同時也將導向引向偏頗。
1959 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之際,在周恩來提出文藝事業(yè)要“兩條腿走路”的思想引領下,涌現了一批質量上乘的獻禮片,形成了新中國電影史上一座創(chuàng)作高峰。《五朵金花》《聶耳》《林則徐》等18 部影片經歷數十年歷史風云的洗禮后,大部分至今仍散發(fā)著藝術魅力。這一時期圍繞電影音樂的討論主要聚焦于創(chuàng)作,作曲家們結合個人經驗展開討論。
1960 年末,文藝界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國民經濟八字方針號召下,開始糾正之前的偏頗。1961 年,“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全國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發(fā)表重要講話,對當前文藝政策進行調整。文藝政策的調整,使得創(chuàng)作隊伍重新活躍起來,藝術家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傳承本國民族文化,弘揚民族藝術特色。電影音樂理論界的相關探討,也隨之偏重電影音樂民族化等方面的創(chuàng)作思想、觀念或理念。1963 年之后,隨著政治語境的轉變,學術論辯被學術批判取代。
新中國十七年間的電影音樂理論探討,盡管因上述多變的政治語境而頗顯繁雜,但如果分析公開發(fā)表的文論,這一時期圍繞電影音樂展開的一系列討論,大部分都具有較強的學理性,某種程度上說,無論對當時還是對之后的影響,皆非今日之電影音樂研究可比擬的。這種基于藝術本體的討論,可以視為一種藝術語境。這種藝術語境與前述政治語境相互交織,因此往往被人忽略。需要肯定的是,新中國初期電影音樂的繁盛與國家支持密不可分,同時,黨和國家對電影藝術的支持也成為將電影音樂當作一個重要論域的前提和基礎。正如列寧所言:“所有藝術中最重要的是電影。”[12]《列寧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594 頁。電影相較于其他藝術形式,具有傳播廣泛、影響深遠等特點,所以受到各國政府和政黨的重視。電影音樂作為電影主題思想的重要符號同樣受到重視。新中國初期,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出現如此繁盛的發(fā)展態(tài)勢,究其根本,來自黨和國家對電影事業(yè)的高度關注,以及從政策方面為該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許多支持。1949 年,中央電影局成立,成為電影事業(yè)新的領導機構,該機構從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工團中選出專門從事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的作曲家和干部,建立起音樂工作室。另外,各大電影制片廠也紛紛設立了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組,并成立所屬的樂團。[13]參見曾田力、巫睿、李菁、王艷《百年中國電影音樂流變》,《電影藝術》2004 年第3 期。7 月,中華全國電影藝術工作者協會宣告成立,來自原國統(tǒng)區(qū)的進步電影工作者和解放區(qū)的文藝工作者聚首北平,交流、學習藝術實踐經驗,使得中國電影在集成三四十年代進步電影和解放區(qū)革命文藝的基礎上,迅速形成新的創(chuàng)作局面。這些機制有效保證了電影音樂的質量,使得在新中國宣告成立之前已為后續(xù)電影藝術的發(fā)展打下堅實基礎。在明確的指導思想、相應的電影政策、迅速組建的電影機構,以及一大批有思想、有能力、有素質的電影工作者的多重保障下,新中國的電影音樂事業(yè)如火如荼地開展 起來。
自中央電影局音樂處1953 年正式成立之后,國家不但選派大批干部出國學習,還組織作曲干部訓練班進行為期一年半的培訓。何士德、王云階、雷振邦和全汝玢等具有豐富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經驗的作曲家講授專業(yè)課,李煥之、馬可、楊蔭瀏和姚錦新講授音樂理論和音樂史等課程。培訓班組織觀摩學習國內外影片,總結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經驗,為其后中國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作曲家,滿足了各電影制片廠影片生產的迫切需要。這批作曲家成為新中國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的中流砥柱。1953 年,為適應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需求,中央電影局撤銷音樂處,作曲家分散至各地電影廠。此后,電影局不再設置指導電影音樂的專門業(yè)務機構,這也為電影音樂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14]參見李煥之主編《當代中國音樂》,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版。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層面推出的一系列舉措,對電影音樂的發(fā)展起到關鍵作用。很大程度上,新中國電影音樂的發(fā)展與國家支持是直接而密切相關的。從這個意義上看,新中國電影音樂的藝術語境同樣是基于國家層面的支持與推動的,而頻繁的政治運動施加了額外的影響,這種影響并非單純針對電影音樂,而是作為一種大的政治語境存在。
三、一以貫之的情懷與追求
新中國成立后,電影成為重要的大眾藝術之一,電影音樂也隨之成為影響力最大的音樂形式。據筆者對可見片源的412部故事片所做的信息統(tǒng)計,有署名的音樂工作者445 人,參與的樂團約70 個、合唱團60 個。與之呼應,這一時期的電影音樂理論探索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如此數量和規(guī)模并非一日之間造就,其與1949 年之前音樂界在電影音樂領域的探索直接相關。
1930 年上映的《野草閑花》,首次配以由孫瑜作詞、孫成碧作曲的主題歌《尋兄詞》,這開創(chuàng)了國人創(chuàng)編電影歌曲主題曲配樂之先河。1931 年,“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上映,實現對白、歌唱、音樂都用蠟盤配置聲音,此后有聲片逐漸興起。[15]參見梁寧《中國早期電影聲音觀念初探》,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1997 年版,第19 頁。1935 年,聶耳發(fā)出“中國為什么不把電影音樂建立起來”的感嘆與呼吁。是年,中國首部完整意義上的音樂創(chuàng)作的影片《都市風光》應時而生。[16]參見王文和編著《中國電影音樂尋蹤》,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版。這部影片的音樂,由呂驥、黃自、趙元任、賀綠汀等音樂家共同完成,他們盡管當時處于不同陣營,卻因為一部電影集合一處,其意義不言而喻。《都市風光》電影音樂一經問世即獲多方贊譽,反映出當時中國優(yōu)秀的音樂家群體強烈的家國情懷和高貴的藝術品質。正如《都市風光》導演兼編劇袁牧之所說:“看到歐美有聲電影觀眾日益增加,國產影片觀眾日益削弱,以及歐美電影對于聲影藝術的超越性運用,自己就感覺渺小,正因如此,就更增加了勇氣,一種孩子般的自不量力的勇氣。”[17]袁牧之《漫談音樂喜劇》(《電通》1935 年第10 期),載馮沛編《電通半月畫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 年版,第164 頁。這種“勇氣”在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藝術家心中普遍存在,它在動蕩的歲月里被淬煉成為一種情懷和追求,無論在何種語境下都一以貫之。
從1930 年第一首電影歌曲的誕生到1949 年短短20 年間,中國作曲家、電影人圍繞電影音樂已經有了很多相對深入的討論。早在1934 年,我國早期一批電影理論家、批評家針對當時電影中的音樂、對白、音響三者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辯論,促進了我國電影聲音觀念的形成與確立。陳鯉庭于1934 年以筆名“思白”在《民報?影譚》上發(fā)表《創(chuàng)造中的聲片表現樣式》,作者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電影音樂“聲片音樂”構想,認為當時占主流的以影像與音樂調和度為評判有聲片優(yōu)劣的看法是十分“愚蠢”的,若一部影片美感的產生完全依靠音樂的精致伴奏,那么音樂的價值將取代有聲電影自身的價值。同時,作者對持“音樂雖為獨立藝術,但絕不能離開電影而存在”的觀點提出異議,認為離開影片仍可獨立存在的音樂是電影音樂有待完善的結果;還認為,理想的電影音樂應該是由畫面與音樂“交錯”而產生的新的音樂效果。這種“理想形態(tài)的音樂”要求導演擺脫作曲家、音樂家的影響,而行使“一切的支配權”,只有這樣,音樂聲片才能完全散發(fā)其魅力。[18]參見思白《創(chuàng)造中的聲片表現樣式》,《民報·影譚》1934 年8 月30 日至9 月20 日。陳鯉庭對電影音樂的態(tài)度和對于音樂聲片的觀點,不僅超越了當時的時代,即便在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仍頗具啟發(fā)意義。
相較于這種基于藝術語境的探討,隨著“新音樂”“救亡音樂”的提出,一種基于政治語境的探討成為電影音樂理論探討的主題之一。如呂驥1936 年撰文《偉大而貧弱的歌聲——一九三六年的音樂運動的結算》[19]呂驥《偉大而貧弱的歌聲——一九三六年的音樂運動的結算》,《光明》(上海)1936 年第2 期。,對當時一些流露出“悲傷主義”與抒情性較強的歌曲提出批評,其中提到了任光為電影《迷途的羔羊》所作的主題歌,以及冼星海的一些抒情歌曲,認為這些“表現悲觀主義”的內容并非新音樂所需要的,而且會對當時的聽眾和演唱者產生消極影響,只有旋律慷慨激昂、救亡內容鮮明的歌曲才是抗戰(zhàn)所需要的新音樂作品。隨著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之前被呂驥批評過的冼星海同樣對抒情歌曲作品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電影《關山萬里》主題歌《長城謠》是“感傷情調”的作品,并對其進行批判。[20]參見冼星海《民歌與中國新興音樂》,《新音樂》 (重慶)1941 年第3 卷第1 期。
可見,政治與藝術的兩種語境,早在20 世紀中國電影音樂產生之初就已經存在,由中國近現代歷史發(fā)展使然。
同時,兩種語境又基于家國情懷下的藝術追求而被統(tǒng)一起來,形成一種特有的歷史存在。
結 語
新中國十七年的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領域,產生了一大批至今依舊耳熟能詳的優(yōu)秀作品。電影音樂作品塑造的鮮明形象,在提升民族凝聚力與自信心,培育集體主義與愛國主義思想等方面,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經典的旋律鑄就了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共同記憶。同時,這種優(yōu)質高產的創(chuàng)作,造就了一大批優(yōu)秀音樂家。與之相應,這一時期的電影音樂理論探索也多有成就。當前,學界正積極響應國家建設新時代中國音樂理論話語體系這一號召,筆者認為,應當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包括電影音樂理論在內的音樂理論探索歷程,進行全面而系統(tǒng)的整理與研究,梳理學脈,總結經驗,為當前與今后的理論建設提供重要的史料基礎與學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