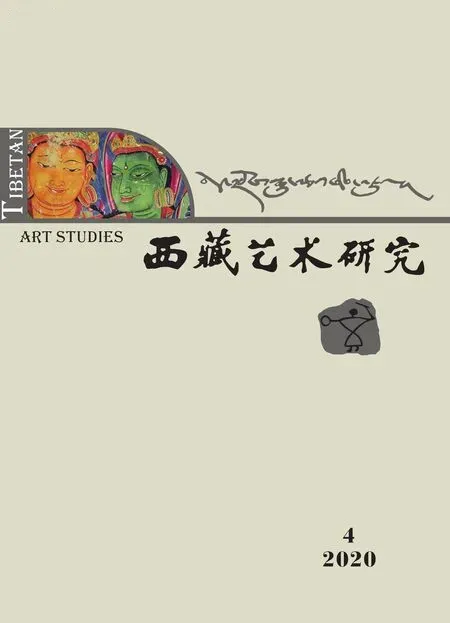關于文博陳列展覽設計構思的幾點思考
達珍
從事文博工作以來,既參與過大大小小的一些展覽,也參觀過國內不少博物館。在這些年的工作實踐中,對于博物館展覽的實際情況也有頗多感想,很多展覽似曾相識,特別在設計手法、用材等方面極為相似,究其原因:一是展覽設計與工期時間緊迫,缺乏足夠的時間在展覽設計上進行創新,從本質上講,設計公司來不及理解、消化、吸收展覽文本內涵,更談不上很好地進行從文本到形式的轉換。第二個,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即在陳列展覽設計的構思上缺乏核心競爭力。結合這幾年在展覽設計工作中的感受,尤其是對展覽實際展出效果的思考,從博物館的基本功能出發,對展覽如何設計構思談談筆者的幾點想法:
一、展覽設計需有核心思想
嚴格地說,圍繞文本策劃進行設計是博物館展覽設計原則,文本是展覽語言中的一種以解釋為主的方式,特別是以歷史主題為代表的展覽。但只是依據文本進行設計是不夠的。因為文本策劃專家有著水平的高下,研究的視野可能會完全不同于形式設計。
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推崇蘇東海先生關于博物館的基本功能的觀點,他認為博物館的三職能在博物館歷史上是依次出現的。物的收藏是第一職能,其次出現的是第二職能——科研職能,最后出現的是教育職能。第二職能是第一職能的延伸,第三職能是第一、第二職能的延伸。三者是同心圓的關系。圓心是物的收藏,內圓是科研,外圓是教育。藏品是博物館的重要組成,是博物館開展一切業務工作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是博物館存在與發展的命脈。①姚安:《博物館12 講》,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9 頁。1990年當選國際博協主席的科納里在他離任就任馬里總統時,就曾告誡博物館“我們不應該為迎合觀眾對博物館的興趣的增長而放棄研究和保管工作,這兩項工作依然是博物館有特色的研究工作。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扎實起碼考證工作的博物館如何從事知識傳播工作。”①蘇東海:《博物館的沉思——蘇東海論文選(卷三)》,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 頁。因此,在我看來,展覽設計核心思想的形成,還需要我們透過文本關注藏品本身。一座博物館就是一部物化的發展史,藏品是展覽的物質條件,同時也承載著豐富的信息,具有相當說服力和感染力。展覽通過藏品與歷史的對話,穿越時空,全面準確地反映某一社會歷史的發展歷程等等。
譬如,前些年由西藏博物館主辦的“沖賽康駐藏大臣衙門陳列館”,由于策展人員對有關駐藏大臣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歷史、駐藏大臣衙門的建立與分布以及歷任駐藏大臣生平事跡、駐藏大臣行使職能的各類公文檔案等眾多文物資料,做了比較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從而在主辦方文物藏品完全空白的情況下,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就順利完成了投資近4000萬元、展覽面積達3000 平方米的該大型展覽,而且做到了展品數量大、展覽內容豐富、展覽體系設置科學合理,成為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有關駐藏大臣歷史沿革的大型常設性陳列。
因此在我看來,展覽設計必須以館藏文物為基礎來體現核心思想,方案設計者應對館藏文物的數量和狀況全面了解,并且具有考古學、歷史學、文物學等多門學科基礎知識與技能,并且能夠根據文本策劃方案確定集中反映主題的展品。
其次,設計的核心要能表達展覽主題。主題是構成展覽的主導因素,它表露于文物的相互關系之中,
蘊含于構成展覽的諸要素的相互聯系之中。主題凸顯館藏的特色與優勢,甚至對每件展品在展覽中的輕重緩急都有規定,如果缺乏主題的安排,再大量的展品,也只不過是展品的胡亂堆放。此外,為了表達主題乃至副主題的不同層次與互動關系,展覽設計的核心思想也隨之多元化,這取決于設計者的視點及角度。以歷史性展覽為例,我們可以真實地復原歷史場景,也可以展示造成這些歷史現象的諸多動因;可以以精英人物敘述歷史,也可以走平民百姓的路徑。總之,展覽設計的核心思想,應該與藏品系統的內在一致,準確地揭示主題,力求最大限度地得到觀眾的認可。同樣以前述“沖賽康駐藏大臣衙門陳列館”展覽為例,由于策展人員不僅對有關駐藏大臣的各類歷史文物有著豐富的儲備和研究,而且有著較為豐富的策展經驗,能夠抽絲剝繭地總結和抽象出每一件展品的歷史背景及其反映的主題思想,從而由小到大地將數量龐大而且紛繁復雜的各類展品依
次組織成版組、單元、部分,通過小主題逐級烘托和反映整個展覽的主題思想。
總之,展覽設計的核心思想,應該與藏品的內在一致,能準確地揭示主題,并力求最大限度地得到觀眾的認可。
二、展覽設計需由連貫的故事線串聯起來
在這一點的認知上,更多地是從作為參觀者的感受出發的。很多時候,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感覺頗有收獲的展覽,往往是將大量的信息蘊藏于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中,在一個個故事中獲益匪淺,“博物館展覽應以自身受眾為衡量標準,為展品構建出一個展覽框架,延伸出一條故事線,并在故事線中添加具有認知性、教育性的元素,使展覽具有整體性,情節具有延續性,從而幫助觀眾更好地利用和理解展品內涵。”①蘇東海:《博物館的沉思——蘇東海論文選(卷三)》,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比如,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就精心布置了明代風格的文人庭園,目的都是讓人聯想到這些作品產生的最初歷史背景與故事情景,這對于觀眾整體了解文物的歷史語境非常有幫助。
事實上,說故事是人類的一種智能,故事可描述事件脈絡,聽故事則是人的天性,是人類傳達記憶、經驗及智慧的方式,人們藉此嘗試再現事件原貌、感受背后的信息意義;故事往往具有連貫性、吸引力與感染力的特征,有著大眾化、通俗化、易記憶的特點與極佳的傳播效果。譬如,西藏博物館主辦的“涉外文物回流展”“葉星生民間珍藏捐贈展”等展覽,將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串聯起來,使展覽極具趣味性。希臘神話、伊索寓言等經典著作無一不是故事的體裁,觀眾借助“故事”來解讀展項,連貫的故事線也是博物館的展覽動線。制造背景故事、讓觀眾身臨其境被證明是最有效的展覽方式之一。
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數學館堪稱營造故事線的典型。據說320 平方米的展廳,前期學術研究竟用了3年時間,串聯了11 個展項。比如展覽各種基本數學原理,如概率曲線、乘法表、運動和萬有引力定律等,用一個個知識點構成整個展覽。從展項上,深入研究每一個知識點;在展覽手法上,采用裝置、運動物、圖樣和寫真照片,把展覽空間打造成既像實驗室,更像一個科學嘉年華;此外,博物館還重塑了一條19 世紀的街道,讓人自然體驗數學、時間、生活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發展,讓觀眾從生活脈絡出發,了解科學常識與數學知識,進而欣賞制作的全過程。
三、展覽設計需要挖掘城市的文化特質與內涵
中國古代有“田忌賽馬”的故事,孫臏幫助田忌獲勝的秘訣在于避敵之長,以己之長攻敵之短。那么中小城市博物館在藏品規模、級別、投入程度、觀眾資源、經濟發展、專業人員配置等方面無法與大城市的博物館相媲美的情況下,如何做到吸引觀眾?拿什么來吸引觀眾?那就需要我們挖掘城市內涵特質,需要我們在展覽中做到融入本地特色與傳統。譬如,作為邊疆民族地區,無論是自然還是人文方面,西藏都有著自己顯著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這無疑是舉辦有關西藏題材展覽的獨特優勢。如果設計人員對西藏的自然特征與人文特質有著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能夠在緊密圍繞展示主題的基礎上,根據展覽的需要,很好地從西藏的自然風光和傳統的民居建筑、日用器具、服裝首飾中等提煉而不是簡單照搬有關圖案、紋飾、色彩,使之得以有效和適當的體現,從而實現與展覽主題和陳設展品很好地契合,必然能夠為觀眾營造出良好的觀展環境與氛圍,得到烘托展覽主題的效果。
尤其是在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加劇了人與傳統的空間分離,本地化的特色漸趨衰弱,許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服務、產品更成為我們現在熱衷的事物。那么,我們如何體現、挖掘、同時賦予本地特色與傳統的現代色彩? 為此,我們不僅需要通過深入研究,以藏品為對象挖掘其中的文化、知識與集體記憶。同時,還需要鼓勵公共參與。西方博物館在改建和擴建中增加的空間基本上都是公共服務的部分,很多博物館根據觀眾需要開展各種本地化的特色服務,應該鼓勵市民階層以自由和負責的方式提出、評價和討論本市博物館所面臨的問題,歸根結蒂,公共參與是博物館本地化的一種有效計劃與實施手段。
四、展覽設計應考慮到觀眾的參觀體驗與感受
博物館是傳播人類文明的重要媒介,它能讓觀眾在展覽中感受到自我,并在親身體驗中加深對事物認識的自信。因此,我們在設計中要考慮到觀眾三種基本需求,即認知需要、神圣感以及文化體驗①這是加拿大文化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sation,CMC)前館長George F Macdonald 提出的觀點。。
博物館展覽必須激發觀眾的好奇心,因為專家和專業人員在觀眾中的比例不足1%,那種讓領導滿意、專家首肯的展覽不一定能獲得大眾的認可。根據內在動機推動行為的理論,展覽要激起觀眾的好奇心,或最大限度地與觀眾的認知結構相吻合,其中誘發觀眾思考和行動極為重要。比如,如果我們需要設計一個介紹地質結構的展項,科學信息豐富,展項充分,還設置了讓人去探求和掌握專門技能的操作設施等等。但關鍵問題是:這個展項與參觀者有什么關系?譬如說能幫助觀眾了解地球嗎?如果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那么,這個展項的設計是平庸的,因為它所提供的信息也不會在參觀者的記憶中留下任何印象。“在博物館的展覽上,我們的宗旨是首先探索能否使用簡單一點的技術,擴大參觀者的活動內容。……更加強調展覽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并盡量降低科技的副作用。”②蘇東海:《博物館的沉思——蘇東海論文選(卷三)》,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 頁。因此,設計者要從空間入手,思考博物館展覽主題和內容帶給人的心理感受,從整體到局部的布置、色彩、文字、圖片、設備、道具、景觀、模型、燈光、照明、聲音、影像、綠化等各個方面,使每個展覽元素服從于整體的統籌規劃,當觀眾對展項發生興趣,并通過感官與之交流,他將體驗到造物之美,展廳也將會是一個引起心靈震撼的場所。
“體驗”事實上是當一個人達到情緒、體力、智力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時,他意識中所產生的美好感覺。今天,人們在關心展覽科技含量的同時,更重視展覽所帶給他們的情感愉悅和滿足,基于體驗理念的博物館展覽應當成為新時期博物館展示設計的主流。人們在獲得展品信息的同時,獲得一種文化的體驗和真實的感受。
現代意義上的展覽在西藏起步較晚,早期的各類展覽不僅數量少,而且由于經費、場地、經驗、技術尤其是理念的局限,其出發點較多地照顧主辦方的辦展意圖,而鮮有對觀眾體驗接受能力的考量,僅僅是對文物展品的直觀呈現,因此相對簡單、平直、枯燥與無味。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尤其是策展與設計能力的提升,西藏區內的絕大多數展覽都能夠很好地考量和運用各種能夠讓觀眾看懂而且喜愛的新穎的展示手段,給觀眾以更加鮮活、生動的觀展體驗,達到展覽主題、內容與觀眾的良好互動,從而更好地實現博物館的文化傳播與教育職能。諸如前述的駐藏大臣衙門陳列館基本陳列、軍史館基本陳列、西藏博物館“歷史的見證”專題陳列、西藏博物館主辦的“涂鴉展”、“凈苑盛蓮—21 度母唐卡展”、“妙相梵容·佛教造像藝術專題展”、“清代帝王生活側影展”等等,這些近年舉辦的大型展覽,都是辦展理念革新與新型展覽手段實踐的成功案例。
最后一個高品質的陳列展覽不僅僅需要考慮上述因素,還涉及到美學、文物藏品、高科技展示手段、展覽環境、心理學等各方面的綜合知識,是一項系統工程,更是一項在前進中不斷探索不斷發展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