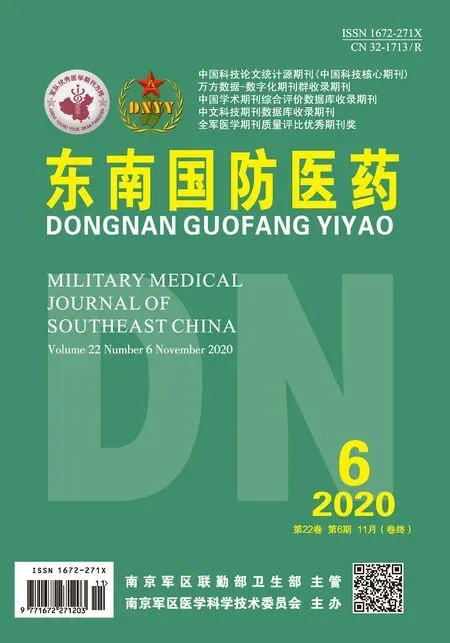腹膜炎患者術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的臨床特點及危險因素分析
郭曉芳,梁 培,陳 鳴,尤 勇,張北源,虞文魁,王 妍
0 引 言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各種原因導致的彌散性肺泡及肺間質損傷和肺血管通透性增加,從而導致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對于急性腹膜炎患者,術期一旦合并ARDS,會延長住院時間、增加病死率[1]。目前ARDS尚無特效治療方法,盡管臨床治療策略不斷完善,如限制性輸液管理、小潮氣量肺保護通氣等,病死率仍高達21.3%[2],目前關于腹膜炎術后發生ARDS危險因素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回顧性分析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后ARDS的臨床特點及危險因素,旨在為防治ARDS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回顧性分析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入住我院重癥醫學科以腹痛為主要臨表現并行急診手術的急性腹膜炎患者臨床資料。入選標準:①年齡>18歲;②麻醉方式為全身麻醉,均為氣管插管;③行急診手術;④住院時間>72 h。排除標準:①合并肺炎及慢性肺部疾病;②合并胸部外傷;③近期30 d內行外科手術治療;④合并神經肌肉疾病;⑤腹部器官以外疾病表現為急性腹膜炎癥狀者。其中ARDS納入標準參照2012年柏林診斷標準[3]。納入符合入選標準的急性腹膜炎患者180例,排除合并神經肌肉疾病1例、胸部創傷性損傷1例、近期主動脈支架置入史1例、肺炎6例及慢性肺部疾病10例,實際納入162例患者,其中男95例、女67例,年齡21~78歲,平均(69.75±14.15)歲。
1.2 研究方法根據患者是否發生ARDS分為ARDS組和非ARDS組。記錄患者性別、年齡、基礎疾病、酗酒及抽煙、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臨床急性生理學及慢性健康狀況評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 Ⅱ)、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入院時呼吸頻率、體溫、平均動脈壓、血清白細胞、白蛋白、降鈣素原、乳酸、C反應蛋白、入院至手術間隔時間、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輸血及液體平衡量、休克及去甲腎上腺素劑量是否>0.1 μg/(kg·min)、手術部位等臨床資料,并統計2組患者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肺炎及病死率。

2 結 果
2.1 急性腹膜炎患者發生ARDS情況39例(24.07%)急性腹膜炎患者于手術后72 h內發生ARDS,其中輕度26例(16.05%)、中度8例(4.94%)、重度5例(3.09%)。
2.2 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后早期ARDS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ARDS組與非ARDS組患者SOFA評分、術中液體平衡、輸血、休克及去甲腎上腺素劑量>0.1 μg/(kg·min)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后早期ARDS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SOFA評分、術中液體平衡、休克、去甲腎上腺素>0.1 μg/(kg·min)、輸血是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后早期發生ARDS的危險因素。見表2。
2.4 術后指標比較ARDS組患者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及30 d病死率明顯高于非ARDS組(P<0.05),2組肺炎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2 急性腹膜炎患者發生ARDS的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表3 急性腹膜炎患者ARDS組與非ARDS組并發癥及病死率比較
3 討 論
急性腹膜炎是急診常見危重癥,因過度激活的炎癥反應及免疫功能抑制,可導致嚴重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等多器官功能障礙[4];另腹部手術切口對呼吸肌造成直接損傷、術后胃腸功能障礙及腹部切口劇烈疼痛等可導致膈肌上抬、氣道分泌物清除障礙、肺容量減少及雙肺下葉肺不張等病理生理改變,是引起ARDS的主要誘因[5]。因此探討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后早期ARDS的臨床特點及危險因素,可以早期規避風險,加強防治并改善預后。
目前國內外關于急性腹膜炎手術后早期ARDS發病率及危險因素研究較少。Serpa等[6]以氧合指數<300 mmHg作為ARDS的診斷標準,發現腹部手術早期ARDS發生率為3.4%,病死率為12.2%。本研究發現我院急性腹膜炎手術后早期ARDS發生率為24.07%,病死率為15.38%,較既往研究明顯升高。究其原因考慮一方面本研究納入對象均為急診手術患者,與擇期手術相比,在術前評估及準備、術中管理方面存在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原因與ARDS診斷標準不統一有關。本研究采用高敏感性的柏林診斷標準,有助于早期診斷,規避風險,評估預后。
急性腹膜炎時,腹膜急性炎癥時,細菌及其釋放的內毒素刺激腹膜肥大細胞釋放組胺等血管活性物質,導致血管通透性增加,血管內液體及血漿蛋白質滲透至腹腔,導致有效循環血容量下降;急性腹膜炎引發機體過度炎性反應,產生過多炎性介質[7-8],致微循環障礙,進一步加重液體滲漏至組織間隙;同時手術過程中腹腔開放,不顯性失水增加,嚴重者導致休克。基于以上病理生理機制,術后液體治療可以穩定大循環,維持有效循環血容量,保證組織灌注。然而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中輸注過多膠體及晶體造成液體負荷過重,導致液體及蛋白質通過高通透性血管滲透至肺泡及肺間質,減少肺泡表面活性物質,降低肺順應性,增加ARDS發生風險[9-10];通過對肺葉切除手術[12]、重癥創傷手術[13]及腹部手術[14]研究均發現,圍術期液體平衡量與術后ARDS發生率呈正相關,且延長住院時間、增加病死率;已有研究表明,與術中自由液體治療相比,限制性液體治療60 d并發癥降低(28%vs45%,P=0.02),住院時間縮短(9.7 dvs11.5 d,P<0.01)[15]。與以往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中ARDS組術中液體平衡量大于非ARDS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為急性腹膜炎手術后發生ARDS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有研究以術中≤5 mL/(kg·h)補液量,術后≤0.8 mL/(kg·h)進行補液,因患者基礎心功能及疾病狀態不同,輔以食道超聲或脈搏指示監測儀等指導個體化液體管理[16];另有研究建議以術中脈搏壓力變異度>10%、心指數>2.5 L/(min·m2)及平均動脈壓>65 mmHg為目標導向性液體治療目標,避免過量補液導致容量負荷過重,減少腹部手術患者術后ARDS的發生率,改善預后[17]。
急性腹膜炎患者手術中輸注液體除晶體和膠體外,也使用血液制品。輸血會帶來多種風險,一方面血制品中的人白細胞抗原抗體,螯合于中性粒細胞促使后者釋放細胞因子及炎性介質,破壞毛細血管內皮,導致炎癥性肺泡水腫[11];另一方面人白細胞抗原抗體與白細胞形成的微聚物阻塞肺部毛細血管,進一步加重肺損傷。術中輸血相關的急性肺損傷發生率為0.1%~2%[18-20],重癥患者可達5%~8%[21],一旦發生肺損傷,病死率可高達43%[22]。研究表明,血紅蛋白濃度、術中失血量大、開放手術及手術時間長是術中輸血的危險因素,其中血紅蛋白濃度是術后肺部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23]。與以往研究結果相同,本研究發現,術中輸血是急性腹膜炎手術后早期ARDS的危險因素。因此,有研究建議以血栓彈力圖為指導,不僅可以評估術中成分輸血需求,同時可以識別術后是否發生大出血風險[24]。
早期評估急性腹膜炎病情嚴重程度有助于臨床監測,減少并發癥,改善預后。SOFA評分系統是評估多臟器損傷嚴重程度的可靠工具,對預后也有重要的預測價值[25]。本研究中SOFA評分越高,急性腹膜炎手術后早期ARDS危險性越大。且一旦并發ARDS,急性腹膜炎患者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及30 d病死率均明顯增加,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對于急性腹膜炎手術患者,常規進行SOFA評分,并關注SOFA評分變化,以血流動力學監測為目標,強調個體化液體管理,并注意加強血栓彈力圖監測評估輸血需求,有助于減少腹膜炎術后ARDS的發生。
另外,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手術中呼吸機機械通氣數據缺失;其次,本研究納入病例平均年齡69歲,老年患者居多,相對而言,老年患者器官功能衰退,對手術應激能力下降。因此本研究結果是否廣泛適用于成年患者尚需進一步研究。
ARDS是急性腹膜炎常見并發癥,延長住院時間及機械通氣時間,病死率高。對于SOFA評分高、手術中大量補液及輸血患者,應嚴密監測呼吸功能,警惕發生ARDS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