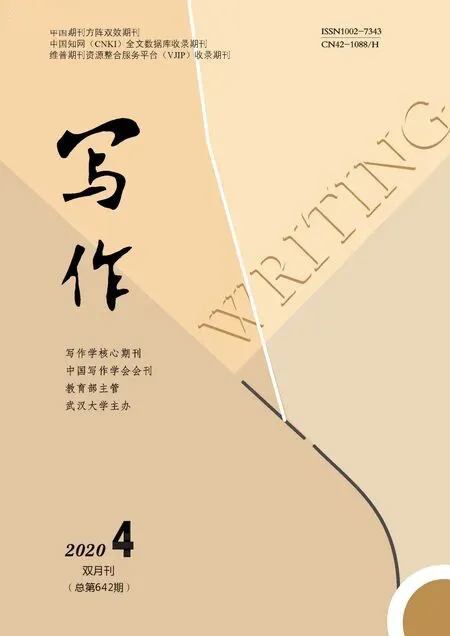美國科幻小說最新潮流
——謝里爾·文特首次中國行演講
[美]謝里爾·文特
何 銳譯 張 凡編校
今天要做的演講中,想綜述一下我認為對近來英語區科幻小說,以及對北美和歐洲的語境中的科幻小說研究,最為重要的幾個趨勢。首先我想指出,這些趨勢與我觀察到的、在中國圍繞科幻小說所出現的發展有所不同;但當然,我必須承認,我對中國科幻小說的了解有些片面。我的所知限于那些被翻譯成了英文的作品,對更廣闊的背景(以及中國文學的歷史)的認識也建立在以英文出版發行的學術著作之上。因此,我提出這些框架性的評論,僅僅是作為一種途徑,好由此和你們展開對話,通過對話確認,或者,更可能是糾正我對中英兩種語境中的科幻小說研究間的差異的判斷。所以,我期待在提問環節能從你們那里學到東西,同樣也期望你們會在這次演講期間有所收獲。
那么,首先,在當代英語區語境中的科幻小說研究和實踐,與我所見的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趨勢之間,我認為有四個重要的差異:
第一,對于所謂“硬科幻”,或者說,從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和工程學外推而來的科幻,雙方的偏好度不同。這類科幻小說的核心是以技術來解決問題,或者是依賴于某種新發明、對物質的新的操作方法,在文中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之間創造出差別。
第二,受歷史影響的方式不同,尤其是殖民主義對兩種科幻小說圖景的影響大相徑庭。殖民主義在當今的英語區科幻小說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而且最受歡迎的作品,其視角常常來自之前被殖民或是被邊緣化的人群,要求我們接受對于技術化的現代性的另一種更富批評色彩的觀點。西方科幻小說過去往往是屬于殖民者和征服者的文學,而最近的一些評論作品(譬如約翰·里德爾的大作《殖民主義和科幻小說的誕生》),讓我們注意到這個事實:科幻小說這一類型文學曾是助長帝國主義者野心的同謀。我有個印象(主要源自對劉慈欣作品的閱讀),中國科幻小說從一開始就站在對帝國主義更富于批判性的立場上,而科學和技術則被視為將人類團結為一的重要工具。
第三,科幻小說和其他類型文學的分離歷程也不同。我的認知里,科幻小說在中國文學中是個比較晚近的發展,但現在,對于這種故事人們格外地感興趣,它們聲名鵲起,被視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創作。而英語區科幻小說的歷史則要復雜許多,有些人聲稱它的歷史要追溯到19世紀(《弗蘭肯斯坦》常被視為第一部科幻作品),而另一些人則聲稱這一類型要到20世紀初才隨著紙漿雜志(pulp magazines)出世——“科幻小說”這一術語也是來自于這些雜志。整個20世紀,這些雜志和其他諸如電影電視之類的大眾媒介,讓整個科幻類型帶上了幾分不太光彩的名聲。科幻小說并沒有被視為能傳達重要理念的文體,常常被批評行文低劣。直到近年,才有若干受人敬重的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科馬克·麥卡錫,等等——把科幻小說的技巧引入到他們的作品當中。
第四,烏托邦的可能性常常和科幻小說關聯,對待它的方式,兩邊也有所不同。這最后一點,主要與在北美和英國的學院中作為科幻小說研究基礎的文學評論傳統有關;在歐洲國家這種研究較少,但狀況正在改變。不過,重要的區別在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這兩套語境中的位置。在英語區傳統中,馬克思主義的理念仍然停留在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夢想的層面上,被許多文化批評家所接受。這方面首先要提一下恩斯特·布洛赫,他在《希望的原理》中贊揚了那些提供了一個更美好、更少異化的世界的作品。達科·蘇文在1977年出版了《科幻小說變形記》,它成為了英語區科幻小說的一個基礎性文本。在書中,他認為科幻小說是“在現實基礎上”(on reality)的反思,而不是“對于現實的”(of reality)反思,它提供了一種讓我們疏離于既定的物質世界,從而預見到社會變革可能發生之所的途徑。因此,科幻小說研究經常與烏托邦主義聯系在一起,尤其是對世界常常持有平等主義觀點;女權主義科幻小說或非洲未來主義科幻小說的優秀作品也會采納這種觀念,對不公加以批判,并提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圖景。顯然,在中國社會中,馬克思主義理念的地位和文化傳播的路徑都與此大不相同,這使得人們閱讀科幻小說做出反應的基礎也有所不同。
在接下來的講座中,我將繼續討論這些不同,我希望在討論期間,我們都可以思考一下英語和中文科幻小說的相似和不同之處。我不會繼續詳述英語區科幻小說的歷史——在提問環節我會樂于介紹更多關于它是如何、為什么以及何時誕生的話題——但接下來,我想向你們就我所認為的當代科幻小說中的最新發展做一簡要介紹。這一介紹基于我認為是當代英語區科幻小說最佳范例的四部作品,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我將按照出版年份的順序進行介紹。
科爾森·懷特黑德:《第一區》(2011)
《第一區》采用喪尸災難敘事,但講的不是世界末日或其隨后的影響,而是直接跳到了重建期。小說的設定是一個周末,地點為曼哈頓。書名“第一區”,指不久前隆重成立的美國鳳凰城政府的重建項目。小說聚焦于馬克·施皮茨的經歷,他曾是一名IT社會營銷員,而現在是掃除隊的一員,他們要掃除最后一批殘存的喪尸——那些沒有被早先的一次大規模軍事打擊殺死的喪尸——以便開始重建。通過倒敘的片段,我們瞥見了馬克·施皮茨在瘟疫導致人類喪尸化之前的世界,以及危機過后更危險的求生時期。懷特黑德的喪尸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我們熟悉的那種,“骷髏族”①原文為紐約俚語,實指街頭流浪漢和犯罪嫌疑人,也是《星球大戰》中一種兇殘野蠻外星種族的名稱。,它們在街頭游蕩,攫人而食,似乎成群結隊地行動;另一種則是神秘的“彷徨者”,一些獨行喪尸,它們被困在某個地方或者重復著某個行動,這些地方或者某個行動在理論上對它們的前身很重要。彷徨者會沒完沒了地站在復印機前,在生前最喜歡的商店里圍繞殘留的商品轉圈,又或是在以前辦公室的小隔間里呆坐。隨著小說的展開,人類幸存者與非人類的“骷髏族”和“彷徨者”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標題“第一區”指的是曼哈頓的一部分,在一堵高墻的屏障之后,那里應該已清理干凈了所有的喪尸,即將做好準備,再次迎來“舊世界”的消費主義社會。
《第一區》將我們對人類過往的眷戀,診斷為妨礙我們想象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和主體性的未來病因。它還使用了喪尸世界末日后“掃除”的景象——以及美國霸權以鳳凰為象征的重生,其令人觸目驚心的失敗——來暗示美利堅帝國已如行尸走肉——一個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已經逝去、仍然以其熟悉的模式移動的喪尸。書中對商品資本主義的批判強烈暗示貧富差距是美國難以為繼的主要原因之一;該書還涉及了美國系統性種族歧視的話題,因為書的結尾揭示出主人公——我們稱之為馬克·施皮茨——是個黑人。這個綽號是個笑話:馬克·施皮茨是一位著名的德國游泳運動員,奧運會冠軍,主角則不會游泳,這導致他做出一個瘋狂的選擇,從一群喪尸中殺出一條路,而不是找個地方跳進河里逃生。我認為,這部小說是美國科幻小說里,有色人種作家中,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的一部分,那就是提供“疏離”于這個白人霸權的世界的視野,這是當前這領域最重要的實踐之一。
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消費文化圖景,表達了喪尸敘事和新自由主義排斥②指新自由主義體制下,貧困者和其他社會邊緣群體會被社會體系“排斥”而出、不予考量的現象。之間的聯系。例如,反喪尸民兵的搶劫受到嚴格監管。這場戰爭有贊助者,他們捐出自己的一些產品——通常是那些很快就會變質的,要不也并非重要的利潤來源——以從鳳凰城政府那邊換取稅收優惠和重建合同。清除剩余的喪尸和經濟中產階級化③城市中心由于地租高昂,低收入居民和租戶被逐漸排擠,導致小區居民多為中產階級的過程。相似,馬克·施皮茨以挖苦的口吻點明了這點:
未來需要很多東西,但馬克·施皮茨沒有想到會需要室內裝飾。……未來是從前所謂的過渡社區。基本服務供不應求,貴賓狗美容院和貓咖啡都是,但如果你到訪的時間正確,哪怕隔壁的大樓滿是骷髏族也沒關系。最終它們會因為租金上漲而被趕到地鐵三站路之外,你就再也見不到了。(167)④原書英文版頁碼。下同。
馬克·施皮茨既沒有野心也缺乏靈感,是個被中產階級化經濟拋下的人。他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最后一份是為一家咖啡公司工作,他“監控網絡,尋找機會散播對產品的了解,培植品牌親密感”(149)。軟件機器人還不夠聰明,不足以在這種交流中采用正確的語氣,但是馬克·施皮茨“輕松掌握了一種技巧,之后發現,這是一種模仿人類的聯系,做出虛假移情姿態的天分”(150)。通過社交媒體,人類與商品的關系很容易取代真實的社會性關聯。
能夠裝出但并不能真正感覺到同理心,這樣的“偽人類”特征讓馬克·施皮茨在喪尸世界中成為幸存者,但也點出了小說對一種雖生猶死的文化的批判。通過講述馬克·施皮茨在旅途中的日子,《第一區》呈現了后世界末日敘事中一個熟悉的主題:人類互相捕食之際,不確定的人際關系很容易遭遇背叛。在鳳凰城政府成立之前,“當他意識到自己首先要做的就是算計是否能擺脫他人時,他就停止了和別人的交往”(115),他的許多記憶也講到了當屏障被打破時,短暫的友誼不可避免地被背叛。他為這些行為辯護,他相信:“他救不了那些陌生人,就像他們救不了他一樣。他的東道主們對他來說跟外面群聚而來的那些骯臟的烏合之眾一樣陌生,那些家伙正在門窗上扒拉著,饑腸轆轆地想要進來”(183)。這個比喻中,美國的經濟分化及其文化根源——缺乏集體主義精神——都清晰可見。
馬克·施皮茨總結道,“街壘是這場混亂留下的唯一隱喻”(97),透過他的回憶,我們發現這個隱喻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位于社會關系的核心。這標志著中產階級無法接受自己不能免于危機,無法動搖那種感覺:“一道無形的屏障包圍著他所在的郵區,每一次逃跑的機會都被他自己破壞于無形之中,因為他堅信一切都將恢復正常,這野蠻的新現實不會長久。”(18)他認識到,這種屏障是“我們一貫的做法。這是這個國家的立國之基。災難只是讓它變得更加形諸于外了,就像是為防萬一你以前沒能領會,于是把它徑直寫了出來”(102),這個陳述也可以看作是小說的主題。他還指出,早在大感染之前,紐約有一個階層已然遭災,那就是“過去的失敗者隊伍”①原文這里再度雙關,“隊伍”的原詞另一個意思是“骨骼,骷髏”。,他們“從單間居室中步履蹣跚地走出來,又或者從他們已寥寥無幾的親友中某位的破舊沙發里把自己拔拉起來”(121)。他想象著自由女神像上的銘文變成了“流膿的大眾”②對應的銘文原文為“(因饑寒而)蜷縮的大眾”,常見的中文譯本這里省略掉了。,并提醒自己,“這座城市并不在乎你的故事,你重塑自身的個別敘述;它接納所有的人,每個移民都在竭力競爭,不論他們的血統,在祖國的身份,以及口袋里的硬幣數量”(243)。
《第一區》代表了英語區科幻小說當前的一個趨勢:在寫作中把科幻的概念或者設定作為隱喻來使用,但并不努力構造能讓人全然信服的另一個世界。《第一區》的要點不是讓我們想象它所創造的那遭受了喪尸之災的世界,而是讓我們看到,喪尸之災的隱喻如何讓我們將這個世界的貧富差距和種族主義問題看得更為清晰。
李昌瑞:《在這滿潮的海上》(2014)
李昌瑞和懷特黑德類似,也是一位以寫主流文學小說聞名的小說家。他在這部小說中轉而描寫科幻場景,因為科幻為他提供了表現他所選擇的主題的最好的途徑。因此,他是科幻文學和“主流”文學日益靠攏的趨勢的一部分。李昌瑞還代表了一種比早先的英語科幻小說更具全球視野的科幻。眾所周知,像《世界大戰》(1897年)或《地球停轉之日》(1951年)這樣的作品會徑自假設倫敦或華盛頓將是統治世界的中心,外星人理所當然會首先前往這些地方。《在這滿潮的海上》則不然,它雖然把舞臺設定在美國(主要是巴爾的摩),但卻設想了一個美國霸權已成往事的未來。它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個被來自中國的移民者們殖民的未來美國;這故事是個復合體,從這些移民的角度打量美國帝國崩潰的廢墟,同時也通過講述這個三種未來文明在同一空間中糾纏的故事,對一個計劃過于嚴密的集體社會秩序提出了批評。
作為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在這滿潮的海上》的標題取自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那幾行臺詞講的是“人類事務中的潮流”③《裘力斯·愷撒》第四幕第三場。,這種潮流要么讓我們的船航向成功,要么把我們導向淺灘和苦難。這一引語提示我們會出現突然的逆轉,并和一種在東西方有著共同文本的新的全球文化展開對話。小說講述了一位姓范的年輕女孩,她離開自己的中層階級漁場,冒險前往缺乏治安秩序的鄉村去尋找她失蹤的男朋友。它實則是描繪了未來美國一副令人不安的圖景,這種圖景由全球化的力量塑造而成,有個突出的特點:其中的階級分化和經濟不穩定比我們現在所體會到的要更為深重。
范來自一個“新中華”的殖民點——巴摩,我們很快就知道那就是巴爾的摩,那里已經沒有了如今還留在那里的非洲裔美國人①巴爾的摩當地人口當中,白人比例近些年一直在下降,目前黑人已經占人口多數。,取而代之的是亞洲移民,他們希望在一個不那么擁擠、機會更多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就像他們19世紀的先輩,后來成為美國人的那些歐洲殖民者一樣。在解釋這座城市的前居民的離開時,敘述者告訴我們,“每個人都離開了,盡管和我們的祖輩離開他們在新中華的河邊小鎮的原因不同。當他們離開的時候,西徐市已由于周圍的農場、工廠、發電廠和采礦作業變得不適人居,水污染業已超出了所有已知處理方法的能力”(16)。講述故事的這個聲音從來不會直接地或公開地傳達19世紀殖民主義者那套理論,比如說白人的天命,或者是剝奪土著人民未被“有效地”或“充分地”使用的土地有多么合理。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會被上面這樣微妙的暗示所提醒,察覺到“潮流”是多么容易逆轉,同樣的論調也會被用來反對美國人。這個故事也追述了全球化的人員和資源流動,這種流動塑造出我們的現在,引領著我們的未來。
小說的大部分內容都著眼于巴摩的社會,故事本身的形式是傳奇式,或者說敘述體的,巴摩人們口口相傳著范的故事,講述著她是如何以及為什么離開這個社會的。因此,盡管小說的大部分內容是關于在范離開巴摩安全區的旅程中,她在美國經濟崩潰后的殘跡中所見的種種不幸,但更尖銳的批評來自敘事者那些經過小心組織的批評語句,他們批評巴摩的條條框框,還有經濟層級制,正是這種制度制造出了巴摩精英協會的專屬領地和危險的鄉村之間的(對立)關系。巴摩的一切都圍繞著時間表、生產力和為整體的服務;盡管人們一再被告知這里的社會是和諧和高效的,但每天的生活中都有詭異的暴力突發,只是會被迅速遏制。因此,盡管范在城市之外的旅程中經歷了種種艱難,她的故事仍然是個關于選擇的夢想,她選擇動態而非靜態經濟結構,后者要確保有一些人總是將自己的生命附屬于向他人提供服務:
從我們的先輩最初抵達此地,已經有將近一百年了;距今天的巴摩最后一次重建和整頓,也已經有五十多年。長久以來,我們一直維持著社區的秩序,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我們從沒有讓我們的窗玻璃灰暗蒙塵,也沒有讓我們的黃銅把手污漬斑駁。我們總是讓我們的孩子在運動之后自己收拾好操場,我們從不允許任何人逃避他或她的責任,或者變得懶惰、依靠他人養活。巴摩運行良好,是因為我們在好好工作;我們的使命感驅使我們采取額外的措施,付出額外的時間,還有,當然了,每當我們疲憊頹喪之際,想起外面的鄉野中的狀況,還有這里在最初的先輩們登陸之前是個什么樣子,我們就再度充滿了干勁。
在講述范的故事時,敘述者也告訴我們,北美是怎樣被劃分給了三個截然不同的階級:被剝奪公民權的人被貶謫到農村,在一片幾乎不可能耕作的土地上艱難求生;中間階級,范這樣的工人,在像巴摩這樣的城市里工作,這些從前的工業城市而今轉而從事更生態平衡的食品生產;以及外人禁入的協會領地,那些飛地擁有諸多特權,人滿為患,只有最具科學素養的精英才能居住其中。盡管將這部小說與科幻小說聯系在一起的最明顯的特征是它的“敵托邦”基調,但科學和科技創新在協會屬地中的中心地位也足以讓它被歸入科幻類型:只有能創造利潤的科技創新才是進入專屬禁地的唯一保證。而且科學在沒有特權的地區所遭遇的部分苦難中也處于中心位置:書中暗示一場疾病消滅了所有的本地動物和大部分人口;從書中還隱隱可知,那些有所需的生物化學或者基因特性的人正被生物科技公司“收割”。
這部小說在某些方面讓人想起麥卡錫的《長路》,但與《長路》不同,《在這滿潮的海上》不僅僅是從那些重新體會到生命可貴的人的角度發出的對更溫柔的時代的懷舊挽歌。它乃是將經濟不穩定性,作為一種人人都可能輕易陷入的普遍狀況而進行的審慎反思。也是在堅持主張,事關絕望和道德妥協的選擇,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事務。《在這滿潮的海上》不僅僅是美國被殖民的反轉式殖民故事,它還是一部體大思深之作,思考的對象是,在凝視全球化資本所創造的嚴酷世界時,來自眾多種族和出身的移民們交織在一起的夢想和希望。
故事的高潮,范得以短暫地和她的哥哥李威重聚。李威在她很小的時候就被帶走了,去上協會附屬學校。被協會接納為會員是一個極大的榮譽,是非凡智力成就的標志,也是通往財富和安全的門徑。李威是一名生物技術專家,他自己的公司一旦售出就可以獲得巨大的知識產權收益,但前提是他必須能夠對自己的產品做出最后一步改善。小說告訴我們,范的血液(以及早先失蹤的她前男友的血液)是這一生物技術創新的關鍵,而在小說的結尾,范僥幸逃脫,沒為了讓她的兄弟可能發財而變成實驗室中的一份實驗材料。“我們”,講述故事的社會集體的話語觀察到了這一事實,同時也提到,協會們前不久出臺的針對巴摩人的經濟緊縮政策有所放松。
現在還有什么好擔心的?局勢相對平穩之下,管理局,或者是我們不清楚的其他機構,已經撤回了前些時的部分令人沮喪的舉措,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于去健康門診就診的限制:限制仍然有效(基于當前的現狀,理應如此),但頻率更合理了。還有進入協會的資格限定(退回到了2%),以及其他一些確實讓日常生活有所不同的小事,比如我們自產的那些優質產品和魚類忽然間拿到了更好的出價。甚至有傳聞說,學校在準備孩子們的午餐便當時會更多地使用我們的產品,而不用那些長期以來一直來自匿名的不明供應商的可疑的西蘭花和土豆,不過這事還得等等看。最后,還出現了新一輪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建設,雖然規模不大;它們以“堅持不懈”為口號,以相當不錯的薪資水平雇了一小隊人馬,剛退休的人,或是失業的年輕人,他們正在打掃街道和人行道,修剪公園里的灌木,對掉了色或者遭人涂鴉的建筑和墻壁進行強力沖洗然后重新粉刷……還有上百個各種各樣的其他項目,旨在為我們這個好地方增光添彩。(337)
李昌瑞和懷特黑德一樣,用科幻小說的語言來討論一個全球化資本的“敵托邦”世界,討論它分化人類和獲取資源的方式。
N·K·杰米辛:《第五季》(2015)
《第五季》是《破碎的地球》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兩部是《方尖碑之門》(2016)和《巨石蒼穹》(2017)。這本書更接近于奇幻而不是科幻,因此我對它的討論會更簡短些,但我想引起大家對它的注意,個中原因有二——不過,如果算上我認為它在近年來出版的幻想文學中是頂尖之作的話那就有三。第一,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標志著英語區科幻小說的另一個趨勢,那就是科幻小說和幻想小說之間的區隔正在瓦解。第二,杰米辛發現自己——由于她的作品遭受的攻擊——處于一場關于種族的爭論的中心。在過去幾年當中,這一爭論在英語區科幻小說的中心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我不想在這件事上糾結太久,因為我不想過多地關注這場辯論的某一方的觀點,但我覺得我也不能不提到它,因為它在科幻小說研究中是一大事件。我認為它正在迅速走向結束——朝著高揚多樣性的方向。不過,正如各位可能知道的,一個人數不多但聲音響亮的白人作家團體最近指控科幻獎被自由主義觀點“劫持”,這些人(你可能知道他們,在互聯網上號稱“悲傷的小狗”的群體)認為科幻獎頒獎的標準無疑是變成了政治忠誠而不是作品質量。也就是說,這些“小狗”們認為科幻獎,主要是雨果獎,之所以頒給某些作家,僅僅是因為人們想褒揚有色人種作家,或是關于社會正義主題的寫作,而不是因為那些書實際上是最好的出版讀物。他們還爭辯說,“真正的科幻小說”更傾向于我在講座開始時談到的硬科幻傳統(也就是說,以工程問題為綱,對社會問題不予置評),并希望讓科幻小說重新回到只有那一種寫法的年代。這些人的觀點大錯特錯:不僅因為像杰米辛這樣的作者獲獎是實至名歸的,也因為英語區科幻小說作為一個整體,從來都包含著一些不僅僅是對新技術進行推想有興趣,而是對推測新的社會形態和更公正的社會秩序更有興趣的作家。因此,我認為這件事很快就會整個翻篇了,它主要是美國目前兩極化的政治爭議引起的共振,而不是來自科幻小說本身,但盡管如此,無論對此多么痛心,我也不能否認,這件事的確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科幻小說的面貌。
不過我們還是把話題回到《第五季》上。它描繪了一個靠魔法運轉的世界,但這種魔法是依據能量循環原理起作用,需要特殊的知識和技巧才可以施展。那些有這種能力的被稱為“造山者”①目前的中文版譯為“原基人”。,他們從大地中獲取能量,尤其是與行星的地殼構造相關的重力能量。他們也能操縱活體中的電能,輸送或抽取能量,或操控器官的功能。我要提請注意的是,杰米辛在這里設想魔法在以類似于科學的方式發揮作用:它是一種技術或者工具,它的力量必須經過學習,它依據與物質世界相關的物理規律發揮作用。我在這里的觀點并不是說這是一本更像科幻小說的奇幻——盡管我認為“破碎星球”三部曲都確實如此——而是杰米辛的作品很能說明為什么我認為,在英語區的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作者的著眼點(通常讀者也一樣),是這些類型小說中的哪些喻體適合他們用來象征或批判,這種使某些隱喻文學化的思辨工具,如何幫助作家把現實社會這個世界的某些方面更清晰地呈現出來,從而進行批判——比如懷特海德把美國視為一個雖生猶死的帝國,或者李昌瑞將個體存在必須被轉化為集體生產力的社會視為一個反烏托邦的未來。
杰米辛用這套魔法作為喻體,同時還把大地本身比喻成了一個有生命的,在跟那些生活在她表面上的人類對抗的活體。由此她做出了兩個方向的隱喻。首先,她讓故事復雜的背景歷史中包含多個不同種族,以及他們之間的殖民、奴役和其他剝削關系,以此置喙于美國的種族主義歷史。主要人物伊松是一個造山者,她一輩子經歷了極端的歧視:我們在小說結尾會了解到,之前表面上的三個人物,實際上都是伊松在她生命的不同階段曾用過的不同名字。當她的父母發現她有造山力時,她就被送走了,之后一度被支柱學院奴役,那里控制著所有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并把他們視為劣等人,她在那里因根植于種族偏見的暴力而失去了兩個孩子。
這部小說探討的第二個主題是環境。“第五季”是一段地質構造的劇烈活動期,將導致地球表面暫時無法居住。我們得知,這種不穩定性來自更早的幾個世代,那時的人們將世界上的自然資源開發得太徹底了,以至于大地開始反抗住在它上面的生民。系列的后兩本書更完整地探討了這段歷史的故事,也提及了如何以另一種方式生活,與大地之力和諧相處,但《第五季》為理解這部作品搭建好了平臺,讓我們能夠將三部曲不是當做一個讓我們逃避到其他世界的幻想作品,而是當做我們因人類活動而被改變的現實世界的一個隱喻來理解。環保主義長期以來一直是英語區科幻小說的一個重要部分,在20世紀70年代環保主義運動開始之后這點尤為突出。杰米辛的作品為這一傳統又添新花,但它還進一步充分考慮了殖民歷史對環境破壞的影響。由此,她所描繪的途徑呼應了后殖民主義學者對術語“人類世”的一些批評,他們堅持認為,地球所受的損害當中,各個人類文化所造成的分量并非等同。杰米辛還表明,環境倫理必須與其他倫理革命協同一致,如果不考慮另外的等級制度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視,就不可能有環境正義。
金·斯坦利·羅賓遜:《紐約 2140》(2017)
我認為金·斯坦利·羅賓遜是當代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而且我覺得在我討論過的所有作品中,他的作品在中國最出名,所以我會把對這部小說的概況評述做得更簡短一些,并簡單提一下他身為作家如此之重要的幾個原因。自從職業生涯開始以來,他的創作始終圍繞著兩個主題,一是對環保主義和未來地球的生命力的關注,二是對貧富差距和資本主義對人類和環境的摧殘的關注。這讓羅賓遜成為踐行我在演講開始時提到過的“馬克思主義科幻小說”的一個榜樣。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火星三部曲”(1992-1996),講述了未來文明在被地球化改造過的火星上發展的故事;近來又寫了許多關于太空探索和人類在其他星球上的流散存在的作品:《伽利略之夢》(2009),《2312》 (2012),《奧羅拉》(2015),還有最新一本《紅月亮》(2018),這本書里面中國占據了顯要位置。我認為羅賓遜是一位特別重要的作家的關鍵原因是,他將對“硬”科學推斷的興趣與關于社會公正和變革的主題結合到了一起。因此,他完美地同時體現了當代科幻小說領域的兩派意見:一派對創新、科學和工程可能會怎樣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更感興趣;另一派則認識到,技術變革總是與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因此更好的科技未來也要有人類生活各個方面都更好的未來為伴。
羅賓遜近期作品中,我選出了《紐約2140》來著重介紹,因為之前的一系列小說更多關注的是太陽系內的擴張,而這本回到了地球,回到了近未來。在我看來,這代表著羅賓遜對正日益加深的環境危機的緊迫感。小說通過對一個海平面上升后的世界的想象,將這一主題迅速而清晰地顯現出來,它更多地是在表述我們必須如何做出創新和改變,而不是嘗試警告我們這一危險正在臨近,試圖讓我們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避免這種未來的到來。《紐約2140》提出,要制止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如今為時已晚,故而我們必須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要如何利用科技讓我們從危機中生存下來,甚或在那個不一樣的未來中繁榮發展。
我選擇這本書還有一個比較個人化一點的原因,這與我研究最近的轉向有關。除了氣候變化的主題,這部小說還深入探討了市場經濟,尤其是金融投機,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如何制造出不平等、并激勵劣化的資源管理決策。盡管羅賓遜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一直關注經濟不平等和資本主義的危險,但只有到了這本書,他才非常直接地談到與當代經濟狀況相關的金融問題,還特別提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未來社會被一分為二,一部分人生活在公社當中,他們的表現就像是預期中的社會組織新模式,我們必須做出那樣的革新;另一部分人繼續生活在特權的高樓大廈之中——就像是自占領運動①指“占領華爾街”運動。以來,我們已經認識到的1%和99%之間被剝削關系區分開來。除了對導致氣候變化的行為進行批判,這部小說還深切關注債務文化的后果:一些人因償債結構而身陷貧困,機會受限,與之相反,另一些人則靠著手握資本而獲得了自由。在這里我們發現,羅賓遜的本作和李昌瑞的《在這滿潮的海上》之間有相通之處。因此,盡管這部小說認為,我們要避免氣候變化可能為時已晚,應該改而做好準備迎接變化,但它同時也暗示,我們仍有可能改變債務—信貸經濟結構所造成的損害。它提出,債務清償運動②近年來歐美部分社會人士組織的運動,試圖通過聯合談判等方式減免個人貸款的償還數額,降低債務人的負擔。是改變現有金融秩序的一種方式。
涉及經濟和債務問題的科幻小說是否會在未來的英語區科幻小說中占據更重要的地位?我認為現在要對此作出判斷還為時過早,但我個人對這個話題興趣日增,一直在尋找答案。一場關于經濟學和科幻小說的對話已經開始,并且也許將是下一個十年的潮流之一。
結 語
總的來說,重要的是科幻小說能改變我們的文化,以及我們的思維方式;它能幫助我們預測新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并最終付諸行動。在我看來,比起僅僅是為最新的技術或裝置提供靈感,像這樣培育新的思維方式要更為重要。科幻小說的力量一直在于激發我們對于社會的想象。
在結束之前,我應該指出,對當下的英語區科幻小說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我在上面重點介紹的這些書籍、作者、主題和軌跡。我相信這些代表了在未來將會持續下去的最重要的趨勢,也反映出了對科幻小說研究者來說什么是最令人興奮的,為什么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寫科幻題材。我認為這里的觀眾們可能會對另一個最近的創新項目感興趣,那就是幾年前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推出的“象形文字”項目:該項目肇基于尼爾·斯蒂芬森的一篇文章,他呼吁科幻小說要在科學上“激發出偉大的壯舉”,編輯選集時有個特殊的導向,入選的故事必須對技術和未來是樂觀的,而不是悲觀的。我們看到,制造業和廣告業正越來越多地利用科幻圖像,其原因是類似的。還有的項目,比如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在洛杉磯建造超環高鐵(hyper loop)隧道的計劃、資助載人火星任務等等,進一步證明,許多技術精英已經把這種科幻式的想象當做了啟動研究的指南。
不過,現在的科幻小說與過去的也有相似之處——太空歌劇軍事冒險小說、與外星生物的星際戰爭故事、和下一次技術飛躍有關的偉大發明的故事……這些在英語區科幻小說中仍然持續存在。與紙質科幻相比,它們在媒體科幻——電影、電視,尤其是電子游戲——中更為常見,這或許表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科幻并不是單一的類型,而是多種多樣的,科幻有用來逃避現實的,也同樣有作為社會評論的。當然,我并不是說只有印刷本的科幻小說才至關重要——像《黑鏡》這樣的作品強有力地表明了今天這么多作家轉向科幻小說,以及科幻小說的讀者比過去大大增加的原因所在。《黑鏡》很好地讓人看到,技術塑造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現在已經變得廣泛普遍,不再局限于精英們的“極客”文化。
科幻小說,以印刷品的形式和更多其他的形式,正越來越多地被主流讀者所接受,其主題恰在當前人文學科的核心:環保主義、后人類主義、后石油峰期①指未來石油產量和消費量出現明顯下跌之后的時代。文化、機器人學等等。正值學術上對科幻的興趣轉向全球科幻想象問題之際,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許多來自中國的科幻作品正參與其中。我期待著進一步跟大家討論在我們科幻小說領域這些激動人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