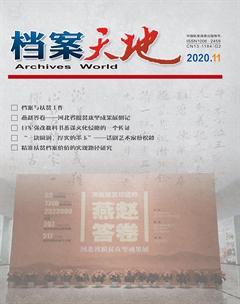“一塊圓潤、厚實的墨玉”
王祖遠
除戲劇界外,一般人都不大熟悉蔡松齡這個名字。然而,他所塑造的三個銀幕形象——影片《烈火中永生》中的華子良、《紅旗譜》中的嚴志和《戰洪圖》中的李老根,卻長久地留在人們記憶中。他,話劇園地里一位默默耕耘的園丁,熟悉他的人都交口稱贊他的人品、戲德和“老黃牛”精神,正如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劉厚生所說:“松齡同志的為人和成就很像一塊圓潤、厚實的墨玉,初看起來不起眼,普普通通,沒有耀目的光彩。但仔細端詳,反復琢磨,卻是璞玉渾金,價值連城……”
把心交給了黨
蔡松齡是安徽蕭縣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1935年22歲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考入南京國立戲劇學校,開始踏上藝術道路。戲校四年,他接受了系統的戲劇理論教育,開始在表演、導演方面展示才華;同時,他也受到了進步思想影響。特別是抗戰爆發以后,他隨全校師生組成“抗戰巡回演出團”,從南京遷長沙,又從長沙遷重慶,沿途所見所聞,使他開始懂得革命,也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
1938年,蔡松齡難忘的一年,他生活中發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他作為首屆畢業生,被留校任教,從此確定了終身從事戲劇事業。
第二件,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是10月的一天,他被悄悄帶到重慶上清寺一個菜場的地下室,由介紹人方琯德(后來成為北京人藝著名演員)主持,面對黨旗,同劉厚生、陳青、劉承清、鄧宛生等一起莊嚴宣誓,從此把一切交給了黨。
第三件,他與熱戀多年的姑娘張蕙楨結為終身伴侶。新婚之夜,她對他說:“我祝賀你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有人也介紹我入黨,你高興么?”他回答:“當然高興,那咱倆就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了。”她笑起來。原來,她早在一年前已在武漢入了黨,只不過現在才把真情說出來。蔡松齡驚愕良久,突然展開雙臂把妻子緊緊抱住,他覺得自己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生活中并不都是順境。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風云突變。國立戲校(此時已改名國立劇專)所在的四川江安縣也籠罩著白色恐怖,黨組織遭破壞,地下黨支部書記許綏曾(梅朵)不幸被捕,方琯德、鄧宛生等連夜撤離。蔡松齡夫婦因住處偏僻,來不及通知,等他們得知消息時,已無法離開。幸好他倆平時公開活動少,估計尚未暴露,便暫留學校觀察。幾個月后,教育部給國立劇專校長余上沅發來電報,要求查清蔡松齡活動情況,余上沅復電:“未查到任何活動,后當注意。”此事不了了之。蔡松齡夫婦就這樣隱蔽下來,但是,也從此和黨失去了聯系。
抗戰勝利,劇專遷回南京,此時蔡松齡已擔任學校高職科主任。他雖然還未找到黨組織,卻始終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當時南京正掀起“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學運高潮,蔡松齡暗中為支持進步學生的愛國行動做了許多工作。1947年他還同進步學生一起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并協助地下黨員做文藝界的情報調查工作。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我黨地下組織從敵人內部獲悉,準備逮捕的黑名單上有蔡松齡,馬上采取措施,將他全家送到上海暫避。隨后蔡松齡很快同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系,并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準備工作。為了解消除后顧之憂,他把兩個孩子送進上海教養院寄養,自己冒著風險去印傳單、貼標語。上海解放那天,他特地親手糊了幾面小紅旗,接出孩子,一家四口來到南京路上,擠在歡樂的人群中迎接解放大軍進入市區。
新中國成立前夕,蔡松齡應邀到北京,協助有關部門籌建最高戲劇學府——中央戲劇學院。他先后在表演系、導演系和院工會擔任領導職務,工作任勞任怨,待人謙恭平易,受到全院師生愛戴。為了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1957年,盡管蔡松齡已年逾不惑,依然報名參加蘇聯專家主持的導演師資進修班,和年輕人一起苦學苦練。他的結業證書上寫著這樣的評語:“蔡松齡具有很好的表演才能和演員氣質。以高度的專業水平扮演了弗拉斯·菲力培奇一角。”弗拉斯是蘇聯話劇《遠方》中一個難度較大的反面角色。蔡松齡把這個表面老實溫順、實質卑鄙奸詐的反社會主義莫羅勘教徒,刻畫得入木三分,受到同行們一致的稱贊。
1958年,蔡松齡奉調來到河北省話劇團。緊接著是三年困難時期,團里聽說北京來了位“大專家”,十分重視,特地給他配備了一名通訊員,生活方面也盡量優待。但蔡松齡謝絕了一切照顧,和普通演員一樣住低矮的平房,吃窩頭、白薯、熬白菜;下基層演出,團里安排他坐小車,他從來不坐,和大家一起蹚水爬山,而且總是搶著扛景片,干重活。遇有演員生病,他馬上頂替上臺,哪怕充當群眾角色,也是認真嚴肅,一絲不茍。團里同志對他十分敬佩,不久他就被推選出席了全國文教群英會。
1960年,河北省話劇院正式建院,蔡松齡被任命為院長兼導演。這一年10月,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又回到了黨的懷抱。劇院黨支部書記、副院長魯速同志不無遺憾地對蔡松齡說:“您1938年入黨的那一段,因劇專黨組織被敵人破壞后情況很復雜,目前還不能算黨齡,希望您能理解。”蔡松齡二話沒說,只問了一句:“什么時候舉行宣誓儀式?”
那以后,蔡松齡的藝術生涯進入了一段“黃金時期”。
探索話劇民族化
蔡松齡作為河北省話劇院導演,在話劇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他先后導演的十幾部戲,都貫穿了淳厚樸實、富有濃郁鄉土氣息的風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推《紅旗譜》。
《紅旗譜》是河北省話劇院第一個自創劇目,它反映了大革命時期河北大平原上農民的斗爭。蔡松齡讀完劇本,就深為它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所感染。他決心把這種民族化的風格特色在舞臺上體現出來。
對話劇民族化,蔡松齡早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時就有所思考。他認為中國話劇必須走民族化的道路,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繼承和借鑒我國民族的(包括民間的)文學傳統和藝術傳統,從中汲取營養,借鑒適于表現我們民族當代人思想感情的手段;尤其要大膽地吸收、運用傳統戲曲和民間藝術的表現方法,按時代特征,從編、導、演、舞臺美術及音樂諸多方面進行廣泛的探索。但他也指出,話劇民族化不等于戲曲化,不能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他的這些科學分析和求實的見解都運用到了話劇《紅旗譜》的排練中。
他首先同編劇一起研究、借鑒戲曲編劇中的“立主腦”“減頭緒”和“有戲則長,無戲則短”的特點,把《紅旗譜》的情節、場景和人物進行合理集中,大膽舍棄了初稿中“二師學潮”“濟南探監”等片段,集中筆墨表現以主人公朱老忠為首的革命農民同地主馮蘭池之間的矛盾沖突。排演開始前,蔡松齡兩次率領劇組到河北農村深入生活。在表演上他指導演員力求做到自然、合理、生活化。例如朱老忠會見祥奶奶時,搶前幾步撲通跪下;大貴被抓兵時,大貴娘被狗腿子李德才推倒,她順勢用“跪步”上前求情;朱老忠聽說運濤在北伐革命軍中當了連長,高興得打了個“飛腳”;朱老鞏面對惡霸馮蘭池,一氣之下用腳把長辮踢起纏繞在脖子上;以及一些演員的亮相、箭步、搶背、丁字步、抓手腕等,都把傳統表演形式同人物和劇情結合得緊湊、和諧,既富有民族風味,也使冀中人民“家家練功、人人習武”的地方特色和鄉土氣息濃重起來。另外,在借鑒戲曲和說唱藝術的語言方面,還學習了氣口、噴口、節奏、韻律;在舞美方面注意了民族形式、地方特色;在音樂、插曲方面,采用了民歌曲調。這些都收到很好的藝術效果。
通過《紅旗譜》的排練,顯示了蔡松齡深厚的藝術修養和善于從民族與人民生活中捕捉藝術養份的功力。長篇小說《紅旗譜》原作者——作家梁斌看了戲后說:“這戲那樣深刻地表現了鄉土風習、地方風光,有意保持了原著藝術風格,并在話劇民族化探索方面作出了成績,使我不由得拍案叫絕。”
戲劇家吳雪撰文說:“導演的處理有許多值得稱贊的地方。最精彩的要算‘護鐘辯理一場。朱老忠那雄壯的身段、鏗鏘的白口,真是聲勢奪人,有如拜山的天霸,卻一點不露痕跡。”
話劇《紅旗譜》連演300余場,到京、津、滬、寧、鄂、閩等地演出均獲好評,被譽為“具有中國氣魄的一出好戲”。它的成功,使蔡松齡在堅持話劇民族化的探索中更加堅定。他曾在《戲劇戰線》上寫道:“我們的民族傳統戲曲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有許多美學原則可與話劇通用。我們要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最新最美的話劇藝術,就必須向傳統藝術學習。只不過在具體做法上必須按話劇自己的形式、特點和規律,有發展、有創造地靈活運用。”
三個讓人難忘的藝術形象
1959年春天,正當話劇《紅旗譜》在天津演出時,崔嵬帶著剛組建的影片《紅旗譜》攝制組來天津“取經”。他對話劇演出的民族化特色深表嘆服,回京后即與凌子風導演商定,邀請蔡松齡和河北省話劇院另一位演員扮演影片中的嚴志和、朱老明。
蔡松齡到攝制組后,多次將他到冀中農村深入生活和在導演上如何保持民族風格與地方色彩的體會向同志們介紹,同時潛心鉆研嚴志和這個角色。曾有人這樣評論小說《紅旗譜》中的人物:“如果朱老忠是一匹闖蕩江湖、久經閱歷的駿馬,那么嚴志和就是一頭土生土長、從未離開過家鄉沃土的耕牛。”這段話使蔡松齡懂得了自己所飾角色的份量。他重讀小說,翻閱深入生活時的大量手記,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牢牢把握住嚴志和忍氣吞聲、懦弱怕事和“碌碡壓不出個屁來”的基本特色。影片拍出后,大家都認為嚴志和的形象創造十分成功,他的性格特點甚至體現在一行一坐及眼神顧盼之中。譬如“賣寶地”一場,嚴志和強抑胸中憤懣,步履蹣跚地來到已經賣掉的三畝寶地前,隨著一聲“爹,我對不起你呀!”一頭撲倒在地,雙手捧起那油黑的泥土,顫抖地送到嘴邊吮吸著,如癡似呆,悲淚盈眶。蔡松齡用這樣幾個簡潔而極富表現力的動作,把嚴志和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的絕望心境,表現得淋漓盡致。
1962年,老導演水華又請蔡松齡在影片《在烈火中永生》中飾演華子良。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重要角色,蔡松齡再一次在銀幕上展放異彩。他把自己解放前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暗中營救被捕共產黨員梅朵,以及在敵人監視下苦度日月的生活經驗都運用到表演上。那在獄中特務盯梢下,巧妙地把江姐試探的紙團掃進簸箕;在地下室對許云峰亮明身份時含淚擁抱的鏡頭,都十分準確地表現出這個表面上瘋癲癡呆,內心機敏沉著,在殘酷惡劣的逆境中進行著特殊斗爭的黨的地下工作者的精神風貌,表演得非常含蓄、深邃,感人至深。著名電影評論家鐘惦棐曾這樣評論說:“影片最為雋永的人物卻是一言不發的華子良。他的一些鏡頭使我們永遠記住扮演這個角色的演員蔡松齡,并為他生前沒有機會在銀幕上為我們留下更多的印記感到遺憾!可不可以有一部片子,從華子良的默不作聲,從他不停的跑步,從他兩只腳的變化并透過這兩只腳和兩只經常瞇縫著的眼睛,看江姐和許云峰?通過他的送飯和挑擔帶出《紅巖》?”
蔡松齡為我們留下的最后一個藝術形象,是影片《戰洪圖》中的李老根。這部影片是根據河北省話劇院同名話劇改編的,蔡松齡在排演原話劇時擔任藝術指導兼演張縣長一角。拍影片時,導演蘇里看中了蔡松齡淳厚樸素的氣質,邀他飾演貧協(下轉20頁)(上接27頁)主席李老根。
李老根的戲并不多,但蔡松齡卻把這個農村老黨員演得很有深度,而且區別于他以往飾演的老農形象,這是很不容易的。“開支委會”一場戲,支書與大隊長在激烈地爭論,李老根默默無言,只咂巴著小煙袋坐在一旁思考,但通過鏡頭中他那緊鎖的雙眉和凝重的目光,便使人看出,他早已卷入到這場事關重大的“分洪”爭論中來。接著他慢悠悠地向大隊長劉大勇說:“你說‘兵來將擋,水來土屯,那水漲一尺呢?”大勇說:“我埝高一丈!”老根問:“那水漲一丈呢?”大勇說:“我埝高十丈!”老根又問:“水漲十丈呢?”大勇笑道:“哪會有那么大水?”“有!”支書丁震洪接著介紹了水勢兇猛的情況。這段戲蔡松齡沒有多少手勢和形體變化,但憑著炯炯有神的雙眼就把這個“小”角色演得深沉內向,很有份量。
遺憾的是,蔡松齡沒能繼續施展才華。1974年重拍《戰洪圖》影片時,他的肝病已很嚴重,可他藏起病假條堅持把所有鏡頭拍完,回到北京便住進醫院,再也沒有出來。
在為蔡松齡舉行的追悼會上,影劇界的朋友來了很多,崔嵬、水華、歐陽山尊、凌子風、石羽、汪洋、黃宗江、方琯德、謝添、舒強、胡可……特別是正在生病的曹禺也扶杖趕來,哀情難抑地說:“松齡是我最好的學生,我不能不來!”
蔡松齡,“一塊圓潤、厚實的墨玉”,無論戲劇界還是廣大觀眾,都會永遠記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