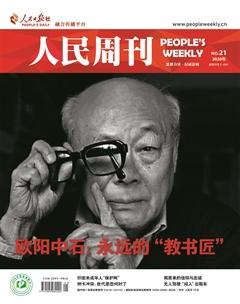數字文化研究的開放視野與問題意識
楊國斌教授現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和社會學系Grace Lee Boggs傳播學和社會學講座教授、數字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研究重點是數字媒體和社會理論、社會運動、在線行動主義、全球傳播、環境行動主義、文化社會學以及中國的媒體和政治。
數字文化與社會:
開放的領域與理論視野
徐桂權:您在《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7期發表的《轉向數字文化研究》中談到“新媒體”這個概念存在問題:“新”與“舊”對立,“媒體”概念也過窄。那么您認為“數字媒介”的概念如何?是不是比“新媒體”更加準確?
楊國斌:概念沒有哪個好哪個壞。概念只是個工具,只要大家有個大致共識就可以使用。但是很多概念沒有共識,比如“新媒體”的概念,國外早就在討論這個概念是不是有問題,因為新是相對舊而言的,但新的媒體很快就會變舊。10年前的新媒體還算新嗎?20年前的呢?另外國內講“新媒體”,通常想到的是新的“媒體”,比如新聞媒體。但是“媒介”的概念更加廣泛,比如U盤、軟件,都屬于“媒介”。所以,用“數字媒介”或“數字文化”的概念也許會拓寬研究的范圍。就“數字文化研究”來說,它包括兩個意思:一方面指關于“數字文化”的研究,包括關于互聯網、社交媒體、智能手機等新技術文化的研究,范圍很廣;另一方面“數字文化研究”也是關于數字的“文化研究”,即運用“文化”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數字文化。“數字媒介”或“數字文化”的概念都只是個工具,并不特別重要,只要大家有共識就可以。
徐桂權:談到數字媒介,現在傳播學界興起了一股媒介理論的熱潮,從媒介環境學、媒介學、媒介化研究到媒介地理學、媒介考古學。您認為數字媒介或數字文化研究需要怎樣的理論觀照?
楊國斌:說到這個問題,我的第一反應是:對理論要保持警惕。理論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常常有一種對理論的崇拜,這是很危險的。我在2018年ICA的主題發言里談過這個話題。從前理論沒現在這么熱,比如文學研究講究作品的欣賞和深度,歷史學要會講故事。當然不是沒有理論,但好的理論,如同神龍見首不見尾,蘊含在內,而不必像招牌一樣掛在門前。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的思潮,包括福柯、阿爾都塞等人的一大批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理論,對學界的影響特別大。理論研究成為顯學,叫作“high theory”,看誰能把文章寫得更抽象、更難懂,誰就顯得更深奧、更博學。
但是經過1968年學運之后,有一些學者開始反思理論的弊端。英國的新馬克思主義者E.P.湯普森有一本書,叫作《理論的貧困》,談過這個問題。法國的學者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也做過深刻反省。他們開始看到,很多理論,雖說對社會現象作了分析和批判,但實際上對改變社會不平等毫無用處,其主要用處是某些理論家建立權威的文化資本,實際作用是對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我做紅衛兵研究的時候發現,紅衛兵的暴力也都是打著理論的旗號,那時候有些年輕人都夢想做理論家。但是理論上非常美好的圖景,一旦脫離歷史環境,盲目地付諸行動,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總之,理論可以指導行動,也可以產生危害。理論是一種象征資本、文化資本,不能盲目崇拜。所以近些年我常說,不如先把現象、故事講清楚,再來上升到理論。這也受到現在學術體制的影響,學術期刊要求上來就談理論。對這種理論的潮流,我覺得還是要保持冷靜的頭腦。
但做研究也不能沒有理論。無論研究文化、社會還是媒介,特別要有一種歷史觀。比如現在有人說互聯網不能促進民主和公民參與,十年前大家對互聯網的看法太過樂觀。這就是沒有歷史觀的表現。我們要分析為什么十年前大家認為互聯網可以促進公民參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是什么,現在互聯網發生了什么變化,受到了什么限制。一切都是在變動中,我們研究一個東西一定看它是怎么變過來的。所以這些年我講得比較多的話題就是互聯網的歷史觀。以歷史的眼光來研究互聯網,就是一種理論旨趣。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早些年也說過傳播學研究缺少歷史觀。大家追逐時髦的題目的時候,就沒有工夫深究歷史,所以說到理論觀照,我認為需要有一種歷史觀。
學術心路歷程:
以“文化”作為問題意識
徐桂權:請您談談您的學術經歷吧。您早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獲得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后,又到美國紐約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完成了關于紅衛兵運動的博士論文。為什么會有這個學術轉向?
楊國斌:我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時候做《文心雕龍》的翻譯研究。那時候在精神上,長時期想象著劉勰時代的文學和生活。后來嘛,對中國的現實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關心中國的現代化、現代性問題。當時卡爾霍恩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給研究生講批判社會學理論的課。后來做完《文心雕龍》英譯的博士論文,看著周圍的朋友都出國深造去了,我也就又隨他去美國讀了社會學博士。他是做社會學理論的,我當時也想做理論,因為原來研究比較文學和翻譯理論,有不少相通之處。不過美國社會學的博士論文,極少純粹做理論的,需要做實證研究。我的社會學博士論文,選了文化和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路徑,研究紅衛兵運動和“文革”社會學。
但我沒有放棄文學研究,文學理論可以彌補社會學理論的不足。這種理論興趣一直貫穿下來。我有意識地想要做些跨界研究,不愿被學科的界限所束縛,想努力打破一些界限。我后來做社會運動研究的時候,用風格、情感等概念,是從文學研究來的。所以從文學到社會學,不能說是一個徹底的學術轉向,有些東西是一以貫之的。
徐桂權:您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頭銜前面冠了Grace Lee Boggs(陳玉平)的名字,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名字?
楊國斌:這個名字是我自己選的。安納伯格傳播學院講座教授的冠名可以自己選。你看看美國大學的冠名教授,很少冠華裔的名字,所以我在考慮冠名的時候,希望選一位杰出的華裔人物。Grace Lee Boggs是華裔,父母是廣東臺山人,辛亥革命那年移民到美國,Grace本人1915年出生于羅德島的州府Providence,2015年過世,享年百歲。她畢生從事民權運動,是底特律市民運動的領袖,在20世紀美國民權運動歷史上影響很大。她還是社會運動理論家,出了很多書。與丈夫James Boggs早年都信奉馬克思主義,1967年底特律黑人暴動后,她開始反思革命運動,提出了漸進式革命的新理論。她本科畢業于我曾經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女子學院巴納德學院,后來在費城的布林莫爾女子學院讀哲學博士,論文是研究米德的實用主義哲學。所以不論是種族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傾向,還是在學術淵源上,各方面我都很認同。同事和學生知道我的選擇之后,也都覺得很恰當,符合我的學術理念。后來我們院方征得她的信托基金會的書面同意,就可以用了。
(本文節選自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新聞業年度觀察報告(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