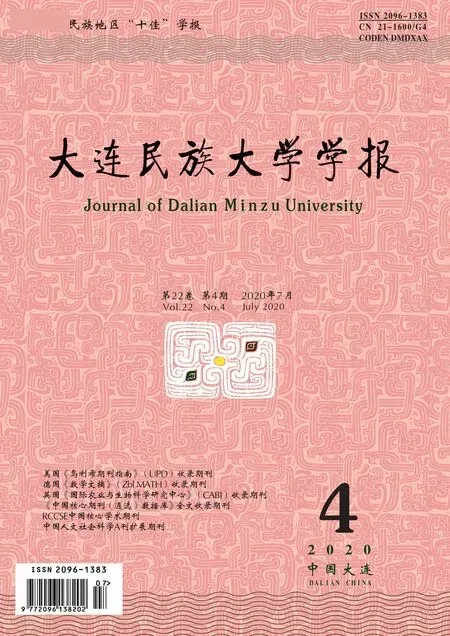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哲學基點
白 屯,張利國,徐麗曼
(大連民族大學 a.馬克思主義學院;b.經濟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605)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不同場合多次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大家庭等概念,逐步形成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視野研究、解讀這些思想,對于貫徹落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基礎與派生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派生的產物,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變化和發展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變化和發展。
1.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和客觀來源
人類社會生活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是物質生活的過程,一是精神生活的過程。物質生活過程是基礎,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方面。作為社會存在的重要表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內涵。社會的精神生活,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受社會的物質生活組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決定,后者是前者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同志深刻論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及以此為根基的精神文化。他指出,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各民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我們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歷史的長河中,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樸、崇禮親仁,草原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健,海洋文明的海納百川、敢拼會贏,源源不斷注入中華民族的特質和稟賦,共同鑄就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1]。中華民族共同體展現在其疆域、歷史、文化和精神上的具體表現及其客觀存在和永恒發展,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客觀基礎、豐富內涵及其變化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立足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物質基礎,其內容和性質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容和性質所決定,其變化發展由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變化發展所決定和引領。
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方面,是其派生物和表現
作為社會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社會物質生活即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派生物和表現。因為社會意識不過是社會物質生活過程的觀念表現,即意識到了社會存在[2]199。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第一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第二性的,是由前者派生而來的。因此,習近平同志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1]。這段論述生動詮釋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互關系,厘清了兩者之間的淵源關系、地位關系和基本屬性。在這個意義上,德國哲學家黑勒(Hermann Heller)甚至認為,人的社會存在整體上決定其意識更多一些,而不是相反[3]53。沒有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共同開拓的富饒遼闊的祖國疆土,沒有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和偉大夢想精神,就沒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產生和存在。
3.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變化和發展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變化和發展
習近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從多個角度表現了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容和特征。一方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變化和發展,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變化和發展。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在經濟、文化、歷史,以及民族關系、情感交流、追求團結統一的行動和信念,不斷鑄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進步和發展。從“茶馬互市”“馬絹交易”中馬匹、茶葉、織物等的各取所需所建立起來的各民族間經濟上的交流和相互依存;從中原文化向周邊輻射和傳遞,如儒學思想的傳播、漢字的使用,以及各民族文化不斷進入中原,如桌椅的使用、飲食中的火鍋、黃瓜等所搭建起來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的歷史;從三國時期諸葛亮對少數民族推心撫慰、唐代文成公主入藏,都極大程度拉近了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從中國歷朝歷代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堅持不懈地追求天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的精神指向等等都雄辯地證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不斷變化發展,推動了華夏兒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各民族間經濟聯系、文化交往、歷史淵源、民族情感意識的不斷進步。
另一方面,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表現了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容和特征。新中國成立70年多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這種歷史性巨變引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走向新時代,產生了習近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推動了黨的民族理論政策在新時代的新發展,成為新時代全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凝聚共識、反對分裂新的理論武裝。
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間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基本關系,對于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想和觀點,特別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存在與意識關系理論、抵御和克服現代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經指出過這一點,他在回顧20世紀60到7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經歷的大量有關事實后總結說,越來越多的“馬克思主義者”從馬克思主義中去除了勞動價值論和利潤下降理論,他們拒絕了“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的命題[4]。
二、反映、能動性與正能量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深度廣度上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表現了社會意識的能動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充分彰顯社會意識的正能量。
1.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理論深度和視野廣度上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作用的程度決定于它所反映的社會存在的深度和廣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蘊含的基本內容和性質,比如其內聚性、包容性、開放性等,則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品格和秉性,從而展現了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基本關系的重要方面。
對此,黑勒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他認為,民族具有自然和社會文化雙重屬性。民族首先是一個“具有自然的共同點”的共同體。他說人類結為一體的最堅實和持久的紐帶,不是組織化的、目的取向的利益結合,而是具有生物器官上的、自然內在的根源。最重要的自然結合,即無需人類的刻意舉動便可完成進而區別于其他人群的結合,是血緣和地理,出身和國別。這兩個方面構成民族的自然基礎[3]70。黑勒還指出,民族的文化共同體則表現了一個民族共同的文化財富。他認為,通過共同的命運,不同的血緣共同體融進一個民族中,即使地理經歷著滄海桑田,共同的命運仍然貫穿一個民族的始終[3]75。這段論述有力地證明,中華民族在歷史過程中的演化發展,既經歷了自然力量的作用,如血緣和地理環境,也經歷了各民族不斷交流、借鑒、學習、融合的過程,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而促成如此復雜、多樣、連續不斷變化的根本動力就是“共同的命運”。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所經歷的歷史上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的目標向往,讓不同民族的百姓自覺自愿地走到了一起,從而揭示了多民族融合發展的根本動力,也形成了具有相應內容和性質,以及內聚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特征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表現了社會意識的能動性作用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刻作用并影響中華各民族,展現了其在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相互作用中的能動性。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宏偉目標,深刻展現了先進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用的能動性。
習近平同志多次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動性作用的思想。比如他提出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出各族人民親如一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定要實現的根本保證;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作為基礎性事業抓緊抓好等觀點,表達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引領”“構建”“推動”的重要作用,也說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說明,當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把自己的感受和意識緊密且廣泛地融入到具體的生活和工作秩序中時,團結的共同體為其提供幫助和依靠,同時也喚醒他們對勞動的熱愛和責任意識[3]58。中華民族共同體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后者對前者每時每刻都起到重要的影響和反作用,發揮著其能動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為中國廣大百姓提供一個“廣泛的工作秩序”,這個“團結的共同體”為百姓提供幫助和依靠,同時也喚醒了百姓的勞動意識、責任意識。
3.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充分彰顯社會意識的正能量
習近平同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鑄牢”。一方面,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的促進中華民族大團結的行動綱領。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中央第一次提出,要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圍繞著這一思想,習近平同志多次講到要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講到要牢固樹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黨的十九大則站在新時代,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全黨的行動綱領,從而在描繪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的過程中,添加了重要的行動保障。
另一方面,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要動員全黨鼓足干勁,以更大的決心和更堅強的意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同志指出,把藍圖變為現實,是一場新的長征。面對新長征,他強調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在包括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五個方面采取行動,實現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5]。在總結中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的基本經驗時,習近平同志再次立足于社會意識的能動性和正能量的角度指出,黨中央把扶貧開發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使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進展。由此可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表達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復興的共同理想,表達了先進、正確、積極的社會意識,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優秀品格,而且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新時代黨中央的動員令。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充分肯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前提下,正確反映社會存在的那些先進思想、理論對社會存在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2]201。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將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存在和發展產生積極而巨大的作用,是保障中華民族共同體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三、偉大實踐的根本力量
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維系并推動著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互關系,成為兩者的紐帶及其發展的根本動力。
1.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根本動力
盡管實踐的概念并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首創,在他們之前包括中國的孔孟哲學在內的古代哲學家就開始自發地探討有關實踐活動的基本內容。而幾百年前,德國古典哲學家們,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等就已經自覺地對實踐的特性、作用等進行了探討,提出了實踐是實現目的性的活動、是具有主體性的活動、是能動的創造性的活動等觀點[6]。與前人的探討不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提出了實踐觀點,(1)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實踐觀點”與其前人提出的“實踐概念”具有本質的不同。參見高清海《哲學與主體自我意識》,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99頁。發現正是人類實踐最基本的活動——人的勞動,實現了人的“兩次提升”,即從自然界物種關系中的人與動物的關系提升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從人與人的關系中提升為人與社會的關系,建立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且辯證而有機的基本關系。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是勞動產生了人的分化,是以勞動為特色的人的能動性的創造性活動產生了世界,創造了世界[7]。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偉大實踐,他們世世代代辛勤勞動和創造,呈現于世界遼闊而美麗的疆土,豐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財富,以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為世界所震驚的“中國速度”——每一分鐘創造GDP1.57億元、每一分鐘“神威.太湖之光”運算750億億次、每一分鐘333萬元投入研究和試驗、每一分鐘生產汽車55輛、每一分鐘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46804G、每一分鐘網上商品零售1043萬元、每一分鐘快遞小哥收發7.6萬件快遞、每一分鐘移動支付金額3.79億元……[8]。所有這些說明,是人民創造歷史,勞動開創未來,勞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勞動造就了以中華民族偉大實踐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2.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動力
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實踐活動與人類認識的基本關系,闡明了“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的深刻道理[9]56,說明了“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預示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的認識過程,解釋了“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了”[10]。從而在不同的意識層面上為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實踐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指導。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基本規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主席就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到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10]292。習近平同志站在歷史的新高度,進一步闡發了這一思想,他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發揮歷史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和不變,永遠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搭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11]。從而深刻闡明了中華民族偉大實踐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而有機的聯系。
3.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是維系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紐帶和根本動力
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紐帶。馬克思指出了從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主要缺點,即一個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另一個卻發展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一方面,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馬克思認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且,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而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9]158。所以,是實踐讓人生存下來,是實踐發展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同時,馬克思還指出,從人類所從事的物質生產活動出發,產生了人類的意識,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9]151-152。唯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最終且永恒地把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緊緊地聯系起來。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關系的根本動力。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生活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9]419-420。這就是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伴隨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變化而變化,而引發這些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各民族人民在歷史上不斷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同時也不斷形成并加深了對這種相互關系的認識和理解,不斷豐富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以,正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維系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互關系,并最終推動著兩者關系不斷發展,走向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