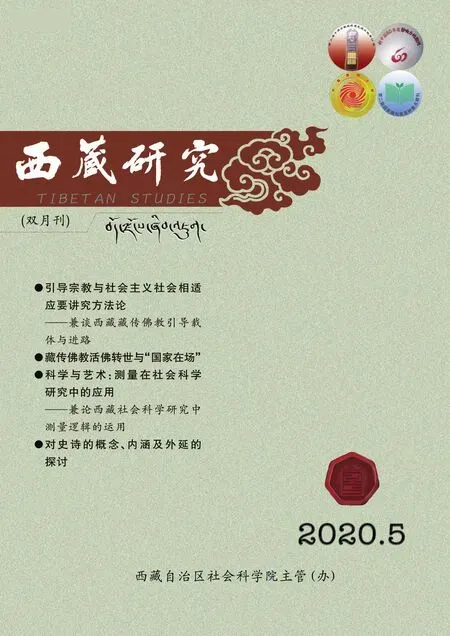論象征符號對藏傳佛教寺院的神圣性建構
廖云路
(西藏日報社,西藏 拉薩 850000)
作為藏傳佛教在社會中的載體,寺院是藏傳佛教實現其社會功能的重要載體。在寺院的時空環境下,藏傳佛教體現為一套象征符號體系。象征符號在人與神之間充當傳遞信息的媒介,不僅是寺院神圣性的所在,使藏傳佛教的實踐可觀察、可理解,還將宗教內化為社會秩序與行為規范。從象征符號分析藏傳佛教寺院神圣性的建構,為理解藏傳佛教之于社會的關系提供了一種視角。
一、象征符號視野下的藏傳佛教寺院
宗教之所以能從人們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中分離出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神圣世界,其特殊性集中體現在人與神之間的對話,為變化不羈的世俗世界提供終極意義。宗教“用其神圣的帷幕遮蓋住制度秩序的一切人造的特征”[1]11,宗教的神圣性是一種觀念的、抽象的存在,為使這種超現實的力量能夠介入到現實環境中并發揮其功能,神圣性又需要附著于實在的象征符號,于是便有了神靈、宗教場所、專職宗教人員等的出現。
符號分類有三個基本角度:一是從符號載體的屬性進行考察,二是從符號與所指對象的關系進行考察,三是從符號與解釋項的關系進行考察[2]。符號有類似語言的組織能力,從而拓展其使用的廣度和深度。象征符號是社會文化的可感知的表達機制,通過類比聯想的方式賦予事物規范、意義、價值,從而在社會關系模式中反映出社會集體情感意識、心理狀態、價值規范體系和文化現象。藏傳佛教寺院借助象征符號,指向一個神圣的領域。
從象征符號的分類上看,以符號自身與建構對象二分對立方式的符號象征體系可以劃分為語言符號、工具符號。語言符號是以具體的文字、聲音、圖像等為載體的符號體系。語言符號建立在參與者共同的認知圖式上,包含著解釋與理解的目的。在藏傳佛教寺院中,宗教器物從世俗之物轉換為神圣之物,離不開與之相關的神話、傳說、禁忌等語言符號的共同經驗積累;而宗教儀式通過彈奏、唱誦、蹦跳、涂抹甚至哭泣等方式,表達宗教教義的同時,起到了人與神之間情感的溝通作用。此時的語言符號是一種策略性行為,旨在強化神圣的主題。
工具符號是除了語言符號之外的意義表征符號體系。它不僅是表示一種事物的標識,還具有支配性的工具效力,能夠作用于發生關聯的個體或群體,使之呈現有關社會秩序的象征表述。在藏傳佛教寺院中,工具符號的介入使人與“神”之間的溝通方式更為豐富,讓不能直接被感知到的觀念、價值、情感等神圣世界變得可觀察、可理解。宗教活動參與者通過工具符號強化了宗教的社會價值,傳遞一種集體規范力量。
象征符號展現了藏傳佛教的宗教教義、宗教活動參與者的內心世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結構體系。作為認知圖景的基本構成元素,象征符號必須通過宗教實踐才能清晰地表達出來。按照楊慶堃對宗教的分類,藏傳佛教屬于制度性宗教,是有系統的教義、儀式和組織體系的信仰形式[3]。藏傳佛教自身無法表達,需要借助寺院這一載體。本文從藏傳佛教寺院中常見的神靈、供品和儀式等構成要素角度,揭示語言、工具符號是如何相輔相成建構起寺院的神圣性的,這套意義體系又是如何推動宗教的社會功能與現代社會環境相結合的?
二、神像的象征符號
神靈是寺院最為重要的資源,是寺院得以成為寺院的基礎。部分寺院甚至可以“有寺無僧”,但必須要有神靈這一象征符號,獨特的神靈往往是寺院神圣性地位的關鍵。“人類在宗教生活中,往往通過將一些特定物品人格化的方式,賦予這些物品以特殊的宗教意義。”[4]護法神是藏傳佛教寺院最重要的神靈之一,誕生之初原為保護該寺僧人能專心學經、寺宅平安,但由于其世間神靈的特征(1)藏傳佛教護法神分為出世間護法神和世間護法神。出世間護法神表示已經脫離輪回之苦,不再管理世間事物,屬于高等級神靈,如大威德金剛、吉祥天母等;與之相對的世間護法神則是還沒有脫離人世,需要不斷建立功德的護法神,如孜瑪護法、扎基拉姆等。在藏族信眾眼中,世間護法神往往比出世間護法神更為靈驗,有很多關于世間護法神附體到人身上的說法,被附身的人于是便有了神跡。,吸引了大量信眾的朝拜。幾乎每座藏傳佛教寺院都有護法神,護法神及其相關的象征符號構成了藏傳佛教寺院的獨特場域,給信眾以區別世俗社會的神圣感。
奧地利學者勒內·內貝斯基·沃杰科維茨曾對藏傳佛教中的護法神進行過細致描述。在容貌上,護法神的嘴因憤怒而齜牙咧嘴,嘴角突出長牙,往往上齒咬住下唇;雙眼凸出而血紅,透露出兇猛的神情,一些神靈在額頭上還有天眼;護法神的頭發蓬亂,上面結滿了污垢,有的將頭發扎成一種發髻,用珍珠、綠松石、龜殼等作裝飾。在著裝上,除少數護法神赤身裸體外,大部分都穿著獸皮或粗毛材料制成的衣物。例如,一些護法神的圍腰是用牦牛或禿鶩等的毛制作而成;許多護法神身著的披風是從馬等牲畜身上剝下的皮、內臟等材料制成,這些衣裝還會搭配絲帶、珍珠帶、金帶或綠松石帶子當腰帶。此外,護法神身上的飾品也十分多樣,胸前的項鏈由人骨或海螺、寶石等打磨而成,許多護法神帶有手鐲、腳鐲,通常是金、銀打制的。
以拉薩扎基寺的護法神扎基拉姆為例,該護法神頭戴人頭骷髏頭冠,吐著火紅舌頭,面目猙獰,還長著一雙雞腳,其外形的獨特性衍生了許多流傳于僧眾口中的語言符號。學者西尼崔臣在《拉薩扎其護法女神及其扎其寺》一文中引用過民間關于扎基拉姆由來的傳說:扎基拉姆原為清朝乾隆皇帝的妃子,年輕漂亮且富憐憫之心,但也引起了其他妃子的嫉妒,被打上莫須有的罪名關入監牢,并遭毒害。由于含冤而死,這位妃子化作厲鬼,時常在皇宮附近嚇人。乾隆皇帝不得不邀請色拉寺吉扎倉堪布強巴敏朗大師到北京舉行酬補儀軌,以平息她心中的怨恨。最終女鬼被降服,并跟著大師回到西藏,成為捍衛佛法的護法神[5]。
還有學者認為,強巴敏朗向皇帝迎請事畢后返藏途中,一位中原內地女神緊隨而來,并停留在了現在的札什寺(指扎基寺)地方,這位女神就是后來的扎基拉姆,“神靈的形象逐漸被藏地化后發生了改變,雞腳可能就是在這一過程中所形成”[6]。由于扎基拉姆的身份由來指向內地,因而又被視為藏漢文化交流的產物,并逐漸代替原來關帝廟的地位,留下了求財非常靈驗的名聲,“每天向她敬酒向她朝拜的人群一直絡繹不斷”[7]。
扎基拉姆來歷的一種版本流傳開后,不同人又根據自己的理解逐漸演化出多個版本,但每一種版本都基本能構成完整的邏輯鏈條,因而也廣泛被僧俗所接受。對于宗教神話、傳說而言,大都難有確實的文字記載,或者說一種確實記載的意義并不大。語言符號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反而增加了神靈的神秘感,成為依附于神靈這一實體之上的文化資源,更能吸引信眾對于神靈的興趣與向往。
寺院既是一個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場所,又是諸神的居所。神之所以為神,在于神圣與世俗間的區隔,“神圣之物是世俗之物不應該也不可能接觸之物,否則必遭懲罰。”[8]寺院通常將神靈置于位置較高的櫥窗中,神靈的目光要高于人的目光。櫥窗是封閉的,一是可以與信眾拉開距離,樹立神靈的神圣性;二是避免神靈被風燭蠶食,保持神靈清潔的同時,便于寺院管理;三是可以在櫥窗里擺放花束等供品,進一步美化神靈。
扎基寺對扎基拉姆作為工具符號的展示卻有所不同。扎基拉姆被單獨供奉在一個開放式的櫥窗里,櫥窗一次可以容納一位信眾進入。扎基拉姆被供奉在桌子上,底座與人的肩部平行,整個佛身則稍高于人的身高。信眾朝拜方式通常是掀起神靈衣服一角,用額頭輕貼神靈的底座,觸摸她的雞腳,同時雙手合十,嘴里念經或許愿。部分信眾還自帶手表、項鏈等小物件在扎基拉姆的軀干部位摩擦,以獲得開光的象征意義。
直觀的宗教體驗是增強信眾宗教委身和信心的重要方式。與扎基拉姆相似,拉薩丹杰林寺的護法神紅面獄卒被供奉在半開放式的櫥窗里,以更加直觀地向信眾展示。紅面獄卒的櫥窗里接出來一根類似于辮子般粗細的繩子,是信眾與神靈交流的工具符號。信眾通常將額頭輕觸在繩子上,開始念經并祈禱;在信眾較少時,還會用繩子在全身“涂抹”一遍,這種更加徹底和深層次的加持方式被認為可以消除人體身上的痛楚。
扎基拉姆、紅面獄卒都是藏傳佛教中著名的世間護法神。從宗教神圣性本身包含的人性異化角度看,世間護法神自然要更多地承擔起人與神之間的交流,神靈作為工具符號的角色凸顯。信眾不會認為觸摸護法神是一種不尊重,甚至降低其神圣性,反而將這種朝拜禮儀視為神對人的加持與關懷,一旦追求的回報實現,會更加歸因于“靈驗”。允許觸摸但不表示沒有禁忌,如觸摸神靈臉部肯定是不可以的,也不允許信眾對僧人、神靈拍照。當然,這些禁忌不可能完全落于紙上,只能依靠工具符號使用中的成規加以約束。
三、朵瑪供品的象征符號
藏傳佛教供品是用來討好神靈的。寺院中最常見的供品是朵瑪——一種用糌粑、酥油和水捏起來的面團,上面貼著酥油花制成的法輪、花瓣樣式的裝飾。根據儀式和供奉神靈的不同,朵瑪的形狀、顏色、大小規格也有所差異。“西藏有很多的文獻記載有關朵瑪供品的情況,有的文獻詳細地記載了朵瑪的制作過程,說朵瑪至少有一百零八個品種。有的朵瑪,僅有幾英寸高,有的則高達十英尺。例如一種叫做護地神朵瑪的朵瑪就是巨型供糕。”[9]419朵瑪也可用作替換物品或伏魔術中使用的物品,在儀式結束之后就要拋棄或者供牲畜食用。
“儀式與暴力、毀滅和尋找替罪羊,密切相關。特別是,它們富有戲劇性。”[10]供品通常不會單獨供奉,與朵瑪同時供奉的還有清水、干花、藏香、大米、青稞和餅干等。當幾種朵瑪供品組合在一起時,供奉時有何講究、有怎樣的情節和故事、背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則基于語言符號對其神圣性的建構。
在一種名為“百供驅魔”的供品中,僧人首先制作了小型錐形朵瑪,一部分朵瑪分別涂上綠色和藍色的礦物顏料,另一部分未染色的朵瑪則是他們的食物。這些朵瑪被圍成四方形,僧人再在中間的地方用糌粑制作了人偶和魔鬼,人偶前面還有一盞糌粑捏成的酥油燈。這個供品的寓意是驅魔,僧人念經之后,將糌粑做成的酥油燈點燃,魔鬼就把信眾替身的人偶吃掉,保佑信眾平安。
西藏有很多的驅鬼儀式也用人的模擬像。“假如有某個妖魔威脅某人、某家族或某部落的安全,人們便有舉行特殊的打鬼儀式,制成模擬像。這樣,所有威脅個人和家族的鬼怪和瘟病都附在人們制作的模擬像身體上,人們便可以安然無恙。”[9]433朵瑪的制作精細而耗時,僧人有時制作一個模擬人偶需要捏出眼睛、頭發和嘴巴,細節的地方還用刻刀,用小木片固定住人物的身體和頭部,并用礦物顏料對細節之處染色。
除了人偶外,僧人們還制作須彌山,須彌山是糌粑壘起來的四方形基座,通常是四層,代表世界;有時制作大象、馬等動物,大象在藏族看來是吉祥的動物,常見于壁畫中,而馬則代表人的牲畜,并有保衛和作戰的意思。一些難以用糌粑捏制寓意,則可以用畫在紙上的語言符號來表達。例如,“姜普”是一種插在糌粑上的扁平木條,木條前面貼著一張紙,上面繪有男人、女人的素描,用來代替某個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成員。一種十字網格的供品名叫“垛”,基本形式是用兩根細木棍綁扎成十字架,從十字的中心向外纏繞彩色毛線,制作完成后的樣子像一張蜘蛛網。“垛”代表著神靈的棲息地,通常插在須彌山上,有時還要加上一把幡蓋,在整個供品營造的故事中,是驅邪降魔的關鍵法器。
“五官供品”的制作比普通的朵瑪更為復雜。五官供品與人的五大器官相對應:一個撕裂的心臟代表覺識或觸覺,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代表視覺,伸長的舌頭代表味覺,隆起的一對鼻孔代表嗅覺,一對寬大的耳朵代表聽覺。五官供品比一般的朵瑪體積更大,制作更加精美,同一類型的五官供品可能有幾種相近的造型。為了凸顯五官的特征,上面還涂著礦物顏料調制而成的幾種色彩。五官供品代表人們尋求來世的意識,“五官及其相應的五覺是‘門’,通過這道‘門’,尋求再生的意識最終感受到了這個世界。”[11]
朵瑪供品具有通靈的媒介、獻祭的禮品、驅魔的道具等功能,沒有這些供品在場,僧人念經的作用和意義就無法實現。朵瑪制作與展示的過程,也是供品作為工具符號介入人與神關系的過程,符號的意指功能與宗教參與主體發生了關聯。
在前一天念經儀式結束后,寺院僧人會根據第二天要念誦的經文,制作相應的朵瑪供品。制作過程通常就在佛殿之中,并不避諱信眾在場,因而又具備了儀式的表演性。當信眾見到供品的制作時,通常會低頭念經,并對僧人和寺院布施。這既是出于對僧人勞動的敬畏,又是對因供品建立起的藏傳佛教與信眾身份關系的確認與強化。
制作完成的朵瑪供品被供奉在寺院神靈之前,通常用一張單獨的藏桌陳放。供品的陳列與僧人的念經,共同指向供品背后的宗教功能,供品也因此作為工具符號聯系著信眾與宗教所營造的神圣世界。在念經儀式結束后,僧人將部分供品切成小塊放在一個托盤里,信眾會像吃餅干似的捏一塊品嘗,年齡稍大的信眾還會拿一塊帶回家中,認為會帶來好運,由此又延伸了宗教對價值觀念與社會規范的影響。
藏傳佛教寺院中的朵瑪供品大都講述著神靈、魔鬼與信眾之間的關系,故事神秘而又難以用語言表達。按照儀軌,這些供品中還要用到替魔人的一些指甲或毛發等,最好用那人洗過身體的水來和制糌粑,以此治療人們因祟于妖魔而得的疾病[9]433。在藏傳佛教與現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背景下,這些儀軌都被較大程度地簡化和省略了。然而,在寺院供品制作和供品展示的過程中,依然保留了大量有別于世俗之物的一面,這既是神圣性確立的過程,又是幫助信眾認識宗教和加深信仰的方式之一。
四、宗教儀式中的象征符號
彼得·貝格爾從功能角度揭示宗教的本質時認為,宗教活動就是建立一種神圣的秩序,而一切的秩序化都具有某種神圣的特征。“它的神圣性要通過種種儀式,才能象征性地得到重新肯定。一旦失去了這種特性,它就成為世俗的了。”[1]6宗教與儀式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儀式構成了宗教的基本特征,宗教以儀式的方式得以實踐。在藏傳佛教寺院中,語言、工具象征符號共同支撐了宗教儀式展演進程。
藏傳佛教寺院通常依據藏歷安排日常性儀式,儀式的時間與內容是固定的,由本寺僧人完成。念誦的經文有多個音調和語速,時而語速輕快、時而渾厚有力。根據經文內容的需要,僧人們各自分工負責擊鼓、吹法號、敲鐃鈸、搖碰鈴等樂器。當誦經聲與樂器聲齊鳴時,寺院的氣氛莊嚴而震撼。
宗教儀式中的象征符號并非以僧人念經的語言符號為開始,儀式準備過程就包含了工具符號的介入。念經之前,每位僧人都要來到寺院正殿中央,面向供奉的神靈磕三個頭。藏傳佛教教義認為,磕頭的目的是洗清世俗世界中的貪、嗔、癡、慢、妒“五毒”,以求接近于佛的功德。僧人念經時身穿紅色袈裟、頭戴千佛冠帽。僧人磕頭后,起身整理好僧服,坐到固定的位置上,靠近主供佛位置由年齡最大的僧人和領經師就座,年輕的僧人坐在最外面。這些工具符號都是從世俗世界向神圣世界轉換的準備。
當語言、工具符號有機結合為一體時,宗教儀式被推向高潮。空行母是薈供法事的一種,每位僧人的眉心涂上紅橙色朱砂,念經的形式從快速朗讀變成誦唱,稱為薈供歌。幾名僧人從卡墊上起身來到正殿中央,面向佛像和其他就座的僧人領唱薈供歌,其他僧人們跟著音調附和。儀式過程中,站在正殿中央的僧人手持供品和用木碗盛著的經過加持的圣水,依次走到就座的僧人面前,每位僧人從碗中蘸取圣水,再灑向空中。這一儀軌完成后,僧人們再順時針繞著佛殿轉,最后將供品和器物供奉在寺院主供佛前。
在藏傳佛教重大節日和寺院傳統的重要時間節點時,寺院還會舉行展佛、講經、火供等宗教儀式。寺院的開放性通常吸引信眾的參與,由此形成僧俗共享的儀式。宗教儀式規模的擴大與儀軌的復雜性,促使象征符號使用的豐富性。
以這類儀式中常見的講經為例,講經原本由德高望重的經師向僧人傳授為僧之道,而廣大信眾也把講經視為面見高僧和提高自身修行的機會。儀式的第一個環節通常為僧眾集體念經,儀軌中由僧人帶頭領誦和吹奏樂器,以信眾熟悉的經文進入主題的方式容易引起廣泛的參與。寺院的氛圍由于念經而變得莊嚴肅穆,調動起經師講經與信眾聽經的積極性,當念經聲停下時,僧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經師身上。
講經儀式以闡釋《入菩薩行論》《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典籍為主,經師根據經文的內容,引用著名高僧大德的名言,再結合僧眾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加以說明。這類語言符號包含著一種理解的目的,而該目的的基礎在于儀式參與者共享的認知圖式。由于大部分僧眾對經文的理解多停留在記憶與背誦,講經將深奧的宗教教義轉換為僧眾可理解的語言符號,有利于引導僧眾思考,在發心起念上遵循教義,喚起僧眾群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在講經儀式中,宗教需要借助工具符號加以固定和強化。工具符號的參與不僅引出情感表達或刺激了欲望,還在參與者互動的過程中實現了宗教價值規范的遵循、完善以及再生產。講經儀式通常持續數日,寺院需要提前裝飾場地、準備茶水和調適音響設施等,這些工作由僧人和信眾共同完成,日常宗教禁忌在勞動過程中被打破。寺院布置上的變化又營造了一個有別于日常性宗教儀式的神圣時空環境,再加上日常性宗教儀式中很少使用的寶座、樂器、僧服等,集中凸顯了講經儀式的神圣性與權威性。
工具符號的介入增加了宗教儀式的表演色彩,其形成的感染力加深了信眾對宗教的信任與委身。“他們堅信通過寺院里舉行的各種宗教儀式,可以洗滌他們身上沾污的前世或現世中的各種罪孽,培育宗教倫理道德種子,為來世有個好報打下行善積德的基礎。”[12]在講經儀式中,工具符號的使用頻率、使用范圍、使用方式的多樣性等,與信眾的虔誠表現呈正相關關系。當僧人身著宗教禮服、奏響宗教樂器、向信眾供茶時,信眾的宗教體驗被激起,更自然地做出磕長頭、雙手合十、向寺院布施等行為。這些行為會在僧人與信眾、信眾與信眾之間相互傳染,由此內化為宗教之于社會的行為規范。
無論是講經中的語言符號,還是作為工具符號的供品、法器和參與者的行動,象征符號讓宗教儀式發生在特定的時空中,并成為神圣意義和宗教經驗產生的催化劑。雖然象征符號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斷重復的,但重復不等于無效,其意義不僅在于通過儀式化的手段加強神圣性,還能促進信眾形成集體記憶,增強對宗教解釋的信心。
五、結語
藏傳佛教之所以成為制度性宗教,離不開一套完整的象征符號體系。藏傳佛教自身無法表達神圣性,必須要借助象征符號在寺院的實踐。象征符號在人與神之間充當傳遞信息的媒介,使藏傳佛教可觀察、可理解,也使得寺院空間明顯有別于世俗空間。
從對神像、朵瑪供品和宗教儀式中的象征符號分析來看,語言符號大都講述著神靈、魔鬼,以及宗教教義與信眾之間的關系,具有很強的敘事性。這些敘事神秘而又難以理解,但恰好是區別于一般世俗語言的神圣性所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符號經過社會再生產,關于神像、朵瑪供品、宗教儀式等載體敘事變得多樣與豐富,成為附著在寺院之中的文化資源,更加吸引信眾對于宗教的興趣與向往。工具符號以宗教載體在寺院中的“自我呈現”,介入到人與神關系的過程,這種更為直觀的宗教體驗是增強信眾宗教委身和信心的重要方式。從朵瑪供品的制作中可以看出,在藏傳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過程中,寺院中的部分儀軌已較大程度地簡化,工具符號的呈現方式也隨之簡略,但符號強大的意指功能依然可以傳達神對人的神圣性影響。在宗教儀式中,語言符號充實了工具符號的內涵,工具符號加深了語言符號的表達效果,兩者的有機結合將宗教儀式推向高潮,宗教的神圣意義和信眾的宗教情感共同達到頂點。
人與神關系不是單向建構的,信眾通過神像、朵瑪供品和宗教儀式中的象征符號滿足宗教需求的同時,也實現了宗教價值的遵循、完善以及再生產。象征符號還具有很強的效仿性,通過在僧人與信眾、信眾與信眾之間相互傳遞,內化為宗教之于社會的行為規范,而寺院也會根據象征符號的傳播效果,適時調整宗教載體的神圣性表達。
總之,藏傳佛教建立在神圣性與世俗性二分關系的基礎上,而象征符號使神圣性處于既敞開又遮蔽的狀態中。作為藏傳佛教實體的寺院,過于敞開神圣性會使其與世俗的界限模糊,喪失宗教的社會功能;過于遮蔽神圣性也容易造成宗教理性化的缺失,與現代社會發展不適應。從象征符號分析藏傳佛教寺院神圣性的建構,為理解藏傳佛教之于社會的關系提供了一種視角;從“以言行事”的角度而言,象征符號又是一種行為,通過象征符號的調適與變遷,亦是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