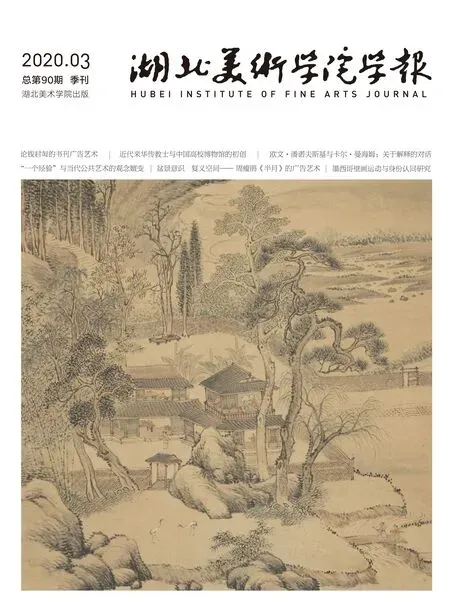中國現代文壇中的“廣告魅影”
——以20世紀20年代文壇的三次論爭為例
湖南師范大學 | 彭林祥
晚清以來,文化市場(出版市場)得以初步形成,文學作品作為商品已成為共識,為文學作品促銷的廣告也應運而生。1917 年拉開的“文學革命”,推動了現代文學的誕生。這種新型的文學自然離不開已經形成的文化市場(出版市場),現代文學的傳播自然離不開廣告的參與。現代文學于是在廣而告之的吆喝中拉開了帷幕,廣告也因此參與和見證了現代文學發生、發展,是現代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現代文學三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各種論爭可謂連綿不絕,幾乎所有的現代作家都曾參與過文學論爭。在現代文壇的眾多論爭中,廣告的因素值得關注。筆者在搜集整理現代文學廣告時,發現一些廣告或為文學論爭的導火線(緣起),或成為論爭的手段(工具),或在廣告文本中留存有文學論爭的信息。本文試以廣告史料的梳理來呈現20 年代文壇的三次論爭中的 “廣告魅影”。
一
1921 年5 月,在得到泰東書局的辦刊承諾之后,郭沫若迅速返回日本,于1921年6 月上旬邀集田漢、張資平、何畏、徐祖正等人在東京帝國大學第二改盛館郁達夫的寓所開會,正式成立了文學團體創造社,籌劃出版《創造》(季刊)及創造社叢書。1921 年7 月初,郭沫若帶著創造社成立時同人們的希望和建議,帶著一批稿子,從日本回到了上海。因創造社諸君都在日本,郭沫若只得單槍匹馬開始編“創造社叢書”和《創造》。由于郭沫若妻兒留在日本,加之他還要繼續完成學業,不能長待在上海。正好這時趙南公又推薦郭沫若去安慶法政學校任教,月薪二百塊,還可遙領泰東的編輯費。郭沫若沒法去,便轉薦了郁達夫。于是,郁達夫于1921 年9 月初從日本回國,一方面擔任安慶法政專門學校英文教員,一方面接任《創造》的編輯出版事宜。
為了提前造成影響,郁達夫于1921 年9 月28 日、29 日連續在《時事新報》上提前刊登了《純文學季刊〈創造〉出版預告》,宣告《創造》季刊創刊號將于1922年元旦出版。
盡管宣稱雜志將在1922 年元旦問世,但刊物在匯集稿件上并不順利,郭沫若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1922 年1 月23 日才完稿。由于郁達夫生性疏懶,他的《〈杜蓮格來〉的序文》1922 年2 月3 日才完成,他的短篇小說《茫茫夜》創作時斷時續,直到1922 年2 月下旬才殺青。從《創造》創刊號上的《編輯馀談》的落款時間“1922 年2 月23 日”看,《創造》創刊號大概在1922 年2 月底才集齊稿件,3 月中旬編校完成,送交泰東書局。由于書局無人負責校勘,故一直愆期到1922 年5 月1 日,《創造》創刊號才正式與讀者見面。郁達夫在創刊號上刊出的《藝文私見》宣稱:“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量的……天才的作品,都是離經叛道的,甚至有非理性的地方,以常人的眼光來看,終究是不能理解的。”可見,創造社正式在《創造》上打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旗幟。
郁達夫在《出版預告》中說《創造》就是要打破文壇偶像壟斷文壇的風氣,他們也是這樣做的。首先,他們與文學研究會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創造》創刊號上郁達夫的《文藝私見》和郭沫若的《海外歸鴻》的兩篇文章矛頭直指文學研究會諸君。郁達夫在文中諷刺“那些在新聞雜志上主持文藝的假批評家”,說他們“是伏在明珠上的木斗”,應該讓他們“到清水糞坑里去和蛆蟲爭食物去”[1]。郭沫若在文中也指責國內的文藝批評中有“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要拿一種主義來整齊天下的作家”[2]。面對創造社的挑戰,文學研究會被迫回擊。沈雁冰在1922 年5 月中下旬和6 月初的《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上,用“損”的筆名連續3 期連載了《〈創造〉給我的印象》,對郁達夫和郭沫若的文章進行了回擊,并評論了發表在《創造》創刊號上張資平、田漢、郁達夫和成仿吾的創作。最后,他說道:“我覺得現在與其多批評別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我極表同情于‘創造’社諸君,所以更望他們努力!更望把天才兩字寫出在紙上,不要掛在嘴上。”[3]此外,署名CP 的作者在《丑惡描寫》中也指出創造社諸君的作品是頹廢的肉欲描寫者。[4]
論爭雙方只要有了你來我往,那勢必要繼續下去。1922年7月,郭沫若和郁達夫又在《時事新報·學燈》分別發表了《論文學的研究與介紹》《論國內的文壇及我對于創作上的態度》《血與淚》。之后,沈雁冰又特地撰寫了《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和《文學與政治社會》,鄭振鐸也寫了《雜談》。在論爭過程中范圍又不斷擴大,你攻我是自然主義,我攻你是藝術派或唯美主義;你攻我沒有震撼人心的好創作或創作不多,我攻你是頹廢派的肉欲描寫者或創作淺薄無聊;你攻我翻譯粗制濫造或濫翻亂譯,我攻你在進行盲目的翻譯介紹,等等。兩大社團的論爭至1924 年7 月才停止。
除了與文學研究會“掐架”之外,創造社自然不會放過新文化界最大的“偶像”胡適。在《創造》第1 卷第2 期發表《夕陽樓日記》中,郁達夫在此文中諷刺胡適“跟了外國的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翻譯幾篇演講“就算是新思想家了”,并怒罵其“同清水糞坑里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學問也沒有”。胡適不得已只好以《編輯雜談·罵人》回應,指出他們為“初出學堂的學生”,“淺薄無聊”而“不自覺”。[5]對于胡適的回應,創造社成員不肯示弱,郁達夫寫了《答胡適之先生》[6]。胡適頗為惱火,又發表了《淺薄無聊的創作》進行辯駁。稍后,《創造》第1 卷第3 期刊出了郭沫若和成仿吾聲援郁達夫反擊胡適的文章。胡適則表示“沒有閑工夫答辯這種強不知以為知的評論”[7],這又激起了郭沫若、郁達夫的回擊。郁達夫寫了《反響之反響》,指出胡適《罵人》文中的譯文有三處錯誤。《創造》第1 卷第4 期又發表了郁達夫的《采石磯》,郁達夫以清中葉的黃仲則自比,而以考據權威戴東原影射胡適。成仿吾又發表了《學者的態度》,指責胡適對郁達夫所采取的態度,又旁征博引證明胡適譯文的錯誤。郭沫若在《創造》第2 卷第1 期發表了《討論注釋運動及其他》,近乎指明道姓地指責胡適:“我勸你不要把你的名氣來壓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來壓人,你須知這種如煙如云沒多大斤兩的東西是把人壓不倒的!”這場與胡適的論爭長達八九個月才告結束。
對于周氏兄弟,創造社也在《創造》上開始出擊。《創造》第1 卷第2 期發表了郭沫若的《批判意門湖譯本及其他》,點名指責周作人重譯的《法國俳諧詩》是“純粹的直譯死譯”,應該將其“屏諸譯壇之外”。當然,對直譯的指責自然也包括魯迅。以后,成仿吾的《詩之防御戰》、郭沫若的《黑魆魆的文字窖》《批評、欣賞、檢察》等都把批評的矛頭對準周作人,但周作人始終沉默不予回應。《創造》第2 卷第2期刊載了成仿吾的《〈吶喊〉的評論》,文中對《吶喊》持基本否定的看法。盡管未引起當時魯迅的回擊,但卻埋下了后來魯迅與創造社展開大論戰的導火線。
同為新文學中人,創造社諸君本應該團結文學研究會諸君、胡適、周氏兄弟等向文化領域的舊勢力進攻,共同致力于新文學的建設,但是卻在內斗中消耗掉大部分精力,這頗令人遺憾。1932 年,郭沫若曾對《創造》與文學研究會、胡適以及周作人等的論爭有過反思:“在我們現在看來,那時候的無聊的對立只是在封建社會中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氣息之相輕,更具體地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而已。”[8]
從創造社諸君與文學研究會、胡適、周氏兄弟等人的論爭過程看。郁達夫擬寫的《純文學季刊〈創造〉出版預告》無疑是始作俑者。作為廣告類文字,抬高自己、標榜自己的主張無疑是一種營銷策略。他們在《創造》預告中指責“我國新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并喊出的“愿與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的口號,自然會引發文壇的注目。《創造》問世之后,又四面出擊,與新文壇偶像(茅盾、鄭振鐸、胡適、周氏兄弟等)等大開筆戰,“立即引起了各方面強烈的反響。沫若、達夫和仿吾的新作吸引了廣大的青年讀者”[9]。《創造》吸引了大量青年讀者,自然也為《創造社叢書》以及隨后的《創造周報》、《創造日》、《創造月刊》等市場銷售助力,從而使“向來不為人注意的泰東書局,忽然間遐邇聞名,門庭若市”[10]。
二
1924 年11 月2 日,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顧頡剛、李小峰、孫伏園等人在北京東安市場的開成豆食店集會,決定出一個不受控制地發表自己意見的周刊,刊名為 《語絲》。
半個月后,《語絲》周刊創刊號問世,周作人主編,北京大學新潮社承擔印刷發行,16 開本,最初每期8 頁,定價每份2 分。由于有周作人、魯迅、林語堂、顧頡剛、章衣萍等數十作者供稿,內容上又力求“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的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刊物很快就在北京文化界引起了反響,第1 期再版了7 次,共印了15000 份,此后每期基本維持在7000 份以上。刊物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介紹研究文學創作及藝術思想,發表學術論著,主要刊載散文雜文,亦刊登小說詩歌創作和學術論文,形成了一種風格幽默潑辣的“語絲文體”。《語絲》創刊不及一月,胡適與陳西瀅、王世杰、高一涵、周鯁生、楊端六等北大教授參與的《現代評論》周刊于1924 年12 月13 日創刊,其撰稿成員多是歐美留學歸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創刊號上的《本刊啟事》宣稱:“本刊內容,包涵關于政治,經濟,法律,文藝,科學各種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態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本刊的言論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該刊16 開本,每期16~20 頁,定價每份3 分。該刊創刊出至第10 期時,銷數已達8000,創刊半年后,銷數已達11000 份。
20 年代中期的北京新文化界,圍繞《語絲》和《現代評論》兩大刊物就形成了兩個作家群,即語絲作家群和現代評論派。盡管兩份刊物篇幅和價格有差別,但作為北京新文化界影響頗大的兩種周刊,發行數量上旗鼓相當,自然成為了文化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由于《語絲》文字大多注重文化批評和社會批評,《語絲》及同人作為一股文化力量在北京文化界顯示了較強的戰斗性。但“女師大風潮”以及后來的“三一八”慘案中,《語絲》和《現代評論》分屬不同的立場,周氏兄弟的《語絲》則站在進步力量一邊,支持愛國學生。現代評論派諸君則以“公正”的“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現,雙方“很打了幾場硬仗”,而《語絲》雜志的促銷廣告也成了語絲派同人打擊對方的利器。
周作人作為《語絲》的主編,不但參與了《語絲》的創辦、撰寫了發刊詞、擔任選稿、積極撰稿等工作,還親自為刊物撰寫過宣傳廣告。這則廣告是在《語絲》出滿60 期之后(似為新的一年的《語絲》的訂閱工作)所寫,刊于《京報副刊》1926 年1 月21 日。全文如下:
北京的一種古怪周刊語絲的廣告《語絲》是我們這一班多少有點“學匪”脾氣的人所辦的,已有一年多的歷史,本年一月四日已出了第六十期。這里邊是無所不談,也談政治,也談學問,也談道德,也談文藝,自國家大事以至鄉曲淫詞,都與以同樣的注意,這是說在我們想到要說的時候。我們的意見反道學家的,但我們的滑稽放誕里有道學家所沒有的端莊,我們的態度是非學者非紳士的,但我們的嬉笑怒罵里有那些學者紳士所沒有的誠實。我們不是什么平衡家,或專門的文士,所以議論未必公允,文章也沒有水平線可說,不過這足以代表我們的真實的心,這一點似乎是值得廣告的。《語絲》的最大特色在于“不說別人的話”,至于“不用別人的錢”或者還是第二點。總之,《語絲》在北京——或是中國雜志界中可以說是有點古怪的一種,這似乎不很難,卻也不很容易做的。在自己的廣告里決心盡量地吹一下,但想來想去,沒有別的話可說,只能寫這幾句,然而也已經覺得用了十分的力了。……
在這則廣告的標題中,周作人以“古怪”來形容《語絲》周刊主要是凸顯它在北京雜志界的特色。他在《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中曾這樣說:“《語絲》還只是《語絲》,是我們這一班不倫不類的人借此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和思想的東西,不倫不類是《語絲》的總評,倘若要給他下一個評語。”當然,周作人口中的“怪”或者“不倫不類”只是一種幽默的筆法。在周作人看來,《語絲》在北京眾多的刊物中顯得很怪主要是因為它是唯一的仍然在繼續《新青年》思想工作的刊物。
周作人所寫的《語絲》發刊詞曾對刊物有過預期:“我們并沒有什么主義要宣傳,對于政治經濟也沒有什么興趣,我們所想的只是想沖破一點中國的生活思想界的渾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盡是不同,但對于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我們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著實的表現,但我們總是向著這一方面努力。”周作人寫這則廣告的時候,《語絲》和《現代評論》正在筆戰,他在廣告中也暗藏機鋒。他說《語絲》“不用別人的錢”實際上暗含《現代評論》是得到政府資助的一種刊物的指責。既然得到了政府資助,“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刊物的言論自由自然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對于周作人在廣告中的指責,現代評論派顯然不會不回應,在徐志摩主持的1926 年1 月30 日刊出的《晨報副鐫》中,刊出了徐志摩的《關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和陳西瀅的《閑話的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對周作人的攻擊也不再帶點含蓄的暗箭往來,而是極盡造謠、污蔑和攻擊之能事。
周作人的這則包含言外之意的廣告很快引起讀者的來信咨詢,在《語絲》第68 期(1926 年3 月1 日)刊出的《反周事件答問》中刊出了讀者王子欣寫給章川島的一封信,有如下內容:“我讀《語絲》,也讀《現代評論》,昔者我臆斷這兩種刊物是水和火,或者說是神和魔;從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之后,我們局外人處處看出來你們的不相容,這一點你們不至于諱言罷。……登在京報副刊中的《語絲》廣告,說到不用人家的錢,這話是否指《現代評論》而發?我看這廣告的文筆極像你,那么現代評論之受津貼,你總該知道,這是真事么?”[11]顯然,《京報副刊》上的廣告和《語絲》上的答問互相配合,進一步指明了《現代評論》之受政府津貼的事實,《現代評論》諸君所標榜的“公理”、“正義”無疑被揭穿。通過這樣的方式,《語絲》再次對現代評論派予以回擊。
在《語絲》第71 期《我們的閑話》中,周作人還緊緊抓住這一要害不放:“《語絲》在幾個小報上等了一個廣告,內中有一句話,說我們‘不用別人的錢’,豈知就闖了大禍,有人疑心是在諷刺《現代評論》的兩千大洋,或者以為是‘自鳴清高!’就是這第二款似乎也已不成事體,以為據現代評論社的陳西瀅先生說,‘要是并沒有人請你去做皇帝,你卻以‘務光許由’自負,非但不能證明你的清高,正可以證明你有進瘋人院的資格。’準此,《語絲》的人可以鑒定是很有瘋氣了,因為你們還沒有拿章士釗的錢的資格而敢妄自尊大,一定是喪心病狂無疑,……瘋人就是瘋人,這倒也沒有什么。關于第一款我想諷刺不諷刺的問題還在其次,重要的還是在《現代評論》到底有沒有那兩千元的大洋。”[12]
稍后,周作人在《論并非睚眥必報》中坦承他與《現代評論》派諸君由交游融洽到勢不兩立的過程,起因就在女士大風潮中,周作人、魯迅等站在學生一方,而陳西瀅等人在《現代評論》上刊登“閑話”,為學校當局以及教育總長站臺。“我看不起陳源的是他捧章士釗,捧無恥的章士釗,做那無恥之尤的勾當。《現代評論》當初雖然不是我們的同志,也未必便是敵人,他們要收章士釗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們不丟丑,不要當作賄賂拿,但是,看呵,這樣一幅情形,由不好惹的陳源先生起來千方百計明槍暗箭的替章士釗出力,閑話俱在,不是別人能夠‘偽造’的。這不但表明陳源是章士釗的死黨,即《現代評論》也不愧因此而謚為‘白話老虎報’。”[13]
但以周氏兄弟為領袖的語絲社諸君與現代評論派的恩怨遠未結束。在《語絲》第79 期刊出的《本報增加篇幅定價預告》中,盡管主要是告知本刊加價的情況,但也不忘再次提及與現代評論派的恩怨:
……但是因為這樣一來,印刷各費要大一點,本社別無收入,不得不仍取諸讀者,所以八十期以后的定價也須略為增加,……
顯然,預告中的“本社別無收入”并不是無端的言辭,而是直指《現代評論》接受政府津貼一事。周作人接著在《語絲》第80 期中刊出了《我們的閑話》,以優勝者的心態對上次的廣告和這次的預告以及與現代評論派的恩怨又旁敲側擊:“前回《語絲》登了一個廣告說及不用別人的錢,豈知觸了受過章士釗一千元津貼的報社之忌,大家很是惶恐,生怕惹出是非了。這回語絲上所登的啟事里又發見了違礙字樣,即是‘本社同人別無收入’,這豈非又要被《現代評論》見怪么?誰起草這個啟事的,真是太不小心了。……倘若能夠仿《三場程式》或《字學舉隅》的樣子,把許多犯諱的字例如士釗,一千元、津貼、收入,別人的錢等都羅列出來,使人一目了然,免得誤用觸犯,那是功德無量的事”。[14]
總之,周作人為《語絲》撰寫的廣告,重申刊物的立場、定位以及語絲同仁的態度,實現了宣傳自己刊物的目的,而且還暗暗貶低了與《語絲》構成市場競爭對手的《現代評論》,而且以“不用別人的錢”擊中了現代評論諸君所宣稱的“精神的獨立”的虛偽,可謂“一箭三雕”。
健全和完善的法規制度是確保會計檔案真實和完整的根本措施。會計人員依法填制的會計憑證、登記會計帳簿、編制財務會計報表及會計文件材料都要納入歸檔范圍。
三
如前所述,陳源參與了《現代評論》的創刊。作為主要撰稿者,除了參與刊物的編輯事物外,還得為刊物供稿。因此從創刊號開始,《現代評論》幾乎每期都有署名“西瀅”(陳源的筆名)的文章。如第1 期有《“非利第四”(Philistines)》,第2 期刊出《民眾的戲劇》,第3 期上又有《開鋪子主義》,等等。談及的話題包括社會問題、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日常生活瑣事等。在1925 年5 月引發的“女師大風潮”中,魯迅起草并和馬裕藻、沈尹默、周作人等七人簽署的《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風潮宣言》在《京報》上發表,揭露楊蔭榆開除學生的荒唐之舉,聲援學生的斗爭。這很快招來陳西瀅的“閑話”,寫了一篇《粉刷毛廁》(刊于《現代評論》第1 卷第25 期),含沙射影地說魯迅等暗中鼓動學潮。陳源既打上門來,魯迅便立刻應戰,當天便寫了《并非閑話》,并于6 月1 日發表在《京報副刊》第166 期上。四天后,魯迅又在《莽原》(第7 期)發表《我的“籍”和“系”》,駁斥陳西瀅的攻擊和污蔑。陳、魯兩人的恩怨結下,稍有不慎,戰火又會點燃,如圍繞對待人民群眾態度、創作沖動論、《中國小說史略》、“三一八”慘案等,魯迅和陳西瀅又重開戰火。
1927 年6 月,胡適、徐志摩等人籌辦新月書店,作為與胡適、徐志摩交好的陳源自然要以稿件支持,這就萌發了把自己發表在《現代評論》等刊物上的文章搜集出版之意。由于因“閑話”引來了與魯迅的論戰,所以,陳源有意把這個作品集命名為“閑話”。新月書店為了促銷,提前在報刊上刊出了此書的預告①,全文如下:
閑話 出版預告 西瀅著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他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閑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
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閑話》!
同時,魯迅對廣告中陳西瀅封為現代派的主將也進行了挖苦和諷刺。魯迅寫完這篇《辭“大義”》之后,還覺得意猶未盡,6 天后,他又寫了《革“首領”》⑤,以戲謔的語言再次對廣告中所封的“首領”進行了批駁。
而對于廣告中把陳西瀅封為“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以及對《閑話》的價值和意義的吹捧,魯迅也自然不會放過⑥,用引號(表示反語)對陳西瀅及其作品大大地挖苦了一番:
至于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閑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閑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這一則廣告的不當措辭又引發了陳(包括徐)、魯的舊怨,而魯迅連寫兩篇雜文予以回擊,顯示了其窮追猛打的精神。顯然,陳西瀅以及新月書店意識到了他們“摸了老虎屁股”,所以在《閑話》正式出版之際,新月書店就不再用預告的廣告詞,而為該書新擬廣告詞,全文如下:
現代文藝叢書第五種 西瀅閑話 西瀅著
前一兩年在每期的《現代評論》里,大家看見過一位署名西瀅的文章,
這些文章又輕輕的冠以“閑話”。漸漸的,看《現代評論》的人,不知不覺要先看西瀅的閑話。
——究竟西瀅是誰?閑話是什么文章?為什么人人要看?
西瀅是誰是不成問題的。閑話是什么文章,現在印在這本書里了。為什么人人要看呢?……
《西瀅閑話》印出來賣給要看它的人。⑦
從新擬的廣告詞看,撰寫者吸取了預告廣告詞的教訓,涉及魯迅的文字沒有出現,而且也不再為了嘩眾取寵,夸大其詞,而是老實規矩了許多。但是廣告中的最后一句“《西瀅閑話》印出來賣給要看它的人”顯然也不是無端的文字,而是從預告中“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而來,意即《閑話》的讀者并不是魯迅及語絲同人,而是賣給站在現代評論派諸君立場的讀者。有意思的是,到《西瀅閑話》再版時,新月書店又在《申報》刊出了如下廣告詞:西瀅先生是前幾年《現代評論》和《語絲》筆戰時候的主角,讀過魯迅《華蓋集》的人,不可不讀此書⑧。可見,廣告撰寫者也有借魯迅及作品來推銷《西瀅閑話》之意。
四
現代文學發生伊始,現代作家就深度介入了現代文學書刊的出版,現代作家為現代書刊撰寫宣傳廣告也是常事。作為文壇中人,作家撰寫廣告自然會容易把現代文壇中的各種文事、恩怨等或隱或明流諸筆端。而廣告文字顯然有別于作家的其他文字,它以吸引讀者、引起讀者對所宣傳的書刊購買欲望為目的。正如羅貝爾·埃斯卡爾皮認為:“讀者是消費者,他跟其他各種消費者一樣,與其說進行判斷,倒不如說受著趣味的擺布。”[15]為了突出某一新文學書刊的趣味,撰寫者在廣告文中常常制造噱頭,使用夸大其詞、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等手法。此外,作為現代文學書刊的廣告主(出版社)來講,能引起文壇的論爭,吸引到普通讀者的關注,現代文學書刊的銷售自然也有了保障。所以,廣告主也希望現代文學書刊廣告的文字內容要有“吸引力”。正是由于作家(廣告撰寫者)、廣告主以及廣告本身性質等的原因,所以現代文壇才出現了“廣告魅影”這一特殊現象。拙文所舉三例還只是20 世紀20 年代現代文壇論爭中出現的廣告因素⑨。三四十年代的文壇論爭中,“廣告魅影”也時有出現,如《太陽月刊》上的廣告中涉及“革命文學”的提倡、《西線無戰事》漢譯引發的廣告大戰、丁玲被捕之后的出版界用廣告來聲援丁玲,《賽金花》廣告中提及的國防文學的論爭、《希望》(徐懋庸主編)雜志創刊廣告中針對魯徐恩怨的戲擬,《雪垠創作集》廣告中涉及對胡風派的反擊,《聞一多全集》廣告中對國民黨當局卑劣行徑的聲討,等等。總之,現代文學廣告是現代文壇各種事件、論爭的見證者、參與者、記錄者,這些廣告涉及的文壇人事、文事,值得全面系統地梳理與研究。
注釋:
① 筆者多方查找當時的報刊雜志,未能找到原刊處。幸好魯迅的文章《革“首領”》把這則預告全文照錄了下來,此處的引文即來自魯迅的文章,特此說明。
② 這則廣告到底是誰所擬,現已不可考。陳子善在《好書,好圖,好廣告——〈愛看書的廣告〉讀后》中認為“早期新月書店的廣告應可認定大都出自余上沅手筆”,這則《閑話》出版預告是否出自余上沅之手,實很難考證。
③ 關于魯迅與徐志摩的恩怨,具體可參考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第二章中“魯迅與徐志摩論爭”部分。
④ 此文寫于1927年9月3日,發表于《語絲》周刊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⑤ 發表于《語絲》周刊第153期(1927年10月15日)。
⑥ 1925年8月,北京的《民報》在《京報》和《晨報》上做廣告,標榜魯迅為“中國思想界之權威”, 1926年1月28日,陳西瀅在寫給徐志摩的信中挖苦過魯迅。這封信后發表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報副刊》上,魯迅自然也會讀到。這次《閑話》的廣告把陳西瀅封為權威,魯迅自然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⑦ 廣告載《新月》第1卷第2號,1928年4月10日。
⑧ 廣告在《申報》1929年4月28日。
⑨ 20年代發生的高魯沖突也有廣告的參與,參見廖久明《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