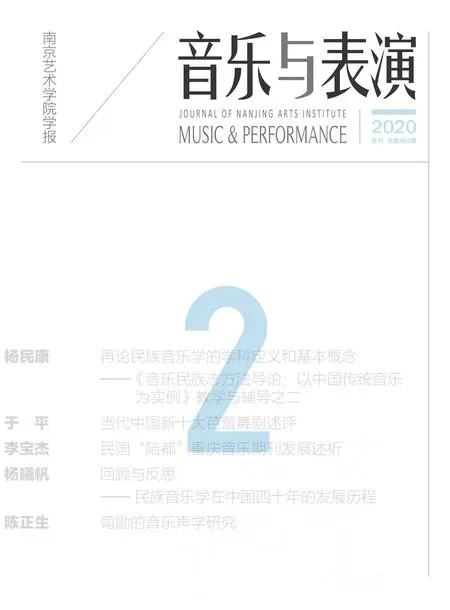漢代雅樂的復興及其內在張力①
韓 偉(黑龍江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禮樂相須以為用,兩者是中國古代進行文化治理的重要媒介。對于漢代而言,漢儒堅定地認為:“大漢繼周”,將周代看成是自己文化的直接源頭,但由于秦火之后典籍的消亡、士人的流散,對周代禮樂的隔代繼承并不盡如人意。與“復禮”相比,“雅樂”的復興更加不容易,樂類典籍的消亡相對徹底,加之音樂演奏帶有更強的技巧性,這些技巧往往要依靠樂工口耳相傳才能流傳下來,但經歷了秦代對儒家文化的摒棄,導致這種傳承出現了斷裂。因此,漢代對雅樂的復興便帶有明顯的一廂情愿色彩,或者說,漢代人更多是在“復雅”的話語下進行自己的獨立創構,這就使得漢代的雅樂建設帶有不同于禮儀復興的時代特征。
一、以俗為雅
俗與雅的問題是先秦以后歷代樂議的重要方面,主流層面往往將復雅看成是建立政治正統性、文化優越性的重要舉措,“雅”與“正”構成了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因此統治者在儒生的提醒、幫助下往往將復興古樂、追慕古樂精神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面,甚至不惜違心地壓抑自己感性層面對俗文化的喜愛,也要在外在征象上塑造這種假象,這也就形成了古代帝王根深蒂固的雙面人格。漢代制造雅樂的最初動機是郊廟祭祀,劉邦建國之后,叔孫通在制禮的同時,還承擔了造樂的任務,《漢書·禮樂志》載其“因秦樂人制宗廟樂”[1]1043,說明它造樂所用的樂工主要是秦代遺留,這些樂工的所學必然與正統的儒家“雅樂”不能一致。除此之外,“房中樂”也開始進入雅樂體系,并成為祭祀宗廟的樂種之一。房中樂起源于周代,主要用于宮廷,多是日常宴飲時由后妃演唱,樂器以琴、瑟為主,當時是一種典型的俗樂。在發展過程中,也會經常從民間樂曲中吸收養料,用以迎合統治者的喜好,因此其俗樂特征愈發明顯。高祖時所造的宗廟樂中,便有《房中祠樂》十七章,最初是唐山夫人所做,應該屬于高祖日常宴飲時所用的樂歌,同時,“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1]1043,后在惠帝時期改名為《安世樂》,由“房中”到“安世”,說明其逐漸被高雅化,并獲得了較為合法的地位②按:郭茂倩《樂府詩集》載“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此段記載與《漢書·禮樂志》有所不同。應該是武帝之前已有此歌,司馬相如等人對之進行了再加工。,直到成帝時,大臣孔光、何武才以“《房中》不應經法”為名,罷免了演奏此曲的大部分樂工,但他們僅認為演出陣容上與古法不合,并未對其完全刪除,仍然保留在宗廟樂的體系中。
“楚聲”是漢代雅樂的基本底蘊,這不僅在《房中樂》中有明顯表現,其他用于宗廟的樂歌也都大同小異。《漢書·禮樂志》載:“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1]1045,這段材料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高祖故地重游時所唱歌詩應該具有鮮明楚地民歌特點,高祖本身文化水平有限,加之這是與家鄉父老醉酒狂歡之際的抒情之作,所以盡管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得知準確的音樂旋律,但其具有鮮明的楚地地域特征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二是,出于迎合帝王好惡的目的,高祖的即興之作被加工為宗廟樂歌,到惠帝時,在高祖發軔之地建立宗廟,其中所用的歌曲便是《風起》之詩。在中國古代,帝王個人興趣往往會成為左右社會文化發展的主導因素,這在我們的文化體系中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高祖對楚地民間音樂的喜好,演變成為制定嚴肅音樂乃至宗廟祭祀音樂的主要標準,是符合邏輯的。
到了武帝時期,社會政治、文化已經達到了空前的鼎盛狀態,相應地,對音樂的復興和討論也愈發興盛。武帝有感于當時一些郊祀不用樂的事實,致力于恢復郊廟祭祀中的雅樂系統,《樂府詩集》卷一《郊廟歌辭序》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互奏之”[2],但實際的情況是,這些郊祀樂歌是樂府的副產品,武帝始立樂府,其目的是以類似觀風的形式,考察政治得失,正因如此,所采樂歌便具有鮮明的民間性和通俗性。武帝將樂府所采的樂歌加以改造,使它們成了郊祀樂歌的來源之一,“(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1]1045。李延年、司馬相如等御用文人根據趙地、代地、秦地、楚地的民間歌謠進行再創造,形成十九章郊祀歌,并在祭祀中廣泛使用。事實上,此時亦有有識之士對此表示擔憂,武帝的同父異母兄長劉德受封河間王(今河北省獻縣),其終身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搜集、整理,曾向武帝表達禮樂與治理之道的關系,并進獻了所收集的前代古樂,武帝將這些雅樂交給主管樂官,并令勤加練習以備使用。然而,在用樂實踐中,這些樂曲卻并未被真正使用,它們自然也就逐漸湮沒無聞了。對此,班固感慨道:“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1]1071,又,南朝沈約在《宋書·樂志》中亦總結稱:“漢武帝雖頗造新哥(歌),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為先……商周《雅》《頌》之體闕焉。”[3]550在班固、沈約等史家看來,當時用于郊廟的樂歌實際上是具有鄭衛特征的新歌,它們已經沒有了雅、頌的氣質。從這個角度來說,武帝立樂府是功過兼半,其功在于促進了文藝的創新,以通變的精神進行文化建設,其過在于這一過程消解了祭祀的嚴肅性,也使人們對祖先的敬畏之情受到影響。武帝立樂府,廣采民間歌詩,為俗樂向雅樂體系的入侵提供了條件。這種有意識的文化策略,由于皇權和政府的參與,使俗樂的地位獲得了空前的提升。出于有利于統治的直接動機,樂的高雅性變得不再重要,相反,樂的功能性成了衡量音樂好壞的最直接標準,這與漢代統治者對禮的努力建構是異曲同工的。于是,相比于對禮的努力復興,樂或雅樂的重建則滯后許多,實際上也并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所以可以說文化建設的功利性是漢代雅樂難以復興的根本原因。
武帝之后,樂府帶來的“不良”影響逐漸顯露出來,甚至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成帝時期,宮廷中很多演樂宦官已經地位相當高,甚至“富顯于世”,同時,一些貴族、外戚也沉溺于靡靡之音不能自拔,驕淫過度以至達到與帝王爭奪女樂的地步。當然,君臣綱紀的錯亂不能完全歸因于雅樂體系的顛覆,但它卻往往成為帝王乃至大臣的救命稻草,或者說是自己失德、無能的借口或替罪羊。于是,哀帝便直接宣布解散樂府,其《罷樂府官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4]驕奢淫逸之風在哀帝時已經普遍蔓延,在哀帝及大臣看來已經到了必須扭轉的地步,否則不會輕易廢棄樂府,這對崇尚孝道的漢代統治者來說需要極大勇氣,因為這意味著對武帝政策的否定。當時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也都迎合哀帝的政令,進而重新編制雅樂陣容,肅清鄭衛之音。可惜的是,單純依靠政令已經很難改變從上至下的審美趣味,所以他們的努力注定以失敗告終,“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壞于王莽”[1]1074。史官往往從正統角度,將漢代禮崩樂壞的責任讓王莽承擔,實際上王莽僅是西漢衰退進程中的一個節點而已。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王莽時,禮儀的建設達到高峰,但雅樂的建設卻情況相反。這說明,統治者出于治理的考慮,在復禮方面用力頗多,相較之下,由于樂對統治的作用不那么直接,所以漢代帝王反而不重視樂。這是禮樂地位開始變化的起點,此后,歷代帝王往往急功近利地重禮、復禮,但對樂卻相對漠視,主流意識層面的雅樂體系的崩塌以及樂之地位的陷落可謂由漢代開始。對此,樂論被文論(如毛詩序)取代便是明證[5]。
二、“孝”的張力性存在
“孝”在漢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亦是道德教化的根本。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漢初統治者的一種文化策略,漢承秦而來,秦以法治國,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在內實際上是在“契約”的層面存在的,因此臣不敬君、父子反目、夫婦背義的現象便頻繁出現。文、景之前,雖然總體上以黃老治國,但并不排斥儒家孝道,甚至努力對之加以建構,比如惠帝便“令郡諸侯王立高廟”“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命令諸侯建立宗廟祭祀祖先,表達虔敬之情,同時在民間廣泛推行忠孝教育,將孝悌之人與勤于勞作之人等而視之,給予免除徭賦的獎勵。這種政治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自此,“孝”在漢代政治、文化領域中具備了合法性。到了武帝時期,與“獨尊儒術”的文化策略進一步契合,遂使其成為儒家道德的最主要表征。
表面看來,漢初推行的黃老體系以清靜無為、淡泊修身為標志,而對孝的推崇則明顯帶有儒家倫理色彩,兩者看似矛盾,實則體現了統治者的治理策略。如果說整個漢代的治理策略是外儒內法的話,那么漢初推行的則是外道內儒,“外道”使民眾體會到國家與民休息的基本態度,“內儒”則保證基本的等級規范不被逾越,使皇權得以鞏固,這在高祖、惠帝時期便已經初露端倪,從中不難看出漢代統治者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功利性。正是基于這個基本的認知,漢代帝王除了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這兩位西漢和東漢的開創者之外,大多數帝王的謚號都以“孝”命名,由此足見儒家孝道被重視的程度。對孝的重視實際上是一種基于人倫基礎之上的政治延伸,傳統宗族層面的孝逐漸擴展為政治層面的敬與忠,以此為國家治理提供思想基礎。到了漢文帝,進一步使孝體制化,將“舉孝廉”作為察舉人才的重要方式,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1]124很顯然,這是對惠帝“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傳統的延續,其目的在于努力建構孝者、廉者、力田者的榜樣地位,宣揚一種當時社會的正能量,自此之后,“舉孝廉”成了漢代選才用人的基本制度。除了這種行政性的直接干預之外,文帝亦進行潛在的文化配套,立《孝經》博士就是重要舉措。在儒家經典中,《孝經》在漢代最早被重視,充分表明它的政治地位,這種政治地位的取得當然與其內容密不可分。《孝經》開篇即借助孔子之口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同時亦有將孝上升到哲學本體的傾向,稱“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盡管到了武帝時期,《孝經》博士被取消,但其影響卻一直存在,或者說孝變成了一種潛在的文化基因,所以東漢鄭玄帶有總結意味地將之視作“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6],甚至認為它是六藝的根本:“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7]武帝時代延續了對“孝”的推崇,并對之進一步強化。一方面繼續將“舉孝廉”制度化,甚至規定若地方官吏不能履行察舉孝者、廉者的職責,將受到免職的處罰。另一方面,隨著陰陽五行觀念的逐漸成熟,開始對孝進行了更為完善的哲學性建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對》中說:“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8]很顯然,《孝經》中的天經地義之說,已經在五行觀念的包裹下,變得愈發堅固而成體系。
可以說,上述政治意圖在漢初的雅樂體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但由于藝術自身的復雜性,在后續發展過程中則出現了主觀愿景與客觀效果之間的背離。高祖至景帝期間,“孝”在政治層面和藝術層面獲得了一以貫之的推崇,它亦成了當時音樂的表現主題。如上文所述,高祖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樂》,至惠帝時改名為“安世房中樂”,并廣泛運用于祭祀儀式中,其歌共有十七章,主體思想就是在宣揚孝道。第一章云:“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云景杳?,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作為祭歌的第一章,具有綱領性質,表明該組歌的主題應與孝道有關,其后各章中“孝”亦頻繁出現,如“大矣孝熙,四極爰轃”“清明鬯矣,皇帝孝德”“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嗚呼孝哉,案撫戎國”等,這組樂歌主要用于祭祀祖先,或者說是家廟舉行祭祀時所用,對天子而言,家是國的模板,因此這組樂歌實際上有以祖宗家法的形式宣揚國家禮法的考慮。在劉邦等漢代統治者看來,“大孝”往往體現在對祖宗的態度上,而宗廟及其承載的情感恰是這種美德的具體展現,小而言之這可以提升自身,大而言之則會營造一種良好的社會風尚,人人尚孝則社會必將歸于和諧。如果說制定禮儀是為了建構君主的權威的話,那么造樂則有為世道立德的考慮,沈德潛《古詩源》卷二稱此歌:“首言‘大孝備矣’,以下反反覆覆,屢稱孝德。漢朝數百年家法,自此開出”[9]。他認為《安世房中樂》是在宣揚“孝德”,為建構統一的道德標準服務。自劉邦開始,漢代以“孝”立國,就是在強調基本的人倫規范的基礎上,由小而大,由家及國,最終形成統一的治理體系,在沈德潛口中,這是“漢朝家法”,也是漢朝維護統治的基本秘訣。
與宗廟樂歌相對的是郊祀歌。宗廟樂歌的歌頌對象是宗族祖先,郊祀樂歌則主要表達對自然山川及四方神靈的敬畏之情。由于材料有限,目前可見的漢代郊祀樂歌是武帝時期李延年、司馬相如等參與制定的《郊祀歌》十九章,對此《漢書·禮樂志》及郭茂倩《樂府詩集》都有記載。與《安世房中歌》相比,《郊祀歌》帶有明顯的娛神特征,據有的研究者考證[10],十九章的第一章《練時日》可能是迎神曲,最后一章《赤蛟》為送神曲,而且其他各章中存在大量歌頌祥瑞的語句,從中可以看出,歌詩制定者歌舞升平的主觀愿望,以及對武帝喜好的有意迎合。漢武帝時期的這種雅樂實踐某種程度上干擾了宗廟樂歌對“孝”的建構,更加構成與主流話語之間的張力關系。這種情況下,廟祀歌努力建構的倫理想象就很容易被郊祀歌遮蔽。原因在于,武帝時期大量進行封禪、郊祀活動,其規模和頻次遠超廟祀,這在客觀上導致了對“孝德”的傷害,“漢武帝雖頗造新哥(歌),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為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3]550,這里所強調的“正德”就是漢初帝王所努力構建的“孝德”。甚至,久而久之郊祀樂的曲目、風格開始向廟祀樂滲透,并產生了混用的現象,鄭樵曾對兩漢用樂亂象做如下表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爼、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群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11]鄭樵提到的叔孫通所造的廟祀樂現在已不可考,應該與《安世房中歌》性質相同,待到武帝時期郊祀樂出現以后,廟祀樂的地位受到了挑戰,在鄭樵等主流文人看來,這是一種越禮的行為,天地、宗廟、君臣無論在等級上還是在特點上都不可等量齊觀,它們所用的樂歌也自然也要有所區別,但武帝以后則出現了混亂現象。本文認為,之所以在武帝時期出現這種雅頌淆亂現象,其一是人性中固有的理性與情感的錯位所致。《禮記·樂記》中曾記載戰國時期魏文侯聽古樂“唯恐臥”,聽新聲則“不知倦”的矛盾,這便是人們在面對雅樂與俗樂時候的微妙心理,這種心理在努力建構自身形象的貴族階層中更加普遍。上文已述,武帝時期郊祀樂由樂府創作而成,帶有明顯的俗樂特征,武帝從情感上應該更加鐘情于此,并且出現了情感戰勝理性的狀態。其二,郊祀樂對廟祀樂的滲透也有建構新的皇權合法性的考慮。在中國古代傳統中,文化建設歷來是為政權建設服務的,武帝重視郊祀天地、自然、神靈甚至大搞祥瑞之說,本質上是在承認孝德的基礎上,展示與文、景尤其是竇太后的不同,以此宣揚大漢新氣象的來臨。因為一味愚忠《安世房中歌》所標榜的孝德,便無法為自己與祖母之間的路線差異找到依據,所以武帝必須建構一種天道流轉、人世推移的文化觀念,從而為自己的“不孝”張目,這恐怕是《郊祀歌》所蘊含的深層政治意味。
三、陰陽五行觀念的滲入
相比于前兩個特征,陰陽五行的滲入更加具有普遍性,它似乎可以囊括漢代文化的所有方面,所以顧頡剛稱“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陰陽五行,無論在宗教上、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12]。陰陽觀念肇始于周代之前,無論是《連山》《歸藏》還是《周易》都已經開始以陰陽來討論世界的演變,春秋戰國時代,道家思想家在堅持“一生二”的世界化生理論基礎上,更加從哲學層面強調了陰陽的辯證統一。戰國末期齊國稷下學宮(主要是鄒衍)進一步將抽象的陰陽加以具體化,于是五行觀念開始產生,在他們看來陰陽相當于最宏觀的宇宙狀態,而金、木、水、火、土則相當于陰陽的具體展現形式,它們不僅有動靜、剛柔的區別,同時它們之間的互相運動也導致了陰陽的逐漸轉化。如果將世界分作三個層次的話,第一個層級是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的第二層抽象就是五行,對五行的進一步抽象就是陰陽,即第三個層次。漢代真正將陰陽五行觀念與政治、文化、藝術進行橋接的是董仲舒,班固《漢書·五行志》稱:“漢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1]1317認為董仲舒在闡釋先秦經典的過程中,將陰陽五行觀念摻入其中,從而建構了一個較嚴密的天人體系,這種嘗試在政治因素的推動下,最終影響了整個漢代文化,因此目之為“儒者宗”并不為過。
若詳細分析現存武帝時期的《郊祀歌》,已經能夠感受到其中蘊含的陰陽五行氣息。從時間上來看,這十九首歌并非一時一地之作,但總體上屬于武帝時期應該不成問題。從內容上來看,主體是展示迎神(《練時日》)、祭神(《天門》)和送神(《赤蛟》)的過程,其間穿插著對泰一(《惟泰元》)、四季(《青陽》《朱明》《西顥》《玄冥》)、眾神(《天地》)的歌頌,除此之外,還包括一些描寫祥瑞的詩章,比如《天馬》《景星》《齊房》《朝隴首》《象載瑜》分別頌揚良馬、寶鼎、靈芝、麒麟、赤雁的出現。在這些郊祀歌詩中,陰陽五行與天人感應的傾向已經有明顯體現。首先來看陰陽五行,《帝臨》在展示泰一帝降臨的過程中,歌頌其功績:“清和六合,制數以五”,認為不僅成就了清明天地四方的偉業,也開創了以“五”統御世界的先河。對此,《惟泰元》中表現得更為明顯,認為泰一神“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在其統領之下“陰陽五行,周而復始”的和諧秩序得以建立,惟其如此,自然界的風雨雷電才能有序施展,百姓才能安居樂業。與此同時,這組歌詩中亦頻繁出現顏色詞,他們又并非純粹客觀的存在,而大多具有道德屬性,諸如“爰五止,顯黃德”(《朝隴首》)、“托玄德,長無哀”(《赤蛟》)之類,實際上其中恰恰體現了漢代以五行配五色、五德的普遍形態,秦漢的其他典籍如《黃帝內經》《淮南子》《呂氏春秋》等都有類似記載,在《樂緯》中更是有針對性地將五聲與五行、五色、五德聯系了起來,總體邏輯為:宮—土—黃—信;商、金—白—義;角—木—青—仁;征—火—赤—禮;羽—水—黑—智。這種邏輯體系往往是從“五”的角度劃分世界萬物,并將它們賦予德行品質。其次來看天人感應。天人感應在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中實際上是為帝王統治服務的,一方面現實帝王是應天的存在,所以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地位,另一方面帝王的德行又與自然界的狀態相聯系,君主有德則天降祥瑞,君主失德則妖邪作祟。很顯然,《郊祀歌》是從正面運用天人感應的,以天馬、寶鼎、靈芝、麒麟、赤雁的出現贊頌帝王的功業。比如《天馬歌》開篇以天神泰一賜福,天馬降臨人間領起,然后對天馬的卓然姿態進行刻畫,并強調它以“龍為友”,是“龍之媒”,其降臨不僅讓自然草木蓬勃生長,也實現了“九夷服”的效果。對于此歌的來源歷來說法不一,總體上遵循實中寓虛的規則,司馬遷《史記·樂書》載:“(武帝)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13]①按:班固《漢書·武帝紀》稱“(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在《漢書·禮樂志》中只稱“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兩處記載都為神話傳說性質,未有史實依據。另班固對《天馬歌》創作時間的記載也存在矛盾之處。,將兩次所作歌辭與《天馬歌》相比較,可知用于郊祀的《天馬歌》乃兩首歌詩的綴合。今天對此歌的產生背景已經不能詳考,但其中蘊含的主題以及要實現的目的則是確定無疑的,詩中泰一與皇帝之間構成了呼應關系,天馬的出現與國泰民安之間亦相互映照,所以整組祭歌表面看來是在祭神、娛神,實則帶有極大的自我夸耀的痕跡,這與這些歌曲的作者多為御用文人有關,聯系漢賦的好大喜功、勸百諷一,會發現這幾乎是武帝時期的整體社會風尚。由此言之,所謂的“天人合一”重點不在頌神,而是譽人、譽權。
綜上所述,出于統治的需要,漢代士人階層及統治階層進行了異常艱辛的復興雅樂努力。通過考察史書文字,我們知道對雅樂的復興是建構新的意識形態體系的重要手段,這種方式雖然在漢代以后司空見慣,但漢代卻具有重要的原型意義。相較之下,文獻對漢代雅樂歌詩的記載非常有限,不過,通過對現存歌詩的細讀還是可以窺見到基本的思想特征,它們扮演了主流層面進行“美治”的具體實施者角色。具體而言,漢代人對“雅”的認知與其說是一種理想,毋寧說是一種策略,在復興雅樂的過程中俗文化、孝德、五行開始進入雅樂體系,并借助雅樂的文化功能變得合法化。由此可以說,漢代文化將周代“成于樂”的傳統認知,從人性培養和人格完善的層面逐漸擴展到了社會意識鍛造、社會制度形成的更廣闊空間,甚至將周代以來的音樂功能論變得更加現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