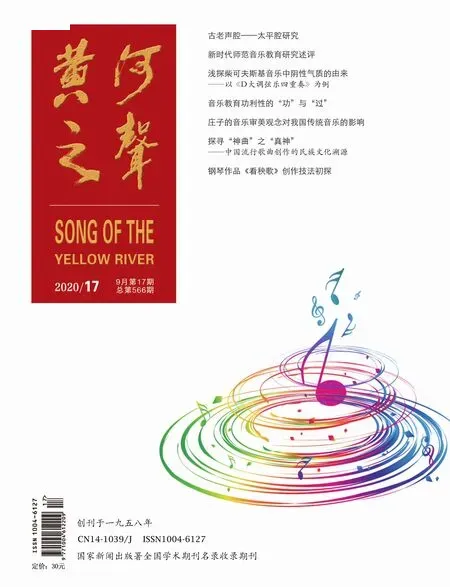古老聲腔
——太平腔研究
◎ 施長斌 (安徽省馬鞍山市中共當涂縣委黨校)
一、太平腔及其特點
太平腔,是產生于古太平州(路、府)治——今安徽省馬鞍山市當涂縣周邊地區的一種古老的戲曲聲腔。
早在明代,戲曲大家徐渭在《南詞敘錄》中就曾有這樣的說法:“稱余姚腔者出于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這里的“池、太”就是“池州府”和“太平府”(治所在當涂)的代稱。明末清初,池州人劉廷鑾在《五石瓠》中曾提到“流離中隨太平府優人逃”。其中的“太平府優人”,就指的是太平府唱戲的人。清代末年、民國初期,戲曲、文學研究專家葉德均在《戲曲小說叢考》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太平腔是產生于太平府(今安徽當涂),而非其它太平縣。”
當涂,是江南魚米之鄉,自古富庶。宋代太平興國年間,朝廷在此設太平州,轄當涂、蕪湖、繁昌三縣,當涂縣城——姑孰,就是太平州州治所在。元代改太平路,明清改太平府,治所、轄域不變。由此,姑孰城宋代之后又被稱為“太平城”,“太平”也演變成為當涂的代稱了——至今當涂城墻上還保留著“太平城”字樣的古磚。
宋元起,直至明清時代,我國各種戲曲聲腔不斷涌現。其中,誕生于當涂周邊,帶有當涂區域特色的戲曲聲腔,就被稱之為“太平腔”了。這也是我國早期著名的戲曲聲腔之一。
太平腔,屬于南戲聲腔的“高腔”形式。明代除昆山腔外,其他南戲聲腔一般都是“高腔”,太平腔也不例外。清代松江人錢學綸在《語新》中說:“府縣前亦俱搭臺唱戲,一式高腔……”有學者認為此處所謂的“高腔”就是太平腔,而不是(老)弋陽腔。戲曲家戴不凡在《小說見聞錄》中提到《堂邑腔·同窗記》中祝英臺的唱段:“驚了些山中麋鹿云中雁,聽了些子弟高歌太平腔。”其中所說的“高歌太平腔”就反映了太平腔具有“高腔”的特征。
明代王驥德在《曲律》中說:“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為‘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其中,除了寫出了太平腔的廣泛影響外,還寫到了太平腔“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的聲調特征及“鄭聲之最”的高腔特點。
從古代《破窯記》等太平腔代表性傳統劇目,以及現今作為太平腔遺存的當涂“采茶燈”戲曲曲調來看,太平腔充分體現了“高腔”清唱、幫腔、滾唱和道白的特征。
總結概括起來,太平腔具有以下的幾大特征:一是徒歌清唱、唱腔委婉,二是曲調明快、簡單重復、無板眼,三是有幫腔唱和,四是有滾唱,五是有道白,六是鑼鼓相伴以助節奏,七是演出角色少、道具簡單,八是采用太平府本地官話,九是內容一般為生活小戲和地方民間(鬼怪)故事,十是表演生動、情節感人、生活氣息濃厚。太平腔的演唱,以清唱為主,音律聲調簡單,一般三兩句,中間夾雜著道白或告白;只有鑼鼓伴奏,沒有管弦等其他樂器伴奏;一段結束,往往有重復的滾唱;一人唱,眾人和。太平腔的部分曲調還與地方民歌一致,與當涂民歌及地方歌舞存在著較深的歷史淵源。
二、太平腔的形成時間比較久遠
我國早期的幾大戲曲聲腔基本都形成于元末明初,清代達到鼎盛,出現了15種聲腔。關于太平腔的形成年代:歷史學家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的“南曲”詞條說:“南曲海鹽腔始于澉浦提舉楊氏,昆山腔始邑人魏良輔,并見《棗林雜俎》。按,又有太平腔,未知所始。”
當今的學者對太平腔的形成時間普遍認為系明代中期、嘉靖年代,其理由主要是以產生的源流為依據進行分析,說法不一。通常因為太平腔的一些曲目和唱腔與余姚腔或弋陽腔有共同之處,因此認為是受余姚腔或弋陽腔的影響后才產生的,也有說是兩者混合影響的產物,甚至還有說是受到更加靠后的青陽腔、徽州腔的影響才誕生的。如:學者流沙在《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中就認為:“太平腔,嘉靖間出于同在皖南的太平府的當涂”、“曾在當涂流傳的余姚腔可能受青陽、徽州腔的影響發生變化,產生太平腔”。
“余姚腔”的名稱,最早見于明成化年間曾任浙江右參政的陸容《菽園雜記》一書:“嘉興之海鹽,紹興之余姚……皆有習為倡優者,名為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凄慘。”祝允明(字枝山)的《猥談》之中也有稱“所謂南戲盛行,…今遍滿四方,妄名余姚腔…之類”。弋陽腔產生于元末明初,這是戲劇史家們共同的認識。另據清代乾隆版《弋陽縣志》記載:“考祝允明《猥談》,南戲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益,如余姚腔、海鹽控、弋陽腔、昆山腔”。這里所記載的,也是后人所說的“四大聲腔”,雖然沒有包含“太平腔”。但是,大量歷史資料顯示:太平腔的誕生并不遲于海鹽腔、余姚腔及弋陽腔,是我國最早的南戲戲曲聲腔之一,形成年代遠早于明初,完全可以追溯到南宋。我們不能因為太平腔的一些曲目和唱腔與余姚腔或弋陽腔有共同之處,就臆斷太平腔是受余姚腔或弋陽腔的影響后才產生的。
明代沈寵綏在《度曲須知·曲運隆衰》中提到:“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雖口法不等,而北氣總已消亡矣”。其中列舉的諸多南戲聲腔中有海鹽、弋陽、太平腔,卻無余姚腔。明末胡文煥的《群音類選》對“諸腔類”明確注明道:“如弋陽、青陽、太平、四平等腔是也。”明末王驥德在《曲律》中說:“今至弋陽、太平之滾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可見太平腔當時與弋陽腔齊名。在這樣幾個明代戲曲類研究專著中,太平腔赫然在列,而余姚腔還未被列入《群音類選》注明的四大代表性聲腔之列。徐渭在《南詞敘錄》中說:“稱余姚腔者出于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其中的“……池、太……用之”,也只能說明“池陽腔”、“太平腔”吸收“借用”了余姚腔的一些優點,這反過來又充分證明了“太平腔”原本的存在。
明代早期,成化年間(1465—1487)進士、慈溪(今浙江寧波慈溪)人揚子器寫過一首《早朝詩》,詩中寫道:“參差臺殿接煙霄,履舄交加萬國朝。門上優伶呈法曲,太平腔板合鸞簫”。從這首詩文中明顯可以看出:至少揚子器所生活的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太平腔當時已經非常興盛,并且已經成為朝堂、宮廷之上戲曲演出的主旋律。由此可見,太平腔的產生時間不可能是明嘉靖(1522—1566)之后,應該比明成化年間(1465—1487)還要早。
元末明初文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就曾記載:元代松江已有演戲場所,稱“勾欄”。明代松江府已有太平腔、海鹽腔、土戲、蘇州戲等戲種。范濂在《云間據目鈔》提到“戲子在嘉(靖)隆(慶)交會時……弋陽人復學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可見,至少明初太平腔已經與海鹽腔一樣,相當出名,在嘉靖年間已經傳到了松江等地,并且弋陽人又在學習太平腔“以求佳”,產生時間不可能在明代嘉靖之后。
明代王驥德在《曲律》中說:“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昆山’。……今自蘇州而太倉、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聲各小變,腔調略同。……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為‘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王驥德在《曲律》中還說道:“……今至‘弋陽’、‘太平’之‘袞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上述兩段引文充分說明了弋陽腔系“數十年來……諸腔之出”,而太平腔并非在“數十年來”新出現的諸腔之列。很顯然,太平腔比弋陽腔、青陽腔、徽州腔等“數十年來”新出之聲腔要早。
南宋《東京夢華錄》載:北宋已有“目連救母”雜劇演出,其故事源出佛經《佛說盂蘭盆經》。而《當涂縣志》記載:當涂歷史上“有專演目連戲者,用‘目連救母’劇本,或節演一宵,或分三宵全演……”至今民間還有在過水鄉的“盂蘭會”和紀念目連的“烏飯節”——可見當涂戲曲演出歷史淵源之悠久。
太平腔的《破窯記》等多個代表性劇目,都屬于元代南戲舊本,而這些南戲舊本代表性劇目并不為弋陽、四平等后世聲腔所有。太平腔對元代南戲舊本的傳承,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太平腔的歷史久遠。
宋代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陳著,景定元年(1260)曾任白鷺書院(緊臨太平府的南京西南)山長,他在《別齡叟八句》里寫道:“翠竹黃花曲曲香。中間猶有太平腔。淡空一飯云山缽,詩夢對床風雨窗。忽動歸心隨晚策,尚留醉興寄春缸。閒行除卻禪關外,牢閉柴門學老龐。”——詩中明確提到了作為戲曲聲腔的“太平腔”。也就是說:至少作為曲調的“太平腔”在南宋已經廣為流傳。這一點充分說明,太平腔與其他戲曲聲腔相比,不僅不落后,而且歷史淵源更為久遠。
三、太平腔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明代胡文煥在《群音類選》中對戲曲聲腔“諸腔類”注明說:“如弋陽、青陽、太平、四平等腔是也。”很顯然,這是胡文煥筆下最著名的“四大”古老戲曲聲腔。明代沈寵綏在《度曲須知·曲運隆衰》中記載:“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雖口法不等,而北氣總已消亡矣”。從中可以看出《度曲須知》也把太平腔與海鹽腔、弋陽腔等聲腔并列。明代王驥德在《曲律》中說:“今之弋陽、太平之滾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還特別指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二三。”當今學者流沙在《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中說:“明代太平腔流傳地域除皖南,還有杭州、松江、上海等地,向北還曾到洛陽”。可見,當時的太平腔在全國的影響之大、影響范圍之廣。
明代松江人范濂在《云間據目鈔》中提到“戲子在嘉隆交會時,有弋陽人入郡為戲,一時翕然崇高,弋陽人遂有家于松者。其后漸覺丑惡,弋陽人復學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上述資料顯示,太平腔不僅與海鹽腔并駕齊驅對昆曲產生影響,還被弋陽腔等所謂的“一級聲腔”所借鑒學習。從中不難看出,太平腔與弋陽腔、海鹽腔一道共同影響著松江土戲乃至昆曲的形成。此外,學界一致公認的昆劇之開山之作——梁辰魚的《浣紗記》中就有“醉太平”曲目,其劇情故事,在當涂周邊早有流傳(李白在《姑孰溪》一詩中,就有“何處浣紗女?紅顏未相識”的感嘆);昆曲《武教場》中的主人公花云、常遇春等都與太平府密切相關,也不排除與太平腔存在著歷史淵源。
太平腔的誕生,最早可以追溯至宋代。而在當涂這塊土地上,繼宋代詞人李之儀定居當涂,采集《田夫踏歌》等民間歌曲之后;元代散曲大家薛昂夫曾于文宗天歷年間在當涂任太平路總管,寫有《過太白祠謝公池》和《塞鴻秋·凌歊臺懷古》等散曲;明代湯顯祖、阮大鋮等詞曲大家紛紛來當涂采風。湯顯祖在南京任太常寺博士時來過當涂,寫有《采石山》、《化城寺》等詩,他在《慈姥竹》詩中寫道:“龍吟未曾聽,鳳曲吹應好;不學蒲柳調,貞心常自保。”阮大鋮也常來當涂,長住當涂文人曹履吉家,并在當涂文友們的陪同下,游覽當涂周邊山水,采集風土人情,在當涂留下了《山房小憩》、《采石吊太白先生》等11首詩。他在《九日曹梁甫招游姑溪》中寫道:“盡醉菰蒲曲,聞香橘柚間;浩歌出漁浦,明月照青山”。他“避暑姑孰十六日,成《牟尼合》”,又“坐姑孰春雨二十日,成《雙金榜》”……也就在這一段時間,阮大鋮在當涂寫出了《牟尼合》、《燕子箋》等多部戲曲曲目。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1),著名文學家、戲曲家蔣士銓也來當涂采風,創作出8場雜劇《采石磯》。以上這些詞曲、劇目的形成,都免不了會受到太平腔的影響。
明末清初,紹興著名的茶葉集市——平水鎮,每年有大宗的茶葉匯聚、外銷,是浙江的茶葉經銷中心。“采茶戲”是茶市活動中種種娛樂活動的泛稱。清代康熙年間,海鹽人彭孫遹在《茗齋集》中有一首“采茶歌”這樣唱道:“山西茶商大馬馱,馱金盡向埭頭過;蠻娘勸酒弋陽舞,邊關侉調太平歌”。“采茶戲”中這首“采茶歌”提及的“弋陽舞”與“太平歌”,很顯然指的就是“弋陽腔”和“太平腔”。也就是說,當時的山西茶商——南方人俗稱的“北方佬侉”,也用“侉調”學唱著“太平腔”。
清代,徽班進京,最終形成國粹——京劇。當年太平腔戲班也是主力徽班之一參與其中,“四大徽班”當中的“四喜班”就是太平腔的典型代表。清代林蘇門《續揚州·竹枝詞》寫道:“亂彈誰道不邀名,四喜齊稱步太平。每到彩場賓滿處,石牌串法雜秦聲。”詩中所說的“四喜”,即四喜班,“太平”即太平腔,“石牌”即石牌腔,“秦聲”即秦腔。太平腔和石牌腔均屬徽戲中的固有聲腔,秦腔則是徽班在揚州吸收的新聲腔。四喜班“步太平”,則說明了四喜班與太平腔的淵源。京劇陶謙《讓徐州》、花云《戰太平》、常遇春《三打采石磯》及伍子胥《過昭關》、《霸王別姬》等著名曲目,都與當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當涂一個地方,能有這么多相關內容成為京劇大戲,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了京劇與“太平腔”的歷史淵源。
清代以后,當涂人唱徽調——京劇逐漸成風。乾隆至道光年間,以太平府當涂為中心的徽調江南派,形成了鴻福、正音、壽音、春福等12個大的班社。光緒年間,以當涂南鄉(今大公圩)人沈彪領銜的“新春班”,徽調——京戲演唱紅遍大江南北。就這樣,以至于當時及后來的當涂縣境內到處有戲臺(俗稱萬年臺)、村村唱京戲(俗稱唱大戲),大多數自然村都有了自己的京劇小戲班。原先本土的“太平腔”,在太平府本地不被推崇,慢慢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只在昆曲發源地的松江府留有文獻記載。徽調——京劇在當涂的蓬勃發展,成為太平腔衰落比很多明代產生的其它聲腔衰落要早的主要原因。
從南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陳著的“翠竹黃花曲曲香。中間猶有太平腔”、明初慈溪(今浙江寧波慈溪)人揚子器的“門上優伶呈法曲,太平腔板合鸞簫”的詩文,明代松江(今上海)人范濂在《云間據目鈔》提到“戲子在嘉隆交會時,有弋陽人入郡為戲,一時翕然崇高,弋陽人遂有家于松者。其后漸覺丑惡,弋陽人復學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到清代康熙年間,海鹽人彭孫遹在《茗齋集·采茶歌》中“蠻娘勸酒弋陽舞,邊關侉調太平歌”的描述;學者流沙在《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中“入清以后太平腔除松江有記載,在安徽太平府本地已難找到。”“明代太平腔流傳地域除皖南,還有杭州、松江、上海等地……”等評述情況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太平腔對海鹽腔、余姚腔產生過影響。
太平腔與海鹽腔、余姚腔、弋陽腔等諸聲腔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借鑒發展,促進提高的過程。同時,還形成了與“太平腔”一脈,卻又不完全相同的局部戲曲聲腔。如:當涂周邊的“目連戲”、高淳“高腔”等。與南京高淳區、安徽宣城交界的當涂縣湖陽鎮,是個四面環水的鄉鎮,曾經村村有戲班,至今還村村有唱京戲的農民。上世紀末,湖陽鎮一個村莊還唱著一種被百姓稱作“黃梅調”的地方戲,卻又有著與黃梅戲迥然不同的戲曲聲腔,據當地百姓說:是太平腔與青陽腔結合的產物。
太平腔除對昆曲、諸腔、京劇有影響外,還對越劇、民歌等其他音樂戲曲產生了影響。《戲曲研究》副主編戴不凡在《小說見聞錄》中提到了《堂邑腔·同窗記》里祝英臺的唱段:“驚了些山中麋鹿云中雁,聽了些子弟高歌太平腔。”可見,屬北方戲腔的山東堂邑腔,也借鑒了太平腔的唱腔。就像山西“侉調”、山東堂邑腔學唱太平腔一樣,南方廣東粵劇二簧專腔中,也有“醉太平腔”的專腔。如今中國的許多地方戲腔、民歌中都有“太平板”、“太平腔”的影子,就連我國西南部的廣西鹿寨縣苗寨平山山歌中,至今還有“從外地流傳而來”的“太平腔”。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上海的華東越劇院選派了十幾位戲曲工作者,來當涂“松塘圩”采風,把至今仍在傳承的太平腔戲曲——俗稱“采茶燈”《同窗記·十里相送》等曲目,采編成越劇《雙蝴蝶》——《梁祝》搬上了舞臺、銀幕。黃梅戲《天仙配》也是取材于當涂丹陽鎮周邊的民間傳說故事——“七仙女三下凡”。《天仙配》是以“槐蔭記”為重點的七仙女一下凡,還有以《送子下凡》為重點的七仙女二下凡和以“哭靈”為重點的《七仙女三下凡》,均在當涂當地登臺演出過……;七仙女的扮演者嚴鳳英青少年時代就來當涂周邊演出過,黃梅戲《牛郎織女》中“牛郎”的扮演者黃宗毅則是土生土長的當涂人,從小看著家鄉當涂的“采茶燈”長大的。
四、太平腔誕生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淵源)
(一)太平腔的誕生,脫胎于姑孰大地肥沃的土壤
歷史上“吳哥雜曲,并出江南”,當涂被稱作“民歌之海”,這些都并非偶然,那是因為江南“魚米之鄉”,歷來系富庶之地。
當涂縣域周邊,古稱“姑孰大地”,歷來是江南魚米之鄉。“姑孰”的得名,據乾隆《當涂縣志·建制沿革》記載:“姑孰、姑熟,通用不一。按:仲雍字孰哉,義取‘饔熟’意。此二字古通。”仲雍,是商代末年采藥衡山的古吳國開創者;其十九世孫,吳王壽夢字“孰姑”。仲雍采藥的江東古南岳衡山——今當涂橫山腳下一直還有個“姑孰塘”。三國初期,東吳大帝孫權在姑孰大地建“姑孰城”,也就是為了紀念古吳王。“饔熟”二字,很顯然是豐收、有的吃的意思,說明這里是富庶之地。
姑孰大地屬于三江交匯之地,長江三角洲的頂端。系大禹治水的核心地,農耕文明發達。這里有大禹治水的中江,有“五湖四海”之古丹陽湖和上古時代的古南岳衡山。三國時,吳景帝孫休在此圍湖造田。這里歷史上有皇帝的糧倉——“太倉”和服務于后宮的“膏脂田”。姑孰大地,土地肥沃,物產富饒,百姓豐衣足食。只有這樣,人們才可能有精神層面的追求——唱歌跳舞,出現歌舞升平的景象。肥沃富饒的土地,才是“太平腔”脫胎、誕生、哺乳的溫床。
富裕了,才有多余的糧食釀酒;而戲曲小調往往伴隨著達官顯貴和文人們的飲酒作樂。這一點,歷來如此,宋及元、明代依然不減。明代何良俊就有:歷史上四方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的說法;旅行家徐霞客在《粵西游日記》中曾記載:“朱君有家樂,效吳腔,以為此中盛事,不知余之厭聞也”,可見徐霞客到廣西時,當地盛行學唱“吳腔”來招待客人,這里的“吳腔”當然指的是吳語地區,包括太平腔在內的諸聲腔;徐海榮在《中國飲食史》中也說:“當時佐酒使樂,流行弋陽腔、太平腔、昆山腔”。姑孰大地不僅富庶,還有丹陽湖龍骨草籽是上好的酒曲,因而善釀米酒,引得許多文人和帝王將相在此邀友相聚。早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姑孰釀酒、飲酒之風就盛極一時,以至于南北朝齊武帝特意下詔,命令姑孰“可權斷酒”。晉王羲之、畢卓、桓溫、孟嘉,南北朝陶淵明、謝朓,唐代李白等人都在姑孰大地留下了與酒有關的詩文、歌舞佳話。作為飲酒作樂的需要,也從另一方面催生了“太平腔”的誕生。
(二)太平腔的誕生,孕育在姑孰大地特定的歌舞環境
當涂所在的江東姑孰大地,民歌舞蹈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時代。
上世紀70年代,在先秦古南岳衡山腳下,出土了兩件戰國時期的青銅俑鐘,這至少可以說明:戰國時期,這里就有宮廷樂舞的存在。楚漢相爭時,霸王項羽所率八千子弟都來自江東這塊土地,“四面楚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江東大地百姓歌舞之盛。據《太平寰宇記·丹楊》載:慈姥山“其竹圓致,異于他處”“歷代賞給樂府”。姑孰慈姥山的慈姥竹,系我國古代做樂器最好的竹子,這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姑孰大地的歌樂文化。
漢晉時代,姑孰大地成為當時流行的代表性歌舞——“白紵歌舞”的中心。“白紵歌舞”是一種誕生于姑孰周邊的古代吳地歌舞,最早是流行于民間的吳歌吳舞,漢代因達官顯貴所青睞而興起,魏晉時代得以盛行;自兩晉以后,普遍為上層文人所喜好,是宮庭皇室常備節目。白紵,即白色的細紵麻,“質如輕云色如銀”,是制作舞衣的妙品。白紵歌舞的舞者多為妙齡女子,著白紵舞衣,飄素回風,如輕云一般。初為獨舞,后發展為群舞。姑孰大地乃富庶之地,是三國吳景帝孫休早期的封地,也是東晉重臣王敦、桓溫、劉裕等人駐扎的重地,自古是優質白紵麻的著名產地,“其女多事紡織”。據《太平寰宇記》記載:當涂城東原有“白紵亭”,相傳因南朝初宋武帝劉裕曾與群臣聚會,唱《白紵歌》,觀白紵歌舞于此而聞名。比這更早的記載,則是晉代姑孰楚山因“白紵歌舞”的興盛,而更名為白紵山的歷史。東晉大司馬桓溫進駐姑孰時,城東五里有山名楚山,桓溫常帶幕僚登山游樂,觀賞《白紵》歌舞,久而久之,原來的楚山也因此更名為白紵山。《樂府詩集》、《宋書·樂志回》等都有“白紵舞歌”或“白紵歌舞”的記載。至今,當涂民歌《十媳婦》當中仍有:“五媳婦來,會打(紵)麻哎”的唱詞。
白紵歌舞最初為田野之作,由于民間的時尚和朝庭的提倡,經樂官加以升華,成為宴會上更具有吸引力的女伎歌舞。深具名士風范的桓溫當得風氣之先,在楚山上多次宴集名士幕僚,飲酒觀賞“白紵歌舞”,楚山因此易名,姑孰因此成為為白紵歌舞的中心。桓溫風流于史,姑孰亦風流于時。
魏晉之后,南朝劉裕又在姑孰城北三里的小黃山上建起了行宮——“凌歊臺”。由此,南朝宋齊梁陳時期,姑孰城北又出現了“三千歌舞宿層臺”(唐許渾《凌歊臺》詩)的佳象。
唐宋以來,當涂文人聚集,百姓歌舞傳揚,李白《丹陽湖》中“少女棹輕舟,歌聲逐流水”、楊萬里《過廣濟圩》中“風流國是太平州”等詩句就是當涂歌舞的真實寫照。尤其是宋代詞人李之儀,以“姑溪居士”為號,與當涂結緣,最終與當涂歌女楊姝結為連理。李之儀在當涂期間,深受當涂歌舞的感染,深入農家田野采集當涂民歌,編輯了《田夫踏歌》歌集,并寫下了“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的千古絕唱。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宋皇親重臣及大批文人渡江南下,第一站就是從橫江渡過江來到當涂。史料記載,富足的當涂鄉紳們傾囊相助,犒勞流離于此的官兵和文人。后來,南宋政權穩定后,趙構也常帶領隨從來當涂賞景抒懷。這期間,北方的歌舞戲曲文化對當涂當地的戲曲舞蹈也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從沈寵綏在《度曲須知》中所說“北氣總已消亡矣”這七個字足以說明,宋南渡所帶來的“北氣”,曾對南戲聲腔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而時至明代,包括太平腔在內的諸個聲腔已經擺脫了宋之金院本、元雜劇之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演唱特點與風格,成為各具特色的獨立的聲腔系統——新的戲曲劇種。
戲曲聲腔的誕生,是在歌舞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的。當涂民歌誕生于百姓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有敘事歌、有情歌小調,也有勞動號子。就像“白紵舞”最初為姑孰田野之作,李之儀采編提煉的《田夫踏歌》來自于當涂農民的歌喉一樣;“太平腔”的誕生,應該是在當涂民歌的基礎上,結合優美的舞蹈,加上故事情節,才孕育而生的。至今作為太平腔傳承的“采茶燈戲”,仍保留著民間歌舞的原始特征——演出角色少、聲調簡單、內容為生活小戲和民間故事,還有不少曲調保持與當涂民歌一致。尤其是“采茶燈”的《藍橋》與當涂民歌《十二月花籃擔》的曲調旋律基本一樣,這無疑就是一個例證。
(三)太平腔的誕生,成型于姑孰大地詩詞文化的滋養
戲曲聲腔的誕生,離不開歌舞、詩詞和故事。詩詞本身是吟唱出來的,歌舞戲曲是詩詞創作的題材,同時也離不開文人詩詞歌賦及故事的潤色、提煉。文人們自古喜好歌舞,欣賞、評判著歌舞。太平腔的誕生與成型,也離不開詩詞文人們的培育和潤色。
以當涂縣為中心的周邊地區,歷史上稱作江東“姑孰大地”,歷來為文人雅士聚集之地。
魏晉時代,晉“八達”駐足于此,畢卓長眠姑孰,王羲之“醉酒脫險”;桓溫姑溪雅集,傳下“孟嘉落帽”之典故,留下庾闡“臨川疊曲流”的《三月三日臨曲水詩》,造就了袁弘的“倚馬千言”及《后漢紀》;陶淵明隱居衡山古南岳,謝朓筑宅大青山;陶弘景在橫山開讀書堂講學,昭明太子在慈湖構“讀書閣”編《昭明文選》、《陶淵明集》,姑孰才子周興嗣一夜編就《千字文》、唐代李陽冰住青山編就李白的詩集《草堂集》……
自唐代大詩人李白常住當涂,最終定居當涂并終老于此之后,唐宋以來,賈島、杜牧、王勃、孟浩然、劉禹錫、韋莊、白居易、杜荀鶴、曾鞏、梅堯臣、黃庭堅、蘇東坡、王安石、沈括、米芾、楊萬里、辛棄疾、朱熹、張孝祥、李清照、陸游、文天祥等六百多位詩詞名人接踵而至姑孰大地。唐代,李白《白紵詞》、《橫江詞》及《丹陽湖》中“少女棹輕舟、歌聲逐流水”、許渾《游謝氏山亭》“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激流”、孟浩然《夜泊牛渚》“棹歌空里失”;宋代,張耒《于湖曲》、辛棄疾《江行采石岸·戲作漁父詞》、郭祥正《凌歊臺》“不知歌舞散,雌鳳叫公竹”、賀鑄《金人捧玉盤·凌歊臺》“巖花磴蔓,妬千門珠翠倚紅妝。舞闌歌悄,恨風流不管余香”、張瑰《白紵山》:“夭夭白紵歌,曾此發清唱”……這些名家詩詞里都有當涂民歌、歌舞的影子,同時也反映出當涂歌舞內容之豐富。文人們游覽美景,聽曲助興,把酒吟唱,使當涂的歌舞與文人們的詩文得以相互吸收營養,從而使當涂的歌舞有著先天的歷史文化條件,得到滋養和提升。
“太平腔”一詞,至少在南宋就已經出現。宋代的太平州州治——當涂,有著深厚的詩詞文化背景,不僅有文人們聽曲、作詞,還有像李之儀那樣的詩詞文人在研究當涂的歌舞。就像湯顯祖《牡丹亭·道觀》中“三五孩童排排坐,天地玄黃喊一年”的唱詞,不僅帶有詩詞的特征,而且還將姑孰特色文化《千字文》的開篇“天地玄黃”融入其間一樣;至今口口相傳的“采茶燈戲”唱詞,依然保留著“七言”的詩詞韻律。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太平腔”的最終成型,與詩詞文人們的滋養、潤色存在著必然的聯系。
五、太平腔在姑孰大地的現代傳承
太平腔的傳承,學術界普遍以為入清以后已經失傳。學者流沙曾在《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第十六章關于太平腔”中這樣評述:“入清以后太平腔除松江有記載,在安徽太平府本地已難找到。太平腔的衰落在其它(很多明代產生的)聲腔之前,原因不明”。
令外界沒有想到的是,筆者田野調查發現:太平腔,歷經幾百年的興衰,代代相傳,至今在姑孰大地上仍有著較好地傳承。姑孰大地上俗稱的唱“采茶燈戲”,就是典型、正宗的“太平腔”傳承。
如同清代人彭孫遹在《茗齋集》中記述的那樣,當時“采茶戲”、“采茶歌”娛樂活動流行唱“太平腔”,就連山西“老侉”的茶商馬隊,也用“侉調”學唱著“太平腔”。外地人口中的“太平腔”,在當涂本地如今依然被稱作“唱采茶燈”或“采茶燈戲”,還依舊保持有古代茶市娛樂活動的演變特征。如今,當涂的“采茶燈”演出前,還保留著幾個孩童著彩妝,駕馭紙扎的“馬燈”、巡游行進的習俗;巡游結束后,馬燈隊伍還要先登臺表演“開場戲”;最后,馬隊撤離舞臺,演員們才正式演唱“太平腔”——采茶燈戲。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原當涂縣境內還有十多個地方的村落,春節期間都在演唱著“采茶燈”戲曲。每當演出,村民們有的邀請親朋好友前來看戲,有的戲迷十多里路趕去看戲。現如今,當涂縣城東部的白紵山腳下、龍王山北面的“百峰山里”,青山東麓和南麓,橫山南麓等地還在傳承著唱“采茶燈”,即“太平腔”。其中,姑孰鎮白紵山下的“松塘采茶燈”,已經被列入安徽省馬鞍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目前,“采茶燈”的演出,依然保持著清唱、只用鑼鼓伴奏的原始特征;一般仍以姓氏村落為單位,自發組織,口口相傳,各村落之間方言有別、少數唱段不完全一樣,步伐、服裝有差異,但歷史上相互學習,大致內容沒變,基本保持原有風格。當今仍在演出的劇目還有:《藍橋》、《杭城求學》、《嘆五更》、《十里長亭》、《大補缸》、《點大麥》、《十二月觀音》、《三戲白牡丹》、《數雞》等。演唱者中,以年長者居多,也有一些年輕人在傳唱,年紀最大的有80多歲,最小的只有十幾歲。但是,由于現代生活方式的改變,年輕人要經常外出掙錢,小孩子學習任務重,學唱太平腔——“采茶燈”的人越來越少,據不完全統計:總人數不過百人。有些村落已經多年不唱了,多數存在著后繼乏人的現象。
當涂民歌也是“太平腔”傳承的一種形式。“太平腔”是在當涂地方民歌優美曲調的基礎上,經過文人雅士的填詞包裝、加上故事情節、配上舞蹈動作才形成的。“太平腔”中的優美旋律,當地百姓朗朗上口,無疑又會在民間得到廣泛傳唱,成為民歌的重要部分。當涂縣,曾被譽為“民歌之海”。“當涂民歌”1950年代就唱進了中南海,2006年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現已整理的225首當涂民歌中,《劃龍船》等不少民歌,都帶有清唱高腔、滾唱重復、唱和幫腔、夾白等特點;《玉蓮子》、《張仙送子》、《看相》等不少民歌都有戲曲聲腔的特征,其中,當涂玩獅子、舞龍燈時“挑花籃擔”常唱的《十二月花籃》,其曲調與“采茶燈”的《藍橋》曲調,幾乎一模一樣。目前,當涂民歌通過非遺文化進校園、進社區、群藝活動、民間傳唱等形式得到傳承,這無疑也是“太平腔”的一種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