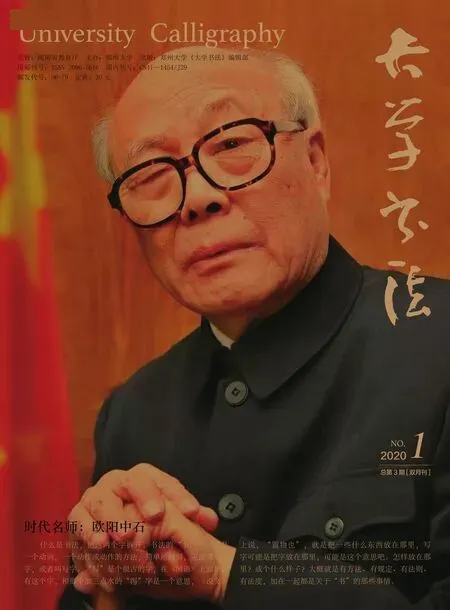三座山峰三件事
——試說侯開嘉先生的書法人生
⊙ 毛二安
侯開嘉先生是大家熟知的一位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和書法教育家,但他本人很謙虛,與人聊起天來,或應有關媒體記者采訪時,總是淡淡地說:“我一生就做了三件事—寫字、寫文章和教學生。”然而,在我看來,正是這三件事鑄就了侯先生書法人生中的三座山峰!
一
與絕大多數書法家成長經歷一樣,侯先生也是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愛上了書法。引他入門的老師有兩位,一位是高步天老師,另一位是銀際霖老師。中學畢業后,侯先生響應政府號召上山下鄉,在極其困苦的條件下,也沒有放棄練習書法。再后來,回城進了工廠,依然摯愛著書法。有志者事竟成,1981年侯先生因參加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受到當地領導重視,被作為特殊人才調進宜賓書畫院,從此開始專業書法創作,走向他書法人生第一件事的康莊大道。
從整體上看,侯先生的書法創作呈現為碑帖互融而又以碑為主的特色。正因為如此,他筆下的作品多為隸書聯與篆書聯,其中隸書聯又偏向平正、厚重與樸茂一路的漢代碑刻隸書風格,篆書聯又偏于大氣、寬博、端莊一路的西周或春秋金文風格。今天,除了到某些博物館,否則,我們很少能直接看到刻于漢碑上的隸書與翻鑄于西周或春秋鐘鼎彝器上的金文,能看到的多是漢隸與金文拓片。這些漢隸、金文拓片,最初固然也是用毛筆書寫,但結果卻經歷了刻與鑄的環節。一刻一鑄,最原始的筆法已難以尋覓。這時,不善學漢隸、金文者,便依樣畫葫蘆,竭力在筆下表現刻、鑄之風貌,而善學者會用學帖的方法來臨仿—把漢隸寫活、把金文寫活。侯先生便是其中的善學者,他學漢隸,主要取的是結體,但在線條上卻將它們一一帖化,讓它們不再那么方折、那么刀戟森森,而增加了一些圓勁、柔韌的成分;他學金文,取的也是結體,但線條一律是“寫”出來的,筆鋒或蒼勁或老辣,與原始“鑄”的風貌已大異其趣。當然,換個角度看,我們也可說侯先生的篆隸創作,吸收了清代書家鄧石如的經驗,在寫隸時融入篆書筆意,而在寫篆時又融入隸書筆意。總之,侯先生是位善學者,他的思考引導著他的創作,重理性又藝術趣味盎然。因而,他成功了,他的創作獲得了世人的認同與推崇—其作品在1988年湖南電視臺舉辦的國際書法電視大賽上獲金獎,在第五屆全國書法篆刻展上獲全國獎。
轉向行草書創作,侯先生遵循行草書的本質規定,在方法上則以帖為本、以帖為主,同時注入碑的一些意趣或氣象,比如剛健的線條、端莊的結體與茂密的章法,而遠遠不同于帖派書家趙孟頫與董其昌等人之行草書風貌,可以說,他更接近于后來康有為與沈曾植等碑派書家的行草書創作。這方面的代表作,可推他的行草書中堂《王世鏜論書》。也許,侯先生本人對該幅作品也極為重視,不然他怎么會將此作作為2014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為他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名家書法集·侯開嘉》作品集之封面呢?
侯先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者與繼承者,但觀念上一點兒也不僵化,也不唯“古”是從。相反,他的觀念很開放、很現代,比一般年輕人還要“新潮”得多。這方面的表現,有兩點特別值得一提:一是對“破體”的嘗試,二是對“現代派書法”的嘗試。
關于前者,侯先生還專門寫了篇文章,題目就叫《論破體書法的緣起和發展》,說明他從事“破體”書法的嘗試,并非一時心血來潮、純感性所致,而有著冷靜的理性思考在前面引導。所謂破體嘗試,就是在一幅作品當中盡量糅合多種書體,而給人們提供一種全新的審美享受。侯先生告訴我們,這種破體嘗試,從王獻之那里就開始了,隨后又有顏真卿、楊維楨、鄭板橋、吳昌碩等人留下破體作品。在我看來,破體書法作為書法創新嘗試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有極少數作品“破”得巧而佳,得到書法史的認同。但更多的破體作品,卻淪于“雜糅”與“牽強附會”,或審美品位低俗,至少鄭板橋的破體書—“六分半書”如此。再看侯先生的一些破體作品,以上述提及的天津人美版作品集為據,有幾副字數少的四言聯或五言聯,很令我心折;而字數偏多一些的中堂則給我帶來步入誤區之感。這種不同效果,為什么會出現呢?原來,篆、隸、真、行、草五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已形成各自不同的審美語言,鄰近書體(如篆與隸、真與行、行與草等)尚有相通之處,而隔之太遠(如篆與真、篆與行、篆與草、隸與草、隸與行等)則很難將它們一一打通,強行“拉郎配”,必然獲取不了應有的審美效果。盡管如此,我還是非常欽佩侯先生不安于現狀致力書法創新的探索精神,他常說:“我寧肯做一個探索的失敗者,也絕不做一個故步自封的懶漢。”書法創新很誘人,多數創作者都在思考并嘗試著,至于破體書法能否成為通向創新殿堂的一條路徑,我想,即便有可能,那也極其偏仄,不容過分樂觀。
對“現代派書法”的嘗試,在侯先生那兒,只是偶然為之,但“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陰”,偏偏這偶爾之作,就是一幅成功之作,這幅作品就是收入上述天津人美版作品集中的《震》作。
《震》作,幅式斗方,主體是一個“震”字,上隸下篆,筆墨酣暢淋漓,充分展示了地震災難后慘不忍睹的景象—房倒屋塌,瓦礫滿地,樹木與生靈被埋壓、吞噬;款字題曰“5·12的記憶,戊子年四月”。另有跋語云:“2008年5月12日,陰,時值中午,余一人在家讀報,突感劇烈搖晃,家什墜地。知是地震,遂跑到屋外。只見天搖地動,房屋樹木如醉漢,明白災難性地震發生了。當時報道為八級地震,震中汶川縣被蕩平,距成都五十公里的都江堰市亦房屋倒塌成片。官方公布死亡人數近十萬。瞬間與死亡擦肩而過,內心如白,覺四大皆空。遂在不斷的余震中作此一幀。以記當時心靈之軌跡也。”這幅作品,在我看來,完全可與日本書家手島右卿筆下的草書《崩壞》相媲美!
二
侯先生的第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已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為眾人所仰慕。但在我個人的心目中,更愿意把侯先生視為一位書法理論家,他出色的理論造詣,使他的第二件事做得更引人矚目,其峰亦明顯高于第一座山峰。
侯先生愛好書法理論,主要是他愛思考的結果,但契機卻在他的兩位啟蒙老師身上。侯先生告訴我們,前述高老師與銀老師皆擅書法,但教他的時候都說對方的筆法不對,這可讓剛學步的侯先生為難了:聽誰的呢?到底誰對誰錯?他后來看了很多書法理論書,方悟出兩位老師說得都對,一是帖學的筆法,一是碑學的筆法。看書有了體會,他就把這些體會變成文字,并樂在其中,一發而不可收。
1981年紹興召開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由剛成立的中國書法家協會和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編輯部等單位聯合舉辦,后來成為實際上的首屆全國書學討論會。侯先生寫了篇《論書法創新的年齡規律》應征,結果不僅入選,而且在大會上予以宣讀(五篇之一)。受這篇會議論文之鼓勵,侯先生的理論才華進一步得到展示。此后,人們果然在有關報刊上經常讀到侯先生的大作,在有關書論會上經常看到侯先生的身影,在有關書論大獎上經常發現侯先生的大名。侯先生自謙寫作速度慢、完成篇目少,實際上數十年下來也積累了一二十萬字。而且絕大部分篇目經得起時間考驗,愈久愈顯其價值,這是最為難得的。單篇論文姑且不論,僅就論文集而言,亦令我們為之贊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到目前,侯先生已經相繼推出數部論文集,它們是:重慶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侯開嘉書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和2009年出版的《中國書法史新論》和《中國書法史新論(增訂本)》,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書法史求真錄》等。
侯先生的文章以史論為主,但問題意識特別強烈,讀來不僅能讓我們得到理論上的啟發,而且能讓我們得到創作思想與創作方法上的解放。像于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發表的《“用筆千古不易”嗎?》《“用筆千古不易”剖析》和《中國書法藝術筆法發展史概說》,主要針對現代帖學大家沈尹默的僵化筆法論(如“五字執筆”論、“筆筆中鋒論”等)而發,力主筆法是多樣的而絕不是唯一的,是發展的而絕不是千古不易的,告訴人們:只要能創作出好的作品來,什么筆法都可以運用,與做人不同,需要的就是“不擇手段”。這對當時書法界沖破陳腐觀念束縛、大膽進行創新嘗試,起到了多么大的促進作用啊!史論文章偏能發揮現實效應,這也許是當下那些一味埋頭碑帖考據、靠羅列史料成文的“理論家”們所難以想象的吧!
寫史論文章注重選題本身的理論意義,這是侯先生的又一追求。史論文章選題多得很,但并非都具有理論意義,這便需要史論研究者具備一雙慧眼。過去,人們對清代書法的史學定位并不高,對碑學運動的成就也估計不足,總以為北宋以后的書法發展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鑒于此,侯先生連續寫了四篇論文—《清代碑學的成因及碑帖論戰的辨析》《清代碑學實踐的成就》《清代碑學實踐的探索》和《碑學論辯三題》予以翻案,真可謂慧眼獨具也!通過這四篇論文,侯先生明確指出,“在中國藝術史上,清代碑學掀開了燦爛的一頁,它以創立的‘碑學’理論來指導實踐,取得了輝煌的藝術成果……使清代書法形成了‘尚樸’的時代藝術特征,造就了一大批書法藝術家,取得了和魏晉、唐宋比肩的偉大書法藝術成就。”“清代碑學的興起距今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了,它是我國的書法史上新崛起的一個藝術高峰。”“以上‘筆法創新’‘改造書寫工具’‘融畫入書’‘書從印入’是清人為建立碑學在實踐上進行探索的四個主要方面,其中以‘筆法創新’的功勛尤為顯著。‘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終于,他們在‘日落西山,氣息奄奄’之際闖開了一個‘碑學’的新天地,為中國書法藝術史樹立了一個高大的里程碑。”“清代碑學已經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將永垂青史!抹掉清代碑學,中國書法藝術史將顯得何等的單薄與蒼白”,等等。由于論證全面、扎實,侯先生的觀點已為當今絕大多數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所接受。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理論貢獻啊!
侯先生的文章亮點還有很多,比如在主攻史論的同時,又不忘關注當下書壇現狀,像前述談書法創新自是一例,除此則表現為相繼發表了《評當今書壇的三大派別》和《中國書法如何才有可能走向世界》兩篇重要時論。而這點與他寫史論文章帶有問題意識又是密切相關的,道理很簡單,不關注現狀,又哪來問題意識?再一個亮點,便是深思熟慮,“每發必有新見”(陳振濂語)。他告訴我們,他的重要史論文章,從觀點形成到文章定稿,有時要花一年多時間。正因為如此,他發表出來的重要史論文章,不僅論據充分,而且觀點新穎獨到,令人信服。聯想起當下書壇,尚有個別“理論家”嘩眾取寵,短時間之內便接連拋出一個又一個新旗號、新名目來,侯先生的治學精神,難道不顯得異常可貴?難道不值得大力提倡嗎?
三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提供的。1996年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想創辦書法專業,找來找去只有侯先生最合適。在四川,在全國,想要找個單純的書法家,很好找,但沒有理論造詣又如何去傳授學生理論知識呢?如果要找個單純的書法理論家,在四川境內沒有,可全國范圍內還是可以找到的,只是手上功夫不行,無法很好地指導學生進行書法創作。試想,書法專業學生幾年下來連毛筆字都寫不好,又怎能稱得上合格的書法碩士呢?侯先生兼擅書法創作與書法理論,人又在四川,于是順理成章地被川大聘請過去當了最合適的書法教授。這樣,侯先生的書法人生在兩件事的基礎上又多了一件事,這就是“教學生”。由于“教學生”亦碩果累累,第三座山峰隨之映入人們的眼簾。
創辦書法專業,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須知這是白手起家,一切從零開始啊!
但侯先生并沒有被困難嚇倒,入校之初,第一步便著手考察全國已有書法專業各大高校的辦學模式。他清楚地看到,北方院校偏于理論教育,南方院校偏于創作傳授。最終決定,川大藝術學院書法專業的特色,當體現為創作與理論并重,既教學生搞好書法創作,又教學生關注書法理論,并獨立撰寫書法理論文章,務使畢業后的學生成為當下書壇的雙棲型人才。
一開始,碩士招生人數少,僅一人而已。到后來,才逐漸增多。但增多后的人數仍極為有限,而不同于本科生或高中生人數那么多。當過老師的人都知道,人數多,上課有氛圍,老師站在講臺上講才充滿激情。而人數一少,老師就沒法站在講臺上講了。對此,侯先生的辦法是開門辦學,或邊示范邊傳授創作經驗,或邊座談邊傳授理論知識,或邊考察邊進行書跡鑒賞,或邊討論邊進行寫作訓練,或鼓勵學生參加全國重要展賽以檢驗并提高自己的創作能力,或鼓勵學生參與全國重要學術會議的征稿活動以檢驗并提高自己的論文寫作能力。在侯先生看來,碩士生平時默默的有序訓練當然是主要的,但適當參與社會上的一些“競技”項目亦有助于鞭策自我、升華自我。光埋頭干自己的,不與他人相比、相賽,又如何知道自己的實際水準呢?又如何明白自己的不足而盡快予以彌補呢?
當書法碩導、博導,對有些人來說,一點也不難,也不辛苦,為什么呢?有的碩導、博導招收的研究生名義上拜他為師,但實際上,卻從不把他們當學生看待,學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學、怎么做,一任學生自己去琢磨,一次也不主動給予悉心指導,更談不上給予系統指導,充其量,學生遇到問題找到了他,他才盡自己所想所能解答一二;甚至,有的書法碩導、博導,將自己的學生當作“打工仔”,知識不傳授,反讓他們盡義務,幫他完成一個又一個“社會課題”,而課題費一個子兒也不給學生;或無休止地讓學生幫自己查找資料、翻譯外文、謄抄與打印各種文稿等等。但侯先生的碩導當得卻十分辛苦,他太認真、太有責任感了。他不僅注重向學生“灌輸”有關知識,而且注重教會學生如何開擴眼界、活躍思維,掌握書法創作與書法研究的方法。他曾親口告訴過我,教學生不花力氣不行啊,學生出不了成果,老師的臉面何在?他的一些學生也向我透露,侯老師待他們如同自己的子女,幾乎是手把手地教。他們入校前拿過毛筆,但從未寫過書法理論文章,但幾年研究生讀下來,全都被侯老師教會寫文章了。多么稱職的“傳道授業解惑”者啊!
教學生是件神圣的事,也是件奉獻的事。社會上有種悖論,就是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最好的學校去接受最好的教育,可又不愿讓自己的子女去讀師范。我們看到,恢復高考以來,每年上大學的人何其多也,但成績優秀者又有幾人主動填報師范院校?我自己當過中學老師,也深知很多老師同我一樣,教著教著就不想教了,何況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呢?但侯先生教學生卻教出了“癮”來,退休了,也不想離開學生。毛峰先生撰文告訴我們:“開嘉兄如今雖已退休,卻還樂此不彼地當起了‘助教’,一如既往地細心指導四川大學書法研究所的學生。我曾當著朋友的面‘嘲諷’他:‘一天不去研究所過不得。’他幾乎是每天晚飯后就賴著去輔導同學們。他回應我:‘我是吃過晚飯后去散步的,是鍛煉身體哩!’我哪肯罷休:‘成都那么大,散步只能去那里嗎?’眾人都笑了……我從這可體會到他對于書法教育的無比熱枕,對于學生學業和生活的無私關愛!”侯先生教學生如此上“癮”,能不讓我們倍受感動嗎?
由于侯先生教學生是手把手地教,所以,學生寫出、發表的論文自然也就凝聚著侯先生的大量心血。這時,如在署名時加上自己的名字也完全合乎情理,但侯先生從來沒有這么做,我們看到侯先生學生發表出來的論文均獨立署名,文后亦不見“此文經侯開嘉老師指導完成”等字樣。這就是侯先生的個性與風格!侯先生一直覺得,作為老師,指導學生寫論文是義務、是分內的事,學生寫的就是學生寫的,豈能在上面隨便掛名,“搶占”學生的研究成果呢?但侯先生又極其珍重學生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論文集《中國書法史新論(增訂本)》中附錄了《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書法碩士研究生論文索引》,在自己的論文集《書法史求真錄》中,附錄了五篇學生撰寫(署名)的論文。對侯先生來說,學生有了這么多的研究成果,倒是自己教學成果的一種展示,僅此足矣!侯先生這種對待學生研究成果的做法,孤立地看并不怎么起眼,但與林岫女史數年前披露的情況相對比,就顯得非常了不起了!該情況指的是,有位名校書法博導,自己一篇像樣的論文、一部像樣的專著都沒有,在申報“中國書法蘭亭獎·終身成就獎”時,卻拿學生的論文、論著來充數,并抹去學生的署名,公然將學生的成果據為己有。
人活在世上,總得做一些事,這些事不在多與少,而在于能否做得有聲有色,為社會留下若干值得稱道的東西。侯先生在他的書法人生中,只做了三件事,但這三件事每一件都做得很精、很有成就,像三座巍然挺立的山峰,引人欽嘆,引人仰止。這是多么璀璨的書法人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