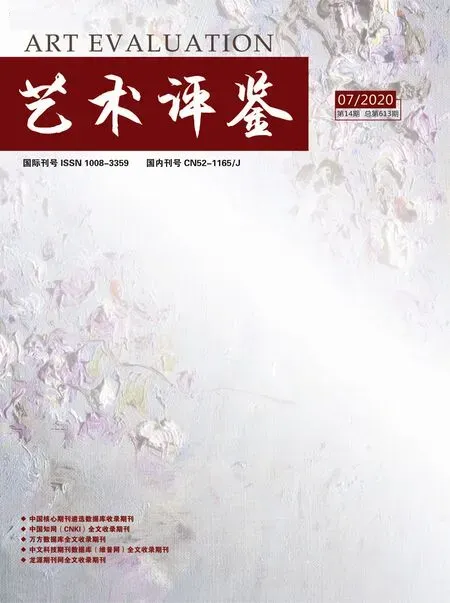電影《太陽照常升起》的荒誕敘事解讀
馬嬌嬌 河南大學
一、姜文和他的《太陽照常升起》
(一)荒誕之于姜文
姜文作為中國電影史上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既不像第五代導演一樣側重于再現歷史、表達民族情感,也不像第六代導演一樣注重對現實客觀世界的切實性描繪。他的作品中往往飽含著對真實的反思和批判,總是能找到一個獨特的視角來剖析人們已經習以為常、慣常接受的現實和道理。他的作品也給人們留下了荒誕不羈、恣意浪漫的印象。
現如今大多數人對于荒誕電影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種喜劇表現形式,具有“黑色幽默”的成分,比如影片中的一些不合理、無厘頭的搞笑情節等;本文所提到的荒誕成分,即是基于田川流先生在《藝術美學》中對荒誕的一個定義:“所謂荒誕,就是指某種情景或狀態的失諧與失衡,表現為對于正常思維模式以及生活節奏與秩序的變形、解體,或把對象按主觀意圖和意念重新組合,表現為主題行動、語言的怪誕與反常,秩序的紊亂與雜亂無章等。荒誕藝術正是這種現象的表現。”其更多了一種諷世的意味。以反常的不合理的手法來進行創作,刻畫人物、推動情節發展。
姜文的電影作品總是內容豐富、細節滿滿、臺詞量巨大,經得起回味和推敲,同時也被公認極具各種隱喻和暗示。看他的電影需要更加的專注,要獨立思考,同時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其電影作品也因此被很多人冠上了看不懂的帽子。每逢“姜文電影”上映我們也總能看到各種耐人尋味的深刻解讀,有的讓人恍然大悟、拍手稱奇,也有的會讓人有“當真如此?”的疑問。諸如此類不難看出姜文是一位具有鮮明個人特色和表達訴求的創作者,這恰恰與電影藝術中以反常規、不合理為主要特點的荒誕敘事表現手法不謀而合、因此經常能夠在“姜文電影”中尋找到荒誕敘事的具體情節展現。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他通過主人公“馬小軍”不斷否定真實的自述,展現了一段記憶中似真似幻、若有似無的青春,這樣的荒誕敘事手法,創造的是一個更主觀也更貼近內心真實的故事。在《鬼子來了》中姜文將荒誕指向了慘痛的歷史,他用反常規、顛覆性的視角和充滿諷刺意味的荒誕情節設定展現了或許更加真實的“小民”、人性和戰爭,影片將鏡頭對準了戰亂中的萬千面孔,戲虐荒誕、直戳人心。在《太陽》中他更是顛覆傳統的敘事結構、用更加晦澀的荒誕敘事手法挑戰著觀眾的接受度,這也將有關《太陽》的爭論推向了頂峰。
(二)輿論下的《太陽照常升起》
姜文因拍攝電影《鬼子來了》被禁七年后,在2007年攜這部被譽為中國電影史上極其荒誕浪漫的《太陽》華麗歸來。《太陽》在藝術上無疑是偉大的,但也因荒誕敘事手法造成了影片在解讀和傳播上的困難,從而在影片上映之后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該影片在敘事結構上采用了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對現當代社會語境中人們習以為常的邏輯性及線性敘事方式進行了顛覆,體現導演對藝術欣賞與藝術接受的獨特觀念;通過荒誕的敘事情節,體現對現當代社會的疑慮與困惑以及對人生和世界的重新審視,使得影片在藝術上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藝術上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在票房、經濟上的成功。田川流先生在《藝術美學》中曾說:“由于該類藝術對于傳統藝術的娛樂性因素的消解,特別是對于某些理性或者在非理性的表面的內里所掩藏的精心追求的理性,造成人們解讀的較大困難,因而也會造成與市場的阻隔,從而給此類作品帶來制作與傳播上的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關于影片故事以及導演本身的評價都是褒貶不一、針鋒相對的,形成了“姜文電影”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不喜歡它的人會覺得姜文在故弄玄虛,故意賣弄才華,從而與一部分觀眾拉開了距離,甚至不明白這部影片到底在講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毫不掩飾的展示了對這部作品的喜愛,如著名中國臺灣影評人焦雄屏曾評價:戛納不戛納,賺錢不賺錢,《太陽》都會是一部傳世之作。
二、荒誕敘事結構分析
《太陽》這部影片是根據葉彌的小說《天鵝絨》改編,突破了小說中的時空限制,大膽運用蒙太奇以及倒敘兼時空交錯的荒誕敘事手法。由“瘋”“戀”“槍”“夢”這四個故事組成,第一個故事“瘋”,是原小說中的一個情節而延伸的。故事發生在1976 年春南部,瘋媽和小隊長兒子的生活片段,影片以瘋媽夢幻似的消失結尾;第二個故事是姜文聽過的一個故事,發生在1976 年夏東部,老唐、梁老師、林大夫的故事,影片以梁老師的自殺結尾;第三個故事是原小說的部分,發生在1976 年秋南部,老唐被下放,夫妻二人在瘋媽消失后的村子與小隊長兒子發生的一系列故事,第三個故事隨著一聲槍響進入尾聲;第四個故事是姜文的一個夢而拍攝,瘋媽尋找阿遼沙、在火車上夢幻般的生下小隊長兒子和老唐妻子尋找老唐的故事。
影片中這些看似若有似無的聯系組成了這部極具夢幻、荒誕的作品,且這四個故事并不是按照邏輯性、線性的順序排列,再加以電影故事情節中的一些極具夢幻的場景,給人們造成邏輯上的混亂。對于敘事結構的反常規、反傳統,姜文的解釋是“不是看不懂,是難歸納,我媽就這么說,不習慣。”在姜文看來看電影的最終目的不是“看懂”,而是“感動”。“相對《讓子彈飛》這樣的影片,《太陽照常升起》更依賴某種觀影的心情,觀賞者的心情,我只不過想喚起人們在不懂的情況下的感動,我認為在感動這件事情上,離開了懂和不懂的前提才是真正的感動,我們現在被訓練成、異化成、被格式化成了‘要先懂,再感動’,這實際上是不對的。想一想,我們看到大自然的感動,看到美女的感動,早晨起來被陽光刺痛眼睛的感動,尤其是你看到一個景物的感動,這些都不是要懂,就是感動。”
姜文曾在采訪中說:“拿一本80 頁的書,一翻,剛好到20 頁。然后開始往后看,看到第40、60、80 頁,覺得不錯。最后,在翻看最前面的20 頁,哦,更不錯。這本書算是看完了。有人可能只記得40 頁的時候有些片段很精彩,卻記不得之前究竟講了些什么。”這部影片如若按照正常觀影習慣來編排的話應是“戀”“槍”“夢”“瘋”,但是姜文用自己對藝術獨特的認知,最終電影所呈現給我們的是“瘋”“戀”“槍”“夢”的順序。這正是與姜文說的“看80 頁書”的比喻一樣。“《太陽》這部影片的情節頗具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細節與細節的連接上并無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處于一種瘋魔的隨意狀態,建構了一座虛實迷宮。”影片的四個故事,每一段單獨來看都是獨立的、完美的,都是一個讓人感動的故事。當沒有按照觀影人的正常邏輯順序來編排時,一片排山倒海的“看不懂”出現了,觀眾所要求的“看懂”,而并非影片個體所呈現的一種切切實實的“感動”。
一部作品最終所要追求的是其對個體所呈現的直觀的感動,如2018 年末導演畢贛的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也極具爭議。影片呈現出“看不懂”“看了一半就睡著了”諸如此類的評價。其反響與《太陽》很是相像,《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典型的文藝片,其所表達的內容與影片的整體畫面是文藝片應有的風格。無論是電影中浪漫的色調,還是影片在后70 分鐘的一鏡到底的夢境,以及穿插著線索和夢境相交織的現實,都是影片所呈現的直觀的感動。
三、荒誕敘事情節分析
除上文所說的影片結構的荒誕敘事手法外,影片中情節的荒誕敘事手法或許更加的顯而易見。“荒誕藝術特點中所提到的荒誕藝術通過對于人的精神的異常表現,揭示人的心理現實。”影片中的荒誕敘事手法亦是如此,通過精神不正常的人去關照和審視正常的或病態的社會與人生,帶給人的情感是復雜的。
第一段影片中,瘋媽和小隊長兒子的故事。在藝術創作上,有很多夢幻的或是離奇的情節表現,比如,瘋媽的鞋子掛在樹上不翼而飛時出現的一只鳥,它反復的說到:我知道!我知道!此段情節的設置與生活常態背離,如此魔幻又荒誕。又如,瘋媽這個人物給人的感覺是時醒時瘋。瘋媽在房頂念著:“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之后忽然到了村口的大樹上,給小隊長兒子講著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樹上的瘋子” 的故事。兒子跟著瘋媽到河邊,瘋媽踏著草坪在水上游動。之后又見到石頭屋,石頭屋里是摔碎后又重組的物品。第一段影片的結尾瘋媽的一套衣服整整齊齊隨著河流飄走,人們不禁想到是瘋媽真的瘋了還是這個社會瘋了。此時亦讓筆者想起蔡康永對圓點女郎草間彌生的評價:“草間彌生不知是在哪面墻上鉆了一個洞,窺知了造物者的某個手勢或背影,她從此寄居這面墻上,在兩個世界間來回顧盼。”故事中的瘋媽也是如此的在兩個世界顧盼著吧,時醒而又時瘋。
由第一段影片的結尾處一陣優美的《美麗的梭羅河》響起,觀眾被帶入到第二段影片,第二段影片與第一段影片所呈現的不同,是其荒誕的表現不同于第一段的夢幻情節,而多以拍攝手法中的荒誕不羈凸顯。其中夜晚用電影放映機的光來抓壞人的場景就極具荒誕意味,錯亂的光影映襯著慌亂的人群,這是對現實場景的一種荒誕的戲劇化處理。在警察查案過程中的情景再現式的偵查手法更是凸顯了影片的荒誕成分,到底是誰騷擾了林大夫?又如林大夫這一人物形象總是以一身濕漉漉的形象來示人。這一片段以梁老師的離奇自殺結尾;無論是構圖、鏡頭還是配樂都營造出了一種荒誕氛圍。
第三段影片,也少了像第一段影片中的夢幻的和不合常理的情節設置,依然沿襲了第二段影片的故事情節及對話的荒誕,第三段的開頭和第一段剛好銜接,這也呼應了在敘事結構上的荒誕。影片中老唐教小隊長兒子打槍、會唱李鐵梅的女孩兒詢問唐妻阿遼沙和喀秋莎、小隊長兒子在尋找瘋媽的過程中與李叔等的對話、唐妻出軌小隊長并對他說老唐說她的肚子像天鵝絨,影片最后小隊長兒子對老唐說:“可是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鵝絨”,老唐的一聲槍響本段影片結束。故事情節并沒有很強烈的邏輯上的因果關系,人物的對話也是處處讓人摸不著頭腦。
電影最后的片段中,瘋媽和唐妻兩人各自尋愛,騎著駱駝分別去往路的盡頭,唐妻最終尋到愛人,而瘋媽最終并未尋到。路的“盡頭”和“非盡頭”的設定、火車掛著飄揚的熊熊燃燒的帳篷,瘋媽在燃燒的光影中離奇將兒子生在了花團錦簇的鐵軌上,這些情節設定都離奇的荒誕和意味深長。這本該是影片的開頭卻放到了結尾處,正是與姜文導演“80 頁書”的比喻相應。最后黑夜過去,太陽升起,隨著同名音樂“太陽照常升起”響起,影片結束。
影片中的一切都似乎都反常規、不合常理,處處充滿著從邏輯出發卻又不符合邏輯的故事場景,引導著人們走入這個魔幻的世界,思考著這個世界和自身。影片選材于現實,卻又與現實相背離、相疏遠,對影片故事情節的扭曲、變形的同時融入異變的主觀情感和幾近于非理性的思索,從而拉開了與現實世界的距離,將生活中的荒謬、不可理喻與毫無意義都呈現了出來,最終讓人們感到荒誕離奇,使受眾感受到極大的震驚和震撼,對現實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意義。其中對荒誕藝術情節的模糊處理,給藝術作品帶來了含義的多樣性,對于這部荒誕藝術的影片解讀很多,但正如姜文導演所說的不需要懂,只需要感動。“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就如你所感受到的正是影片所要帶給你的。
四、結語
影片結尾太陽升起,“一代人來,一代人去,太陽照常升起”,故事還在一代一代的進行下去。姜文的《太陽》充滿魔幻、荒誕與離奇,從現實生活出發又背離現實生活,讓人們不禁發問:到底是現實生活的扭曲還是人性的扭曲?荒誕藝術不像悲劇一樣使人在觀影后感到莫名的悲烈與崇高,其有的是對影片的莫名的感動。這就是荒誕藝術的魅力所在,看似雜亂無章的影片中處處都是對現實的重現。結構上的荒誕與情節上的荒誕,以及本部影片中浪漫的藝術表現手法共同創造了這部在中國電影史上最具爭議作品,優秀的藝術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果觀眾對于這部影片的期待只是同以往的觀影習慣一樣,只想讓影片給你講一個故事,那么這部影片有可能無法滿足,所以“不適應”成了觀眾口中的“看不懂”。擺脫偏見是通向美的必經之路,尊重個體的直觀感受,你所看到的正是影片所要帶給你的,也只是你的。所以在這部影片中你是被第20 頁的那段故事感動?還是被第80 頁的那段故事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