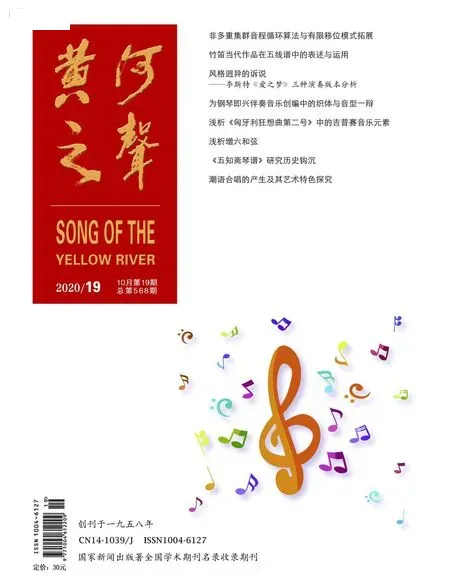北魏平城時期宮廷音樂構建考述
閆錚 (山西大同大學)
源起大興安嶺北段嘎仙洞的拓跋鮮卑,在十六國后期,經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的征伐戰爭,于公元439年結束了一百三十余年的十六國分裂割據局面,建立北魏,統一北中國。公元386年拓跋珪稱帝建國,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其間共歷十二帝,立國148年。北魏政權在天興元年(398)至太和十八年(494),以平城為統治中心,稱北魏平城時代。
一、“變夷從夏”文化觀
北魏時期是華夏民族共同體發展的重要階段,儒家民族思想觀念中蘊含的華夷認同思想被重新詮釋,發展出“夷可主夏”觀念,拓跋鮮卑稱華夷同源共祖,稱華夏始祖黃帝為遠祖。《魏書》載“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后,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涉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①“華夷”有別的觀念,逐漸被新“華夷認同”觀取代。拓跋鮮卑選擇“變夷從夏”的漢化道路。正如馬克思所言:“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②
登國元年,拓跋珪重建代國,天興元年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③;同年十一月,“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品爵,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宴饗之儀。”④北魏初建,定國號、營宮室、建宗廟、立品爵、建禮樂,一系列的國家政策,拉開了經濟、文化、政治、哲學,胡漢雜糅的大幕。胡漢音樂文化“經過這次融合以后,新的血輪注入漢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又轉變成支持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⑤
二、“戎華兼采”雅樂觀
拓跋鮮卑“戎華兼采”的雅樂思想,構建出一套南北交響、四方相諧的北魏宮廷音樂。清商樂、龜茲樂、疏勒樂、西涼樂、安國樂、高麗樂等紛至沓來,百花齊放,構成了多元融合的華美交響樂章。云岡石窟音樂圖像是北魏音樂的活化石,石窟內雕刻有各種樂隊組合70余組,樂器圖像530多件,伎樂飛天2400多身,他們有的手持樂器演奏、有的翩翩起舞,有的昂首高歌,生動的再現了北魏平城時代的音樂盛況。云岡石窟中有各類樂器27種,分為吹奏樂器、彈撥樂器、打擊樂器。云岡石窟第12窟以音樂、舞蹈雕像精美著稱,其前室所塑造的盛大歌舞場面實屬罕見,被譽為“佛籟洞”和“音樂窟”。第12窟中有西域樂器篳篥、琵琶、豎箜篌、五弦、細腰鼓等,西涼樂器義觜笛、齊鼓,西北游牧民族樂器胡笳,漢族傳統樂器簫、橫笛、琴。胡漢交融的樂器圖像,從一側面展現出北魏宮廷音樂的形態、風格,也印證了北魏平城時期的宮廷音樂與西周初建立的宮廷雅樂已大相徑庭。北魏宮廷音樂既有別于正統周代雅樂,也不同于漢魏清商傳統,它是華夏雅樂體系奔潰后的解構與重建,是融西域、河西、關隴、江東、荊楚等文化于一爐的新華夏正聲的先聲。
三、構建宮廷音樂
“魏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期間所發展變遷,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采用”⑥自西晉永嘉之亂后,持續戰亂,漢晉宮廷音樂體系分崩離析。《魏書·樂志》載:“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⑦永嘉之亂,晉室南渡,胡族爭霸北方,宮廷音樂數度易手,散落流失。
(一)艱難起步
從拓跋始祖力微到太祖397年定中山,數次獲得中原禮樂器物。《魏書·樂志》載:“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⑧397年前,北魏獲得樂物、樂伎,定中山時獲得樂懸,雖未創改,但被因時所行而用。這一時期,拓跋鮮卑宮廷音樂成果集中于樂物、樂伎等物質層面的獲得。
(二)平城初創
道武帝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標志著北魏宮廷音樂進入初創時期。《魏書·樂志》載:“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后更制宗廟。”⑨定律呂、協音樂、追諸帝、用八佾、舞《皇始》,道武帝用禮樂制度推崇鞏固皇權,建立郊廟之樂,拓跋氏雅樂思想逐步建立。《魏書·樂志》載“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⑩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于殿庭,如漢晉之舊也。”?由郊廟之樂、宴饗之樂、掖庭之樂、百戲之樂構成的北魏宮廷音樂體系基本構建。
(三)增修演化
在“華夷認同”、“華夏文化正統觀”、“夷可入夏”等觀念影響下,拓跋鮮卑自上而下的漢化徹底而決絕。從拓跋珪與漢人名儒合作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拓跋宏即位時,鮮卑貴族中已有很多人精通漢學。拓跋宏即位,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漢化改革,隨著遷都洛陽,割裂了與胡文化的聯系。北魏宮廷音樂的增修、演化、發展,便是在拓跋宏漢化改革時期。拓跋鮮卑繼承、發展了周雅樂思想與禮樂制度,為中國古代禮樂制度的演化起到了催化作用。
1、定方樂之制,增四夷樂舞
《魏書·樂志》載:“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秘群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眾議,于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于往時矣。”?高祖垂心古之雅樂,然遍訪吏民,洞曉者甚少,其事彌缺。高祖制定方夷之制,增四夷歌舞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豐富了宮廷音樂的色彩,彌補雅樂有失的缺憾。
方樂之制是北魏重建宮廷音樂的制度。方樂,四方樂舞。雅樂崩缺的現狀下,拓跋鮮卑主動吸收異質文化精華,重建宮廷音樂體系。清商樂、漢魏民間俗樂、胡樂、鮮卑樂等不同民族的樂舞形式,共同構筑了北魏宮廷音樂的基礎,也促成隋唐多部樂的建立。
2、非雅不宜,鐘懸鏗鏘
太和十一年春,文明太后:“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裨增鐘懸鏗鏘之韻。”?庭奏之曲非雅樂不宜,雅樂必取正聲,不典之曲不入,增加金石樂懸。金石之器為周雅樂中使用的鐘磬樂,既是樂器,也是禮器。樂懸在秦漢時,只允許宮廷和王侯所用,普通的貴族已禁止使用鐘磬,改用鼓吹。北魏宮廷加強金石樂懸的地位,是對漢魏傳統的繼承。這一時期的北魏宮廷音樂,在平城初創的基礎上,經過增刪,進一步向華夏傳統融合。
3、稽古復禮,樂正雅頌
《魏書·樂志》載: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于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孝文帝深受漢雅樂思想影響,提出稽古復禮,樂正雅頌,并對樂官的職責提出了規范。北魏宮廷雅樂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提升。
4、詳采古今,增修禮樂
《魏書·樂志》載:“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同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采音塤,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曲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然心喪在躬,未忍聞此。但禮樂事大,乃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孝文帝對禮樂崩缺,痛心疾首,深知禮樂是教化的根本,要重視禮樂,后令中書監與太樂詳采古今,增修禮樂,并強化禮樂規范和標準。
經過三個時期的構建,北魏宮廷音樂體系基本成熟,此外,太樂署、樂府、鼓吹署、樂部等音樂機構的建立以及樂官制度的完善,都成為后世宮廷音樂建設的基礎。
北魏雖是重建宮廷音樂,但經過長期的戰亂,華夏雅樂流失嚴重,勢必引入新的音樂形式來補充。經過增修的北魏宮廷音樂與舊華夏體系,已有很大的不同。公元前1058年(西周)制定了禮樂,禮與樂緊密結合,建立了較完備的宮廷雅樂體系,作為維持社會秩序、鞏固王朝統治的有效手段。雅樂用鐘磬伴奏,主要在祭祀、郊廟等大型儀式中使用。秦漢時期,宮廷雅樂遵循周禮,沿用先王之樂,但增加鼓吹等形式進入宮廷音樂體系。魏晉之時,南北分裂,頻繁的戰爭致使雅樂衰微,宮廷音樂分崩離析。事實上,秦漢已經開始了宮廷音樂的演化,北魏時期演化加劇,將中國宮廷音樂推向了轉型發展的道路,直至隋唐新體系定型。
注釋:
① 《魏書·紀》卷一《序紀》[M].中華書局,1974:1.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70.
③ 《魏書》卷2《太祖紀》天興元年條[M].中華書局,1974:33.
④ 《魏書》卷2《太祖紀》天興元年條[M].中華書局,1974:33.
⑤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M].中華書局,2006:3.
⑥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3.
⑦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7.
⑧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7.
⑨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7.
⑩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7.
?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8.
?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8.
?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9.
?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29.
? 《魏書·樂志》卷109[M].中華書局,1974: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