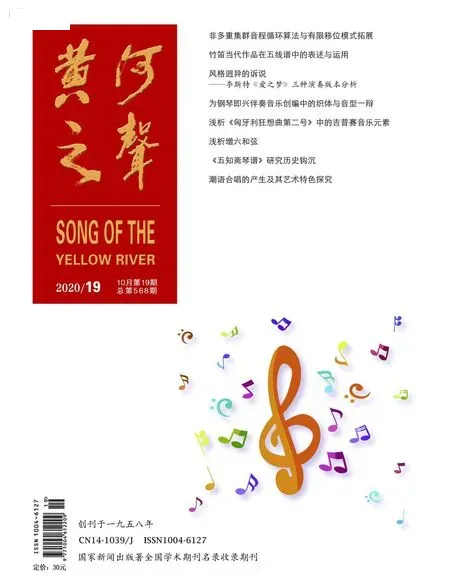情感元素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運用
阿衣先木古麗·木合買提 (新疆藝術學院)
近幾年,音樂事業實現了蓬勃發展,為了滿足人們的各類音樂賞析需求,越來越多由民歌改編的藝術歌曲被創作出來,使得民歌再次回歸人們視野中,也使得民歌再次流行了起來。民歌改編的藝術歌曲與以往民歌有著明顯的共性,體現在情感元素的運用上,情感元素極大化的豐富與拓展了歌曲的意境和神韻,值得為此探究一番。以下是歸納總結的情感元素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具體運用內容。
一、民歌改編藝術歌曲與情感元素的之間的關系
情感是構成民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沒有情感的穿插,則不能稱之為成功的音樂作品。也正是因為有了情感,民歌作品才有了靈魂與生命,作品也才能更打動人,由此才能引發與延伸出啟示與感受。由此可見,民歌改編藝術歌曲與情感元素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既相互影響、也相互成就,缺一不可。
細化而言,旋律與情感也是密不可分的。旋律較大程度可以代表一個人的情感波動與心理變化,或緊張、或開心、或焦慮等情緒,旋律就可加快、緊湊、輕緩或低沉,很多情感的表達都是建立在旋律的配合之上的。旋律的產生與發展,也由環境的不同、創作者心境的不同而充滿各中不確定性,所謂“千人千面”,旋律雖相似,但是在細節處盡是細膩、不可言說的情愫,這是旋律于情感上的價值體現。此外,在表達人物個性上,旋律依舊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部分,或鏗鏘有力、或輕生細雨,都是一直與思想的最好表達,有時代表著獨立的個人,有時又是一個民族的象征。
民歌中的歌詞,更是傳達重要信息的工具,它與情感仿若人的口與思想,一個在表述、傳遞,一個在吸收和思考,很難想象在沒有歌詞的民歌中,歌曲的情感表達將是多么匱乏,那么民歌的傳唱意義也將不復存在。可以說情感是修飾歌詞的重要內涵,而歌詞是表達情感的重要內容,兩者相互協調與配合,才譜寫出更多、更好的民歌篇章,為更多人體會更多不同的情感做出了突出貢獻。
二、情感元素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運用
(一)對甜美愛情的追求之情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運用
在眾多民歌與民歌改編的藝術歌曲中,歌頌愛情的歌曲數量較多,也最為常見。愛情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有甜美、有酸楚,各類滋味摻雜其中,也因此成為了各類作曲家的創作源泉,被較大程度的應用到民歌改編中。如有名的民歌作品《小河淌水》,如果只是單純的對人物、場景進行闡述,很容易單調與乏味,正是有了對情感的描寫與細致入微的刻畫,才使得該作品有了靈魂,使得愛情的主題更為凸顯,不僅在高超創作技法的搭配下使得該作品傳唱度更廣,也使得其中的愛情元素更為打動人,很容易引發人們對愛情的向往之情,這正是運用愛情元素的獨到之處。其中為了更凸顯愛情的甜美氣息,更是將旋律設計的清新優美且扣人心弦,猶如愛情中的兩人含情脈脈,也猶如四年中的兩人輾轉反側,結合心理特點與愛情特色,使得該作品的意義遠超于表面的旋律與歌詞內容,更具地域特色。隨著一聲“哎......”,歌曲被拉開序幕,鋼琴伴奏輕輕附和,和聲對主旋律音調進行著疊加和襯托,仿佛能夠看見姑娘在撫摸著情郎送與自己的定情信物。而通篇中的高潮也由“哥啊”的呼喚就此展開,字眼、語音、語調各不相同,仿若體現著姑娘的萬般柔情與情意綿綿,加上悠揚的琶音,使得愛情情感被烘托的異常熱烈,更是凸顯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氛圍。該歌曲中的主題選擇與曲調設計搭配合理,整體韻味偏清新雅麗,使得藝術層次瞬間提高,也使得該歌曲更具品味與欣賞價值,奠定了該部作品的成功,使得它成為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另一首值得介紹與解析的作品是《槐花幾時開》,對甜美愛情的追求之情也在該部作品中體現的淋漓盡致。該作品原本是四句體單樂段篇幅短小的民歌,想象空間較為局限,其濃郁的川韻鄉情還是可以感受出來的。丁善德先生對這首作品進行了改編,用鋼琴的音色與節奏,凸顯了一個愛情主題,使得改編后的歌曲更令人動容。歌曲整體圍繞姑娘情竇初開的愛情,在歌詞上少做了調整,采用了烘托、設色、渲染等手法,精心的進行了編排與設計,使得青澀而美好的愛情有了延展的空間。改編后的歌曲共50小結,前奏、間奏、尾奏所占比重較多,擴展了以往的民歌容量,形成了較為完美且契合的結構,深入剖析與體現了姑娘的內在情感變化,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鮮明、品味愛情的各類滋味更為顯著,整體而言,是提高了歌曲的價值與品質。
(二)對苦難生活的衷訴之情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運用
民歌題材中不僅有對甜美愛情的向往、追求之情,還包含對苦難生活的衷訴之情,這類情感也來源于生活的感悟和體會,對日后的民歌改編藝術歌曲有著較深遠的影響。多數對苦難生活的衷訴之情多在舊社會、遠歷史的背景下產生,且融入了那個年代的民歌,雖然已經不再適用現代生活,但只需稍作改編,衷訴之情與歌曲藝術價值將再次提升,也可迎合潮流,從而被廣泛傳唱。
蒙古族世代傳唱的《嘎達梅林》就是一首歌頌人民在土地與自由方面與封建勢力進行斗爭的經典民歌作品,該作品中有代表人物,且在對苦難生活的訴說基礎上也表達了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嘎達梅林》這首民歌經桑桐先生改編為藝術歌曲,全曲采用上下兩句節奏對稱的單三段曲式結構進行呈現,上半部分用鴻雁是表達和襯托當地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搭配上由低向高的旋律去將故事推向高潮,使得嚴肅狀態愈加明顯;下句旋律又由高到低進行呈現,是真正體現苦難與英雄的部分,稱頌之情與贊美之情貫穿下半部分。桑桐先生正是借助著民歌中故事的跌宕起伏合理的設計了旋律的變化,為我們構建出了苦難場景與英雄事跡,從而豐富了歌曲內涵,使得歌曲的歷史價值與自身音樂價值鮮明的體現出來。第一段伴奏用柱式和弦在最穩定的主屬、下屬中打開了雄偉篇章,英雄名字出現的同時,音樂力量稍有加強;第二段提示音量更輕,包含低聲嘆息與靜默中的致敬,高音中蘊含的旋律寓意著與英雄的惜別;第三段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伴隨情緒的高漲,音樂旋律與氣勢也得到加強,襯托著蒙古族人民不屈的意志和頑強的生命力,也潛藏著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就現在來看,該首作品依然具有較高的賞析價值。
同樣敘說勞苦大眾的苦難歷程的作品還有赫哲族民歌《烏蘇里麻木》,該首民歌被王云才先生和錢正鈞先生進行藝術歌曲改編,并在改編過程中保留了特有的襯腔。第一段整體音域從高向低發展,仿若在低嘆和小聲抽泣;第二段中的高音趨于平穩,仿若看穿苦難并無助的呻吟著;第三段加入了些許裝飾音,這些音符在跳動、在活躍,仿佛添上了一抹歡樂氣氛。整體而言,整體襯腔的情感趨于飽滿、豐富,并氛圍三個階段去闡述,使得改編后的歌曲情感因素被大大挖掘與展現出來,其獨有的赫哲族音樂色彩也在隱隱閃現,更為改編歌曲提升了品味與意境。
(三)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運用
民歌中對于親人思念之情的作品也很是常見,著名的云南民歌《想親娘》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原貌簡單、質樸,由上下兩個樂句構成四個小節的單樂段結構。整首描述的是一個在外游子思念母親的故事,也為此千里跋涉,帶著歸心似箭的心最終見到了思念深深的母親,但是相遇之時有著湍急的河水在阻礙,只能悲傷的離去,這份感人至深的情節與內容深深的打動的丁善德先生,該首原創作品也經由丁善德先生的手筆得以改編為藝術歌曲。顯而易見的是,該民歌原貌對于情感的表述和傳達有不盡人意的地方,仿佛未寫完的故事,丁善德先生調整了歌曲結構的同時,也進一步挖掘與延展了思念之情,從而把原來的雙句體結構擴充為有承上啟下的四句體結構,從原來的四小節擴充為四十八小節,相對單一的單樂段創新與設計成了相對復雜的單三段結構。在歌曲上半段旋律中,盡可能的保持了原作品的民歌風格,主題不變,仍舊是思念親人之情;接下來,降E語調轉變為了F語調,音區實現了較大程度提升,將主人翁的“行動”很清晰的展現出來,在音樂力度上稍稍做了調整,使得音符跳動的有韻律,實現了節節遞進,進而引出第三樂句,而后轉到第四樂句,描述與呈現的是水流湍急的危險場景,與主人翁的急切情緒形成呼應;在下半部分,降E語調重新歸來,雖然與上半段的語調基本一致,但是情緒已然不同,由最初的殷切變為了失落,凄慘氛圍縈繞開來,那是深深思念之情的鮮明刻畫,顯然是個悲情結局。
丁善德被原創民歌深深觸動,也竭力將該首作品以全新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不僅要求做到內涵與情感的傳承,還需做到內容與意境的緊密結合,可以說,正是由于復雜而殷切的情感的轉變,才最終成功的將該首作品改編為了藝術歌曲。歌曲中的亮點是加入了鋼琴伴奏,這使得傳統民歌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藝術歌曲。不管是伴奏的織體選擇還是旋律的變化,都注入了較多的心血,可謂用心良苦。藝術歌曲在保留原創民歌的風格與樣貌上,盡可能的加入了更多新穎元素,使得歌曲中的人物特點、人物心理及情感轉折更為鮮明和突出,營造了氛圍、激活了生機,音樂情緒被千呼萬喚的引導出來,而鋼琴伴奏的鋪墊是奠定情節的基礎,使得原民歌的靈魂及情感得到較大程度完善與升華。
結 語
綜上所述,情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源動力,是人們的所感、所發,這些都可在民歌中探取,而情感元素在民歌改編藝術歌曲中的運用更是不可或缺的,是值得研究與探析的。不管是民歌還是藝術歌曲,都是情感元素的重要載體,音樂創作者都應重視情感元素的應用,并竭力進行表現和傳達,使得藝術歌曲煥發生機與活力,切實展現其價值、意義,為更多人帶去更多、更美好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