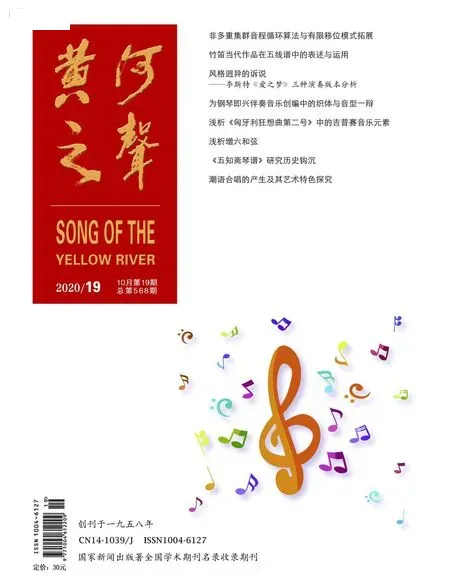“我住長江頭”不同演唱版本之我見
李德永 (山西藝術職業學院)
歌曲《我住長江頭》是我國藝術歌曲中的一首經典之作,由音樂家青主根據北宋詞人李之儀的《卜算子》而創作。青主原名廖尚果,早年參加國民革命軍,1912年赴德國留學,1920年獲法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還學習了鋼琴和作曲理論。1922年回國繼續從事國民革命工作。1927年廣州起義失敗后,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改名“青主”,并開始了“亡命樂壇”的生活。歌曲《我住長江頭》既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完成。詞人李之儀在作品中傳達出了同住長江邊,共飲長江水,卻因分隔兩地而不能相見的思念之情。此情如奔騰不息的江水長流不斷,此恨綿綿更無絕期,只能遙祝君心也似我心,彼此不負相思意。曲作者青主在隱姓埋名的生活中,既不能繼續自己熱愛的事業,也不能與相知的人見面,那種心境定是沒有體驗而無法理解的苦楚。但恰恰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生活符合了他創作《我住長江頭》的心情。所以筆者以為,青主在曲子的立意上與詞作者能夠完全吻合,除了一定的作曲技法以外,還有一樣東西彼此更貼近,那就是心境。帶著這樣的心境,筆者欣賞了《我住長江頭》的幾個不同版本的演唱,以下是筆者對不同演唱版本的一點拙見。
一、張權版本
張權是我國第一代女高音歌唱家。這個版本的演唱是鋼琴伴奏,歌聲在行如流水的分解和弦伴奏中開始,而且這種分解和弦始終貫穿全曲,給人以長江之水的流動之感。
下面首先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張權演唱這首歌曲的呼吸。張權在歌曲演唱開始進入時幾乎沒有痕跡,就像海水漫過沙灘時的悄無聲息一樣,這樣的狀態沒有很好的呼吸支持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全曲稍慢的速度,在音樂上形成了思念的氣氛,而這種稍慢的速度對演唱者的氣息支持更是一個考驗。張權在演唱這首作品時,氣息綿延悠長,連續不斷,起句與落句之間、聲音與氣息的把握和控制恰到好處,不漏痕跡。每一個樂句的呼吸都能把聲音送到結束處并繼續保持呼吸的張力。樂句間的銜接如水浪此起彼伏,源源不斷。整首歌曲的演唱和伴奏緊密貼合,絲絲入扣。
其次,讓我們來感受一下張權的咬字。在樂曲21小節處,演唱“此水幾時休,此恨何事已”這句時,“此”字咬字的力度和唱出輔音“C”時氣息的控制與把握極為到位。因為漢語拼音中聲母“C”是一個看起來不難但實際操作很難把握的舌尖音。如果在這個音上太強調咬字,則聲母“C”會有過重之感;如果故意不咬,則顯得沒有字頭有突兀之感;而張權版本的演唱所有這樣的字音處理的都非常恰當。在唱到29小節處,歌詞“只愿君心似我心”時,鋼琴伴奏右手由原來的分解和弦換成了柱式和弦,而左手低音區則變成了流動的分解和弦。在這種低音江水流淌,高音意志堅定的柱式和弦伴奏下,演唱者把“只愿君心”幾個字唱的飽滿而又有力,充分的呼吸和飽滿的聲音與伴奏融為一體,表現出了內心美好的愿望。在演唱“定不負相思意”這句時,鋼琴伴奏左右手都沒有了分解和弦的流動,這兩個小節是全曲伴奏中唯一一處沒有分解和弦的地方。這樣的配器處理好像讓人的思想從前句的美好憧憬中又回到了現實當中,演唱者稍帶一點哭腔和“思”字音上做的滑音處理,給人以現實的哀婉和怨愁之感,緊接著伴奏從“意”字開始又進入了分解和弦的流動,把人的思緒再次與永不停歇的長江之水相連,而演唱者把整句的呼吸和“意”字一直送到了人的內心深處,讓聽者有“情到深處人孤獨”的惆悵之感,以至于每次聽到此處必定會淚流滿面。本人以為此處是張權演唱此曲最催人淚下的地方。在歌曲的結束句上,唱出“定不負”之后,快速的深吸一口氣,在全曲的最高音小字一組的a音上唱出了“相思意”的旋律并一起呵成,而“意”字從ff-——ppp的過渡處理,氣息控制的恰到好處,在極具控制力的聲音中把人的思緒帶到了遙遠的長江那頭,聲音雖然越來越弱但是人的思緒和情感卻是越來越濃。
對于張權演唱的《我住長江頭》,筆者以為全曲完整、流暢、連貫并充滿了濃濃的思念之情。與一度創作者的立意完全吻合,這大概與其生活經歷有一定的聯系。曾經背井離鄉去異國求學,懷著赤誠之心回國后,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與自己的愛人天各一方,所以張權是在用心靈歌唱,故而能與一度創作者意境吻合,而這心靈的訴說又與用心聆聽的聽眾間產生了共鳴之感。
張權演唱的這首作品,唯一的瑕疵在于19小節的“水”字,從小字一組的e音向上方四度小字一組的“a”音跳進時,氣息似乎淺了一些,母音“ei”似乎唱得稍顯擠了一點點,這是筆者聽這首歌的唯一的一點遺憾之處。而藝術的美正在于有遺憾,所以我們一直在不懈的追求。
二、迪里拜爾版本
迪里拜爾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本人聽到的版本是她在北京舉行的獨唱音樂會中所唱的。這個版本的演唱與張權版本相比,速度快了很多,而且是管弦樂伴奏。就個人的感受而言,本人更喜歡鋼琴伴奏和速度稍慢的張權版本。迪里拜爾的演唱技術無可挑剔,但是這樣的演唱速度,筆者認為難以達到作者意圖表達的樂思,而且在聲音的運用上似乎戲劇性音色稍強了一些,反而有些破壞了藝術歌曲應有的意境。特別是“定不負相思意”這樣的樂句,表決心的態度有些過于外在的堅定,最后的結束句與張權做了相反的處理,她是在“f”的基礎上做了“ff”的結束。與張權的版本相比,反而缺少了含蓄內斂的詩意的傾訴,不容易讓聽者沉浸在音樂中,而只是從音樂的外部欣賞美好的聲音。不過在全曲最難唱的第19小節處,“水”字要從小字一組的e音向上方四度小字一組的a音跳進時,氣息和聲音的配合卻非常完美,而且窄母音“ei”在咬住字頭之后,迅速做了寬母音處理,因而此處聽起來聲音有支持,氣息很飽滿。這是與張權版本相比筆者較為欣賞的地方。
三、廖昌永版本
廖昌永是我國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的演唱版本是2001年春節歌舞晚會中唱的。歌曲伴奏是MIDI音樂,在整首作品的演唱中,很多間奏的部分加入了合唱。總體感覺是在那樣的配器下,再加上合唱大概對電視臺的娛樂形式來講頗覺熱鬧,但是如果從藝術的角度來理解,這似乎太“鬧騰”了些。當然作為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的聲音絕對無懈可擊,曲子的速度雖然比張權演唱的版本快,但是作為男聲的演唱筆者以為這樣的處理是可行的。因為男性和女性表達情感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對于廖昌永演唱此曲時的速度,筆者以為是可行的。但在唱到“只愿君心似我心”和“定不負相思意”兩個樂句時,速度略有些趕,到結束句時尤為明顯。對這首作品的處理筆者最不能茍同的是在樂曲第40小節和44小節處,也就是第二次反復演唱“此水幾時休”與“此恨何時已”這兩個樂句之后的兩小節間奏中,都無一例外的加入了銅管樂的音響,卻抹掉了原作本身流水般的分解和弦。第三次重復此句時,間奏做了同樣的處理,給人的感覺是把音樂的線條或者說思緒,從中間生生的切斷了,而且這個音響效果的出現極不合乎曲子的意境。筆者認為配器是這首作品的一大敗筆。而到這時,作為傾聽者已全然沒有了欣賞作品的心情。這也許與電視臺的分秒不差有些關系。然而欣賞一首作品,絕不止是欣賞一個演唱者美好的聲音,我們更多的想聽到演唱者內心對作品不同于他人的理解和詮釋。因為這個世界上并不缺乏美好的聲音,但不一定準能找到對音樂完美的詮釋者。
筆者認為廖昌永這個版本的演唱,一定有他不得已的初衷。如果在音樂廳換成鋼琴伴奏,相信憑借他那美好的音色和音樂修養一定能帶給觀眾超越這個版本的不一樣的結果。
結 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三位演唱者的聲音和演唱技術都無懈可擊,但是在本人的審美意向中更趨向于張權演唱的版本,同時在伴奏上也更趨向于用原版的鋼琴伴奏。因為作曲家為旋律編配的伴奏已經無可挑剔而又恰如其分,并且在演出中,鋼琴和聲樂能夠做到最完美的融合。這一點是這首作品的管弦樂版本所無法比擬之處。張權的演唱從聲音到情感既干凈又純凈,而且能把人帶入音樂的意境中,讓你打開心扉與之相通。當聽者的內心和歌者的內心互相交融時,音樂這個媒介做了我們之間最好的橋梁。
當然,對藝術的追求應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世界上如果有一千個讀者,那么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此通過對同一首作品不同演唱版本的分析,并不是抹煞三位演唱者深厚的演唱功底和藝術造詣,而是將有助于讓我們通過對比找到屬于自己的音樂風格,并能通過自己獨特的藝術魅力詮釋出最美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