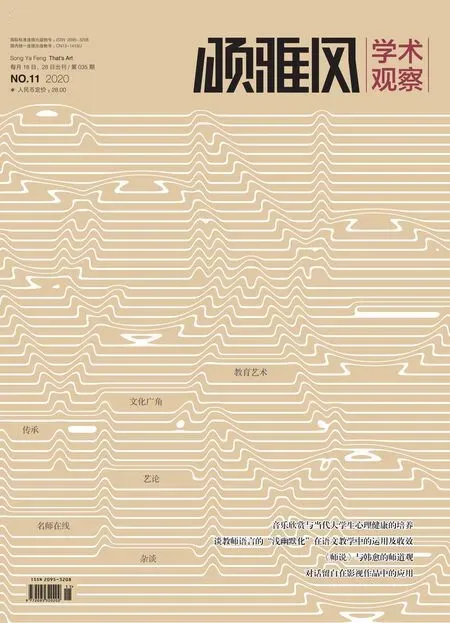外來文化對中國畫影響的具體體現
——以禪宗為例
◎吳丹燕
儒釋道三大哲學思想經過漫長的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藝術文化,在中國畫的繪畫題材、造型技法、創作目的、創作理念以及創作思維等方面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在中國畫的表現技法和繪畫創造觀念、創作題材和風格流派的表現之中最為明顯。石窟藝術是儒釋文化融合發展的產物,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包含著本土化的外來文化內涵,不僅僅影響著石窟藝術的內涵,也影響著表現技法。
一、對中國畫表現技法影響
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國畫就已經和釋家文化結緣了,到了唐代便已經發展到了巔峰狀態,比如在當時流行的人物繪畫的四種花樣,稱之為“四家樣”。四種畫風分別以張僧繇、陸探微、吳道子和周昉的姓命名。張懷瓘評語“象人之美,張(僧繇)得其肉,陸(探微)得其骨,顧(愷之)得其神”。“吳家樣”把異域人物中國化了,無論是從臉型還是從衣冠服飾上來說。形象上首先從魏晉風度的“秀骨清像”到“張家樣”的面短而嚴厲,后面到“吳家樣”中融入的佛像當中的圓潤的臉龐和氣象的氣質。最具特色的是吳道子畫中“行筆磊落,揮灑如莼菜條,圓潤折算,方圓凹凸”的線條。這種加粗加厚的線條,不像之前的鐵線描那么單一,變化較多,運用了筆的抑揚頓挫輕重緩急,有節奏韻律地增加了對象的質感和立體感。從單一的線條到線條有節奏的變化,這個發展對中國畫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線條的把握上又傳承了陸探微和顧愷之的神形兼備,再到后來的以胖為美,表現為相傳周昉所作的有著貴婦般圓潤的《妙創水月觀音》。到了這,唐代的人物繪畫就已經完成中國化,形成了中國所特有的繪畫體系和風格。
二、對中國畫創作題材的影響
自從釋家思想在中國盛行以后,中國畫出現了以此為題材的繪畫,如趙孟頫的《紅衣羅漢圖》,作品中畫了一紅衣僧人,頭上有光環,坐于大樹下,滿頭深褐色短發,絡腮胡須濃密,鼻子隆起,耳佩金環,目光深邃,皮膚黝黑,壽眉朱唇,座下鋪朱紅毛氈,身傍置一雙紅色僧鞋,面帶微笑,表情靜穆而慈祥,左手伸出,手心向上。作品是借悼念去逝的薩迦派帝師膽巴之名,隱喻正在薩迦大寺做總持的故宋恭帝(瀛國公),以寄托畫家內心的哀婉情思。在繪畫的表現下,故事栩栩如生,十分鮮活,還有表現禪宗的公案故事,以及自然界中的山河大地、花果鳥獸(如猿鶴、牧牛等),均假借物相,以寓意禪機,他們在作品中借用禪意寄托情感表現自我。也有佛菩薩像,或羅漢像,他們多以自在為特色。更有在繪畫中題跋,使畫中有詩,詩中有畫,詩畫中有禪意,古代的山水畫中大都會有題跋,用來表達意境,其中就不乏表現禪宗思想和精神的作品,也使繪畫的意境更上一個層次。
三、對中國畫創造觀念的影響
唐代創立的凈土宗和禪宗,為釋家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新的契機,也推動了外來文化的兼容性發展。禪宗的出現,融入了中國的道教思想,而禪畫又是中國禪宗的一大特色,是修禪者用筆墨表達禪道的繪畫。所以說禪宗又是中國化后的外來文化,然而這也激發了唐宋以來中國繪畫的新紀元。禪宗講究頓悟成佛,“一剎那間,妄忘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通過禪定達到無我、忘我,達到心如止水的境界,他們在創作上格外注重心靈的感悟。將心靈的感受融入到作品中,達到忘我的境界。五代兩宋是禪畫的興盛時期,隨著禪宗的興盛,禪法更廣泛而深入地體現在中國畫中。“元四家”也都曾潛心參禪學佛,清“四僧”對后人的影響也都很大。他們大都以山水畫為主,表現自我或者是某種意境。如表現弘仁的《山水圖》表現禪宗的空凈寂寥的意境;朱耷的《魚石圖》《忘機圖》,表現了意趣、超塵、凝練之氣。這些作品不僅僅旨在描述經典的故事,更在于表現禪宗中的“靜”“意境”,表現對這些故事的頓悟之情,表現物我和一,內心與外境的融合在作品中的呈現。可以說中國古代畫家有不少的禪修者,禪宗精神對于中國畫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中國傳統藝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語
綜上所述,雖然外來文化對于中國畫的影響在作品上,在觀念里,同時也在技法表現中,但是也不僅僅只在其中。歸根結底,外來文化對于中國畫的影響主要還在于對人們的深層思想觀念上的影響。禪宗對中國畫的影響,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處處都表現出中華人民對外來文化極大的包容度以及對新興事物極大的變通能力,懂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也是中國畫過了這么久,歷經千年經久不衰,依然能夠綻放光彩的原因吧。藝術中不可缺少思想,外來思想對中國繪畫的影響,呈現為一種本土化,中國化的狀態,我們可以從那奔放的線條,美麗的色彩,動人的形象,豐富的構圖中感受到無所顧忌的吸取和創新,無所束縛的開放與自由,對人間現實的肯定和憧憬,同時更能夠感受到充滿想象和熱情的中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