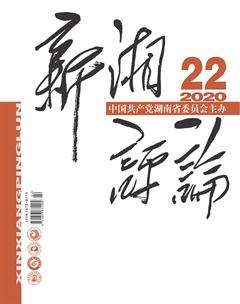我的苗家房東
申宸

如果你走進十八洞村,見到一個穿苗服的婆婆,臉上布滿皺紋,身體狀態卻很好,并不費力地拄著一根拐杖,臉上帶有慈祥而溫暖的笑容,那很有可能就是碰到阿婆了。
阿婆是五哥的媽媽,在村里工作的一年多時間,我吃住都在五哥家。
阿婆今年86歲,阿爺今年91歲。在這個年紀,阿爺和阿婆身體之好實在是讓人驚嘆。每逢鎮上趕集,他們還會自己背上包,走上幾公里路去鎮上轉轉。
一年四季,阿婆都穿著苗服。對她來講,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大概就是早上起床之后包頭帕了:先把頭帕整理好放到板凳上,將頭發一遍遍梳順后盤起,然后左手舉起用于固定,右手用力一圈圈地把頭帕裹起,裹好之后還要讓阿爺看看直不直、挺不挺。阿婆的動作始終穩健莊重,以至于我覺得更像是在進行一種儀式,一種她的外婆她的母親教給她的,與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祖先對話的儀式。
湘西苗族地區,流行著方言(西南官話的一支)和苗話兩種地方話。阿婆只會說苗話,方言就會講“七飯”(吃飯),而苗話我只會說“汝”(好)和“幾客”(謝謝),一開始,我和阿婆有效的語言交流,也就局限在這幾個詞。有時阿婆用苗話和我說上半天,我知道她肯定是在說某件很有意思或者有趣的事情,但又聽不懂,就只能時不時地點頭,不過到后來,隨著了解的加深,再借助手勢和動作,我對婆婆講的話慢慢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了。有一天,阿婆和我講話的時候,五哥也在場,他吃驚地問我:“你現在聽得懂苗話了?”我自豪地告訴他,我是從阿婆的表情和手勢猜出她要說什么。
工作不忙的時候,我會一個人坐在屋里看看書。這時只要阿婆在,肯定會四處“翻箱倒柜”,找家里好吃的給我。“落落,七!”(來來,吃!)如果我拒絕,阿婆就會換一種吃的,繼續遞給我。有一次,五嫂跟我說:“婆婆讓我告訴你,她不會用液化氣做飯,看你在家里沒東西吃,只能拿零食給你,希望你不要嫌棄。”這讓我特別不好意思,其實我只是不太愛吃零食。在這之后阿婆如果再遞給我吃的,我都會馬上接住。
村里的冬天特別冷。有一次進城,我去超市買了雙厚厚的老布鞋準備在村里穿,到村里后才發現,收銀員忘記解開防盜扣。阿婆主動來給我幫忙,但我倆忙乎半天還是沒打開。等我回到房間,阿婆竟然爬上二樓狹長的木樓梯,給我送了兩把菜刀來,想讓我用菜刀把防盜扣給劈開。那一刻,我先是覺得好笑,后來卻有點想哭,這么大歲數的老人家,冒著危險爬上爬下,愛護晚輩之情令人動容。
我離開村里的時候,阿婆從柜子里拿出一匹家織布,讓五嫂拿出皮尺給我量好身材做兩件衣服。我不好意思拿,阿婆卻一定要送,甚至擋在了家門口,不拿不讓走。村干部勸我:“收下吧,婆婆這是把你當自家人了!”
第一次見到阿爺的時候,他剛從縣城回來,藍色中山裝扣得整整齊齊,里面還穿著件白襯衣。阿爺雖然年紀大了,但他是個閑不住的人:白天喜歡在自家地里“搞勞動”,去鄰居家里幫忙,到村部看看有沒有什么新活動……為了去遠點的地方,阿爺還買了臺電動輪椅。到了晚上,阿爺就愛看電視新聞,并對著字幕一字一句地讀出來,我曾經和他開玩笑,說他白天是體力勞動者,晚上是“口力勞動者”,把他逗得哈哈大笑。
阿爺年輕時搞過社教,修過鐵路,去過全國各地,是“革命、建設、改革”的親身經歷者。每次和阿爺聊天,他跟我講起解放前老百姓和國民黨的尖銳斗爭,講起大隊干部舉火把走夜路去開會、公社干部從家里帶大米去上班,還有聊起苗族的“巴代”“趕秋”“接龍”等習俗,我都覺得自己像是在聽一部湘西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變遷的“口述史”。阿爺講得口若懸河,我聽得津津有味。
阿爺還有個光榮的身份:共產黨員。村里修了新村部之后,我第一次從村部參加完主題黨日回到住所,平時一直和顏悅色的阿爺卻很嚴肅地叫住我:“為什么今天開黨員會沒通知我?”村里考慮到阿爺年紀大了,住的地方離新村部遠,就沒有通知他參加。我跟阿爺解釋之后,阿爺仍然很有意見:“我又不是走不動了,支部開會我當然要去。”此后,每次黨員過組織生活我都會通知阿爺,阿爺也是一次不落準時參加。后來,村里組織黨員和群眾結對互助,阿爺主動申請擔當結對工作,要求和年輕黨員一個標準。阿爺常常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共產黨這樣對老百姓好!”
湘西州第一條鐵路是上世紀70年代修建的枝柳鐵路,阿爺一直很自豪自己作為民工參與了這條鐵路的修建。他從電視上得知湘西正在修建第一條高鐵,經常問我:“這高鐵修到哪里了?建好了去長沙要多久?”阿爺從沒乘過高鐵,他說到時候自己一定要去感受下,每小時350公里到底有多快。
阿爺和阿婆的兒子五哥個子不高,身材偏瘦,從不多話,性子也不急不躁。家里姊妹六人,他排行老五,大家就都叫他“五哥”。
五哥早些年并不在村里,而是在吉首跑出租。2017年,五哥看到村里旅游發展形勢好,他放棄了在城里收入還不錯的工作,回到家里開起了全村第一家民宿。他和五嫂,既是老板也是員工,不管有沒有客人,每天都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凈凈。五嫂從小就學苗繡,也喜歡苗繡。在政府的幫助下,五哥五嫂成立了苗繡合作社,帶領周圍的繡娘們在增加收入的同時,也積極推廣苗族文化。
五哥勤懇、善良,又有一手好廚藝,于是村里旅游公司成立后專門聘請他給員工做飯。五哥每天早上6點起床,去鎮上買菜,回來之后洗菜、切菜、煮飯、炒菜,等員工們吃完,馬上洗碗搞衛生,忙得腳不沾地,往往要到晚上七八點才能閑下來。這一天天循環往復,五哥也不覺得單調辛苦。在他看來,靠自己勞動掙得的收入,踏實又安心。村里旅游紅火起來之后,五嫂也被旅游公司聘請,每天坐在特色紀念品商店織布、繡苗繡,承擔起了向游客展示苗族非遺工藝的任務。五哥五嫂,一個是“站著掙錢”,一個是“坐著掙錢”,用村里人的話來說,“不用種地、在家門口掙錢的事,以前哪敢想啊。”
今年過年,五哥給我寄來了親手熏的臘肉,吃著臘肉,我心想明年高鐵通到湘西,一定要回村里去看看,看望阿婆和阿爺,看望五哥一大家子人,也重溫自己在村里工作的那段難忘而又充實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