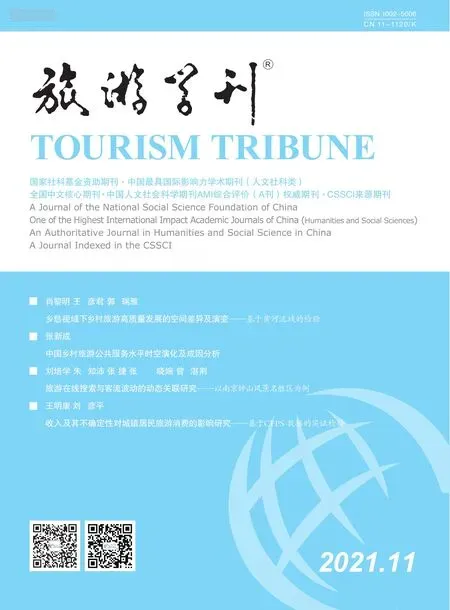自然災難地黑色旅游發展:居民感知與社區參與
王金偉 謝伶 張賽茵



[摘? ? 要]近年來,黑色旅游已成為自然災害地災后恢復重建的一種重要形式,受到國內外旅游學界和業界的廣泛關注。社區居民作為核心利益相關者,在黑色旅游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現有相關研究卻十分缺乏。文章以吉娜羌寨為例,運用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法,探討了社區居民對黑色旅游發展的感知及其應對旅游業發展演化所采取的參與行為。研究發現:(1)對于當地居民來說,地震遺址是見證和紀念災難、緬懷逝者、傳承社區記憶的“物”和“場”;(2)當地居民對發展黑色旅游普遍持支持態度,他們認為黑色旅游是推動災區恢復重建、促進傳統文化保護和族群認同的重要力量;(3)社區居民與“他者”(游客、外來商戶)角色關系的重構,導致了“我者”和“他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給當地旅游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4)社區居民采取了多種“自覺”參與旅游發展的行動,助推旅游業轉型升級。當地的社區參與已開始從“外部推動”向“內部自覺”轉變。
[關鍵詞]黑色旅游;自然災害;社區居民;汶川大地震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20)11-0101-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0.001
引言
自然災害是“一場自然觸發的人道主義災難”[1],常導致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同時還可能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但其所遺留下的遺址遺跡、遺物、遺構,以及后期修建的紀念性設施亦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遺產”和景觀[2],并演化為災后旅游消費(consumption)的重要方面[3]。長期以來,前往地震、海嘯、颶風等自然災害發生地或相關場所進行參觀游覽的活動經久不衰,并受到眾多旅游者的追捧[4-6]。一些學者常將這種旅游形式稱為“災后旅游”(post-disaster tourism),其屬于“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一類典型形式[3]。近年來,利用災難廢墟、遺址遺跡、紀念設施等發展黑色旅游已成為國內外眾多自然災害地災后恢復重建的一種重要形式[4,6-7],備受旅游產業界和學術界關注。
社區是旅游業發展所依托的重要社會實體。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產方式常會受到旅游開發的影響,但反過來,他們的態度和行為也會影響到旅游開發和管理[8-9]。同時,在旅游世界中,社區居民扮演著多重角色,他們既是目的地的主人,又是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和人力資源的重要提供者[9]。相應地,社區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態度也是多重和復雜的。自然災害地的社區居民大多曾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和嚴重的心理創傷,災后發展黑色旅游不僅涉及地域經濟重建,還會含涉諸多倫理道德和社會文化問題[10-12]。因此,黑色旅游對于他們來說,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鏡像”認知以外,可能還隱蔽著繁復的多重心理面相和特殊社會文化意義。探究社區居民的黑色旅游發展感知和特殊生活形態,對于刻畫其復雜心境和構建災后旅游管理體系至關重要。
縱觀現有黑色旅游相關研究,多聚焦于“供給”,探討黑色旅游與社會文化的關系、黑色旅游開發和管理問題[13-14],以及立足于“需求”視角關注游客動機、黑色旅游體驗等[3,15-18]。而對于作為目的地“主人”的“社區居民”則關注不足,相關研究甚少[19-20]。毫不夸張地說,社區居民已成為一個被現有黑色旅游主流研究沉淪的“邊緣人”。
因此,本文擬以汶川大地震后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北川縣”)吉娜羌寨為例,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探尋當地居民對黑色旅游發展的感知及其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希望通過本研究,提供一個基于社區居民層面的黑色旅游發展研究新視角,同時也為案例地及相關自然災害地的旅游經營管理提供參考。
1 文獻回顧
1.1 黑色旅游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黑色旅游”最初由Foley和Lennon于1996年提出,意指“到與災難、死亡、悲劇等相關的地方進行參觀游覽”的活動[21]。由于特殊的情感和倫理道德內涵,“黑色旅游”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提出至今,一直備受傳統倫理挑戰。一些人批判此術語可能會傳遞負面的信息和消極情緒(例如焦慮、憂愁、悲傷),讓人產生“不適”或者帶來社會矛盾沖突,甚至是道德恐慌[22-23]。為了規避“黑色旅游”一詞所帶來的“負面風險”,一些學者試圖用其他較為褒性的詞語來進行同義替換,例如:祈福旅游(prayer tourism)、復興旅游(reconstruction tourism)等[24]。同時,由于旅游對象物(tourism attraction)常與死亡和災難交織纏繞,黑色旅游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對死亡和災難的“商品化”,甚至是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會對受災(難)者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有悖倫理道德,因而備受爭議[25-27]。
但黑色旅游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學者們提到,在一些與戰爭、種族滅絕(大屠殺)等相關的地方,黑色旅游不僅可以作為一種展示與紀念過去悲慘歷史、祭奠遇難者的重要方式,同時還能夠提供一個讓人們正視和反思人類過去的殘暴與過失,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和自由的機會,并防止類似悲劇重演[28-29]。同時也有學者認為,黑色旅游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直面災難和死亡的機會,使人們可以更好地探尋生活和生命的意義[20,30-31]。更為重要的是,對于許多旅游地來說,黑色旅游是一種地域振興的重要手段。尤其在那些剛發生自然災害不久的地方,黑色旅游可以在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文化復蘇(重建)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4,32-34]。
毫無疑問,黑色旅游作為一種重要的現代性“休閑活動”[35],不僅對旅游者個體本身具有積極的作用,同時也對旅游地,尤其是受重大自然災害襲擾后百廢待興的受災地來說,是一種對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進行恢復重建的重要力量。正因如此,近年來,對自然災害地及其相關物象進行針對性保護和旅游活化(黑色旅游),已然成為一種流行做法。
1.2 社區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感知與態度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社區居民旅游發展感知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相關成果大量涌現。現有研究一般認為,旅游對社區的影響包括經濟影響、社會文化影響和環境影響3個方面,同時每個方面又包含正面和負面兩類[36-37]。社區居民對上述旅游影響的感知常常同其對旅游發展的態度緊密相連。一些研究者發現,通常情況下,當居民所感知到的積極影響越大時,對旅游發展支持度會相應地增大;反之,支持度則可能降低[38-42]。此外,社區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和旅游發展態度也并非簡單的贊成或反對,而是可以細分為多種形式,例如完全反對、憤怒、容忍、中立、漠不關心、擁護等[43-45]。同時,一些學者還指出,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和旅游發展的態度,并不是處于“真空狀態”,而是受到旅游發展階段、當地社會文化環境、政策條件等因素的影響[44,46-47]。另外,當地居民的一些自身因素,例如性別、受教育程度和從業經歷等也影響著他們的旅游感知和發展態度[48-50]。
作為目的地的“主人”,社區居民是黑色旅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主體。Yuill指出,社區居民(包括災害幸存者、遇難者家屬等)是黑色旅游發展中的重要利益相關者,必須對其加以關注[10]。黑色旅游地居民常常是災難和悲劇的遭受者及(或)其家屬,因此對于黑色旅游這種“對災難和悲劇的消費活動”會非常敏感[10]。他們的傷痛記憶和心理敏感性,及其關于黑色旅游的態度會對后續相關開發和管理產生重要影響[11-12]。因此,不論是在黑色旅游的實際發展過程中,還是在理論研究中都應該對當地居民的態度和情感加以充分關注。
近年來,學者們已逐漸意識到社區居民在黑色旅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對其進行了深入探討。Kim和Butler以澳大利亞臭名昭著的雪鎮謀殺案為案例,運用觀察與訪談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當地社區對發展黑色旅游的看法[12]。Wang等通過對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當地居民的調查,分析了居民的地方認同動因(place-based identity motives)與黑色旅游發展態度之間的關系[20]。同樣地,Wang和Luo以汶川大地震后的北川縣為例,通過問卷調查對當地居民的黑色旅游影響感知和態度進行了分析,并揭示了居民對黑色旅游發展的態度差異[19]。盡管學者們對人為事件(謀殺)和自然災害(地震)相關地的居民進行了調查研究,但是總體來看目前學術界對黑色旅游地社區居民的關注還較少,不利于從理論和管理視角深入認識和理解黑色旅游地發展與社區居民的關系。
1.3 旅游發展中的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的概念最早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它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要素被提出,是西方民主運動的產物[51]。1985年,Murphy首次將其引入旅游研究之中,提出了以社區為導向的旅游規劃[52]。此后,基于社區的旅游發展規劃被認為是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與方法[53],受到了國內外旅游學界的廣泛關注。真正的社區參與看重社區的發展,而非單純的旅游發展。因此,學者們認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在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和需求,并將其作為主要的開發主體和參與主體,以便在保證旅游可持續發展方向的前提下實現社區的全面發展[54-56]。
早期研究者們更為關注旅游發展與社區的相互關系,以及社區在旅游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多數學者認為,作為目的地管理中的重要因素,社區應最大限度地參與到目的地的旅游發展和管理之中,以促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和社區的和諧進步[57-58]。隨著研究的深入,社區參與的關注重點開始轉向社區參與的影響因素和權利問題(如社區增權、法律權利),以及社區參與模式等。學者們研究發現,社區參與受到許多來自不同維度的復雜因素影響,包括諸如社區居民的性別、職業、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統計學特征[59-60],居民的興趣偏好、參與程度、地方依戀等內在因素[61-63],以及地理環境、文化環節、社會經濟等外部因素[62,64-65]。此外,增權作為影響社區參與的重要因素和實現社區參與的重要途徑,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研究發現,它不僅有助于被邊緣化的社區產生和培育社會資本,還可以增加社區福利,為社區發展提供可持續動力[66]。近年來,在中國本土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除了西方學者所倡導的信息增權和教育增權以外,還需將增權的范圍擴展到制度增權和個人權利的增進,以打破不平衡的權力關系,保障社區在旅游開發中的合法權益[53]。目前,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制度增權已大體形成了立法增權與依法增權的二元分野態勢,但如何全面保證社區權益,還需從根本上加強制度建設和權利實施[67]。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模式,大致可分為社區主導型、企業主導型、政府主導型和混合型等類型[56],但對某一旅游目的地來說,具體適合哪種發展模式,還需要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并考量內外部條件,進行綜合研判。
總的來說,學界對于旅游發展中的社區參與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且較為深入,但研究對象多集中于民族地區和鄉村旅游地,黑色旅游地社區參與的相關研究尚未見諸紙端,缺乏關注。通常來說,與一般意義上的旅游地有所不同,黑色旅游地更具情感性(尤其是悲情化)的要素,同時,當地居民對于死亡、災難事件以及倫理道德方面的關注也更加強烈[11-12]。因此,對黑色旅游地社區的研究不僅需要考察社區居民作為旅游地“主人”的感知和態度,同時也需要關注他們在黑色旅游發展中所展露出的特殊行為。本文立足于社區參與和社區居民感知的現有相關研究,考察自然災害地居民對于黑色旅游發展的感知及其應對旅游業發展演化所采取的行動措施(社區參與),希望能為全面理解黑色旅游地發展和當地社區居民關系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也為相關旅游地管理提供參考。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案例地
吉娜羌寨,位于四川省北川縣擂鼓鎮,屬于羌族居民聚居村寨(圖1)。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當地位于地震極重災區的核心地帶,遭受到毀滅性破壞,幾乎所有房屋倒塌,20余人遇難。地震后不久,當地政府便啟動了災后重建工作,并按照傳統羌族聚落特征對當地進行了規劃設計,在原貓兒石村一社和二社范圍內修建了碉樓和羌族傳統院落。同時,為了恢復和保留羌族文化,還設計建造了篝火廣場(又名文化廣場)、祭壇、傳統文化景觀小品等,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空間”。吉娜羌寨是當地災后經由政府統一規劃、最早建成的羌族村寨,被譽為“北川第一村”。
寨子依山傍水,碉樓傲然挺立,風貌獨特,加之位于前往汶川大地震重要核心紀念地“北川地震遺址區”(含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唐家山堰塞湖等)的主干道上,每年都能吸引大量游客到訪。據當地村委會統計,僅2011年就接待游客20余萬人次,實現經營收入約200萬元①。2013年,吉娜羌寨同北川地震遺址區、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館等多個景區(點)共同組成“北川羌城旅游區”,成功晉級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成為汶川大地震災后產業重建與旅游業融合發展的一個典范。
2.2 資料收集與分析
文章以吉娜羌寨為案例地,主要采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質性方法展開研究。研究人員于2013年4月深入吉娜羌寨和北川地震遺址區進行田野調查。通過參與式觀察的方式與當地居民和游客深入接觸,同時了解村寨的地形、布局、居民生計方式、旅游發展狀況、主客互動情況等。在后續的深度訪談中,為兼顧樣本的代表性和完整性,同時考慮到自然條件、交通因素等對當地旅游發展造成的影響,研究者采用隨機抽樣與定點抽樣相結合的方式②,以理論飽和為原則,最終選取了23位吉娜羌寨居民進行訪談。受訪者的主要構成情況如表1所示③。樣本涵蓋了不同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在不同區位的受訪者,且除原住民外,還包括3位來自外地的旅游餐飲經營者。如是,確保訪談對象的代表性。
深度訪談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主要側重3個方面的研究問題:(1)地震遺址的價值認知;(2)黑色旅游發展感知和態度;(3)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和管理情況。考慮到“黑色旅游”一詞較為敏感,可能觸及當地居民的傷痛心理,因此除了個別特殊情況以外,訪談中已盡量回避使用該詞,而使用“地震遺址旅游”等當地居民較為常用的詞語作為替換。此外,訪談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與受訪者進行互動和探討,并在需要時進行適當的引導、追問和探究,以確保獲得更全面、有效的信息。調研結束后記錄下部分居民的聯系方式,以備后期補全缺漏和追加調查。
本研究采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這是一種在質性研究中較為常用的分析方法,它強調對訪談資料進行組織和深描(thick description),從而識別出資料中所要表達的主題觀點和隱藏的微觀情境[68-69]。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按照質性研究和主題分析法的程序[68,70-71],首先對訪談資料進行開放式編碼,然后分析總結不同編碼間的邏輯和語義關系,對類似編碼進行合并,進而歸納并提取出高一層次的類別或主題。為了確保編碼的科學性和可信度,由接受過培訓的兩名編碼人員分別對訪談文本進行獨立編碼,提煉文本中的關鍵事件主題。而后,比較兩者的編碼內容,找出不一致之處,進行反復討論,最終使編碼歸類達到一致。通過這一過程,最終從訪談材料中歸納出兩個核心主題:社區居民對地震遺址和黑色旅游的感知,以及旅游發展中的矛盾沖突與困境突圍。
此外,在對編碼后的內容進行解讀和分析時,注意反復比對、多次回歸原始情境,從受訪者角度理解其話語表征,力求在具體多變的情境中解釋事實表面之下的心理隱蔽,以透析當地居民對黑色旅游及其發展的感知、態度和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行為。
3 地震遺址與黑色旅游的居民感知
3.1 地震遺址:被賦予意義的“物”和“場”
汶川大地震后,北川縣保留了大量災害遺址、遺跡和遺構,并修建了相關紀念設施。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當地居民往往將這些遺址遺跡、紀念設施等統稱為“地震遺址”,并對其表現出高度的關注。同時,他們還賦予“地震遺址”一定的社會和空間意義,使其成為“有價值”的事象,并演化為日常生活世界中必不可少的“物”和“場”。
首先,對于當地居民來說,地震遺址是汶川大地震的見證物,真實記錄著災難的信息。汶川大地震使當地居民遭受了嚴重的財產損失和難以愈合的心理創傷。雖然地震后當地社會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基礎設施得以重建,但是對于當地居民來說,這段悲痛經歷刻骨銘心,永遠無法抹去。地震遺址展示了地震災難和抗震搶險的全過程,是記錄災難信息的重要載體。將地震遺址保護起來不僅可以讓人們銘記這場災難,同時也能讓子孫后代知曉和了解這段悲傷歷史。例如,居民I-22提到:“把地震遺址保護起來很有意義啊,讓你知道那年的地震有多震撼、又有多少人遇難……很多人的親人、家屬都在地震中遇難了,(將地震遺址)保護起來,讓后人知道這件事……”
其次,在當地居民的視野中,地震遺址是遇難者的歸宿地,是緬懷親人、祭奠逝者的場所。“老縣城死了很多人……還有很多人沒有挖到,找不到了(失蹤了)”(I-21),那里就是一個“大墓地”,里面埋葬著眾多遇難者遺體。筆者調查中還得知,有的家庭更為悲慘,在地震中“全部遇難”“無一生還”。每到地震紀念日(5月12日)和一些中國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節),許多當地居民都會攜帶祭祀物品,到北川老縣城地震遺址和其他親友埋沒地祭奠遇難親友,焚香點燭。
另外,在當地居民心目中,地震遺址不僅是“我者”(當地人)緬懷親友的地方,而且隨著旅游業的發展,也演化成了“他者”(游客)紀念和緬懷地震遇難同胞的場所。居民I-01在訪談中提到:“有的游客給他們(遇難者)燒紙,有的又給他們(遇難者)磕頭……對死者很尊重”。在筆者的多次實地調查和參與觀察中,也屢有見到類似情景,對那些看似沒有血緣關系的遇難同胞,諸多游客卻肅穆緬懷、掩面慟哭或默哀獻花。毫無疑問,在旅游世界中,地震遺址已經演化成為“我者”和“他者”共同的意義象征物。
3.2 黑色旅游:社區發展和族群認同的推動力
吉娜羌寨的旅游業是在災后社區重建和傳統文化復興的基礎上孕育起來的典型“社區型黑色旅游”。在旅游業的發展過程中雖然融入了諸多羌族傳統文化和鄉村社區要素,但是“災難”“悲情”等黑色要素一直是吸引游客前往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貫穿游客整個游程的核心話題。在這里,社區居民不僅是地震災難的受害者和當地文化的展示者,同時也是當地旅游業開發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他們對當地旅游業所帶來的影響最為敏感,在他們眼中,黑色旅游已成為帶動社區發展、促進傳統文化保護和族群認同的重要力量。
首先,受訪者認為旅游業促進了社區經濟發展,改善了社區生活環境,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發展旅游業好啊,能給我們帶來財富”(I-19),“最多的時候,村子里有50來戶經營餐飲的。游客多的時候生意很好,收入也還是很可觀的”(I-20)。一些居民表示,地震后的兩三年間有好些農家樂的經濟收入都非常可觀。“(某某家)天天賣一萬多兩萬……那天80多桌(客人),賣就賣了兩萬多”(I-07),“(某某家)三年中賺幾百萬”(I-08)。筆者調查得知,地震前當地幾乎沒有人有“小轎車”(私家車),但由于經營農家樂賺了錢,很多人都購買了私家車,這一點也得到了I-06等居民的認同。當地居民還提到,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我們這(里)現在環境好了,以前有時候還臟兮兮的”(I-16)。2012年制定的《貓兒石村未來三年幫扶發展計劃》中寫到,“(計劃)山上種樹,山腰種李子、核桃等觀花嘗果的經濟林,山腳和房屋后種植觀賞性花卉和盆景,將村子建設成花園式羌寨”1。雖然這是調查時收集到的“未來發展規劃”資料,但是筆者發現,當地社區環境已屬“花園式”優美,看不出太多地震遺留的“傷痕”(圖2)。同時,居民們還提到“(村民)都更有素質了,不像以前那樣會說粗話”(I-16),“現在治安還是搞得好了,沒有了違法犯罪現象”(I-17)。此外,受訪居民還表示,因為發展旅游業,交通、通訊條件等基礎設施也得到改善,極大方便了當地居民的生活。
其次,發展旅游業有利于羌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居民的社區和族群認同。“我是羌族人,但小時候一般都是和漢人接觸,不會說羌語……不管什么就像你干活一樣,久了不用就慢慢淡忘了。地震后因為要搞旅游,有人來教我們說羌語,開始不曉得是啥意思,后來慢慢就知道了……以前唱歌用漢語,原來跳的舞也不是這個舞(羌族舞蹈),地震那年說要發展旅游業,就請了鎮上川劇團的老師來教,又在茂縣請了幾個唱酒歌的人……現在我們都會跳羌舞唱酒歌”(I-16)。在筆者的走訪中還發現,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羌族文化不斷被搬上舞臺,成為“他者”凝視的對象,無形中也刺激了當地居民反思在歷史長河中早已淡漠的族群文化,激起羌族傳統文化保護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居民的社區和族群認同感。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進一步考察當地發展旅游業可能帶來的倫理道德沖突,筆者多次直接或間接詢問當地居民旅游開發是否會“觸碰當地人的傷痛”“揭傷疤”“不尊重遇難者”等,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否定的。似乎外界廣泛關注的黑色旅游倫理道德問題,在大多數當地居民心目中并不存在。反過來,雖然有居民提到個別游客的行為有所失范(如在地震遺址中大聲喧嘩),但他們認為旅游者的到訪大多是出于“關心”和“同情”,甚至是對遇難者的“紀念”,因此不會帶來“傷害”,更不會有悖倫理道德。“沒有哪個來看笑話……外地人(游客)來,好多都是同情我們的……外地人對我們關心的很多,關心我們的人占80%嘛”(I-03)。“游客對死者很尊重,又給他們燒紙,又給他們磕頭,應該是對他們很尊重的。地震遺址旅游對地震中的死者不尊重,我就非常不同意這句話……”(I-01)盡管如此,對當地旅游開發時還是有必要綜合考慮倫理道德問題,以及當地人的情感和心理承受能力。同時,加強對游客行為的引導和規范,以避免對當地居民造成不必要的“二次心理傷害”。
當然,旅游業的發展也會給當地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尤其是因旅游發展不均衡所導致的經濟差距。受訪者提到:“不好的影響的話……發展旅游業對老百姓最好了嘛,但是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連肉都吃不起”(I-16)。“我們住在上面(山上)的都沒掙到錢,人家住在下面的一天至少要掙好幾百塊”(I-04)。“人家開館子搞餐飲,位置好的,一年要掙一二十萬,我們地理位置稍微差一點的,一年掙個一兩萬,還有掙不到錢的,那些地勢高的、最上面的(山上),一分錢都掙不到”(I-19)。此外,還有很多受訪者反映,村民間由于爭搶客源以及經營競爭而出現了一些矛盾。毫無疑問,當地旅游業發展也給社區帶來了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盡管如此,絕大多數受訪者對當地旅游業發展仍持積極態度,并表示贊成和支持發展旅游業。“發展旅游業,(我們)肯定很高興嘛”(I-18)。居民I-17提到:“我們這退耕還林的地很多,有的家有兩三畝,最多的有五六畝。還了之后每年可以領錢,不過一年才一百多塊錢一畝。就這么一點地,不搞旅游業還怎么活?所以搞個旅游業還是好……非常支持發展地震遺址旅游啊,(而且)今后的發展肯定會比以前好”。但是,仍有少部分受訪者對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前景表現出一些擔憂。“支持肯定都愿意支持,主要是這個錢搭進去了,就怕……就怕以后虧了,錢就沒了”(I-06)。“因為我們這個寨子是地震之后才建起來的,怎么說呢,近處的該來旅游的都來過了,遠處的又不一定要來。而且假期只有那么長,而且人家來了又會走,消費不了多少錢吧”(I-14)。
4 旅游發展中的矛盾沖突與困境突圍
4.1 主-客角色變化帶來社區困惑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于汶川大地震和地震災區的關注熱度逐漸消退,在這一背景下,因地震而興的吉娜羌寨旅游業也經歷了從繁榮到衰退的過程。調查中,居民幾乎都表示,現在游客的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大不如以前”,甚至出現“一年不如一年”的慘境。“人最多的時候是(20)09年、(20)10年,(20)11年以后人數明顯減少了”(I-20)。在筆者多年來對北川縣的跟蹤調查中發現,不僅吉娜羌寨存在這種情況,很多依靠地震“發家”的景區(點)也都經歷了這樣一個從巔峰到跌落的過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外界對當地的關注度降低,以及一些景區(點)缺少核心產品和經營理念跟不上市場變化而造成的。
同時,隨著外界對“地震”的淡漠,游客的旅游動機和旅游行為也逐漸發生了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困擾。“最開始旅游者過來是慰問災區的,但是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就不是這個樣子的了,他們現在就是來玩、來購物、來尋求開心的”(I-20)。“最開始你的服務再不好都無所謂,游客是來同情你的……現在這種感覺淡了,因為一開始每個顧客都會問地震的時候我們是什么樣的,是如何逃生的,家里有沒有什么傷亡之類的。但是現在沒有一個游客這么問,現在已經變成了真正的旅游”(I-12)。
游客行為和心境的變化,打破了原有角色分工局面,為“主-客”沖突埋下了隱患。
一方面,游客的角色從最初的“慰問者”和“關愛者”逐漸向理性“消費者”轉化。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的歷史記憶,以及北川縣的地震遺址旅游地的形象構建,為當地貼上了“災難”的標簽。部分游客仍將自我定格在過去的情境中,以“捐助者”的身份來看待當地旅游和居民,導致吉娜羌寨從事旅游經營活動的居民受到了一些不合理的譴責和道德批判。同時,他們對于當地的服務和旅游商品,不再是那種處于悲憫和同情的“零容忍”,而是基于更為符合自我消費價值和生活觀念的評判。訪談過程中,社區居民提到部分游客會過高要求當地經營服務,有的甚至會出于倫理道德譴責當地的某些商業行為。“有些人(游客)說我們吉娜羌寨的人沒素質……我們賣東西的時候,那個東西本來要值那個價,但是他們(游客)就會說我們沒良心,說地震的時候給我們捐了好多錢,我們現在還要賣給他們這么多錢”(I-03)。雖然訪談中,當地居民反復提到這樣出于倫理道德的責難只屬于少數游客的行為,同時此處筆者暫且不論這種行為是否屬于“道德綁架”,但這確實從某個層面上體現了游客的心理轉向和角色變化。
另一方面,當地居民的角色則正在經歷一個從“受災者”和“被關愛者”到商業“經營者”的轉變。在旅游世界中,他們身上的“悲傷”和“災難”成分在不斷被滌蕩和淡化,而“商業”成分在不斷被凸顯和固化。在這個從“被給予”(愛心)到“被要求”(服務)的轉變過程中,當地居民短期內存在一定的失落感,難以適從。同時,剛從“農民”轉化為旅游“經營者”不久的當地居民短時間內難以擺脫傳統農業經營理念的“桎梏”,旅游業經營水平也難以迅速提升。這種游客和居民之間角色的變化,給當地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成為當地社區旅游發展中的一個隱秘、卻不容忽視的嚴峻問題。
4.2 “我者”與“他者”的矛盾糾葛
隨著知名度的提高和游客的不斷涌入,一些外來經營者窺探到吉娜羌寨的商機,開始與當地沒有經營能力(如無充足勞動力)的農戶達成協議,轉租后者的房屋用以經營農家樂(旅游餐飲和住宿接待)。據當地村委會工作人員介紹,2010—2011年,高峰期有近10戶外來商家經營農家樂,但“他者”(外來經營者)的闖入,埋下了社區沖突的“禍根”。剛開始時,外來經營者與當地村民和平相處、相安無事,但隨著吉娜羌寨整體游客接待量的下滑,競爭日益白熱化,許多農家樂紛紛倒閉(含外來商戶),雙方矛盾凸顯,并出現了吵架、打架等惡性沖突事件。
在此過程中,外來商家被當地居民貼上“宰客”的標簽。當地居民幾乎已經達成共識:這些外地人“不守規矩”,他們的“高價”“宰客”等行為破壞了吉娜羌寨良好形象,而當地人還要為他們的“不守規矩”買單,“背黑鍋”。“我們這有兩家外來的人,賣東西賣得很貴,宰客宰得很兇”(I-01),“我們的野雞肉賣50塊錢一份,他們(外地人)賣95(元),有些客人不知道,只看見他們家裝修得高檔、豪華……吃完飯之后又抱怨價格太高……壞名譽就我們攤了”(I-03)。雖然后來大部分外來商戶由于經營不善,撤離了吉娜羌寨(到筆者調查時僅留下兩家外來戶經營的農家樂),但是一些當地居民還是把村寨游客量的下滑歸結為外來人的“損人利己”和“宰客”行為。也正是因為如此,部分當地居民采取過激的行為,到外來商戶門口去堵截和拉客,甚至辱罵外來商家,導致矛盾不斷升級。
而外來商家始終認為價格高是因為品質好,同時自己一直是被“去權”的弱勢群體。“我們這兩家(外來商戶)為啥生意比他們(當地人)好?我們的裝修、味道、服務,包括衛生,都是做得最好的……”(I-10)。“我們價位確實比他們高,那為啥人家顧客還是愿意來吃呢,這都是有原因的,顧客是最聰明的,一吃就曉得了,我們的醬都是自己做的,味道就是不一樣”(I-12)。同時,外來經營者認為生意不好是當地人自身經營理念和產品品質問題,但他們不愿自我反思,反倒因嫉妒而詆毀。此外,外來商戶還指出因為“外地人”的身份使他們在社區受到了不公平待遇,這是一種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比如說,有啥事要開會,我們連發言的權利都沒有,又沒得發言權,又沒得參與權,還有就是這個菜要怎么怎么(做)根本沒有人聽我們的建議……”(I-11)。“這個寨子……思想他必須要開放……太保守了,地方保護主義(太濃)”(I-12)。
據筆者跟蹤調查得知,后來由于沖突的升級以及當地旅游業的持續下滑,外來商戶最終全部撤離了吉娜羌寨。這場“我者”與“他者”的沖突終告一段落,但其中所隱秘的原因發人深思。表面上看這是一場由于經營競爭、經營理念差異所引致的利益沖突,但細致分析可以發現,其中可能還包括文化心理沖突等深層因素。當地社區居民在長時間的磨合和地震后的互助互救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社群關系,而外來商戶的突然闖入,打破了“我者”世界的“日常”。隨之,當地居民的“我者”意識被激活,行為上往往會因族群向心性,對闖入的“他者”產生排斥心理。起初,客源充足,兩者之間沖突并未充分顯現,即使有些許矛盾也能被豐厚的“利益”(旅游收益)所沖淡。但隨著游客量的持續減少、競爭加劇,利益沖突凸顯,整個“我者”群體的“排異”心理被不斷點燃,“我者”和“他者”之間所搭建的臨時“鏈接”關系變得脆弱而不堪一擊,矛盾難以調和。
4.3 來自社區內部“自覺參與”的困境突圍
旅游發展的持續萎靡,促使當地居民開始自覺反思,主動尋求改變和突圍。這是一種典型的居民自覺參與社區旅游發展的行為。同時,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村委會多次組織居民前往省內外旅游業發展情況較好的旅游地進行考察,學習先進經驗。“每家每戶抽調一個人去(考察)……主要是考察別人怎么發展旅游業,去學習……去考察他們的經營模式和理念”(I-20)。通過多次外出學習考察活動,村民們逐漸意識到自身發展的困境,并開始探索未來發展路徑。“……其實有幾種模式我們原來都探討過的,合作社也是相當于管理委員會這種……也有這種模式,比如說今后你自己經營,我們該怎么要求就怎么要求,我們成立一個監督小組,根據你的經營效益我們收取一定的費用”(I-20)。經過多次研究討論,村委會決定選擇“旅游合作社”的模式,并于2013年4月正式成立“吉娜羌寨旅游開發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合作社采用股份分紅制,集體經營、統一管理。居民自愿參與入股,加入合作社后不得單獨接客,旅游者的所有餐飲均明碼標價并由合作社提供,住宿則由合作社輪流安排至具有接待能力的農戶。根據合作社規定,所有費用由合作社統一收取,并在分紅時按照股份大小分配給各戶,住宿接待戶除紅利外可分得每位旅游者每晚5元的補貼費用。合作社還設立了理事會和監事會,在合作社上班的社員每月有固定的工資,沒有在合作社上班的社員除紅利外則沒有工資。
從訪談中筆者了解到,全寨有近70%的居民參與了合作社。這些居民均對成立合作社持贊同態度,認為合作社的成立有利于當地旅游業的后續發展,能解決餐飲和住宿定價的糾紛,減少居民間搶奪客源的矛盾,還能夠幫助到地理位置不好的住戶,帶動全寨居民共同富裕。“這個(農家樂)做的人多了客人少了,就會有拉客呀,喊呀,糾紛呀,爭這樣爭那樣的呀”(I-20)。“有矛盾的話,大家都做不成生意……現在做合作社,把菜單、價格都統一了,也就不存在‘宰客現象了,而且合作社食品(安全)也能讓人放心……”(I-03)。“大家合在一起,抱成一團做生意,(把生意)做活了以后,大家日子就都好過了”(I-23)。據了解,全寨有48戶人家加入了合作社(截至調查時),許多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也返回村寨,并積極參與到旅游開發之中。
除成立合作社外,吉娜羌寨還積極推動旅游業的轉型與升級,從發展黑色旅游為主向發展文化旅游轉變。地震后,吉娜羌寨以外界對災區的關注為契機,利用國家政策發展旅游業,屬于典型的“外部推動型”發展模式。隨著外界對災區關注度的降低,純粹依靠外界“關心”和“同情”的黑色旅游已不能完全適應社區的發展,尋求內生發展動力勢在必行。據相關負責人介紹,吉娜羌寨將深度挖掘和宣傳羌族傳統文化,大力發展民俗文化旅游。目前,寨子里設置了免費的觀光車,增加了羌族文化講解、羌曲吹奏表演、羌族美食品嘗、羌族特色商品選購等活動,該負責人還表示,將進一步推出一些以休閑為主的體驗性項目。“下一步,我們將推出一些讓游客參與的表演與互動,也設置一些喝茶、喝咖啡的地方來吸引游客”(I-20)。同時,為了延伸產業鏈,當地還制定了以“旅游觀光為主,帶動種植業、特色養殖業和加工包裝業鏈條式發展”的發展計劃,逐步形成“觀光、品嘗珍稀魚類,吃正宗散養土雞”的旅游接待特色,并爭取興辦“小型旅游紀念品加工和羌繡小作坊……羌族土特產產品精加工包裝廠”1。
總的來看,吉娜羌寨的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外部推動”向“內部自覺”的轉變過程。而這種轉變是在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困境凸顯的雙重推動下形成的。盡管當地成立“旅游合作社”并非是由村民提出,“由下而上”自行組織,而是由政府支持,村寨領導考察,經過領導討論“自上而下”下達的指令產生的。但是,不可否認當地居民積極參與,并投身至旅游發展決策和實踐的意識已大大提高。同時,當地社區也正在積極主動尋求一種通過挖掘自身特色(如羌族文化)和參與旅游發展的形式來突破當地旅游發展的困境。毫無疑問,當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這種轉變不是村民隨意性的“自發”行為,而是一種內生性較強的“自覺”行為。可以說,地震導致吉娜羌寨整體環境突變,使旅游業走進當地居民的生活,而旅游業的震蕩則促使了當地社區的主體性成長。反過來,這種成長又推進了旅游業的轉型升級。
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社區居民視角出發,以吉娜羌寨為例,探討了自然災難地社區居民對災害遺址和黑色旅游發展的感知,及社區應對旅游業發展演化所采取的行動措施。研究發現:
(1) 災難遺址是被賦予意義的“物”和“場”
對于當地居民來說,災難遺址具有見證和紀念災難、緬懷逝者、傳承社區記憶等特殊的社會和空間意義,是其生活世界中必不可少的“物”和“場”。同時,隨著黑色旅游的展開,在這個充滿“意義”的場域中,當地居民和旅游者頻繁接觸、情感交織,災難遺址的空間意義和社會意義得以延續,逐漸從當地居民的“我者”之物演化為居民和旅游者的共有之物,并據此產生“我者”和“他者”的物理空間和心理情感的勾連(圖3)。這與Stone和Dunkley等的觀點具有一定相似之處,他們指出,黑色旅游地是悼念遇難者、傳承集體記憶的重要象征空間[13,72]。只是Stone和Dunkley等的研究是從旅游者視角出發,而本研究則基于當地居民認知視角展開。可見,盡管災難遺址對于旅游者和當地居民這兩個群體的功能不同,但卻常被賦予較為相似的意義。
(2) 社區居民普遍支持當地發展黑色旅游
當地居民對于依托社區災后重建和傳統文化發展起來的黑色旅游表現出較為積極的態度。在他們眼中,這種典型的社區型黑色旅游已成為推動當地社會經濟恢復重建、促進傳統文化保護和族群認同的重要力量。鄭詩琳等提出,災后重建為災難地社區的重構帶來了機遇,并能有效推動實現社區的轉型、升級和發展[73]。作為災后恢復重建的一種重要方式,黑色旅游在社會文化、經濟建設等多個方面推動了災區的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Miller、Korstanje和Ivanov等提出的黑色旅游有助于推動受災地社會經濟發展的觀點[32,34]。同時,本研究的結論也與Wang和Luo的調查結果基本吻合。他們研究發現,社區居民普遍認為黑色旅游能夠有效推動當地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方面的恢復重建和發展,同時當地居民對地震遺址的黑色旅游開發也普遍持支持態度[19]。雖然與一般意義上的旅游地有所不同,黑色旅游地的居民對于情感和倫理道德方面的關注會更加強烈[11-12],但是通過本研究筆者發現,當地居民并不認為黑色旅游會給其帶來心理和情感傷害,也不會違背倫理道德,反而認為這種旅游形式是一種對生者的關心和對遇難者的紀念。這一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部分學者和社會大眾關于黑色旅游會產生倫理沖突,并給當地居民帶來情感傷害的擔憂。但需要強調的是,在自然災難地,尤其是在一些災難事件發生后不久的災區,開發黑色旅游時一定要注意尊重當地居民的情感,并充分考量其心理接受程度,以免導致不必要的道德爭議和受災群眾的“二次心理傷害”。
(3)黑色旅游“主-客”關系重構引致角色沖突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于災難事件本身和災區的關注度逐漸降低,黑色旅游地的“主-客”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游客逐漸從最初的“慰問者”和“關愛者”角色向理性“消費者”轉化;而當地居民的角色也逐漸從“受災者”和“被關愛者”向商業“經營者”轉變。通過研究可以發現,黑色旅游消費中涵蓋了理性和感性雙重要素。理性要素是作為“消費者”與“經營者”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經濟關系,是一種經濟性的平等關系;感性要素是作為“慰問者”和“被關愛者”之間的“給予”與“被給予”的情感關系,是一種情感性的不平等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感性要素呈現弱化趨勢,而作為理性要素的經濟關系(服務是否能夠匹配價格)則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主-客”角色隨之發生漸變。這些變化不僅給社區的旅游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同時也給新的“主-客”關系處理帶來了新挑戰。此外,作為“他者”的外來經營者闖入,導致“我者”(原住民)經營空間被不斷擠壓。由于缺乏社會文化和情感基礎,使得“我者”和“他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并演變成阻礙當地旅游經營發展和社區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對于黑色旅游地社區來說,更新發展理念,調整管理模式,協調“主-客”關系和社群關系,顯得尤為必要。
(4) 自覺性社區參與推動了當地旅游業轉型? ?升級
近年來,案例地社區為了走出旅游業發展的低迷,主動采取了成立合作社、尋求傳統文化要素植入等措施。這些行為是不斷調整發展和尋求突破的重要“自覺”行為,而這種自覺性的困境突圍,體現了災害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已開始從“外部? ? ? 推動”(自發發展)向“內部自覺”的轉變。該轉變是由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發展困境凸顯共同決定的。汶川大地震后,當地社區以災后恢復重建為契機大力發展社區旅游,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旅游業績。但是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和內部經營管理問題的凸顯,當地旅游業一度陷入發展困境。為了走出低迷,當地社區主動采取了諸多突圍措施。這? ? 些行為是受到內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影響而做出的自覺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Tosun等關于社區參與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他們認為,社區參與會受到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響,且這些因素會不斷影響并推動社區走向“自覺”[74]。同時,學者們提出,社區參與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經濟收入,還能增強居民的權利意識,促進社區的主體性成長[53,58,65],這一觀點也在本文的研究中得到了體現。通過社區參與和困境突圍,居民的權利意識不斷凸顯,反過來,這種社區主體意識的增強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地旅游業的轉型升級。
5.2 研究不足與展望
雖然旅游地的發展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社區居民感知態度會因旅游發展階段的不同、地方政策的改變而有所變化,但從時間上來看,本研究正好處于自然災害地社區初涉旅游業并面臨轉型的階段,能較為完整地反映黑色旅游地生命周期初始階段的特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也為黑色旅游地社區相關后續研究提供了基礎1。
在本研究中,筆者盡量運用了在該地的多輪次田野調查所獲經驗數據,同時也試圖回顧和梳理歷時性發展問題,但是本文的主要數據和資料來自一個時段的橫斷面調查,可能難以全面、歷時性地描繪案例地社區發展的演化全貌。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對案例地進行持續性跟蹤調查,并統合多方數據資料進行綜合性剖析尤為必要。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PELLING M. Paradigms of risk[M] // 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3: 3-16.
[2] 王金偉, 張賽茵. 災害紀念地的黑色旅游者: 動機、類型化及其差異——以北川地震遺址區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8): 1576-1588. [WANG Jinwei, ZHANG Saiyin. Dark tourists motivations and segmentation at disaster memorials: The case of Beichuan Earthquake Site Area,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8): 1576-1588.]
[3] BIRAN A, LIU W, LI G, et al. Consuming post-disaster destinations: The case of Sichuan, Chin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7(2): 1-17.
[4] GOTHAM K F. (Re)branding the big easy: Tourism rebuilding in post-Katrina New Orleans[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7, 42(6): 823-850.
[5] 植村貴裕. 「負の遺産」と観光[J]. 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 2009, (128): 53-73. [UEMURA TAKAHIRO. “Negative heritage” and the sightseeing[J]. The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Rissho University. 2009, (128): 53-73.]
[6] FUNCK C. Mourn, rebuild, remember, prepare: Messages of the 1995 Great Hanshin-Awaji earthquake[J]. Asia Pacific World, 2014, 5(2): 12-31.
[7] 井出明. 東日本大震災における東北地域の復興と観光について : イノベーションとダークツーリズムを手がかりに[J]. 運輸と経済, 2012, 72(1): 24-33. [IDE AKIRA. Post-Earthquake Tohoku area re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Innovation and dark tourism[J]. Transportation & Economy, 2012, 72(1): 24-33.]
[8] RASOOLIMANESH S M, RINGLE C M, JAAFAR M, et al. Urban vs. rural destinations: Residents perceptio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147-158.
[9] 孫九霞. 旅游人類學的社區旅游與社區參與[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9: 76; 241. [SUN Jiuxia. Community Tourism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nthropology[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76; 241.]
[10] YUILL S M. Dark Tourism: Understanding Visitor Motivation at Sites of Death and Disaster[D].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2003.
[11] WRIGHT D, SHARPLEY R. Local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disaster tourism: The case of LAquila, Italy[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8, 21(14): 1569-1585.
[12] KIM S, BUTLER G. Local community perspectives towards dark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nowtown, South Australi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5, 13(1): 78-89.
[13] STONE P R. Dark tourism and significant other death: Towards a model of mortality medi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3): 1565-1587.
[14] MILES W F. Auschwitz: Museum interpretation and darker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4): 1175-1178.
[15] YAN B J, ZHANG J, ZHANG H L, et al. Investing the motivation-experience relationship in a dark tourism space: A case study of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relics,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3): 108-121.
[16] ZHENG C H, ZHANG J, QIAN L L, et al. The inner struggle of visiting “dark tourism” sites: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nstraints and motivation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8, 15: 1710-1727
[17] ZHANG H L, YANG Y, ZHENG C H, et al. Too dark to revisit? The role of past experiences and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4: 452-464.
[18] 唐勇, 向凌瀟, 鐘美玲, 等. 汶川地震紀念地黑色旅游動機、游憩價值與重游意愿認知結構關系研究[J]. 山地學報, 2018, (3): 422-431. [TANG Yong, XIANG Lingxiao, ZHONG Meiling, et al. Dark touristic motivations, recreational value and revisit intention to the Memorial Sites of Wenchuan earthquake: 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J]. Mountain Research, 2018, (3): 422-431.]
[19] WANG J, LUO X. Resident perception of dark tourism impact: The case of Beichuan county, Chin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8, 16(5): 463-481.
[20] WANG S, CHEN S, XU H.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s dark tourism, a perspective of place-based identity motive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9, 22(13): 1601-1616.
[21] FOLEY M, LENNON J J. JFK and dark tourism: A fascination with assassin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96, 2(4): 198-211.
[22] SEATON T. Thanatour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n appraisal of decades work with some future issues and directions[M] // The Sage Handbook of Tourism Studies. London: Sage, 2009: 521-542.
[23] BIRAN A, PORIA Y. Re-conceptualizing dark tourism[M] // Contemporary Tourist Experienc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2: 57-70.
[24] 大森信治郎. 「復興ツーリズム」或いは「祈る旅」の提言[J]. 観光研究, 2012, 24(1): 28-31. [OGMORI SHINJIRO. Proposal of “reconstruction tourism” or “prayer tourism”: Review on the use of the term “dark tourism”[J]. The Tourism Studies, 2012, 24(1): 28-31.]
[25] COATS A, FERGUSON S. Rubbernecking or rejuvenation: Post earthquake perceptions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practice in a dark tourism context[J]. Journal of Research for Consumers, 2013 (23): 32-65.
[26] POTTS T J. ‘Dark tourism and the ‘kitschification of 9/11[J]. Tourist Studies, 2012, 12(3): 232-249.
[27] BUDA D M. Dark tourism and voyeurism: Tourist arrested for “spying” in Ir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3, 7(3): 214-226.
[28] STRANGE C. KEMPA M. Shades of dark tourism: Alcatraz and Robben Island[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2): 386-405.
[29] LEE C K, LAWERENCE J, BENDLE Y S Y, et al. Thanatourism or peace tourism: Perceived value at a North Korean resort from an indigenous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14(1): 71-90.
[30] STONE P R. A dark tourism spectrum: Towards a typology of death and macabre related tourist sites, attractions and exhibitions[J]. Tour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6, 52: 145-160.
[31] STONE P R, SHARPLEY R. Consuming dark tourism: A thanatological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 574-595.
[32] MILLER D M S. Disaster tourism and disaster landscape attraction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An auto-ethnographic journ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08, 2(2): 115-131.
[33] PEZZULLO P C. “This is the only tour that sells”: Tourism, disast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Orleans[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09, 7(2): 99-114.
[34] KORSTANJE M E, Ivanov S. Tourism as a form of new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inception of dark tourism[J]. Culture: Revista de Cultura e Turismo, 2012, 6(4): 56-71.
[35] SEATON A V, LENNON J J. Thanatour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Moral panics, ulterior motives and ulterior desires[M] // New Horizons in Tourism: Strange Experiences and Stranger Practices. Wallingford:CABI 2004: 63-82.
[36] AP J, CROMPTON J L.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 37(2): 120-130.
[37] KIM K, UYSAL M, SIRGY M J. 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3): 527-540.
[38] KEOGH B.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0, 17(3): 449-465.
[39] YOON Y, GURSOY D, CHEN S J. Validating a tourism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4): 363-372.
[40] VARGASS?NCHEZ A, PORRASBUENO N. Explaining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Is a universal model possibl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2): 460-480.
[41] DYER P, GURSOY D, SHARMA B, et al. Structural modeling of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nd associated development on the Sunshine Coast, Austral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2): 409-422.
[42] ROSIGLEYSE C S, LUCI C C P, RAUQU?RIO M C, et al. Management of estuarine beaches on the Amazon coast 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dic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9: 216-225.
[43] AP J, CROMPTON J L. Residents strategies for responding to tourism impact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3, 32(1): 47-50.
[44] DOGAN H Z. Forms of adjustment-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 16(2): 216-232.
[45] DOXEY G V. A causation theory of visitor-resident irritant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in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tourism[C] //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Trave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1975: 195-198.
[46] LAWSON R W, WILLIAMS J, YOUNG T, et al. A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10 New Zealand destin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1998, 19(3): 247-256.
[47] LAI P H, NEPAL S K. Local perspective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Tawushan Nature Reserve, Taiwan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6): 1117-1129.
[48] KIM S S, PETRICK J F.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impacts of the FIFA 2002 World Cup: The case of Seoul as a host c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1): 25-38.
[49] JACKSON M S, INBAKARAN R J. Evaluating residents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to act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gional Victoria,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8(5): 355-366.
[50] CORDERO J C M.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A crit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view[J]. Ciencia Ergo Sum, 2008, 15(1): 35-44.
[51] 廖軍華. 國內外社區參與旅游研究綜述[J]. 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149(1): 34-39. [LIAO Junhu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research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J].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5, 149(1): 34-39.]
[52] MURPHY P.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M]. New York: Methuen, 1985: 179-190.
[53] 左冰, 保繼剛. 從“社區參與”走向“社區增權”——西方“旅游增權”理論研究評述[J]. 旅游學刊, 2008, 23(4): 58-63. [ZUO Bing, BAO Jigang. 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 “tourism empower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 (4): 58-63.]
[54] 孫九霞, 保繼剛. 從缺失到凸顯: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脈絡[J]. 旅游學刊, 2006, 21(7): 63-68. [SUN Jiuxia, BAO Jigang. From absence to distinction: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7): 63-68.]
[55] 保繼剛, 孫九霞.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中西差異[J]. 地理學報, 2006, 61(4): 401-413. [BAO Jigang, SUN Jiuxia.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4): 401-413.]
[56] 塔娜, 盧松.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進展[J]. 云南地理環境研究, 2019, 31(1): 30-54. [TA Na, LU Song. A study on the return of ancestral worship local emotions: Take Hancheng Dangjia village as an example[J].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19, 31(1): 30-54.]
[57] INSKEEP E. Tourism Planning: 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1: 29.
[58] SIMMONS D 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lanning[J]. Tourism Management, 1994, 15: 98-108.
[59] CEVAT T. Expected natur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3): 493-504.
[60] HALLAK R, BROWN G, LINDSAY N J. Examining tourism SME owners place attachment, support for communit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model[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 21(5): 658-678.
[61] RASOOLIMANESH S M, RINGLE C M, JAAFAR M. Urban vs rural destinations: Residents perceptio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147-158.
[62] YANG J, RYAN C, ZHANG L. Social conflict i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5: 82-93.
[63] 胥興安, 孫鳳芝, 王立磊. 居民感知公平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影響研究——基于社區認同視角[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5, 25(12): 113-120. [XU Xingan, SUN Fengzhi, WANG Lilei. Effects of perceived justic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12): 113-120.]
[64] SALAZAR N B. Community-based cultural tourism: Issues,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20(1): 9-22.
[65] TAYLOR S R. Issues in measuring success in community-based indigenous tourism: Elites, kin groups, social capital, gender dynamics and income flow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7, 25(3): 433-449.
[66] CLARK 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Isle of Wigh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254-266.
[67] 王維艷.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制度增權二元分野比較研究[J]. 旅游學刊, 2018, 33(8): 58-67. [WANG Weiyan. Comparative study of dual division in the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for the involvement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8): 58-67.]
[68] MARSHALL C, ROSSMAN G B.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6: 51-74.
[69] 甘露, 陳娜, 劉麗君, 等. 佛教僧侶視野中的游客、旅游和旅游業[J]. 旅游學刊, 2016, 31(5): 55-63. [GAN Lu, CHEN Na, LIU Lijun, et al. Visitors, sightseeing and tourism: A Buddhist perspective[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5): 55-63.]
[70] 陳向明. 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0: 277-288. [CHEN Xiang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oes[M].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00: 277-288.]
[71] 錢俊希, 楊槿, 朱竑. 現代性語境下地方性與身份認同的構建——以拉薩“藏漂”為例[J]. 地理學報, 2015, 70(8): 1281-1295. [QIAN Junxi, YANG Jin, ZHU Hong.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Tibe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281-1295.]
[72] DUNKLEY R, MORGAN N, WESTWOOD S. Visiting the trenches: Exploring meanings and motivations in battlefield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4): 860-868.
[73] 鄭詩琳, 薛熙明, 朱竑. 新生的旅游地: 災后重建背景下的地方重構——以四川省彭州市白鹿鎮為例[J]. 旅游學刊, 2017, 32(5): 59-70. [ZHENG Shilin, XUE Ximing, ZHU Hong. Newborn tourist place: The place reconstruction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 contextualized Bailu village, Pengzhou city, Sichuan province [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5): 59-70.]
[74] TOSUN C. Expected natur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3): 49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