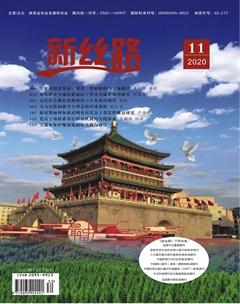淺析當(dāng)代山水畫的美學(xué)意蘊(yùn)
在傳統(tǒng)的中國(guó)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有遠(yuǎn)比色彩、線條、形式和技法更為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作品的精神------藝術(shù)家的人格精神歸屬。即使是那些以觀念為主和以形式技藝取勝的作品也不能忽視內(nèi)在精神的傳達(dá),舍此藝術(shù)便徒有其表。反之,任何作品的精神都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所以,它唯有借助直觀的藝術(shù)語言去顯現(xiàn)才具有特定的實(shí)踐意義。因此,作為具象表現(xiàn)的手段—語言的選擇和運(yùn)用就來不得半點(diǎn)玄虛造作,如果沒有精妙的藝術(shù)語言哪里會(huì)有藝術(shù)創(chuàng)造可言?其實(shí)這就是繪畫的“自己顯現(xiàn)”,是繪畫“肇始于自然”的本來意義,其山水畫的美學(xué)意蘊(yùn)也就在此。
故而,中國(guó)人的藝術(shù)歷來講“畫品即人品”。譬如,具有寧靜、深遠(yuǎn)、典雅的人才能夠畫出如是作品,而也只有在寧靜、深遠(yuǎn)、典雅和飄逸的畫面里我們才能夠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心靈、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觀念與畫中境界已然交融為一,化身為一,這才是我們?cè)诂F(xiàn)實(shí)時(shí)空捕獲到的超越式的、與傳統(tǒng)文化有關(guān)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水墨文化重建的具體顯現(xiàn),當(dāng)然,這也是傳統(tǒng)只能鮮活地生活于現(xiàn)代語境的明證。
晉人郭象批評(píng)莊子的哲學(xué)是極高明而不道中庸,他所主張的自同于大全者是神游于象外,而這種神游于象外并不是說要離開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生活,離開世俗的世界靜默于無人的高山之林,所以他所追求的是“圣人常游外以宏內(nèi)”意思是說,圣人的境界雖然是最高的,但其行為則可以是最平凡的日用,所以要求中國(guó)的山水畫家都有著一種從天空觀看山川風(fēng)物的襟懷和眼光。這是傳統(tǒng)中國(guó)畫最可寶貴的精華,其實(shí)宗炳講的“圣人澄懷味象”也是這個(gè)意思。這就表明形式語言的表現(xiàn)方式是不能離開精神旨意的,換言之,只有在形式語言的語用中,筆墨才能見其精神,我們“八荒”系列與“唐詩”系列作品之間存在著這種互文的關(guān)系。
傳統(tǒng)的中國(guó)畫講究通過物態(tài)形象、筆墨境界表達(dá)主體對(duì)形而上的宇宙之道、人生之道的認(rèn)知和體驗(yàn)。所以,畫家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前提是“心”中要有一個(gè)“境界”。我們前述的“靜觀”、“坐究”所追求的其實(shí)是人格光輝的圖像顯現(xiàn)。這“光輝”或深沉、或古樸、或清新、或飄逸,匯合在一起筑成了一座視覺的豐碑。所以,所謂的山水精神實(shí)質(zhì)上是以貌似出世的超逸思想做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的入世事業(yè);是在文化的異化的威脅中重建著充滿自信的隸屬中國(guó)文化思想的精神家園。所以,作為畫家我們應(yīng)該永遠(yuǎn)生活在追求的過程中。中國(guó)的藝術(shù)家要有這樣的品質(zhì),也只有這樣做才能把我們的美好祝愿還給自然—這是造化和我的關(guān)系、自然和人的關(guān)系的還原。所以,還給自然也就包括還給了人民、還給了觀眾,也就理所當(dāng)然地顯現(xiàn)出天地精神。
西方繪畫崇尚自然美,自然而然會(huì)有其貼切的形式、語言;中國(guó)畫家心馳神往的天地大美,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筆遂墨順”的美學(xué)追求。我們使用中國(guó)畫的特有的工具材料,它們有如它所是的質(zhì)理,所以一旦當(dāng)畫家對(duì)自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認(rèn)知,就會(huì)希望能夠以“心馳神往”的方式去實(shí)踐。
這就是說,恰恰是由于特定的工具材料,畫家在實(shí)踐過程中才會(huì)認(rèn)為這樣的實(shí)踐會(huì)產(chǎn)生美好的作品。有了這樣的理解、達(dá)到了這樣的境界,我們會(huì)用美好的思想、情感和觀念去欣賞、感受藝術(shù)作品,會(huì)去挖掘出生活中更多更有價(jià)值的東西。對(duì)畫家來說,這是令人“心馳神往”的境界,是“筆遂墨順”的境界,是抒發(fā)“天地大美”的境界。這樣境界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所體現(xiàn)的就是自然界中最美的東西,我們?cè)谛蕾p它們時(shí)不會(huì)有雜念,會(huì)覺得畫家把心里最美的世界呈現(xiàn)在了你面前,那是畫家對(duì)自然的“天地意識(shí)”的理解—“天地意識(shí)”是最高貴的精神,是洗滌塵渣的超以象外的“太虛”境界。中國(guó)繪畫最終要用中國(guó)文化來詮釋,我們看白石老人的作品,實(shí)際上他已經(jīng)達(dá)到了這樣的境界。欣賞中國(guó)畫就是在品評(píng)作者,有時(shí)候也需要了解作者的人生,在這個(gè)意義上,中國(guó)畫的文化內(nèi)蘊(yùn)必定會(huì)受到全世界熱愛和平人們的敬重。
眾所周知,孔子所說的“溫柔敦厚”的美學(xué)意蘊(yùn),道家美學(xué)中的“平淡天真”的審美品評(píng)標(biāo)準(zhǔn),二者的結(jié)合一直作為中國(guó)美學(xué)的最高端的。石濤有句名言叫“不似之似”,齊白石講“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這些都表現(xiàn)出中國(guó)畫的審美本質(zhì)是寫意的。如是的寫意,既是在一筆一畫之中抒發(fā)著個(gè)體的思想、情感觀念,是通過個(gè)體生命對(duì)自然物化的理解與認(rèn)知,寄托對(duì)萬事萬物的理解與體悟。同時(shí),這也表現(xiàn)出中國(guó)人對(duì)個(gè)性自由的高度尊重的前提下不走極端的特點(diǎn)。基于此,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么中國(guó)畫中的“天地大美”實(shí)際上就是宋人陸九淵所說的依據(jù)“本諸心,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zhì)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而建構(gòu)的“天下之正理、實(shí)理、常理、公理”的具體變現(xiàn)了。這也正好說明,中國(guó)畫美學(xué)圖像中蘊(yùn)含的天地大美,在本質(zhì)上為什么既是對(duì)遍存于自然界的客觀萬物存在之理的高度概括,也是能夠?qū)嵈嬗诿恳粋€(gè)人心靈之中的德性之理的變現(xiàn)了。
自宋元以來,人們把陸九淵稱為“心學(xué)”始祖。明王守仁說:“圣人之學(xué),心學(xué)也……陸氏之學(xué),孟氏之學(xué)也。”所以,所謂“心學(xué)”,一方面是以“心”為中心范疇或最高范疇的哲學(xué)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心學(xué)”也是包括儒家在內(nèi)的內(nèi)圣之學(xué)。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兩宋之時(shí)水墨寫意開始濫觴,并于嗣后成中國(guó)畫的主流發(fā)展方向。傳統(tǒng)的水墨寫意圖像語言和表現(xiàn)手法中,我們前述的心馳神往而筆遂墨順的境界,其實(shí)就是通過尚屬的本心發(fā)動(dòng),令心與理合一而使作為人的理性精神載體的筆墨語言在其精神的感性的顯之真切處能夠令人的審美活動(dòng)回歸到生命主體中的具體體現(xiàn)。這是一種自然沒有但能在人的德行生命之中存在的內(nèi)外相應(yīng)的內(nèi)證功夫。于是,石濤所說的“不似之似”、齊白石所講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也就成為生命的真與善的自覺合一的橋梁。
在宋元以后的中國(guó)畫畫論中,我們常常能夠見到以理氣詮釋筆墨的存在,中國(guó)古代畫家的觀念中,人的品性、格調(diào)為道德實(shí)踐的先天依據(jù),所以中國(guó)古代畫論中也就常能見有“心法”的記載,這是因?yàn)樗^的“心法”實(shí)乃是超越畫家個(gè)體的氣質(zhì)之性而可以返歸天地之性的橋梁。中國(guó)古代畫論中有“以心造物”的觀點(diǎn),但不能離開“道法自然”,于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一畫法原則也就被歷來的畫家們所普遍認(rèn)同。這是中國(guó)畫美學(xué)精神值得我們高度尊重的基本原因。因?yàn)椋凇靶募蠢怼钡乃枷牍饷⒌墓庹障拢嫾覀兘K于能將中國(guó)古代士人心中最可寶貴的“仁”攝歸于心,并最終使得中國(guó)畫的審美活動(dòng)(包括畫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與欣賞者的審美欣賞過程)具備了亦審美體驗(yàn),亦心性修為的雙重內(nèi)涵。
綜上所述,傳統(tǒng)的中國(guó)畫的筆墨精神的顯現(xiàn)中有促使人的心靈在審美的愉悅中通過心靈的共鳴而達(dá)到的文化認(rèn)同的功能,在我看來,這是當(dāng)代畫人須臾不可忽視的文化精神。《禮記·樂記》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當(dāng)代山水畫中所遵循的仍然是陸九淵所主張的以尊重自然的樸實(shí)方式啟發(fā)包括自我在內(nèi)的人的本心,通過審美活動(dòng)使人能夠成就巍然可觀的隸屬中國(guó)文化的理想人格。
思想家不一定是藝術(shù)家,但藝術(shù)家沒有思想,就絕對(duì)不是一個(gè)真正的藝術(shù)家。事實(shí)上,思想的高度決定了每一個(gè)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高度。當(dāng)代山水畫之所以異軍突起,正在于其大山大水蘊(yùn)含著異常豐富多彩的審美內(nèi)涵。換言之,我們?cè)谠S多當(dāng)代以水、墨、色形之以紙上的峰巒云霧的圖像中,觀照到的是畫家參天地之造化而跡化的藝術(shù)世界,而畫家正是在這個(gè)創(chuàng)造出來藝術(shù)世界中,把我們引入到“心騖八極,神游萬仞”的審美體驗(yàn)中。許欽松說:“中國(guó)山水畫應(yīng)該是中國(guó)繪畫史中體系最為完善、思想最為完備、成就最為輝煌的一個(gè)畫種,它記載了整個(gè)中國(guó)文化視覺,表現(xiàn)了中國(guó)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從歷史上講,它把中國(guó)文化的佛家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入其中,承載了一種很深厚的文化及宗教的思想,在各個(gè)不同朝代的不同時(shí)期都有不同的表達(dá)。”很多當(dāng)代畫家正是在作品中藝術(shù)地傳達(dá)了自己的思想理念。
相對(duì)于古典山水畫而言,現(xiàn)代山水畫與之不同的就是意境的轉(zhuǎn)換,即從古典的筆墨意境轉(zhuǎn)換為現(xiàn)代空間意境。當(dāng)代很多畫家非常重視傳統(tǒng)在繪畫中的作用,中國(guó)畫的傳統(tǒng)有兩條線:一條是唐宋元時(shí)期的意象美學(xué),一條是明清的筆墨美學(xué)。他們強(qiáng)調(diào)繼承傳統(tǒng)的筆墨程式,但更強(qiáng)調(diào)繼承中應(yīng)注入現(xiàn)代精神和現(xiàn)代審美的元素。相對(duì)注重筆情墨趣的明清的筆墨傳統(tǒng),更注重宋元的意象美學(xué)傳統(tǒng)。
水墨性與色彩性的拓展,同樣是現(xiàn)代山水畫的重要藝術(shù)特征。當(dāng)代很多山水畫以大山大水為主框架,具北派雄渾氣概,但同時(shí)又有南方的滋潤(rùn)、空靈、綺麗,這正是源于畫家對(duì)水墨和色彩語言的拓展性運(yùn)用。意境常常發(fā)端和穿游于虛幻和飄渺之處。
總之,在當(dāng)代語境下,如何將兩宋時(shí)期的造型法則及明清時(shí)期的心性學(xué)說觀照下的筆墨精神與學(xué)院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知識(shí)技能作適合時(shí)代發(fā)展需要的整合,仍然是當(dāng)代山水畫家的風(fēng)格語言建構(gòu)的重要的課題之一。由以上闡述可見,我們對(duì)當(dāng)今中國(guó)畫文化的理論研究仍然有許多尚待深入挖掘的地方,這需要研究者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善于尋找新的研究方法,從而做出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學(xué)術(shù)闡釋,這里我只是拋磚引玉,闡釋出個(gè)人的觀點(diǎn)和看法以求教于同道。
作者簡(jiǎn)介:
唐妙玲,西安市高新區(qū)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常務(wù)副主席兼秘書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