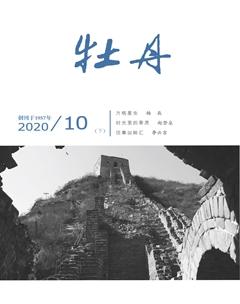散文兩篇
我的三叔——朱璧富
真是時光荏苒,轉眼間,三叔璧富也都七十有余了,自我2001年南下東莞謀生,就很少與三叔見面了,一年,二年,記得最長一次七年我都沒回鄉。但無論走到哪里,家鄉里的人與物都深藏在我的記憶深處難以忘懷,三叔他那樂觀向上、大公無私的心態,時常在我腦海閃現出來……
小時候,我們一群孩子都叫三叔“三爺”,三叔小父親三歲,在父親兄弟五個當中,三叔的個頭最矮,身高還不到一米七五,大伙都特別吃驚,我阿公(指爺爺)身高足有一米八以上。
阿婆(指奶奶)常對我說,看你這些孩子啥時候能懂事,看看你三爺不到十八歲就能當生產隊隊長了。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一點都沒錯,那年頭,家里人多,家庭就困難。三爺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再加上一個妹妹都要上學,三爺初中畢業后,就放棄了繼續上學的機會,進生產隊掙工分來了。當年大伯父高中畢業就當兵去了,父親也在讀師范。阿公常對孫輩說:“你三爺在這幾個孩子中,學習成績是最好的一個。”因為這件事,阿公自責了好多年,說他沒本事,耽誤了三爺的前程。
二十多年來,三爺一直在生產隊當隊長,任出納,當會計。三爺打得一手好算盤,當年在鄉里是出了名的算盤高手。
正因為三爺能說會算的名聲,打動了遠在幾十里開外、當時還只有半大姑娘王春花的心,后來她便成了我三娘。三娘頭次被三爺接進門,阿婆殺了只雞,燉得香噴噴的。三娘端著碗只顧喝湯,不敢對雞肉下口,三爺趁阿婆不注意,就伸筷子去夾三娘碗上的雞塊,啃下雞皮來再偷偷送到三娘碗里。這一舉動當時就被阿婆發現了。后來,三娘不吃雞皮的事在幾代人間流傳。在當年物資缺乏的年代,莫說吃雞了,連舍不得吃的雞蛋阿婆全都要攢起來拿去換針頭線腦的,殺雞給新進門的未來兒媳那是阿婆對待客人的最高禮遇了。
三娘當年是住在鎮上的,外公勤勞有加,家庭殷實,養成了三娘不吃雞皮的習慣。后來,幾個孩子的出生徹底改變了三娘不吃雞皮的歷史。
三娘進門后,一個女娃又一個女娃地生,接連生了五朵金花,盼兒子,三爺都盼白了頭發。1985年,三娘又有喜了,肚子慢慢地大了起來。阿婆說:“這回準是個孫子,我昨晚還做夢有蛇追我來著。”阿婆的話可真靈啊!這一年,三娘真的給阿婆添了個孫子,我們都叫他六弟,三爺給他取名朱鐘良,希望他長大后是個正直、善良、有出息的人。
父親是當老師吃供應糧的,我家隊里沒勞力,常年超資,糧食少,常年吃不飽肚子。每到吃飯時,我就端著小碗常往三爺家廚房里鉆,每次三娘都不會讓我空著碗回來,讓我記憶最深的是三娘做的薯渣粑,看起來黑黑的,足有我端的碗口那么大,吃在嘴里軟軟的、柔柔的,至今讓人回味。
三爺在生產隊里都是主要勞動力,鄉里如有安排組織勞動力抗洪、搶險、救災時,三爺身為隊長,猶如大干部一樣一直沖鋒在前,絲毫不顧個人安危。
歲月如流,人生經歷的很多事大都成了過往,但總有些事讓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每年春夏季,漲水的幾天里,隊里就要組織人去放排,賣楠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鄉村公路還沒修通,楠竹都依靠河道水運,這是種高危的工作,技術含量高,途中風險也無處不在,要是失手炸了排,損失竹子或木料不說,生命也有危險,常常有排工溺水而死。每年放排的日子,家里人都會十分擔心。
漲水了,三爺帶上干糧又去放排了,三娘在家里焦急地等了兩天兩夜,第三天半夜,三爺拖著疲倦的身子回來了。也就是這一夜,三爺鐵打的身軀累倒了,腿痛抽筋,翻滾在床上。他那痛苦的號叫聲驚醒了我,我慌張地爬起了床,望著哭成一團的妹妹與慌亂的三娘、阿婆,我手足無措……
日子還在不停地苦過著,后來,田地包產到戶了,改革開放了,可以自由經商了。為了方便鄉村鄰居,又好給一群孩子賺些學費,三爺便在村里率先開起了小賣部,賣些油鹽醬醋、針頭線腦等日常用品。小賣部不是那么好開的,有公路沒車子,所有的貨都得三爺一擔又一擔地壓在肩膀上挑著往山上爬。七八里陡峭的山路,三爺一爬就十多年,直到2004年,六弟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兩年后,三爺才停住了爬山的腳步。
后來,六弟也成家立業了,在鎮里買了房。隨著城鎮化的發展,鄉親們一個一個地搬走了。三爺也依依不舍地進了城。
去年,兒女們為三爺做七十壽宴,五女拜壽的熱鬧景象讓人心醉。如今望著滿堂飛跑的小孫子,三爺滄桑的臉笑得如葵花盛開般燦爛。
今年三娘又說,我也像當年阿婆那樣夢見蛇了。真靈驗啊,六弟今年又喜添貴子了。
稻穗飄香
每到秋風拂過,獨在異鄉流浪的我仿佛就能聞到故鄉稻穗的芳香,流浪的心就找到了家的方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田地已經包產到戶,爺爺就耕耘在大山深處那片肥沃的土地里。秋味漸濃,它帶來了豐收的喜悅和希望。在茫茫梯田里,那些稻穗手牽著手,肩并著肩。它們是秋天的光芒,牽引著爺爺的靈魂、父親的期盼。
狗尾巴草在風中招搖,秋風來了,田壟間,稻穗目光就會變得羞澀,頭顱就不好意思地低垂下去。是時候了。爺爺帶來了鐮刀,開始勞作。書上有句話說得好:“又是一年陌上秋,稻溢金黃可染天。云透新香風助力,且看深山喜開鐮。”
爺爺左手撐著稻禾,右手鐮刀稍加用力,一把把稻禾就整整齊齊一排排地堆放著。我與父親緊隨爺爺身后,拖著脫谷的拖斗。雙手合拿稻禾,大把稻禾用力甩過肩膀順著勢子下來,猛烈地拍打在拖斗兩個角上,隨著撞擊聲音,金黃金黃的稻谷就會瞬間脫落下來。父親望著金子般的稻谷,心里樂開了花,懸掛在半空中的太陽也跟著傻笑,烤得爺爺滾燙的汗水順著脊梁滴落。累彎了腰的鐮刀,便會趁機躺在田埂上喘息。
困了累了,爺爺又向我們這群孩子講述太爺爺的事。爺爺說:“太爺爺到山上犁田,忙起來把頭上戴的斗笠丟到一邊,直到傍晚收工,他拿起斗笠,才發現斗笠下方蓋著一塊田還沒犁……”直到我們笑得肚子痛,伸不起腰來,爺爺才肯罷休。
那時,日出而去,日落而歸,行走在大山中的田野里,再苦再累,心中每天都是美滋滋旳。如今獨在異鄉,黯淡了每個佳節,而我不能放棄漂泊。為了生活,我只有把思念記錄在文字之間,寫在紙上,刻在腦海里。
思念是個解不開的情結。那慈祥的村莊,只要有秋風拂過,就會帶來五谷豐登的消息。只要看見裊裊升起的炊煙,我就心存感激,那種熟悉的味道就會在我腦海里不停地泛出。母親在那兒深情地呼喚我的乳名,回家吃飯的鄉音永遠隨風飄蕩。
回到故鄉,一定要去看望那些老屋以及比老屋還老的鄉親,他們定會把歷經的滄桑與苦難深深地鐫刻在故鄉的土地里,埋藏在心中。
站在半山腰的老屋往下望,只見壟壟梯田像螺、像塔、像腰帶、像月亮、像爺爺的煙斗,像奶奶的繡花鞋……美得千姿百態,美得驚心動魄,美得不能讓人忘懷……
(穗東石油公司)
作者簡介:朱鐘昕(1968-),男,湖北武漢人,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詩詞學會會員、通山縣作家協會會員。已在《河南科技報》《讀者報》《國防時報》《鴨綠江》《青年文學家》《文學少年》《參花》《湖北文學》《中華文學》《儷人》等報刊上發表散文、小說百余篇。作品《打工記》曾獲第三屆“百花苑杯”全國文學大賽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