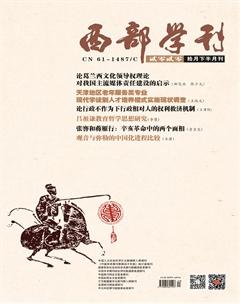觀音與彌勒的中國化進程比較
摘要:早期印度的佛教圖像學研究證明觀音和彌勒曾經作為釋迦佛的左膀右臂。在進入中國時卻成為兩位相對擁有各自獨立法門的菩薩。二者以差異化的方式與中國的文化實現了融合。觀音的中國化方式盡管出現性轉這樣重大的變化,卻與其原本的內涵頗為契合,而彌勒則由于種種原因,成為了大肚和尚,在中國發展出了“樂觀”“寬容”的全新積極含義,讓我們看到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發展的另一種可能。
關鍵詞:觀音;彌勒;菩薩中國化;垂跡化現
中圖分類號:K87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20-0147-03
一、觀音和彌勒的起源
菩薩的起源問題通常可以從經典、神話以及圖像等不同層次進行考察。《悲華經》《觀世音菩薩授記經》等佛經中都有記敘觀音的前世經理,但作為起源故事顯然晚于觀音信仰的出現。在印度本土的傳說里和觀音產生關聯則是南部的寶馬拯救海難的故事。即楞伽島(斯里蘭卡)的羅剎鬼、羅剎女總是誘發黑風海難,試圖加害海上的商人,而有一匹神通廣大的寶馬總是護佑著商人和船員。這一寶馬最終則被認定是觀音的化身①。
而彌勒的身份相較而言更為可靠。彌勒被認為是佛的弟子之一,名阿逸多,姓彌勒,是釋迦牟尼欽點的接班人卻先于老師去世。然而許多研究表明阿逸多與彌勒原本是兩個人,二人都是佛的弟子。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彌勒的起源同猶太教基督教等一神宗教有所關聯。除了語源學上彌勒與彌賽亞的近似,未來佛彌勒下生的模式與未來出現的彌賽亞救世主的模式也如出一轍。而彌勒和彌陀/觀音信仰中都存在的凈土與他力救贖觀念,也被認為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響。
貴霜王朝的犍陀羅地區是最早出現佛像的地方,其造像的圖像學分析所得即使有限,卻可能更為可靠。宮治昭發現了貴霜造像從印度教延伸至佛教的兩個尊像系列:由梵天到彌勒的求道者/婆羅門型造像,和由帝釋天到觀音的世俗關懷者/剎帝利型造像。前者著裝較為樸素,通常一手結無畏印或手心朝內的手印,另一手則手持水瓶(后期也出現了手持龍華的造型);后者的服飾更為華麗,頭戴菩薩冠,手持華鬘或蓮花。通過和當時的釋迦王子造像的比較,宮治昭認為彌勒和觀音或許正好體現了成佛之前的悉達多王子智慧求道和慈悲救世的兩種性格,同時或許還隱含了小乘與大乘的兩方面主張。
從貴霜時期的犍陀羅和秣菟羅,一直到笈多時期的釋迦三尊像,作為釋迦牟尼脅侍菩薩的幾乎都是彌勒和觀音(僅有極少數被認為可能是文殊的例子)。這與在中國,釋迦牟尼往往與文殊普賢形成華嚴三圣的固定組合完全不同,而觀音和彌勒一起的造像組合也幾乎不在中國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從貴霜后期的馬圖拉開始還出現了頭戴寶冠式樣的新式彌勒造像,似乎與原先求道者的性格有所不同。這或許是彌勒內涵中轉輪法王和救世主的特征開始抬頭的體現。因此在觀音(代表剎帝利和悉達多王子的世俗身份)和彌勒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王權特質的因素,也難怪后世的統治政權經常選擇觀音或彌勒作為自己的象征(吳哥王朝觀音的微笑、作為觀音化身的松贊干布和達賴喇嘛,或是武后面容的彌勒大佛等等)。但是相較本身更具救世/入世屬性的觀音,彌勒內涵中王權和求道者性質的關系或許更為緊張。
二、在中國流行的經典與菩薩的職能差異
關于觀音和彌勒的經典都數量浩繁,但根據性質和重要程度可以區分出幾個較有代表性的種類。與觀音相關的《法華經》系統,《觀無量壽經》系統,般若系統,密教系統等等。與彌勒相關的彌勒六經、瑜伽行派系統等等。
《普門品》是觀音信仰中最基礎也最廣泛的經典,講述觀音以三十三現身救助苦難的內容。這一信仰在印度大約起源于笈多王朝時期,于南北朝時進入中國。這一法門門檻極低,只要念誦菩薩名稱,就能即時得到解救。這也確立了觀音無差別的慈悲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需要小心祭祀,稍有不滿便要降下災禍的威權神,而是對所有平民的切實需求具有深切關懷的慈愛之神。
然而如此低的門檻和如此具體的救助內容無疑是宗教的大忌,因為一旦遇到不靈驗都無法用“不夠虔誠”“時機未到”之類的理由搪塞過去。即使再怎么考慮“幸存者偏見(survivorship bias)”的理論,也很難解釋現存靈感錄中清一色的正面記載。在實際實行時如果不存在一種解決機制,想必這種結構的信仰會很快衰落。那么很可能是觀音信仰中另一個重要內涵解決了這一悖論:《無量壽經》系統以及彌陀凈土信仰將觀音納入其中。同樣十分簡單的稱名念佛法門,但是卻對死后世界作出了更美妙的允諾。一旦口誦觀音名號仍然沒有得到解救,那么可以認為仍然有助于被接引到西方極樂凈土,而且理論上往生凈土還比現世得救更有價值。
其余的幾種經典類型中,《華嚴經·入法界品》固然也十分重要但與觀音相關的內容看起來只是對《普門品》延續;各種密教經典諸如《大悲咒》《千手經》等等在中國的實踐中也逃不出現祈求世利益的范疇(即身成佛與護國的主旨在中國相對在日本和西藏并不那么受到重視);而《心經》《楞嚴經》等則為觀音添加了般若智慧的屬性,但這種屬性相對次要,以至于也有人認為《心經》中的觀自在菩薩并不是一定專指觀音,而可以泛指一切了知空性的大菩薩。
而彌勒菩薩方面,最重要的“彌勒六經”中有五部下生經和一部上生經。王雪梅把彌勒經典大致分成三種。第一種《阿含下生經》為印度最初彌勒信仰的形態,即把彌勒作為未來佛崇拜,實際上是對現在佛釋迦牟尼崇拜的延續。第二種形態即是其他四部《下生經》中體現的把龍華三會的彌勒作為現在佛,而把釋迦佛作為過去佛看待。這里的彌勒實際上成了“馬上就要出現的未來佛”,并擔負起了把人們從末世、惡世里拯救出來、創造美麗新世界的職責。這無疑是救世主/彌賽亞觀念給彌勒內涵帶來的新發展。而時間最晚的《彌勒上生經》則與彌勒凈土觀念相關,更多的是信徒自身上生的愿望。
《彌勒六經》之外,般若系經典也與彌勒有關,特別是早期的《道行般若經》中彌勒頗為重要,后期也有諸如《彌勒大成佛經》《大乘方等要慧經》《彌勒菩薩所問經》等都屬于般若系的彌勒經典。但是在這一領域,文殊菩薩在中國作為大智菩薩的形象過于深入人心,無論是彌勒還是觀音都難以撼動其地位。
當然,由無著、世親兄弟所開創的瑜伽行派也將彌勒作為祖師。然而盡管玄奘一系在中國也創立了法相唯識宗將這一系統的思想引入中國,但有宗的思想體系過于繁復,終歸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很快沉寂下去。《瑜伽師地論》系統的彌勒信仰在中國也未能流行。
因此二位菩薩相關的佛經典籍盡管十分多樣,只有少數真正被中國所接納,并形成與之相應的信仰形態:觀音的稱名救難與凈土往生,彌勒的未來佛/救世主信仰與凈土往生。
二者都涉及到凈土信仰,歷史上對兩種凈土的比較也早已有之。盡管在北朝時期,彌勒凈土的流行度遠超彌陀/觀音凈土,但彌勒凈土由于仍在三界之內,根本性質與超脫輪回的彌陀凈土有所差距。再加上彌勒凈土的修持法門最初也比彌陀凈土要要求更高,作為面向下層民眾的凈土信仰,彌陀凈土最后勝出并不讓人感到意外。
三、白蓮教中的觀音與彌勒
道安是中國第一個推崇彌勒凈土的高僧,但他的弟子慧遠卻在廬山建立“白蓮社”,開始弘揚彌陀凈土。到了宋代,在家居士茅子元創立白蓮教,成為觀音和彌勒在中國化進程中又一次相遇的場所。
白蓮教最初自然也是崇拜阿彌陀佛,期望往生西方極樂凈土,并且將原本就很簡便的修行工夫“十念”更加簡化為念佛五聲,宣揚“念念彌陀出世,處處極樂現前”。由于在宋代開始妙善公主的故事廣為流傳,白蓮教中的女信徒法名中往往含有妙字,妙善與觀音在教中廣受推崇,這或許也進一步鞏固了觀音向女性的轉變。
但是到了元代,白蓮教性質發生了變化,彌勒信仰被添加了進來,又與摩尼教發生了某種形式的融合。兩種宗教都穿白衣,吃素食,以至于時人往往混淆不清。白蓮教借鑒了摩尼教的組織形式而成為更有力的革命機構,“摩尼教提供了一個由世俗教徒組成、有自己的經文、圍繞著世襲領袖嚴密組織起來、實行互相幫助的獨立教派的著名范例。”更重要的是,摩尼教的明王下世觀念也被帶入了白蓮教。這恰好與彌勒下生的救世主內涵是完全契合的——原本脫胎于伊朗宗教的摩尼教就與密特拉、彌賽亞乃至彌勒有著內在聯系。
其實代表“慈悲——愛”的觀音與代表“救世主”的彌勒結合起來,已經十分類似于基督耶穌,但白蓮教始終沒有像基督教那樣取得成功,而是更接近摩尼教在伊朗所遭遇的命運。其面對的外部環境似乎并不比當年羅馬帝國更為嚴苛,但這一運動中一直沒能出現一個像基督耶穌或者哪怕是摩尼那樣道成肉身的核心人物,其教民之中也或許充斥了更多的愚昧、迷信和狂熱。白蓮教的被禁是彌勒內涵中已經延綿千年的救世主屬性遭到的又一次重大打擊。事實上從北魏就開始出現假托彌勒下生而進行的造反活動,到了隋代更是連續發生了三次大規模以彌勒為名的叛亂。這令歷代統治者都多少對彌勒信仰抱有某種警惕。彌勒最具差異化的未來佛/救世主屬性,始終無法像基督教那樣,找到與世俗政權和諧相處的模式。追根究底,佛意味著涅槃寂靜,而救世主意味著他力救贖,這組觀念或許原本就難以真正調和。
四、靈感事例與神僧化現
觀音的靈感故事數不勝數,對此已經有過頗為充分的學術研究,從中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特征:1.靈感故事的主角人群十分廣泛,上至帝王下至販夫走卒,從僧人、文人到老嫗或者罪犯,幾乎無所不包,但是占據數量最大的還是普通百姓②;2.靈感故事的內容同樣無所不包,常見的類目包括拔病苦、救水火難、救鎖械難、得子興福、得慧、延壽、度生死、孝行所感與往生善處、業報、神力攝化、示現消災、示現垂護等等,其中的子類目又可以分出許多。基本上觀音展現神跡并無差別心,但是從人口比例而言救助普通百姓的事例自然更多,而且大多回應與百姓生活疾苦息息相關的問題。
而彌勒的靈感故事則有所差異。其中一種模式是信徒往來兜率天面見彌勒,并向彌勒就佛法問題進行求教。另一種則是以生身入定以求待見彌勒下生的故事。這兩類故事的主角往往是大德高僧、知識分子,且需要信徒或是對真理或是對信仰有極高的熱情。這種求道者屬性并不利于彌勒在底層群眾的傳播。
菩薩神跡的另一種展開模式是神僧化現,即將菩薩的神跡投射到現實中的僧人身上。觀音的神僧化現有兩個十分著名的例子,即梁武帝時代的寶志禪師與唐代的僧伽禪師。對寶志的記載描述他可以“數日不食亦無饑容”或者“一時之中,分身數處”,甚至可以在帝王面前撕開自己的臉皮,變出十二面的觀音之相。僧伽的傳說也和寶志十分類似,他的神跡包括用自己的洗腳水治愈人們的疾病;據說他的頭頂有一個小孔,從中有異香飄出等等。
無論如何,這兩個傳說中除了“神奇”的要素,“怪異”的要素也讓人印象深刻,這也和后世以離經叛道著稱的濟公、布袋和尚等事例一脈相承,似乎作為肉身化現者施展神力,若不添加些“怪異”要素便難以抓住民間的吸引力。但當妙善公主的故事興起之后,一個更符合觀音慈悲內涵的女性的化身似乎比怪異的神僧更受到中國人的認可。寶志和僧伽的模式在觀音的中國化進程中就此終止。
而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彌勒在中國化的進程中遭遇了一些困境,凈土的屬性被彌陀/觀音取代,未來佛/救世主屬性為統治者所抑制,在般若智慧的層面又難以與文殊抗衡,甚至“大慈”的特性也多多少少與觀音重疊。在這樣的情況下,彌勒完成了向布袋和尚形象的轉化。被認為是布袋彌勒原型的契此和尚,其部分事跡幾乎是前人的翻版,比如分身、預知天氣等。根據記載,契此“形裁腲脮蹙額”,即總是愁眉苦臉,最初的布袋彌勒造像身材也尚算適中。在演變的過程中,卻變成“笑口常開”“大肚能容萬物”的Happy Buddha——然而這些作為布袋彌勒的核心元素卻已經是彌勒最初內涵中完全沒有的內容了。彌勒與神異僧模式結合,發生了從內到外的巨大變化,幾乎成了另一位全新的“偶像”,卻最終受到了中國人的真正接納,這也許是一種無奈的偶然?
結語
觀音和彌勒從菩薩信仰興起開始就是最為重要的兩位大菩薩,早期印度的佛教圖像學研究證明了觀音和彌勒曾經作為釋迦佛的左膀右臂,緊密相關。但是經過后期的演變,在進入中國時已經成為兩位相對擁有各自獨立法門的菩薩,甚至在部分領域還需要“一較高下”。二者在中國化的進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內涵而遇到不同的問題,并采取了差異化的方式與中國的文化實現了融合。觀音的中國化方式盡管出現性轉這樣重大的變化,卻與其原本的內涵頗為契合,而彌勒則由于種種原因,成為了大肚和尚Happy Buddha,在中國發展出了“樂觀”“寬容”的全新積極含義。二位菩薩也曾在某些場合再次相遇,盡管不一定成功,卻讓我們看到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發展的另一種可能。盡管如果以某些世俗角度而言,觀音目前或許受到更多的崇拜,但其宗教實踐也往往變得更加功利化,令人忘記了佛法的本意。而彌勒下生作為其最為核心的內容,則需要與其新加入的內涵一起,從“救世主—動亂”的狹隘框架中走出來。或許只有這兩位菩薩的精神能夠再度聯合在一起并被世人所真正理解接受,“人間佛教”的理念才能最終實現。
注 釋:
①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第72—77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②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第169頁,法鼓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參考文獻:
[1]宮治昭.涅槃和彌勒的圖像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3]王雪梅.彌勒信仰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王忠林.可能與必然——論彌勒圖像的轉型與定型[J].世界宗教文化,2010(6).
[5]唐嘉.《彌勒為女身經》探微[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6]趙超.略談中國佛教造像中彌勒形象的演變[J].中國歷史文物,2003(2).
[7]范立舟.彌勒信仰與宋元白蓮教[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
[8]梁工.彌賽亞觀念考論[J].世界宗教研究,2006(1).
[9]張子開.試論彌勒信仰與彌陀信仰的交融性[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
作者簡介:樂源(1986—),男,漢族,浙江省寧波市人,單位為北京大學哲學學院,研究方向為宗教學。
(責任編輯: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