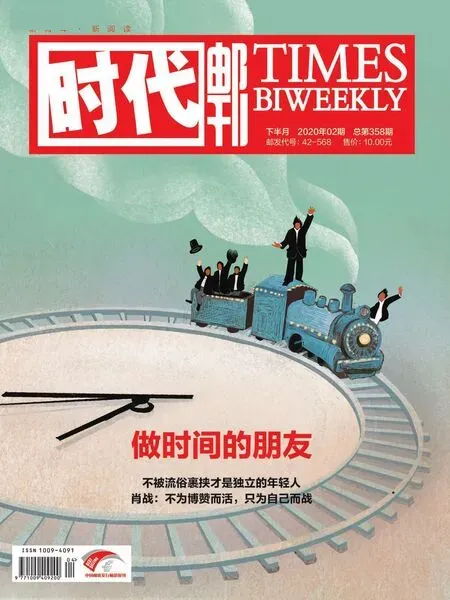小心那些敢做不敢當的隱性歧視
文 楊鑫宇
深藏在人們心底的不平等觀念,常常在層層偽裝的包裹下,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出現,雖無歧視之名,卻有歧視之實。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歧視”一詞的含義十分簡單:“不平等地看待”。這短短的六個字,以一種清楚透徹而又言簡意賅的方式,將這個備受爭議的社會現象明明白白地解釋了出來。不論在外在表現形式上如何變化,追根究底,歧視的本質都是“不平等”。歧視的受害者,因為無法得到平等的對待,而不得不在生活中蒙受欺凌,而歧視的施加者,也正是在其腦海中不平等思想的影響下,走向了傷害他人的歧途。
在口頭上,幾乎每個人都會堅定地宣稱:自己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然而,落實到行動層面上,依然能夠身體力行地踐行這一原則的人,卻顯得少之又少。這使得那些公眾未能及時發覺的歧視,如同一道道隱秘的傷口,持續不斷地撕裂、傷害著我們的社會。為此付出代價的,不僅是那些受到歧視的群體與個體,也是整個社會的正義與文明。
誠然,那些讓人一眼就能看穿的歧視行為,早已成了人人唾棄的社會公害。面對針對特定地域與人群的惡毒侮辱,或是那些毫無依據的性別門檻,誰都不難像模像樣地喊上幾句與地域平等或是性別平等相關的響亮口號。但是,一旦我們將視線延伸到細致入微的生活細節當中,便會發現:深藏在人們心底的不平等觀念,常常在層層偽裝的包裹下,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出現,雖無歧視之名,卻有歧視之實。而制造并維持著這些“隱形歧視”的人,正是那些嘴上喊著“拒絕歧視”,實際上卻并不愿意真正對不同的人群平等相待的人。
當我們判斷一件事究竟是不是歧視的時候,最常用的標準,便是考察這件事里是否存在對不同群體的差別對待。然而,這個標準固然沒錯,但許多時候,實質性的差別對待,都是在某些看似“正常”的現象的“轉譯”之下,通過偷梁換柱、暗度陳倉的方式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歧視的施加者不會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被歧視者都未必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其實已經遭遇了不公。
倘若一所學校拒絕招收女性入學,人人都會承認,這是赤裸裸的性別歧視;一個在群里公開表示“本公司不招某省人”的HR主管,必然會因其地域歧視行為被全國網友罵到抬不起頭。然而望向身邊,熱衷于給不同地域總結標簽的人,在我們的社交圈里卻隨處可見。事實上,這些現象無一不是徹頭徹尾的歧視,但是,面對這些歧視,普通人卻很容易為其借口所惑,以至于對其中的歧視實質視而不見,渾然不覺。
伴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反歧視”逐漸成了社會上的主流話語,但是,僅靠話語的變遷卻是遠遠不夠的。大多數“聰明”的歧視者,并沒有從心底摒除自己的不平等觀念,而是收起了自己的獠牙與利爪,換上了文質彬彬的偽飾。“我不歧視女性,但女性就是沒有男性理性。”“我不歧視河南人,但河南人就是素質偏低。”——盡管這些論述無不是以“我不歧視”開頭,但其中的主旨思想,卻都是對不同人群毫無依據的不平等看待,完全符合“歧視”的原始定義。唯有洞察到此類“敢做不敢當”的歧視論調的不堪本質,我們才能看穿那些躲藏在“轉譯”機制背后的隱性歧視。隱性歧視也是歧視,其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完全不亞于明目張膽的歧視,也只有對這些隱秘的傷口及時“止血”,我們才能避免不公不義讓社會付出更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