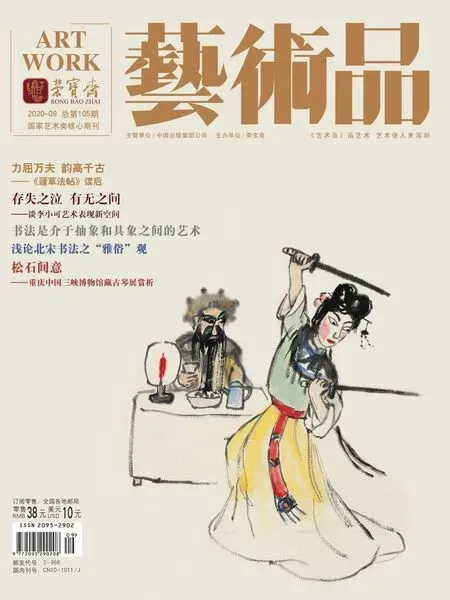法門與轉換
——談《臨摹與創作》系列
文/王祥北
(本文作者任職于榮寶齋出版社)
書法學習如何從臨摹過渡到創作?這是書法愛好者面臨的難題,這個難題沒解決好,就很難進入書法的自由王國之中去。
臨摹的方法有多種,但臨摹的目的卻只有一個,就是自如地創作。關于臨摹,我們在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人經典作品寶庫時,往往會不知所措,什么都喜歡,什么都不想擱下。因此,一方面不知從何下手,另一方面則眉毛胡子一把抓,都很迷茫,時間花了不少,但一離開臨摹的對象就不會寫字了。還有的人,臨摹方法很正確,臨摹的功夫很深,水平也很高,幾乎能將所臨的碑帖臨摹得非常逼真了,卻長期停留在臨摹的世界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創作的時候則無從下筆,即使勉強創作出來的作品也非常僵硬,與臨摹的作品有天壤之別,感覺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這兩類人所面臨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如何處理好從臨摹到創作的轉換問題,中間缺少過渡的途徑。對集字的臨摹與創作就是一個非常實用的途徑。
古人對集字是非常重視的,大家熟知的唐代的《懷仁集王圣教序》就是最為著名的集字作品,這件作品字數多、字形美、效果好,因此,一直以來成為學習行書的必經之路,也可以說是行書學習最好的范本之一。這部作品里的集字,大部分是從王羲之作品中直接引用過來的,還有一些是利用王羲之作品中的偏旁部首組合起來的,還有極少的一部分是根據王羲之筆意重新勾摹出來的。《懷仁集王圣教序》只是針對王羲之一個人的作品而言,沒有涉及其他作者的作品,也沒有局限于王羲之的某一件作品,可以說是集王羲之用字之大成的。不過,在面對篆書、隸書、楷書的集字時,情況就有所不同了,不能像行草書那樣可以把作者所有的作品作為采集對象了,只能局限于某一件作品。比如我們古人對隸書《石門頌》的集字,就只能從《石門頌》中選字,其他作品中的字是不能選用的。同樣,在篆書、楷書的集字中也是如此。古人集字的作品或者圖書得到了廣大書法學習者的喜愛,因而長盛不衰。
由于科技的原因,古人集字的難度是較大的,尤其是《懷仁集王圣教序》這種集作者所有作品于一爐的集字方式就更難了,懷仁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才把《圣教序》的集字完成。古人在對一碑一帖的集字中,往往都是以集聯的形式出現,因為,對聯的字數終究較少,比較便于對原碑帖中的字的選用,也更有利于對碑帖的臨摹。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的集字相對古人來說方便多了,各種設備和軟件的出現,方便了我們的集字,也拓寬了我們集字的范圍,豐富了我們集字的種類。不過,如何集成一件完美的作品,依然還是一件難事,同樣要求集字者具備良好的書法水平,對書法的美有正確的認知,知道如何去體現書法的美。這樣才能保證集字作品更便于臨摹,更便于學習者體會到一個創作的新思路,從而使學習者快速地進入到創作這個層次上來。另外,集字者還必須具備熟練掌握電腦和各種集字軟件的操作能力,使集字既快速,又高效。
本套叢書的行、草書部分,所選用的范本都是“二王”帖學一路的經典作品,打破了某家某派的界限,把不同帖上的字,按照需要合理組合成一件作品;所選的文字內容都是優美的古典詩詞,非常適合創作。篆、隸、楷等書體部分,依然按照古人的集字方式,一碑一帖獨自成書,所選文字內容有些是集字者自己創作的對聯或詩詞,也有些是精選的古典詩詞。
本套叢書的編著者都是既有較高的書法創作水平,也有文學鑒賞能力和創作能力的書法工作者,同時,也是電腦和各種集字軟件的熟練操作者,在工作中克服了不少困難,但在編輯出版成書時也可能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不過,我們的出發點就是想為書法學習者提供一條從臨摹到創作轉變過程中的新思路,為書法學習者尋找一條行之有效的學習之路,并期望學習者能在這條道路上走得越來越遠,水平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