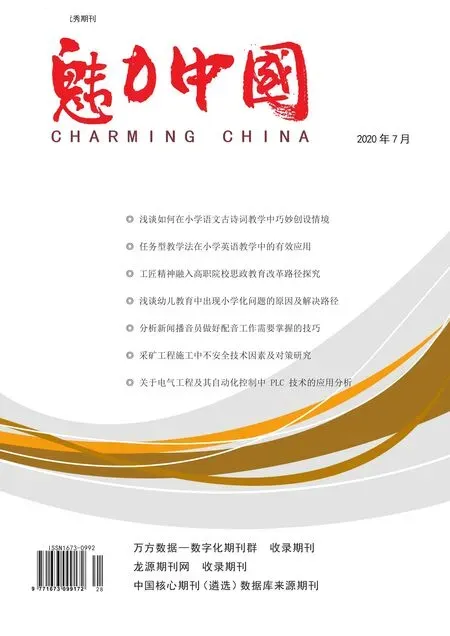親屬證人出庭豁免制度的剖析與完善
(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
一、歷史與現實基礎
(一)歷史沿革,維護人倫
我們能夠從傳統法制觀念“親親相隱”中找到親屬拒絕出庭作證權的影子。孔子曾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強調了兒子與父親相互隱瞞惡跡的封建綱常禮教,充滿了人倫色彩。雖然古今社會現狀大不相同,但這種維護人倫秩序的做法對維護人的尊嚴和社會秩序有著重要作用,具有某種程度的正面效用。
(二)家庭穩定,社會和諧
一方面,我國法律賦予親屬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對維系被告人的家庭關系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法律賦予了當事人選擇是否出庭的機會,以此來柔化特殊情形下強制出庭的制度。另一方面,該制度對維護社會良好秩序也具有積極影響。親屬證人負有出庭義務會使家人之間關系變得緊張,進而影響社會和諧,出庭豁免制度能對此進行緩和。
(三)融情于法,預防風險
親屬證人出庭豁免制度正是情理交融的體現。強制親屬和強制證人出庭相較而言,由于親屬關系對人們而言往往更為寶貴,前者的風險更深一層。確立拒絕出庭權是立法者基于人倫親情的考慮,意使親屬間免受當庭對質的痛苦。此外,若能使當事人由此對法律產生敬畏,并將其轉化為守法的動力,便能自然地降低道德和法律風險。
二、存在的問題
(一)權利的歸屬者不明
首先是權利歸屬問題。由于出庭作證需由親屬來完成,權利的主體似乎應該為被告人的親屬。這樣的設置能讓親屬掌控出庭的機會,但卻難免其惡意。若是出庭作證豁免權的主體為被告人,便又不符合權利的人身屬性,還可能阻礙親屬出庭。
其次是親屬的范圍問題。法律規定的出庭作證豁免權主體的范圍比“近親屬”范圍更窄。這或許是立法者基于對親屬之間親疏差異、司法資源配置考慮后的抉擇。不少學者認為應該將其擴展,至少與“近親屬”的范圍相吻合,從而使法律整體更相協調。
(二)妨礙被告人質證權
被告人依法享有對控方證據質辯的權利。通過對證人的詢問,可以讓證人全面深入地陳述證詞,從而暴露虛假的證言。依照作證豁免制度,被告人親屬對被告人有罪的指稱無法在法庭中得到充分質證,等于是一定程度上將控方證據與能夠質疑甚至將其攻破的辯方證據隔離開來。這樣不僅會妨礙被告人的質證權,導致控辯雙方不平等,同時也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實。實踐中,有時控方還會通過欺騙、引誘等方式從親屬的口中套出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并極力勸說證人不要出庭。[1]
(三)難以查實言詞證據
言詞證據具有“冰火兩重天”的屬性,既能直觀反映案件真實情況,又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片面性。[2]一項證據是否真實有效賴于證人的品質、記憶力等主觀因素。一旦證人不能出庭作證,言詞證據便始終無法被充分質證。
法官在認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時,往往需要對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確實性和充分性進行審查。行使出庭豁免權的前提是該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可見其效力會大大影響審理結果。
(四)影響司法效率公正
首先,親屬不出庭作證會影響司法效率。即使在重大非死刑案件中,親屬在庭外提供的有矛盾的證言也不能被排除。因此控方要更多時間來完善證據鏈;辯方獲得反抗空間,拖延審判進程;法官也需要更多精力來審查證據。
其次,親屬不出庭違背了直接言詞原則,損害司法公正。親屬證人出庭豁免制度的前提之二是公訴人、當事人等對其證言有異議且該證言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既已受質疑,說明親屬證言本身很可能存在漏洞。此時親屬不出庭則有違程序公正。
三、完善思路
面對種種問題,有學者認為該制度無法實現立法初衷,因為對家庭關系維系產生沖擊的是出庭而非作證。[3]與此相對,有的學者主張確立真正的免證權,同時明確例外情況。[4]后種觀點可以破除親屬作證義務前后齟齬的困境,使制度更加自洽,值得借鑒。基于對相關難題的剖析,現提出如下完善建議。
(一)免證為原則作證為例外
確立真正的親屬免證權規則也就是要將提供證言和接受質證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使出庭豁免問題不復存在。如果親屬在庭審前提供了證言,就不再享有出庭豁免的特權,從而縫合上違反直接言詞原則的口子。但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免于作證。例如在侵犯國家和社會利益的案件中,為了打擊犯罪,親屬不能行使免證權。
(二)明確權利的主體及范圍
綜合來看,將出庭作證豁免權賦予被告人親屬似乎是更好的選擇。至于親屬范圍的問題,學界普遍認為法律規定過于狹窄,而具體如何界定則眾說紛紜。如果太寬泛會影響案件偵辦,妨礙公平正義;反之則會觸犯倫理界限。基于此,我們可以考慮誰作證會對其家庭以及家人之間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和無法挽回的傷害,從而進行衡量。
(三)完善行使免證權的程序
首先是權利的行使時間上,應當允許在訴訟各階段都可以行使。但若親屬先前放棄權利,不得再以此為由拒絕出庭。其次是權利告知上,辦案人員在訴訟各階段都應告知權利和放棄權利的后果。最后是權利被剝奪的救濟上,應賦予親屬向其上一級機關申請復議的權利。[5]此外,當證據的收集違反了法定程序時,應排除相關證言。
(四)規范證人證言采信規則
親屬作證制度產生頭尾不相匹配的尷尬狀態,一大原因就是我國的證人證言采信規則尚不完善。若要從根源解決問題,應當從根本上明確其采信規則。考慮到親屬證言更可能具有虛假性,我國可以先從被告人親屬入手實施證人證言的直接言詞采信規則,由點及面,最終推行到所有證人證言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