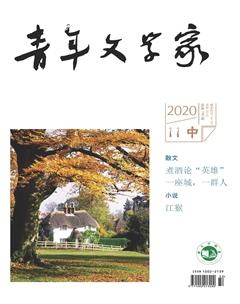女性:從空洞能指到自為主體的話語建構
摘? 要:女性在某種意義上一直處于男性的附屬地位,或作為其“衍生品”而存在。有所不同的是,古代的女性更多的是一種空洞的能指,喪失了自我的意義與話語權利,女性自身對此則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接受或認同,而近代以至于今天的女性則逐漸開始覺醒并尋找失落的自我,同時也在探索中建構屬于女性自身的話語系統。
關鍵詞:女性;空洞能指;話語建構
作者簡介:喬文東(1996-),男,漢族,河南周口人,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2-0-02
從女人作為男人的一根肋骨的創世論開始,女性便已經作為男性的附屬存在,而這種附屬地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型中女性不得不面對的窘境。隨著母系社會的終結便隨之確立了男性的地位,而這種男性絕對權威的確立使得女性的意義逐漸邊緣化,成為男性視角下的“他者”和男性欲望化的象征,從而喪失自我,成為一個空洞的能指。盡管有個別的女性意識到這種不平等,但這種個體的覺醒在女性的集體失聲狀態中是難以對抗男性絕對權威的。及至近現代以來,這種女性的集體失聲才被打破,開始走向反抗男權壓迫的道路,尋求女性地位的重建和與男性話語權的爭奪。本文便以蘇青的《結婚十年》為例,對女性作為空洞的能指與在“菲勒斯”困境下話語建構的道路進行觀照。
一、女性作為空洞能指的邊緣話語
在幾千年來男性權威統治下的中國,女性很大程度上沒有個體的權利與地位,而是作為第二性和一種失我的“空洞能指”而存在。在父權制的符號系統內,女性處于集體失聲的狀態,盡管在某些情況下存在一定的女性聲音,但往往是假借于男性發出的“偽女性”話語,實際上更像是男性話語的“影子”,另一種是可以看作是隱匿化的民間話語或作為被封殺的異端而存在于官方話語界外的邊緣話語。男性絕對權威以及由男性所制定的“規則”使得女性個體意識被遮蔽成為虛化的個體。正如蘇青的外婆把接納丈夫在外的另一個女人看做是一種賢惠的行為。此刻,男人出軌不是男人的錯誤,反倒是女人無能的表現,可見其社會評價標準的畸形和女性自我的虛無化。
《結婚十年》中懷青的婚姻也彰顯了我們所提到的兩種邊緣話語狀態,懷青第一次懷孕生下的卻是女兒時,整個家庭的陰郁氛圍是顯而易見的,“我心中只覺得一陣空虛,不敢睜眼,仿佛慚愧著做了錯事似的”,[1]直到后來生下了兒子元元,似乎她才得以“揚眉吐氣”。蘇懷青的這種心理癥候即是傳統的“母以子貴”的思想因襲下,女性需要憑借另一個男性的權威來支撐自己的地位和話語權。懷青盡管有著這種因襲舊思想的無意識,但更多的是她作為新式女性的存在,正如在結婚當天由于等的久而急于小解的懷青“忽然得了個下流主意,于是輕輕地翻過身來,跪在床上,扯開床套,偷偷地小便起來”。[2]以及后來她選擇去學校教書和寫文章并表達了某種女性獨立的見解,盡管還不成熟,但已經對于傳統的男權文化有了反抗的意識。盡管那種女性意識所傳達出的話語依舊無法與主流話語系統所抗衡而淪為一種隱匿化的民間話語和邊緣話語。但值得肯定的是,這種女性自我的意識充分表現了女性開始覺醒和進行思考、質疑,開始從真正意義上建構女性主體。
正如蘇懷青的新舊雜糅的矛盾性那樣,她一方面作為新式女性去挑戰男性權威話語,從而獲得主體的確立,建構屬于女性自身的話語系統。而另一方面又渴望借由男性之手來完成自己權威母親話語的舊夢,卻又無意識掉進男權文化的陷阱,充當著男性欲望的“符號”和“次生物”。而這種新舊參半的女性內心的對于新舊思想的博弈,時至今日,依舊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大小舞臺之間”。
二、走向自為主體的話語建構
自近現代以來,女性開始覺醒,走向話語上的自為,這種自為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政治自為,主要體現在女性為了反抗男性壓迫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爭取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享有比肩于男性的權利,也即爭取為“人”的權利。另一方面是文化自為,也即女性并不滿足于以男性標準來定位自己,而是強調自我的存在,試圖找回曾經被遮蔽的女性情感、女性價值,從而進一步爭取做“女人”的權利。《結婚十年》中,懷青不甘于做家庭的“零余人”而渴望出去工作,從而來獲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和在家庭與社會中地位的認可,我們可以看作是女性在政治自為上的一種實踐。而同時,懷青在新婚當晚便知道了丈夫與嫂子瑞仙的不軌后,她并沒有選擇離婚或者大鬧,因為她明白這是徒勞無益的,反而會落得一個多事、不賢惠的名聲,既然她選擇了這條路,她就不得不遵守這種社會的男權“法則”懷青盡管難以擺脫舊社會、舊家庭、舊思想的束縛,但作為新女性的她還是為爭取女性權利勇敢地邁出了第一步,也即政治自為的實踐。
當懷青有了一定教育與經濟地位時,她便開始向更高層次邁步,也即精神層面。在婚姻中,她只是“被標簽”,被認為門當戶對的婚姻象征著完美,但女性卻處于完全失聲的狀態,這一切仿佛與女性沒有任何關系,但她卻不甘如此,于是我們在文本中看到了“兩顆櫻桃”的故事,現實中婚姻不幸卻難以逃脫的懷青在校園里遇到了那個令她心動的應其民,兩人一見傾心,而此刻的懷青可以說是真正體會到作為女性的那種情感萌動,那一刻,她是她自己的——開始了客體、“他者”、非主體到主體的過渡,而這同樣也是對文化自為的一種實踐。但這種實踐的結局并不理想,懷青因為懷孕而只能忍痛選擇離開應其民回歸了家庭。蘇懷青與徐崇賢這新舊合璧的婚禮已經在冥冥之中注定了這種矛盾化的悲劇,同時也注定了懷青的悲劇,而這卻不能完全歸罪于懷青,她只是女性集體失聲下的次聲波,無力挽狂瀾于既倒。
也許更應該注意的是,隨著像懷青一樣的先覺者女性愈來愈多,呼喊聲愈來愈強,于是政府賦予了女性一定的權利,但這種賦予同樣是在男性主導下的賦予,女性被承認、女性權利被賦予,使得女性對“自己是否是女性解放中的主體,她今天的一切究竟是她應該有的一份權利還是被強制規定的一種身份”[3]產生了質疑,并在這種狀態下重新陷入男權文化的無意識遮蔽,因此說,對于女性主體建構以及構建女性話語系統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
三、“菲勒斯”困境下女性未來的路
精神分析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認為,“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將永遠蒙受著菲勒斯(phallus,它不是真正的生物性的陽具,而是父權的隱喻與象征)缺失的焦慮與恥辱,她只能通過從男人處獲取一個孩子——一個想象中的菲勒斯,并借以進入象征式。”[4]換言之,也即《第二性》中所談到的“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個有性征的人,才能夠成為一個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5]實際上就是說女性若想進入到權威話語中,便只有借用男性話語或尋找一個“替代”作為自己進入男性話語的渠道——母親話語,只有自己誕下一名男嬰擁有了做母親的權利,才能將這名男性作為自己的替代的象征而進入男性話語系統,而這種進入也是無我的。
面對這種困境,女性應當何為?這是一個在女性尋求主體以及話語建構歷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大課題,從《結婚十年》來看,蘇青仿佛在文本為女性探索到了一些自我解放的道路,一是在于經濟上的獨立,二是主體精神的自尊。但立足文本來看,作者對于這種道路的可行性同樣存疑,而正是這種疑問使得蘇懷青的自救展現了許多矛盾點。
首先是經濟上的獨立,由于丈夫后期頹廢致使家庭困頓,懷青渴望能夠擁有經濟能力來支撐家庭,而現實中女性并沒獲得社會的職業認可,可供她們賺錢的方式少的可憐,更何況是有尊嚴的生活。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可謂遭遇重重困頓,丈夫的輕視、孩子的負擔、社會的不認可及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結構和部分女性狹隘的職業心理導致她們在經濟上難以取得與男性比肩的收入。盡管女性在社會的經濟地位中處于弱勢,但只有邁出了第一步,才有繼續反叛的可能性,而這種反叛會給男性造成一種權威旁落的失落感,這種失落感地逐漸加劇才有可能使得男性重新思考女性及其本身,同時也使女性占領一定的意識高地和建構主體以及話語系統的可能性。
其次便是精神的自尊,即一個人希望在各種不同情境中有實力、能勝任、充滿信心、能獨立自主的精神狀態。而這種精神狀態在蘇青的文本中可以說是一種對未來的試探和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信,當懷青收獲愛情卻又因為懷孕不得不放棄,而離婚卻又帶著肺結核的面紗,朋友的勸告又暗示了女人所謂的貞節,蘇青以這種方式結尾表現了她對于女性集群未來的失望。但蘇青的文本敘述與她內心的想法卻是一種鏡相關系,她內心渴望建構女性話語主體,但卻表現出對未來的失望,正是這種失望才能折射她內心的渴望狀態。從長遠來看,在我們所提到的精神的自尊實際與蘇青內心的憧憬是不謀而合的,只是她有種歷史負重的無力感,所以并未完成她的理想建構。
對于菲勒斯困境下女性自我建構的不斷失敗或被命名的無奈在某種意義上被看作是一種“結構性缺損”,而這一系列的“結構性缺損”實則也正是為了意識形態的完滿和理想的女性主體建構與找回失去的話語權,盡管這條道路走得并不順利,但是既然稱之為“缺損”,那么說明本就有曾屬于這個模塊的東西丟失了,或者說被他者所竊據,而這種本位性的缺失則在一定程度上為女性地位的重新確立起到了正名的作用。
盡管蘇青囿于時代背景以及認知能力,在主體理想中建構完成的意識在現實中卻無法實現,但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女性的先覺者,她已經完成了在那個時代的使命。女性作為空洞能指的歷史由來已久,并非某個人或某群人的奔走呼號或者行動便可以從實質上改變這種現狀。對于女性主體以及話語的建構,是一個歷時性的問題,是一個需要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斷向前推進的工程,它就像人類的進化一般,只要一代比一代有了向好的變化,那么未來就有希望,困境才有可能被打破。
參考文獻:
[1]蘇青.結婚十年[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2009:51.
[2]蘇青.結婚十年[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6.
[3]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23,51.
[4]蔡笑岳.心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07-108.
[5](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