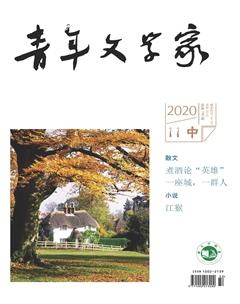掙脫牢籠的渴望
摘? 要:《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籍西班牙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創作的一部反映少數族裔女性成長的小說。作品中融合了成長小說的典型元素,又從女性的身份視角出發,展現出主人公埃斯佩朗莎在移民社區內掙脫重重牢籠,渴望實現夢想,獲得自由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女主人公的掙脫是為了更好的回歸,作者將自己的成長經歷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具有為族裔女性發聲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
關鍵詞:困惑與牢籠;少數族裔;女性成長
作者簡介:李倩蕓(1996.4-),女,漢族,山東日照人,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2--02
一、引言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一本典型的女性成長小說。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居住在拉丁裔貧民社區芒果街上的女孩埃斯佩朗莎。她在一步步邁向成熟的過程中用自己敏銳的洞察能力和共情能力觀察體驗著所生活的世界,講述年輕的熱望和夢想。但她的成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埃斯佩朗莎作為一個具有少數族裔女性的“邊緣人”,需要掙脫重重牢籠。懷著沖破牢籠的渴望,在目睹了周遭女性被困在牢籠下的生存狀態之后,在身邊人物的正反面激勵與影響下,她的自我意識和女性意識開始覺醒,她不愿再被束縛,渴望用讀書寫作改變命運,并且有高度的使命感,愿意在掙脫之后回歸,幫助整個族裔社區在“大熔爐”的美國社會發聲,體現了作者希斯內羅絲對于和境遇相似的少數族裔移民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
二、束縛成長的困惑與牢籠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其著作《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曾經說到“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弗吉尼亞,2010),這部成長小說的主人公也是一樣,埃斯佩朗莎居住在擁擠臟亂的社區里,也渴望擁有一座屬于自己的房子,一個使其感到有歸屬感的房子:“于是我明白,我得有一所房子。一所真正的大屋。一所可以指給別人看的房子。可這里不是。”(希斯內羅絲, 2006:5)在這個夢想的驅動下,埃斯佩朗莎努力地想如何實現它,但是隨著她慢慢地開始與周遭社會產生接觸,生活的殘酷真相漸漸浮現,在經歷了困惑后發現,加載在一個少數族裔女孩身上的是一層層看不見的隱形牢籠,而成長就意味著沖破牢籠。
1. 美國主流文化的沖擊
作為進入美國的移民,融入主流文化是少數族裔移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割裂還是妥協,年紀輕輕的埃斯佩朗莎陷入了成長過程中的困惑。貓皇后凱西的出現對埃斯佩朗莎是一種誘惑和沖擊,凱西是一個白人女孩,擁有著讓人羨慕的資源,而埃斯佩朗莎想和她做朋友卻被告知只能做到“下星期二”,因為她即將要搬走,理由是“這個社區的人越來越雜了”(希斯內羅絲, 2006:16)。對于友情的渴望受到了來自美國主流文化的沖擊,但埃斯佩朗莎的內心卻依然懷有對自己傳統族裔文化身份的堅守,她不愿為了友情而被同化。只有在對族裔文化的認同中,埃斯佩朗莎才能感覺到真正的快樂,這也為她后來的回歸留下了伏筆。
2. 傳統墨西哥男權社會的束縛
埃斯佩朗莎對族裔文化的認同,對美國主流文化的掙脫并不意味著接受傳統墨西哥男權社會的束縛。在《我的名字》這一篇中,埃斯佩朗莎介紹了自己名字的寓意:
“在英語里,我名字的意思是希望。在西班牙語里,它意味著太多的字母。它意味著哀傷,意味著等待……”(希斯內羅絲, 2006:10-11)
主人公的名字和她曾祖母的一樣。曾祖母雖然年輕時反抗過,但還是被曾祖父用麻袋套住頭扛走,然后只能“用一生向窗外凝望。”埃斯佩朗莎繼承了她的名字,可她不想繼承她在窗邊的位置,一輩子只有“悲傷”和“等待”。祖輩的女性逃脫不了被男性束縛的命運,而埃斯佩朗莎不想接受命運,于是她希望取個新名字。換名意味著她想要重構身份,改變女性傳統命運。墨西哥傳統文化留下的男權專制社會是埃斯佩朗莎急于擺脫掉的禁錮。
3. 居住地區的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一直是美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在女主人公居住的少數族裔社區也不免受到來自美國WASP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
在年輕的埃斯佩朗莎看來,種族帶來的差異是一種成長過程中的困惑,自己所居住的社區與其他種族居住的社區一樣被白人主流社會排斥,而少數族裔群體之間又會產生新的互相歧視。而埃斯佩朗莎反抗的方式就是通過寫作去為自己所在族裔群體發聲來擦除種族歧視。
三、被困在牢籠的傳統女性
種種的牢籠構成了對埃斯佩朗莎成長的阻礙,然而對于多數傳統族裔女性來說,這種根深蒂固的阻礙一直是困住她們尋求自我的牢籠,年輕的女主人公在這些傳統女性的身上看到了她們窘迫的生存狀態,加深了掙脫牢籠,獲得成長的渴望。
1. 瑪琳
在埃斯佩朗莎的成長過程中,瑪琳是她目睹的一個被父權制下的婚姻困住的女人。她比埃斯佩朗莎大一些,懂得許多事,她渴望改變現在的生活狀況,過美好富足的生活。但是她把這個期望寄托在了男人和婚姻上。“瑪琳,街燈下獨自起舞的人,在某個地方唱著同一首歌,我知道。她在等一輛小汽車停下來,等著一顆星星墜落,等一個人改變她的生活。”(希斯內羅絲, 2006:33) 她想要到市中心找份工作,不是為了自力更生,而是為了能有更加精致的外表來在地鐵里遇到個會與她結婚的男人。
2. 媽媽
母親對孩子的成長影響是巨大的,在外界看來,埃斯佩朗莎的媽媽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她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逐漸意識到母親也是一個被社會和家庭束縛住的女人。“我本來可以出人頭地的,你知道么?”(希斯內羅絲, 2006:123)這是母親內心的真實渴望。她會說兩種語言,會唱歌劇,知道怎么修理電視機,也會用針線畫畫,但是她還是深陷在父權和種族歧視的牢籠中。“身邊的諸多母親們不僅從身體上無法獲得社會物質性自由,精神上更是完全被閹割,沒有自我言說的能力。”(劉蓉, 2012)精神上的自由對于母親來說是難以實現的渴望,她有健全的身體卻喪失了自我言說的精神自由,失去了接受教育改變命運的機會。
四、追求自由的成長之路
“生活就是最好的教師,它教會成長者以最合理的方式面對自己的生活”(王政, 1995)埃斯佩朗莎一直在追尋著少數族裔獨特的女性身份,懷著掙脫牢籠的渴望和殘酷的現實生活做斗爭,并在周圍環境事物的影響下,實現了自己的成長,完成社會教育和自我教育的過程。
1. 自我覺醒與頓悟
埃斯佩朗莎在從未經世事的小女孩到成為一個具有成熟思想的女性的過程中,她自己的親身經歷讓她體會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當她和朋友們穿上高跟鞋,將自己的身體商品化,取悅男性,渴望進入成人世界,卻差點被性騷擾。女性想靠外表來改變命運,獲得男性的尊重是不可能的。埃斯佩朗莎頓悟:要獲得真正自主和強大的思想,不能靠美麗的外表。她的獨立意識開始覺醒。
同時,在對“四棵樹”的觀察中,她也汲取了自我成長的力量,自我意識開始萌芽,明白了堅強獨立的重要性。
2. 正反面人物的激勵
每個人的成長都會受到引路人的影響,埃斯佩朗莎也不例外。從與正反面人物的接觸和了解中,社會教育的客觀因素使她確定了自己的使命。“正面人物正面引路人包括知識和道德上接近于完美的人、伙伴式的人物以及主人公成長旅途中遇到的過客。”(芮渝萍, 2004)埃斯佩朗莎最終決定通過讀書和寫作來完成自己掙脫牢籠,獲得自由的過程也是受到了正面的激勵。阿莉西婭是促使主人公通過教育來改變命運的正面激勵之一。為了擺脫為全家操勞、卻處處受男性管制的命運,她拼命學習,選擇了去上大學。她也要像阿莉西亞一樣,努力學習,通過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另一個正面激勵是主人公偶然遇到了神話人物似的三姐妹,她們預言她會走出去,走得很遠,但是再三提醒她要記得回來,記得自己永遠是芒果街的人。
反面人物也是促使埃斯佩朗莎走向自我成長的關鍵因素。薩莉作為埃斯佩浪莎的好朋友,因為長得美,父親擔心她會和人私奔,于是把她鎖在家里。在這個社會群體中,父權制占絕對優勢,父親把女兒當私有財產,不能擁有自由。薩莉為了擺脫父親的束縛,匆匆結了婚,可是婚后的她仍舊生活在牢籠里。傳統父權的壓制,造成了她的懦弱和順從,最終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她的命運對于埃斯佩浪莎來說是一種直觸人心的沖擊,也更加使埃斯佩浪莎意識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五、結語
《芒果街上的小屋》作為一部成長小說,主人公的成長故事是少數族裔所經歷的典型,她成長中的困惑是墨西哥裔美國人的悲哀。(楊銘,2011)然而小說的女主人公埃斯佩朗莎作為年輕的少數族裔女性,雖然有著雙重邊緣人的身份,但是憑著敏銳的洞察力和感悟能力,在生活點滴中獲得傳統女性不得完成自我獨立與成長的反面激勵,在思考體驗自己的成長經歷中找尋自我,在四棵樹上汲取力量,通過寫作,掙脫社區,構建自我,堅持一所房子的夢想,逐漸完成了自我的成長。掙脫是為了更好地回歸,作者將自己的成長經歷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具有對族裔女性發聲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弗吉尼亞·伍爾夫. 一間自己的房間[M].田翔 譯. 沈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10.
[2]桑德拉·希斯內羅斯. 芒果街上的小屋[M].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06.
[3]劉蓉. 論女性成長的自我主體構建——重讀《芒果街上的小屋》[J]. 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 7(05):106-110.
[4]王政. 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M].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127.
[5]芮渝萍. 美國成長小說研究[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6]楊銘. 族裔女性的困惑與成長——析《芒果街上的小屋》[J].文學界(理論版), 2011(08):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