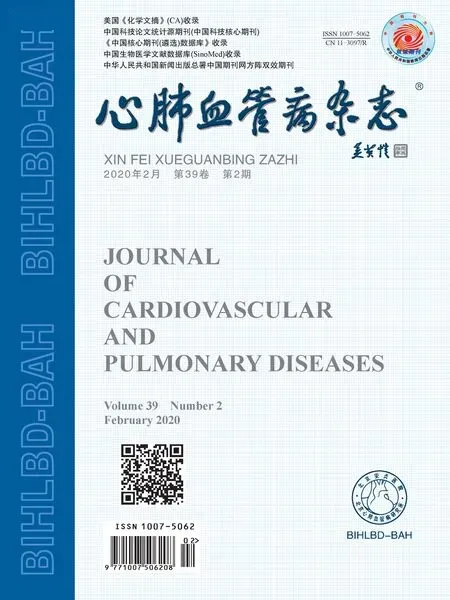馬方綜合征治療現況及前景概述
武玉多 何怡華 谷孝艷 張宏家
馬方綜合征(Marfan syndrome,MFS)是由原纖維蛋白-1(FBN-1)基因突變引起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急性主動脈夾層是患有MFS并且大動脈中層退變和動脈瘤形成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盡管MFS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但出生時癥狀和特征通常不明顯。在兒童期或青春期期間,受影響的個體出現嚴重的組織缺陷,特別是在主動脈,心臟,眼睛和骨骼中。考慮到這一點,即使年輕患者也應該避免對主動脈和心血管系統施加額外壓力和進行會導致額外壓力產生的活動。因此,如果做出診斷并及時開始預防性治療,MFS及其初步的病理生理血管重塑可以成功地改善,從而降低危及生命的并發癥的風險。本綜述將從MFS的外科和基因治療及其新機會、分子發現等方面進行分析。
馬方綜合征是最常見的遺傳性結締組織疾病之一, 發病率為2~3/10 000,由編碼FBN-1的基因突變引起[1],上世紀70年代初,一份關于MFS患者預期壽命和死亡原因的報告稱,受影響個體的預期壽命約為未受影響個體的2/3[2]。一些研究表明,與患有MFS的女性相比,男性患主動脈疾病的年齡更小[3]。與此同時,過去40年里患者預期壽命基本上翻了一番,但主動脈疾病似乎仍然是MFS患者過早死亡的主要原因[4],雖然MFS患者預期壽命普遍增加,但其他年齡相關疾病(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家族史、冠心病等)及影響心血管疾病發生發展的危險因素也可能影響MFS患者,仍然需要根據指南改進此部分患者的相關隨訪內容[3]。
1.手術治療
目前主動脈根部擴張仍然是MFS患者危及生命的并發癥,因此預防性手術治療一直是多年來的首選。1999年,Gott等[5]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進行一項包含675例患者的實驗中證實了,預防性手術優于急診根部替代的優勢,報告顯示預防性手術的30 d死亡率為1.5%,緊急手術為11.7%[5]。由于本研究中近50%的成年患者在手術時主動脈夾層和主動脈根部直徑為6.5 cm或更小,因此作者建議早期干預直徑應遠低于該尺寸。如果與動脈瘤相關的癥狀擴大,無論直徑如何,都建議進行緊急手術。
然而,在無癥狀患者中,手術干預的時間仍然是臨床醫生爭議的主題,根據目前2017年歐洲心臟病學會/歐洲心胸外科協會心臟瓣膜疾病管理指南和2014年歐洲心臟病學會/歐洲心胸外科協會主動脈疾病指南的建議,在不存在其他風險因素時,當主動脈根部直徑≥50 mm(I級,證據水平C)時就可以進行手術干預,這導致主動脈根部直徑的臨界閾值降低[6-7]。這個閾值的基本原理來自Jondeau等[8]的研究結果,如果主動脈直徑超過50 mm,他們計算得出發生主動脈事件的風險會高4倍。 然而,有風險因素的患者如主動脈夾層家族史,嚴重的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或二尖瓣關閉不全,有懷孕意向,全身性高血壓,主動脈大小增加>3 mm /年或患有洛伊-迪茨綜合征應在主動脈直徑<45 mm甚至在更少的情況下,在專業的馬方中心進行高度個性化的決策后再進行操作。
雖然這些風險因素確實已經在指南中給出解決策略,并且通常使用比例法如體表面積與主動脈直徑或Z-評分來評判主動脈根部直徑大小,但絕對直徑似乎仍然是手術適應癥的基本原理。在我們看來,對于適應癥的關注和影響應該越來越多地給予相對主動脈直徑,因為其考慮到家族史,性別和體表面積而不是絕對直徑。雖然這些影響傾向于導致降低手術時主動脈根部直徑,但其結果也證明了外科手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特別是對于年輕的患者。
2.基因治療進展
基因治療是與MFS相關的主動脈并發癥的令人興奮的治療選擇,并且可以提供用于長期表達的一次性載體應用的優勢。此外,該疾病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和動物模型的進步使得能夠鑒定涉及主動脈瘤進展和解剖的新靶標。到目前為止,因兩個主要局限性的存在,只有有限的研究涉及對動脈瘤穩定的適用性的基因治療:第一,遺傳性血管疾病的基因治療需要一個合適的載體系統來有效和長期的進行進入血管壁的基因轉移。第二,與杜氏肌營養不良等遺傳性疾病相比,編碼纖維蛋白基因的遺傳缺陷并不會導致纖維蛋白的完全缺乏,而是對血管壁產生顯性負作用,破壞纖維蛋白多聚體的形成,進而導致血管壁損傷。因此,僅僅重新表達原纖維蛋白可能不足以產生治療效果[9]。
未來遺傳性血管疾病基因治療策略的核心是轉移到血管壁有效和安全的基因載體系統的可用性。關于血管基因遞送的非病毒和基于病毒的方法有幾個報道,質粒介導的基因轉移具有無可爭辯的優點,例如相當低的生產成本,以及低免疫原性和毒性。然而,由于它們在體內較低和瞬時轉導能力,讓其在基因治療方法中的使用受到阻礙。相關研究報告了使用可擴張支架局部質粒遞送,該支架允許在冠狀動脈中控制釋放治療性DNA[10-11]。此外,涂有不可降解聚氨酯聚合物的支架被證明可有效地將質粒DNA輸送到兔髂外動脈[11]。重要的是,轉基因表達不僅可以在平滑肌細胞中檢測到,而且可以在巨噬細胞中檢測到。通過 用DNA-聚陽離子復合物離體孵育兔頸動脈來實現外膜和內皮細胞的轉染[12]。
盡管如此,轉基因表達顯示是短暫的,僅持續幾周[12]。迄今為止,常使用腺病毒載體將治療基因遞送到脈管系統中,雖然有幾種方法可以提高腺病毒載體的血管轉導效率,但使用腺病毒載體的主要問題仍然是靶組織內載體引起的炎癥反應強烈程度,即使使用第二代病毒構建體也是如此[13]。此外,腺病毒給藥后的組織免疫應答被證明是血管系統中唯一瞬時基因過表達的主要原因之一。
腺相關病毒(AAVs)代表了基因轉移到脈管系統的強大載體,因為它們與腺病毒和長期轉基因表達相比具有低免疫原性[14]。到目前為止,臨床前研究AAV受到脈管系統相對較低轉導效率的阻礙,此外,大多數AAV血清型不能充分轉導培養基中的平滑肌細胞,這在血管功能障礙的情況下是必需的[15]。
不同AAV血清型的趨向性主要取決于衣殼蛋白與細胞受體的相互作用。因此,最近的努力旨在通過直接修飾AAV衣殼表面來開發改善血管細胞轉導的新策略,例如通過選擇隨機化AAV衣殼文庫,已經報道了其他平滑肌細胞和靶向衣殼肽的內皮細胞的設計[16]。
除基因轉移載體系統外,MFS本身的治療靶標也是一個挑戰。如上所述,突變的FBN-1對血管壁發揮顯性負效應[17]。因此,降低突變體原纖維蛋白的表達水平可能對彈性蛋白結構具有有益作用。實際上,基于RNA的策略的靶向突變體FBN-1的反義錘頭狀核酶的過表達被證明成功地下調了蛋白質的沉積。然而,這種方法的效率僅在體外進行測試[18]。需要優化的血管基因轉移載體以在體內進一步研究該方法。
盡管病因不同,但有幾篇報道描述了基于基因療法的腹部動脈瘤的治療方法的可行性,這可能適用于MFS相關的動脈瘤進展。改善血管壁穩定性的直接方法是通過腺病毒轉導重新引入原彈性蛋白,其在大鼠腹部動脈瘤的小鼠模型中進行測試,處理過的動物呈現重建的彈性纖維,這反過來可以為主動脈壁提供穩定性[19]。進一步的實驗必須解決這種方法的長期影響。
血管炎癥是與MFS相關的主動脈瘤的另一個標志。 已經在主動脈壁中檢測到巨噬細胞和促炎性CD4 + T細胞的慢性浸潤,且顯示與疾病嚴重程度相關[19]。巨噬細胞是尿激酶纖溶酶原激活物(uPA)的主要來源,發現其在主動脈瘤的血管緊張素II輸注模型中高度增加,uPA是通過水解纖溶酶原形成纖溶酶的MMP的活化劑之一;局部外膜腺病毒介導的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1(PAI-1)的過度表達被證實通過減輕主動脈壁中的基質金屬蛋白水解酶活性顯著降低腹主動脈瘤夾層的發生率[20]。
總之,一方面有解決當前載體系統血管基因轉移效率改進的有希望的方法,另一方面鑒定至少治療馬方患者的血管疾病的新治療靶標。從長遠來看,未來的研究可以利用有效的新型載體系統進行修復潛在的原纖維蛋白突變。
3.新的研究機會和分子發現
1991年,Dietz等[21]對MFS進行了更好的分子理解的第一步,發表了位于15號染色體(15q21.1)的FBN-1基因的第一個突變,并將其與MFS相關聯。由于這種突變,使主動脈介質中形成的功能性彈性蛋白纖維和彈性蛋白穩態嚴重受損,此發現導致了這樣的假設即主動脈介質中功能性微纖維的閾值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相關[2]。接下來的幾年中,動物模型被用于闡明原纖維蛋白的分子生理學,增加TGF-β組織水平和MFS的病理生理學。
在這些分子發現的基礎上,開發了治療選擇。TGF-β拮抗劑如TGF-β中和抗體或血管緊張素II1型受體阻斷劑氯沙坦可以預防TGF-β信號傳導的增加。最近由Sator和Forteza[22]總結的最近幾年尋求藥物減緩疾病進展的研究數量顯著增長了。然而,盡管氯沙坦在MFS小鼠模型中預防主動脈根部生長具有顯著的前景,但在人類的隨機單盲對照試驗中,它似乎沒有任何顯著的優勢超過傳統的β受體阻滯劑治療[22]。此外,即使作為附加療法也無法檢測到阿替洛爾的益處,甚至開放標簽研究延伸評估隨機分配給氯沙坦或阿替洛爾的MFS患者的長期結果顯示,治療組之間臨床事件或主動脈擴張率的存在沒有差異。
盡管SMAD蛋白被鑒定為TGF-β1依賴性途徑中的關鍵信號轉導物,但已顯示SMAD蛋白和其他轉錄因子如活化蛋白-1(AP-1)參與TGF-β1信號傳導[1]。 靶向AP-1活性為治療與MFS相關的血管表型提供了新的潛在策略,因為AP-1中和寡脫氧核苷酸(ODN)在MFS的小鼠模型中降低了MMP2和MMP9活性巨噬細胞浸潤和主動脈彈性溶解[23]。有趣的是,他汀類藥物也可以抑制AP-1的活化,這可以解釋馬方小鼠已經證實的治療效果以及對胸部動脈瘤患者有積極作用的回顧性試驗,此外大鼠的初步研究結果表明,多西環素作為MMP2和MMP9的非特異性抑制劑可以減少主動脈根部腫大[24]。
miR-29家族的microRNA在主動脈發育中顯著上調,據報道,在馬方小鼠動脈瘤形成的早期過程中,microRNA 和升高的aomiR-29brta參與主動脈根部的細胞外基質重構;miRNA是小的內源性單鏈非編碼RNA分子,通過與mRNA內靶序列部分或完全的互補結合來抑制基因表達,在產前給予這些小鼠miR-29b抑制劑導致動脈瘤減少,MMP活性降低和彈性蛋白分解減少[25]。相比之下,一旦動脈瘤已經發展,miR-29b阻斷并未減緩主動脈生長,miR-29家族通過與結構蛋白的基因靶點如彈性蛋白,膠原蛋白,原纖維蛋白-1和普遍存在的MMP結合,參與細胞外基質的重組,但miR-29b的確切調節仍然未知[26]。已知白藜蘆醇是一種來自紅葡萄酒的抗氧化多酚,可增強sirtuin-1活性并延長壽命,同時可以抑制馬方小鼠模型中主動脈根部擴張事件的發生,這些作用是基于促進彈性蛋白完整性和平滑肌細胞存活,涉及主動脈中miR-29b的下調[27]。因此,白藜蘆醇可能是MFS患者的一種新型干預策略。除miR-29b外,還發現其他幾種miRNA與人腹主動脈瘤有關。除了與腹部動脈瘤的關聯外,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幾種有希望的miRNA和mRNA作為Marfan患者外周血樣本中未來預后相關生物標志物的候選者,所有這些都與參與心血管疾病發病機制的基因相關,并顯示出在MFS中被上調[28]。
MFS中另一個新興的分子靶標是mTOR(雷帕霉素的機制靶標)信號家族,發現其可以被miR-29過表達激活,是一種高度保守的信號通路,能夠控制幾乎每個哺乳動物細胞的細胞周期,蛋白質增殖和凋亡[29]。使用氯化鈣誘導的大鼠胸主動脈瘤模型中,雷帕霉素抑制動脈瘤的形成,通過mTOR介導的促炎介質(如癌癥)的下調,但TNF-α,IL-6,IL-1β和MMP2 / MMP9水平與對照組相似,但導致這種有益效果的確切途徑仍然未知[30]。第一個無偏移的蛋白質組學篩選將整聯蛋白組成的變化與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標雷帕霉素(Rictor)信號通路中雷帕霉素非依賴性組分的TGF-β依賴性激活聯系起來,以改善馬方小鼠動脈瘤的發展;Rictor是雷帕霉素非依賴性mTOR復合物2的一部分,也在細胞骨架細胞內的組織中起作用。同時表明Rictor是一種新型非經典TGF-β效應因子,其活化在MFS小鼠中具有依賴性,因為盡管TGF-β刺激不斷,但它僅在疾病晚期出現;發現TGF-β誘導的Rictor活化受到β3-整聯蛋白和玻連蛋白等其他因子表達的調節[30]。
最近,氧化應激和NADPH氧化酶的NOX家族成為MFS研究的焦點,已經研究了活性氧(ROS)在主動脈瘤發病機制中的作用。已經證實,在MFS中觀察到的主動脈病變部分是由于在平滑肌細胞和巨噬細胞中檢測到的大量ROS,這被證明是由NADPH氧化酶-4活化介導的TGF-β信號傳導增加引起的,有趣的是,NOX4被AP-1轉錄調節,用中和誘餌ODN處理馬方主動脈平滑肌細胞導致ROS積累減少[23]。涉及來自MFS患者的主動脈或培養的血管平滑肌細胞以及缺乏NOX4的馬方小鼠模型的模型顯示,確實NOX4對MFS中的主動脈擴張和主動脈中膜的結構組織的進展,內皮功能和VSMC表型調節具有影響[31]。
綜上,目前關于MFS的治療主要還是以預防為主,對于有家族史的患者更應該密切監測相關指征,預防危及生命的并發癥發生,隨著醫學的進步基因療法的實現在未來可期,但是目前我們能做的就是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預防,早干預,改善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