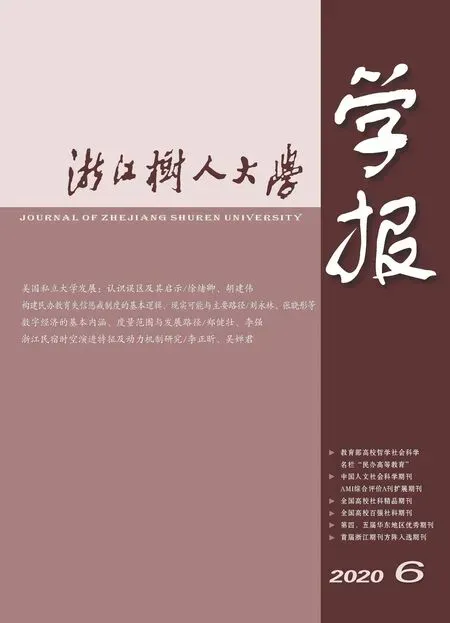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方法
——以傅蘭雅為中心的考察
張美平
(浙江樹人大學 人文與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310015)
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于1861年來華從事教育、報刊編輯等文化傳播活動。1868年5月,受上海江南制造局總辦馮焌光之邀,正式入職該局,主持其下屬機構翻譯館的西書譯介工作,由此啟動了中國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成效最為顯著的西書翻譯運動。以他為首席翻譯的翻譯館沿襲起源于東漢、在晚明前清時期普遍采用的西書翻譯的老辦法——“西譯中述”,即“譯書率皆一人口授,一人筆述”(1)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出自張靜廬:《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編),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 年版,第60頁。,這種由中外人士合作的口譯和筆述相結合的模式,在近代中國最大的官辦譯書機構翻譯館里更是得到了廣泛運用。借助這種方式,傅蘭雅和徐壽等中方合作者以翻譯館為平臺,為近代中國貢獻了140余部西方科學書籍,為早期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重要的知識資源和思想資源。
作為曾經流行約1 500年的譯介外來書籍的老辦法,“西譯中述”(2)中國有明確文獻記載的“西譯中述”活動已有約1 500年的歷史。前秦皇帝苻堅(338—385)命趙政和道安開設譯場,集體翻譯佛經。譯場分工明確,除口授、傳言和筆受外,還有記錄(梵文)、正義和校對三道工序。參見方夢之:《譯學詞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頁。傅蘭雅主持的翻譯館也基本采用這種方法,只是譯員構成更為簡化,一般是口譯1人,筆述1人,有時另加校對一二人。受到了學界的重視,除了在相關研究中提及以外,于醒民(1985)(3)于醒民:《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譯著中的代筆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4期,第59-63頁。、傅良瑜(2005)(4)傅良瑜:《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翻譯西書方法考》,《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005年第2期,第119-127頁。以及夏晶(2011)(5)夏晶:《晚清科技術語的翻譯——以傅蘭雅為中心》,武漢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頁。等還對此作了專題研究。筆者認為,現有的研究不夠充分,仍須深入探討。
一、“西譯中述”運用的背景
(一)缺乏經過系統訓練的西學和外文人才
一個能夠獨立翻譯的譯者至少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是通曉外文;二是精通母語;三是熟練掌握相關學科的知識。按此條件,在1895年之前,除嚴復外,幾乎沒有人能夠獨立從事翻譯工作,不通西文的徐壽等人做不到,在華西人也做不到。傅蘭雅來翻譯館之前,已有7年在華從事漢語學習、教學與管理以及報刊編輯的經歷。他漢文功底深厚,寫作能力強,進行一般性的翻譯毫無問題。但為何沒有像嚴復那樣獨立翻譯,而要找助手為其筆述?這里涉及專業素養問題。嚴復中學根基深厚,又在福州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浸淫西學多年。在英留學期間,除專業學習以外,他還專門研究西方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6)張美平:《晚晴外語教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所以,他翻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專業性較強的西學著作時,都能得心應手。傅蘭雅是一個僅接受過當下所說的通識教育的師范生,尚未深入內容艱深的專業領域。盡管具備了一定的數理化等基礎學科的知識,但他所受的科學教育相當有限。他自稱“半瓶子醋”(only a half-educated man)(7)Ferdinand D, 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頁。,這雖有自謙的成分,但科學素養不足無疑是不爭的事實。姚崧齡說:“傅蘭雅加入翻譯館后,日夜從事科學之自修,以期無負委任,緣彼對于科學,本屬門外漢也。”(8)姚崧齡:《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頁。江南制造局高薪禮聘其為專職翻譯,要求翻譯的學科非常廣泛,涉及數理化、機械、制造、礦學和兵工等數十個學科領域。洋務派準備引進這些學科領域的知識,大都是國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生事物,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科學術語。因此,要勝任移植西學的使命,譯者必須是擅長相關領域的專門家。對傅蘭雅而言,絕大多數的學科都很隔膜,他說:“我必須努力學習,以便跟我的職責相匹配。”(9)Ferdinand D, 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頁。可見,傅蘭雅難以單獨承擔起移植西學的使命。
再來看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以移植西方知識和技術為職志的洋務運動啟動之前,雖然西方傳教士引進過少量的數學、天文等西學知識,但總體而言,當時中國仍處于西學荒漠之中。其原因在于通曉西學的外文人才極度缺乏,無法進行有效的西學移植。翻譯館創辦時,全國僅有北京、上海、廣東3所同文館,雖系官辦,但招收的人數極少。如北京同文館創辦時,其英文館僅招10名學員,后來的俄文館、法文館也各招10名。滬、粵兩館和京館一樣,招生人數很少,學制3年。這些新式學堂教授外文和西學的程度較淺,相當于中小學程度。此外,一些教會學堂也教授一些簡單的外文和西學。盡管這些官辦學堂培養了鐘天緯、鳳儀等優秀人才,但總體而言,這些學堂學生的外文和西學程度非常有限,很難勝任獨立移植西學的使命。可以說,當時通曉中外語文和西學的本土譯者鳳毛麟角,找尋像嚴復這樣貫通中西的大家,有如大海撈針。
(二)缺乏具有深邃舊學基礎又有新學背景的人才
筆述所使用的語言必須是正統地道的古代漢語,因為現代白話文是在新文化運動以后才在社會上普遍使用的。而當時形勢的要求,不僅要引進西學知識,還要讓身處一線的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管理者、工程技術人員和學堂教習等,借助譯本了解和掌握所引進的知識。客觀地說,善說華語者車載斗量,但要讓他們駕輕就熟,用中國地道的古漢語進行筆述,其難度猶如登天。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華40多年,有傳教、從事慈善、創辦機構以及編輯中文刊物等經歷,稱得上是社會活動家和漢學權威,但深奧晦澀的古漢語仍讓其沮喪萬分,“中國文字之繁難,讀書者費十年之功而猶不能盡識群書之字(李提摩太)”;“我等外國人實在看不明白中國書(李佳白)”(10)于醒民:《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譯著中的代筆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4期,第59-63頁。。所以,筆述的重任落在了雖不通西文、但具有深邃舊學基礎、又有新學知識背景的中國學者身上。
(三)上海人才薈萃,為“西譯中述”創造必要條件
上海匯聚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外語和西學人才(11)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擊敗,被迫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五口通商”,即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允許洋人進入上述五地居住、經商、辦廠、興學等。1843年,上海正式開埠,成為中國第一個向西方開放的城市。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上海取代廣州,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商貿城市。1861年,洋務運動啟動后,擁有不同背景的洋人紛至沓來,從事傳教、教育、醫務、經商和興辦企業等各類活動。。自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抵達中國澳門開始,各個層次和類別的西籍人士先后踏入中土,其中不乏傅蘭雅、林樂知等具有真才實學、關心中國發展的傳教士。這些人以英法等語言為母語,大多具有較好的西學基礎,又通曉漢語,進入翻譯館之前都有一定的翻譯和教學經歷,這是很好的可資利用的資源。上海也是洋務派的標桿企業江南制造局的所在地,擁有眾多精通近代科學的技術精英,“徐雪村(即徐壽)識辨五材,化分礦產;賈步緯胸羅歷宿,考驗璣衡;功參岐伯,趙靜涵(即趙元益)醫理纂明;步計大章,李丹崖(即李鳳苞)地輿熟識;更有數通算學,莫不為妙疇人”(12)《格致匯編》正月卷,卷首,1877年3月。。而且他們自小接受私塾教育,擁有深邃的傳統文化功底。這些科技精英在與傅蘭雅等西人的合作中,能以明白曉暢的語言闡釋近代西方高深莫測、晦澀難懂的科技知識。
綜上,由于歷史條件所限,以英法等語言為母語,掌握西方科學和初步漢語能力的西方學者與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技術精英攜手,以“西譯中述”為手段,成就了翻譯館的輝煌。
二、“西譯中述”在傅蘭雅及其團隊中的應用
(一)知識準備
為傅蘭雅筆述的21位中國學者,分別來自史學、農學、工藝、數學、化學、重學、醫學、測繪、礦學、航海、機械、法政、海防和兵學14個領域,這對于僅有普通師范教育背景的傅蘭雅而言是極大的考驗和挑戰。為了能順利進行西書譯介,傅蘭雅一邊翻譯、一邊學習,進行必要的知識儲備。1868年7月11日,他在致函約翰遜時提及他從事譯事工作的同時,還得鉆研相關學科的知識。“目前我所從事的工作絕對讓我感到無比快樂。我熱愛科學,但沒有時間或機會去從事科學活動。現在它成了我的工作,一份非常快樂的工作。我非常熱心地從事科學活動,雖不可能成為科學家,但我渴望精通它的若干學科。我已同時學習和翻譯三種科目:上午學習和研究煤、采煤及各種相關事項,下午專研化學,晚上學習聲學。”(13)Ferdinand D,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頁;第414-415頁;第32頁。
傅蘭雅除了不斷刻苦進修相關學科知識以外,還置身于古人所說的“莊岳”之間,不僅和中國學者一起譯書,而且一起生活,錘煉漢語口語,特別是專業知識的口語表達。“中國人很容易相處。他們對我,比對那些和我在中國有聯系的歐洲人更加充滿善意,更加公平……有一個頂戴花翎的知縣級別的中國小伙子,幾乎已成為我的兄弟了。我們一起勤奮地譯書。他經常來到我的住處,和我一起用餐,他的名字叫徐仲虎(即徐建寅)……現在我們相處非常和諧。他甚至說不會視他所遇見的其他我的同胞為蠻夷那樣對待我。相反,他視我為他們中的一員……在我現在的工作中,和中國人聯系非常密切,說漢語的機會遠超英語,我已成為半個中國人啦。”(14)Ferdinand D,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頁;第414-415頁;第32頁。
正因為經年累月的學習、積累,傅蘭雅打下了深厚的中文和近代西方知識的基礎,極大地方便了他的口譯工作。“當時絕大多數的譯者用自己熟悉的方言譯出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然后由中國筆述者記錄下來加以潤色,使之符合文理。傅蘭雅博士和丁韙良博士是僅有的能按中國文字表達習慣向筆述者準確地傳達信息的人。他們無須中國助手潤飾,直接傳達自己的思想,從而為世人所知。”(15)Ferdinand D,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頁;第414-415頁;第32頁。華蘅芳是傅蘭雅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代數術·序》中說,傅氏“一日數千言,不厭其艱苦,凡兩月而脫稿繕寫付梓”(16)傅蘭雅口譯,華蘅芳筆述:《代數術·序》,江南制造局1872年版。。
(二)合作譯書
翻譯館創辦以后,制造局總辦馮焌光先后將傅蘭雅等中外才俊網羅至麾下,如美國的金楷理、林樂知、瑪高溫,英國的偉烈亞力等,中方有徐壽、華蘅芳、王德均、徐建寅、李鳳苞等人。翻譯館(1868—1913)在運行的46年時間里,共聘譯員可考者63人,其中西人9人、華人譯員54人(17)元青、齊君:《過渡時代的譯才: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中國譯員群體探析》,《安徽史學》2016年第2期,第32-43頁。。口譯者大都為西人,也有少數接受過新式學堂外語教育或留學歸國的華人學者。華人譯員大都充任筆述,“協同司事,日與西人口講筆述,悉心研究”(18)《海防檔·丙·機器局(一)》,臺灣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102頁。。“口講筆述”即西人口譯、華人筆述的“西譯中述”。時人記述:“制造總局翻譯之書,必先將所譯者令西人熟覽,且義理使之胸中雪亮,本末瞭然,方與華士同譯,舉西士之義逐句讀成華句,華士以筆述之……既譯之后,華士將初稿改正潤色,俾合于中國之法。”(19)于醒民:《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譯著中的代筆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4期,第59-63頁。
口譯者當中,傅蘭雅是最為杰出的一位,成果最多。自1867年與徐建寅合譯《運規約指》開始,至20世紀初,他一共翻譯了140余部反映西方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西學書籍(見表1),涉及物理學、數學、化學和機械學等約20個學科領域。

表1 傅譯西書簡表
以傅蘭雅、徐壽為代表的翻譯館中外翻譯家們通過“西譯中述”模式,秉承“因制造而譯書”之理念,創造了近代翻譯史上最為輝煌的成績。“閱數年,書成數百種。于是泰西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實學遂以大明,此為歐西文明輸入我國之嚆矢也。”(20)徐珂:《徐雪村主譯西書》,出自:《清稗類鈔(第8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33頁。
(三)“西譯中述”的特點和要求
“西譯中述”為近代大規模的西學翻譯運動提供了方法,使“歐西文明輸入我國”成為可能。倘若沒有“西譯中述”,就沒有大量西書的引進,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將會受到影響。通過“西譯中述”,口譯和筆述雙方通力合作,實現知識結構、語言表達、思維方式和譯述方法等方面的優勢互補,產生了許多佳作。然而,這一模式對譯述兩端的要求較高。首先,就口譯者而言,不僅要求具備較好的專業基礎,而且要求通曉譯入語及其使用規范。傅蘭雅和華蘅芳合作譯書時,在華居住已有10年,且有在多個文教機構從事教學、管理和編輯刊物的經歷,對漢語的使用相當嫻熟。英語是其母語,能較好地理解原著的內容,并以流暢的漢語將所譯內容傳遞給筆述者。其次,對筆述者而言,既要精通專業知識,又要有深厚的漢語言基礎。華蘅芳舊學功底深厚,雖不通西文,但精通數學,有《開方別術》《數根術解》《開方古義》《積較術》《學算筆談》等多部數學專著面世,因而不僅能在數學領域和通曉漢語的傅蘭雅進行對話、磋商,而且能以專業語言將近代西方數學成功移植中國。因此,傅、徐合作翻譯的西書大都質量上乘。如25卷本《代數術》,“為代數之叢書,較《代數學》及《代數備旨》為詳備,編輯既精,譯筆尤善,為算學家必讀之書”(21)翻譯館編:《江南制造局譯書提要》,江南制造局1909年版,第30頁。。因此,作為譯述兩端的傅、徐,在具備良好的語言和專業知識的情況下,“西譯中述”模式便利其互相切磋譯藝,共享智慧。他們在固定的時間及地點,一邊進行譯述,一邊切磋譯藝,誠如傅蘭雅所說:“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22)傅蘭雅:《譯書事略(四)》,出自:《格致匯編》1880年版,第9頁。互相切磋、斟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中一方的疏忽、漏譯、誤譯,保持譯述文本的準確性,這對雙方來說都是很好的學習和提高機會,這是個人獨立譯介所不具備的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在為傅蘭雅筆述的華蘅芳等21位華人學者中,鐘天緯、應祖錫和李岳衡三人畢業于上海廣方言館、京師同文館等外國語文學堂,其接受英文教育的背景更方便其與口譯者溝通,為譯出較高質量文本提供了條件。如傅蘭雅和應祖錫合譯的《佐治芻言》受到梁啟超的推崇。他說,該書“皆用幾何公論,探本窮源,論政治最通之書”(23)梁啟超:《讀西學之法》,出自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5頁。。
可見,“西譯中述”對口譯者和筆述者都有很高的要求,不僅需要高效的協同合作機制,還要在共有知識、表達能力等方面實現匹配,否則既難取得滿意的效果,也會在心理、表達等方面給對方帶來異常恐怖的折磨,特別是在口譯一方表現不佳時,這種折磨尤其明顯。瑪高溫在口譯《地學淺釋》時,讓筆述者華蘅芳吃盡了苦頭。瑪高溫“于中土之學不甚周知”,華蘅芳則“于西國文字未能通曉”,這一狀況使雙方的合作變得異常艱難。華氏是一位數學家,幾乎不通地學,既要面對眾多的“名目”“頭緒”,又不能閱讀英語原文,僅靠瑪氏的面部表情和手勢才能勉強進行筆述。但是,“其所記之事跡每離奇恍惚,迥出于尋常意計之外,而文理辭句又顛倒重復而不易明”,加上華氏居住環境惡劣使其“忽患血痢之癥,日夜數十次,懨懨無復人色”,差一點魂歸天國,從此“精力亦大衰”(24)瑪高溫口譯,華蘅芳筆述:《地學淺釋(卷一)》,1896年小倉山房校印,序。。瑪高溫是一位醫生,1841年來華,但他掌握的中國語言文化和科學知識不足以完全勝任西學知識的口譯。加上他忙于傳教、行醫及社會活動,在譯書時間的安排上顯得捉襟見肘。而且,地學并非他的專長,所以,口譯起來相當困難。
同樣,筆述者如果文筆欠佳或語言表達不清,也會造成口譯者的誤解,導致溝通受阻。1869年11月,傅蘭雅在致函其親友時述及其和徐建寅初次合作時,很難聽懂后者的話,因為他講的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方言(25)Ferdinand D,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頁。。在部分受詬病的館譯西書中,語言表達粗糙、知識傳遞失真等問題,雖有不少系口譯一方所致,但筆述者的話語表達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由于教育背景、學科素養、領悟力以及漢語表達能力等方面的差異,不同的譯者對同一專業術語的理解和表達同樣存在差異,從而造成同一事物的名稱存在兩個及以上的中譯名,其直接后果是影響了西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與普及。瑪高溫口譯、華蘅芳筆述的《地學淺釋》和傅蘭雅口譯、潘松筆述的《求礦指南》中,同一地質年代術語的中譯名完全不同(見表2)。類似情況,在翻譯館所譯的西書中并不少見。

表2 《地學淺釋》與《求礦指南》譯名比較
三、“西譯中述”的影響與問題
(一)影響
通過“西譯中述”,傅蘭雅等人翻譯了大量的西學著作,在近代中國產生重大影響。首先,培養了一批博通中西之學的新式知識分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人才資源。翻譯館的中方筆述人員中,科舉正途(即進士、舉人、秀才)出身者僅占32%。其余是貢生、監生、諸生等學生群體以及僅接受過私塾教育的平民,他們都是科舉時代的底層知識分子(26)齊君:《近代“筆受”譯員群體探析——以江南制造局翻譯為中心的考察》,《歷史教學》2017年第11期,第46-52頁。。這些人當中,雖然功名最高的是江衡、王季烈,兩人是進士,但其進士身份是在離館后獲得的,因而實際最高的是舉人(丁樹棠、應祖錫、趙元益、周郇),大部分人都是秀才以下的平民。在科舉時代,沒有秀才(27)明清時期,秀才是指通過了科舉中院試(即在縣或府里參加由省里的提督學政主持的考試)的生員,屬士大夫中的最基層,大致相當于現在的鄉鎮公務員。以上的功名,一般不能算作人才。但是,洋務派人士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從當時國家急需先進的西方科技的現實出發,不拘一格,將散落民間的沒有功名卻有真才實學的普通士人網羅其間,讓他們發揮既有深邃舊學根基又有新學知識的優勢,從事西書譯介。他們在為國家引進新學知識的同時,獲得了證明自身價值的機會,也獲得了才學、人格、精神的成長。李鳳苞自幼接受中國傳統語言文化教育,愛好歷算,精于測繪,在館翻譯了《克虜伯炮說》《營壘圖說》等10余部西書。通過翻譯館的歷練,又進一步擴大了他的眼界,為他從事洋務、駐節海外打下了必要的知識基礎。1877年3月,他率領嚴宗光(即嚴復)、劉步蟾、薩鎮冰、鄧世昌等12名福建船政學堂學生前往英國學習海軍,并出任留學生監督。這些學生學成后先后擔任軍政要職,如北洋艦隊12艘主力艦的管帶(艦長)中,留英學生占了7名;薩鎮冰在民國時期擔任海軍總長;1878—1885年間,李鳳苞又兼任出使奧、意、荷、法等國大臣。“他久駐國外,熟悉洋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旅順為北京東方門戶,應建立軍港的建議,并前往考察旅大形勢,確立其為海防重鎮而付諸實施,這就是后來旅大和威海、大沽成為三角防御體系,保衛京津的海上長城的始肇。”(28)鄒振環:《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與近代上海譯才高地的構筑》,《東方翻譯》2009年第2期,第41-49頁。趙元益精于醫學、格致之學,在館翻譯西書20余部,其數量僅次于徐壽父子。1889年,他接受派遣,前往英、法、比、意等國使館工作。1897年,與董康等人創立上海“譯書公會”,并創辦《譯書公會報》,傳播西方知識。同年,他與吳仲韜創立上海著名的醫界團體——醫學善會。王韜去世后,他主持上海格致書院工作,為國家培養近代科技人才。瞿昂來在館主要從事交涉、軍史、格致等領域的筆述,并兼任上海廣方言館的英文教習。他思想進步,曾任維新派刊物《經世報》編輯。
其次,實現對部分封建士大夫和普通民眾基本的西學知識啟蒙,為近代中國思想現代化奠定基礎。館譯西書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發展與安全,大部分是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所急需的。這些譯著中所承載的內容,雖然有些已過時,而且簡單淺顯,系啟蒙類讀物,但對仍處于“學問饑餓”時期的中國來說,彌足珍貴。館譯西書雖沒有給中國帶來富強,卻推動了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解放,有力地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當時維新領袖們所掌握的西學知識,除嚴復等個別人外,大都從制造局等譯書機構所翻譯的書籍中得來(29)張美平:《翻譯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江南制造局的翻譯及其影響》,《中國翻譯》2010年第6期,第38-42頁。。1882年,康有為參加北京鄉試,歸途經過上海,悉數購買翻譯館及教會機構翻譯的西書,“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3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其弟子梁啟超也受益于館譯西書的啟蒙。萊文森說,1890年,這個偉大的世界開始和梁啟超對話,梁是中國最有影響的政論家之一。在一次訪問上海時,他雖然買不起制造局的西書,但他能夠找來閱讀。在6年后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890這一年是他人生中重要的分水嶺(31)Joseph L,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7.。可見,閱讀館譯西書,使康、梁等人有機會洞察更廣闊的世界。
鐘天緯是平民知識分子成長的典型。他長期在翻譯館工作,與傅蘭雅合作譯書共8種,校勘1種,凡35冊66卷。他在廣方言館僅接受過基本的英語和西學訓練,其深厚的西學素養是在翻譯館翻譯、學習的過程中習得的。他撰寫的文章在傅蘭雅、王韜主持的上海格致書院課藝征文中斬獲超等、一至四等獎,“先后有10多篇文章收錄在影響很大的‘經世文編’中,足見他對時務的評判和見解達到了極高水平”(32)薛毓良:《鐘天緯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頁。。僅《皇朝經世文三編》就收錄了《西學古今辨》等7篇文章。其《中西格致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別》等多篇文章中的一些觀點,對新文化運動產生較大影響。他有強烈的國家安全意識,警惕列強的侵略野心,為加強國防出謀劃策。有論者認為,在19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或者說在嚴復之前,論對西學理解的程度,鐘天緯不光在上海,就是在整個中國,無出其右(33)熊月之:《序言》,出自薛毓良:《鐘天緯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二)存在的問題
對于“西譯中述”,外交家、語言學家馬建忠卻持否定態度。他說,“今之譯者”或請稍通華語之西人為其口譯,筆述者則“為仿佛摹寫其詞中所欲達之意”。若未能解其意,筆述者則會“參己意而武斷其間”。由通洋文而不識漢文、通漢文而不識洋文者所譯的西書,“皆駁雜迂訛,為天下識者所鄙夷而訕笑”(34)鄭振鐸編:《晚清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頁。。馬建忠所言雖有偏頗,但也反映了“西譯中述”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一是筆述者隨意增刪。時人提及:當時存在“惟華士改正”“只要合于中國之法”“而不必西人核對”的情況,從而使筆述者的增刪之權極大(35)于醒民:《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譯著中的代筆問題》,《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4期,第59-63頁。,導致譯文的準確性難以保證。二是譯述人員的專業素養參差不齊,使部分譯書質量存在問題。吳妍人曾供職江南制造局,在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借小說人物之口抨擊部分館譯書籍的質量。他說有的譯書“作為談天的材料,是用得著的;若是打算從這上頭長學問,卻是不能”。譯員“始終是這一個人,難道這個人就能曉盡了天文、地理、機器、聲光、電化各門么……談何容易,就胡亂可以譯得!只怕許多名目還鬧不清楚呢?何況又兩個人對譯,這又多隔了一層膜了。”(36)吳妍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264頁。
四、結 語
金圣華說:“翻譯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像一座橋,而‘譯者’就是‘驛者’,經年累月,奔波往返于連接兩岸的譯橋上,不管天晴天陰,日曬雨淋,春風和煦或秋風蕭索,總是身負重擔在長橋上不停地來來回回。”(37)金圣華:《橋畔譯談新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傅蘭雅就是這樣的“驛者”。他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艱難,將妻女放在英國,以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西學譯介事業中去。除了主持益智書會和格致書院的日常工作、編輯《格致匯編》、參與新式學堂的外語教學以外,傅蘭雅以翻譯為中心,幾無空閑時間。作為一名只有普通師范教育背景的職業翻譯家,他要面對如此多“無聊”“吃力不討好”的多學科領域的西學書籍,如果沒有海量的時間投入學習,沒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堅定的信念”(38)John Fryer, 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80, p.81.,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憑著頑強的意志,他為中國貢獻了140余部西書,占240余部館譯西書的58%。在通過譯本“成了學習西方科學的主要途徑”的背景下,這些知識和精神產品,不僅成為士大夫和平民知識分子的啟蒙讀物,而且被當作課本,登上了清末新式學堂的書桌,甚至在甲午戰后的興學高潮和救亡圖存運動中“被銷售一空”(39)張美平:《傅蘭雅與益智書會的譯名統一與標準化》,《外國語文》2020年第2期,第121-127頁。,出現小型印書作坊靠盜印館譯西書發財的景象(40)Ferdinand D,The John Fryer Papers,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18頁。。
其實,在嚴復獨立譯介西學之前,翻譯界只能采用“西譯中述”模式,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模式,誠如論者所云:“早期口譯筆述的方法雖說無奈,也算是當時最善之事了。”(41)傅良瑜:《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翻譯西書方法考》,《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005年第3期,第119-127頁。當然,這一模式存在諸多缺陷,但它作為“近代新詞語創制路程中被界定為是一種‘過渡形態’”(42)夏晶:《晚清科技術語的翻譯——以傅蘭雅為中心》,武漢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頁;第34-35頁。,迎合了近代早期中國向西方世界求知的迫切要求,是中國早期知識分子在不通外文的“坡行”階段不得不依賴的一種譯介手段。即便它有艱難晦澀、概念混亂、與原文出入較大的毛病,但是在那個風氣未開的年代,對于對西學求知若渴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仍彌足珍貴(43)夏晶:《晚清科技術語的翻譯——以傅蘭雅為中心》,武漢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頁;第34-35頁。。況且,在這一模式下,中外學者譯介了許多質量上乘的書籍,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即便在今天,這種利用在各自領域獨當一面的語言專家和技術精英合作翻譯的做法,仍有借鑒價值,不僅能夠避免很多翻譯笑話,而且能大大提高翻譯文本的質量。
總之,以傅蘭雅為中心的中外翻譯家團隊,在“合作的過程中飽浸西學,成為近代最早系統接觸西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譯書事業中殫精竭慮,創榛辟莽”(44)元青、齊君:《過渡時代的譯才: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中國譯員群體探析》,《安徽史學》2016年第2期,第32-43頁。,充分、恰當、合理地利用“西譯中述”,為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行進的中國貢獻了數量龐大的知識和精神產品,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