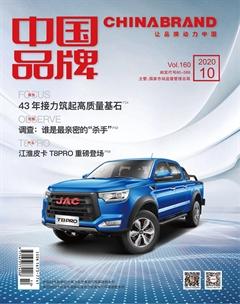規制電商市場“二選一”監管勢在必行
翟巍
華東政法大學競爭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近年來電商市場的二選一行為呈現出越來越普遍、越來越隱蔽的趨勢:一方面,以往只有超大型平臺企業在集中促銷期間涉嫌實施二選一行為,但當前一些大中型平臺企業也有動機與能力,于非促銷期間在細分市場上實施二選一行為。另一方面,電商平臺已經意識到二選一行為的違法違規風險,因而在使用這一方式時變得更加隱蔽。這種紙面合規而實質違法的行為嚴重扭曲市場競爭機制。
從微觀效果上看,大多數二選一行為不僅損害平臺企業競爭對手的公平競爭權與平臺內商家的自主經營權,而且也侵害了廣大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從宏觀效果上看,如果此類行為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電商平臺企業將會日益傾向于以此攫取市場競爭優勢,最終喪失競爭動力與創新意識,并因此導致市場競爭機制傾覆的后果。
盡管大多數二選一行為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果,但我國執法與司法機關在規制這類行為時卻面臨不小的障礙和挑戰。首先,電商平臺在實施二選一行為時,會刻意采取隱秘方式,以防止留下違法違規證據,因此受此侵害的企業在舉報或訴訟時,很難提交相關證據,由此也導致執法與司法機關難以依法支持受侵害企業的訴求。其次,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在規制二選一行為方面處于“多龍治水”的尷尬境地。雖然反壟斷法第17條、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電子商務法第35條均可規制二選一行為,但這類法條的適用各有軟肋。反壟斷法第17條規制二選一行為的前提是:實施行為的主體必須具有市場支配地位。這一苛刻前提導致反壟斷法只能適用于處置少量二選一行為。就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的適用而言,雖然大多數二選一行為可被視為一般性不正當競爭行為,但一般性不正當競爭行為卻沒有相對應的行政法律責任,因而執法機關無法直接依據該法處罰相關電商平臺企業。近年來,電子商務法第35條被寬泛地界定為禁止二選一行為的條款,但這一條款所禁止的行為相對應的行政法律責任較輕,因而它無法對濫施二選一行為的電商平臺企業產生足夠的威懾力。
為營造電商市場良好競爭秩序,切實保障廣大消費者權益,我國公權力機關應當從立法、執法、司法層面對二選一行為進行規制。在立法層面,全國人大可以考慮仿照《德國反限制競爭法》模式,在反壟斷法中新增規制“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的條款,并設定相對嚴苛的行政法律責任,使這一新增條款與原有的規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條款構成全面規制二選一行為的反壟斷條款體系。在執法層面,我國執法機關可以通過強化前置性與穿透式監管的方式,主動開啟針對電商平臺企業二選一行為的調查活動,并借助科技監管模式實現對二選一行為的回溯性調查與取證。執法機關還可以通過設置正面清單、存疑清單與負面清單方式,為電商平臺企業設定清晰的二選一行為合規指南。在司法層面,司法機關有必要在長期實踐基礎上,設定關于二選一行為合法與否的細化評判標準,并逐步解決由二選一行為所導致的“消費者群體福利損失的量化計算問題”與“損害賠償的公平分配問題”。